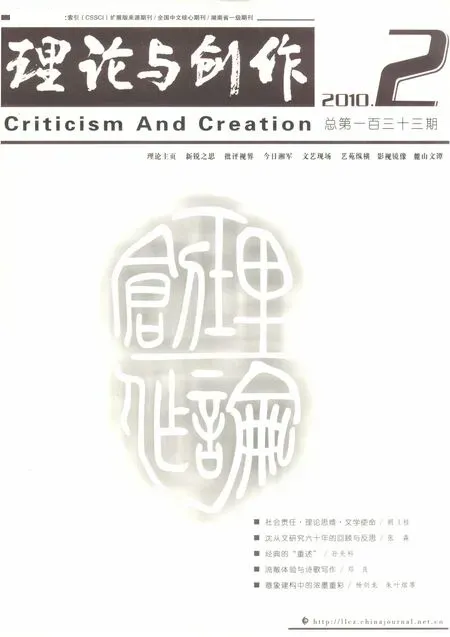解讀新都市小說:在市民文化精神的視野中
■ 肖佩華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出現了新的市民階層,中國新都市小說迅即崛起,帶來了新都市小說的繁榮。這些作品表現出對新市民生活理想、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的認同,充滿市民文化精神。然而,當前許多的研究忽略了它們生成的本土性——中國語境,大多硬套西方時髦理論來解讀新都市小說。其實中西文化、文學、歷史等迥異,我認為應該回到新都市小說生成的本土性語境,充分注意到我國傳統市民文化精神和市民文學對新都市小說的重要影響、作用,當然,這其中也有西方現代城市文化的沖擊融合,正是中西合璧,土洋結合,從而構成了當代新都市小說具有新質的當代市民文化精神。
一、城市化浪潮:新都市小說崛起之背景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以來加速推進市場經濟進程,帶來了我國城市化、現代化的較快發展。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促進了新的市民階層的興起,他們在城市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市民文化精神正滲透著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因此,我國新都市小說遽然崛起。新都市小說實際上已一躍成為當下的文學主流。一掃傳統的“都市文學”萎靡不興的局面。眾所周知,由于我國城市化、現代化起步較晚,受鄉土中國文化的制約,故我國都市文學較之鄉土文學遜色不少。盡管20世紀30年代的海派文學曾掀起過一陣浪頭,然而由于救亡與內戰,加之缺乏都市文學發展的必要的土壤,都市文學遂曇花一現。而從1949年直至1980年代前,國家采取高度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權威意識形態,都市文學更沒有成長發展的空間。“鄉村被美化為帶動人民的精神之源,而城市則是資產階級與官僚買辦腐朽思想的泛濫所在。《霓虹燈下的哨兵》(1963)就體現了這種將城市置于鄉村對立面的‘時代思想’。”①1990年代以來新都市小說的崛起,正應了丹納在《藝術哲學》中闡釋過的觀點:任何文學藝術流派、藝術品的產生與流變都是當時當地之“時代精神”與“風俗習慣”進行“選擇”與“自然淘汰”的結果。這里的“時代精神”與“風俗習慣”既是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氛圍的總體體現,又是以上眾多因素融合共生的產物。社會時代的變遷必然引起“時代精神”與“風俗習慣”的相應變化,進而引發文學藝術的變化。從根本上說,當代新都市小說的崛起乃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整體變化與變化了的“時代精神”的產物,是社會轉型期的客觀產物,具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對當代新都市小說的研究、評論角度很多,其中多以西方后現代主義、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等時髦、熱點理論來解讀我國新都市小說。筆者以為見仁見智很為正常。而當我多次閱讀這些新都市小說,又覺得恐不盡然。西方社會與中國并不一樣,現代化實現也有不同的路徑。我國新都市小說的崛起、解讀也應有自己的情況(語境)。為此,我嘗試提出“市民文化精神”命題,以此觀照、解析當下中國的新都市小說。
二、解讀新都市小說:在市民文化精神的視野中
文學的生命本源在于它的社會性和群眾性。當代中國新都市小說正是在中國當代都市土壤上適應我國當代都市市民的需要而產生的。從歷史上看,我國有悠久的市民文學傳統。從宋代開始,市民文學頗見興盛。可以這樣認為,市民文學的發展幾乎與市鎮商業的演進同步前進,也即:“市民與城市工商業經濟的發展,乃是市民文學滋生的土壤。”②明末清初,經濟、社會政治的巨大變革,倫理與功利觀念在內的整個意識形態更加沖突動蕩,從而掀起了一股具有近代嶄新的市民資本主義特質和啟蒙意義的新思潮。與此相應,“隨著印刷業的興盛,市民自我表現和娛樂的文學樣式得到了較為迅速的發展和傳播,說話、表演等時間藝術借助書面文學的存在形式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流行和賞析。一大批文人雅士染指其間,或取其謀獲利之徑直,或因其敘事抒情之簡便,從宋元話本到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清白話短篇小說,從講史話本、英雄傳奇到《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長篇章回小說,從元雜劇到明清傳奇,從魏晉六朝文人短篇小說到《聊齋志異》,如此種種,構成了一股洶涌跌宕、興旺發達的通俗文學洪流,傳統的詩文詞賦相對地反而不那么顯眼注目了。”③宋元話本所具有的民主精神和社會進步意義,所表現的富有現實人情味的世俗生活,對于平等、自由、民主意識的向往,在明清通俗文學中得到了擴展、弘揚,達到了輝煌的頂點。這中間特別重要的是市民文化精神的凸顯,反映市民階層要求的理論逐步形成,王學左派,李贄掀起了人性解放的啟蒙思潮。他們抨擊儒家圣人理學文化,弘揚個體價值,返回人生真相,大膽踐踏了僵化的儒家禮教,為形而下的民情民欲正名。于是,在明清市民通俗文學中,我們看到一幕幕商人們追財逐利的艱難歷程,市井間家庭的悲歡離合,市民對情與欲的大膽擁抱。這些包含著市民的人生體驗以及作者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的生動事件在作品中顯得生氣盎然。從而完成了把人作為個體的人,從禮教的牢籠中,從軍國大事中,從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中解放出來,而放進日常的平凡生活中,展現了人性的本來面目。它們所表現的正是市民階層的愿望和審美趣味。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國當代新都市小說的興起與明清之際的市民文學大體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其一,是社會轉型和商業性文化環境的形成;其二,是作家對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文化)的反撥和純文學性的消解。建國近30年的國家權威話語的膨脹,社會政治生活的高壓,情與欲的禁忌,十七年文學的宏大敘事,特別是“文革”文學的徹底政治化和烏托邦化,文學與現實生活出現了裂隙,文學疏離了現實大眾的真實生存,即便是“文革”結束后,這一趨向并沒有徹底終結,知識分子話語與大眾話語間的裂隙還存在。個人生活和情感的被消除,使大眾疏離拒絕著如此“慣性”的文學。當然,最重要的乃是改革開放促成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各種禁忌的被打破,私人生活空間的自由度的擴大,城市化、現代化浪潮的迭蕩,市民社會得以逐步形成。按照西方市民社會理論,市民社會是與商品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相聯系的,具有明晰的私人產權及其利益并以契約關系相聯結的,具有民主精神、法制意識和個體性、世俗性、多元性等文化品格的人群共同體。而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新與舊、民主法制與專制特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錯綜復雜,矛盾重重,但即便如此,一個已邁上現代化征途的大國前景仍被看好。
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當代新都市小說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上崛起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當代中國的市民文化精神一方面繼承和弘揚了中國自宋以來,特別是明末清初的傳統市民文化精神,即追求“個性自由、閑適享樂”,反映在文學中的“直面世俗性”,這也是主要的一面。其二,當代市民文化精神也吸收融合了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理性和個人化是現代都市最大的文化特征;西方后現代主義、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對中國市民也沖擊不小。一定意義上,現代化就是世俗化。但與中國傳統市民文化相比其影響要小。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普列漢諾夫的“社會心理”,馬克思的“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或許很能說明這一點。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也認為:“文化是一個綜合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習慣。”④美國學者C·克魯克洪也認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應的各種業已模式化了的方式當中,通過各種符號可以獲得并傳播它;另外,文化構成了人類群體各有特色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制造物的各種具體形式;文化基本核心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傳統(即從歷史上得到并選擇)的思想,一是與他們有關的價值。”⑤這里充分說明民族傳統文化的穩定性與滲透性。而當代中國新都市小說便滲透了更多的中華民族的傳統市民文化精神。正是中國傳統市民文化精神與西方當代城市文化的融合,才催生了中國當代新都市小說。并且從當代新都市小說的主題和藝術形態上看,它的確更多地承繼了我國市民文化傳統。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是中西文化有著根本的迥異,先哲們早已認識到這種差異,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⑥誠然,中國文化以儒道為主脈,但其哲學觀與人生觀卻都是世俗的。由于中國農耕文明悠久,民眾“重實際而黜玄想”,很少生發那種超出實際生活之外的欲求與愿望,故以儒道為主脈的本體論都是將人的注意引向現實人生而不是引出現實人生,即立足于世俗人生建立宇宙觀和本體論,而非總是以彼岸世界為參照,設計宇宙與人生圖景。中國傳統哲學帶著這種內在的“此岸”情結,故對世俗生活一直持認同與肯定態度,即使孔孟儒學從來也沒有否定人的正常與合理的生活欲求,“它所要求的只是人應當將自己的欲求置于理性框架之中,在倫理規則的約束下實現內在的和諧。”⑦所以說中國文化根本上是一種世俗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一種宗教文化。基督教認為,人類此岸的生活微不足道,它不過是彼岸的準備,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恪守原則,死后才能升入天國,否則就要在地獄中受煎熬。所以在西方,人與神、人與上帝的交流、溝通就成了生活中最有意義的事情,人們在生活中常常進行反省與懺悔,力圖通過承受肉體與心靈上的痛苦清洗據說人類生來就有的原罪,以便皈依神性,獲得精神上的救贖。西方文化所具有的這種內在的超越性,使其不可能將價值取向定位在一種世俗的追求上,盡管西方歷史在神性與世俗生活的兩極之間也常發生擺動。如著名的文藝復興運動期間在反抗神性、張揚人性旗幟下的世俗生活,誕生了薄伽丘的《十日談》,拉伯雷《巨人傳》等作品。但基督教文化畢竟根深蒂固,已作為一種天啟的戒律深入到人的無意識中。所以我們常常看到,西方文學對神性與精神超越性的認同被大大超過對世俗性的興趣,他們不斷探索、追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一定程度上,這或許正是西方文學區別并高于中國文學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國文學大多缺乏西方文學這種宗教性精神意義的永恒叩尋,而多沉溺于世俗情懷、日常生活意義之中,這根本上也是由中國的世俗性文化特點所決定的。所以,反觀中國當代新都市小說,往往也難逃脫此“窠臼”,盡管我國新都市小說已取得巨大成就,然而捫心自問,當下中國新都市小說哪一部能與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卡夫卡《城堡》等媲美一下?當然,文學的情況很復雜,不能硬性這樣比。中國有自己的語境。但同時更能說明這樣的道理:文學作為人的精神活動,是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產生、發展都受到后者很深的影響。正如湯學智所言:“一種文學,之所以可以區分為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關鍵在于其不同的民族風格,而決定這種民族風格的關鍵,則在于不同的文化精神,中華民族的文學正是以自己獨具的文化精神為靈魂,為內在的生命。”⑧的確如此,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是作家在生活中積累的體驗、感受的提煉與升華,所以作家所處的物質生活環境、歷史傳統、時代特點,自然、人文景觀、風俗人情等等特點自然而然會在其創作中反映出來。在此意義上,作家確實是本土文化的代言人,文學則是對本土文化的藝術表達。因此,文學必然是民族的,它的軀體中流貫著民族文化的血液、精氣,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著本民族文化的鮮明印記。所以我們一點也不奇怪地看到:首先,市民文化精神影響了作為創作主體的中國當代新都市小說家,他們的身上更多地流淌著中華民族傳統市民文化之血液,盡管許多人本身并未感覺到這些;其次,當代新都市小說家所反映的客體——都市景觀、市民生活,也主要是中國市民社會、市民文化傳統之積淀,加上外來文化——西方消費文化、大眾文化之影響。遂造成當下中國新都市小說喧囂多彩奇特之“景觀”,它們呈現目下都市的種種景觀,市民生活“物”與“欲”的沉迷,乃至墮落,進而展現出現代都市的生命哲學意識。
三、敘事策略:世俗化欲望化圖景
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激活與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與效率,同時也把適者生存的原則帶進了社會生活,這是一個被物欲所驅使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以物的名義,人們可以暢所欲言、為所欲為,物已成為這個時代的《圣經》。脫貧致富便是這種世俗精神的實現目標和實踐形式,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文化語境,新都市小說在1990年代就逐步確立起欲望化的敘事法則。我們知道,新都市小說的主力作者被稱為“新生代”,像北京的邱華棟,廣州的張欣,江蘇的韓東、畢飛宇、魯羊,上海的唐穎、殷慧芬,東北的刁斗、述平,湖南的何頓,廣西的凡一平,海南的李少君等。他們大多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在文革期間處于兒童時期,沒有經歷過嚴峻的政治時代,他們形成自己世界觀的時候正是中國開始加速城市化的時候,可以說,他們是第一代完全意義上的都市人。這些作家深知新市民的審美趣味,在大多數新市民眼中,文學是消費,是娛樂。在為金錢奮斗的過程中,他們拒絕崇高,也不需要沉重,因而他們的閱讀取向標準是傳統民間文學的“快樂原則”。為了迎合普通市民閱讀中的“快樂原則”,新都市小說將作品反映的重心投向平民生存原相,投向人自身生存的各種庸常現實層面,并建立起一種“欲望化”的敘事法則。這種欲望化的敘事法則,具體表現為敘事對于“物”與“性”的依賴。“性”在小說中成了情節發展的動力和情節的樞紐,整個敘事圍繞著“物”與“性”展開。其主要代表性作品有邱華棟《手上的星光》、《環境戲劇人》,韓東《障礙》,朱文《我愛美元》、《尖銳之秋》,何頓《生活無罪》、《我不想事》、《無所謂》,張欣《愛又如何》、《歲月無敵》,唐穎《糜爛》、《紅顏》等。這些作品描繪的主要形象是一群走上市場競爭的城市平民,他們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也是經濟轉軌、市場競爭中的“悲歡離合最直接的體驗者”。小說的作者們以近乎平行的視角展現新時期這個龐大人群的生活方式、欲望和追求,展現現代都市的紛繁、絢爛、動蕩、充滿挑戰性的狀態。可以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首次出現的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量的農民、小職員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鄉鎮,從窮鄉僻壤來到城市,中國社會出現了巨大的邊緣人員層——流民。他們無戶籍、無固定工作與居所,希望有一天能被欲望燃燒的城市接納,這些“闖入者”成為了新都市小說著意描繪的對象。“闖入者”一進入城市,便被五光十色的都市繁華迷惑,欲望的都市點燃了他們內心蟄伏已久的欲望:“我必須要進入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在這樣一個社會迅速分層的時期,我必須要過上舒適的生活”。⑨為此,“闖入者”們使出了各種手段,《音樂工廠》里的楊蘭離開鄉村到城市打工,一度陷入困境,于是這個小姑娘便毫不猶豫地出賣自己青春的肉體來賺錢,獲取金錢上的最大滿足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目標;《新美人》中的那些漂亮女人更懂得充分利用她們的優勢資源——身體,嬌嫩靚麗的臉蛋,妖嬈苗條的身材,來換取她們的享樂、金錢與地位。《我愛美元》更極力描摹了性欲的饑渴狀態,顛覆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父慈子孝的完美關系,具有反文化的色彩,這些作品體現了城市的光怪陸離。“欲望的敘事”成了當代文壇一道眩惑的風景線,而從這些新都市小說中我們既感受到了撲面而來的西方現代都市旋風,同時又分明嗅著了我國古代《金瓶梅》等明清市井艷情小說的遺味。
總之,從新都市小說熱潮中,我們可明顯看到我國市民文化傳統精神的承續和弘揚,當然這是結合了新世紀新時代風尚的具有嶄新特質的當下市民文化精神。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國家意識形態,精英知識分子們往往有意無意地壓抑、攻擊、蔑視市民社會,動不動就斥為“小市民”,市民意識被戴上庸俗、功利、簡單的帽子,這種觀點,時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市場。殊不知,現代化轉型的過程,就是市場經濟大潮中相伴隨的城市化、世俗化的過程以及市民社會的崛起過程。隨著商業社會的發展,市民開始大步躍上社會舞臺,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強行操縱松弛后,在知識分子話語中心位置偏移后,市民的意識和精神空前的活潑,城市的空氣到處可以嗅到他們自信的氣息,可以預言,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社會秩序中,市民意識是可以與主流意識、知識者意識對等發言的。正是中西合璧,土洋結合,使得當下中國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識龐雜紛亂。但我們應該看到,“市民社會”是現代社會的基石,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乃至政治民主、人性的解放、思想自由、學術繁榮,都有賴市民社會的壯大和市民意識的完善。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市民社會正在傳統與現代、中西碰撞的語境中對話、磨合。當代新都市小說以極大的熱情反映此種變化著的如萬花筒似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意識,新都市小說所開啟的充滿市民精神的文學空間,愈來愈活力四射。當然,我們也毋庸諱言新都市小說中的狹小、平庸乃至惡俗的一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家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身份也許會成為歷史,但對人類精神性因素的追問和對平庸現實的抗拒,則永遠應該是文學不可推卸的職責,須知文學作品的精神高度與市民文化精神并不相互抵牾。在此我們深切期待新都市小說創作有更大的突破。
注 釋
①裴毅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頁。
②鐘嬰:《明末清初市民文學與江南社會》,《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3-4期。
③許建中:《論明清之際通俗文學中社會價值導向的嬗變》,《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3-4期。
④汪澍白:《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⑤鄒廣義:《文化·歷史·人》,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8頁。
⑥李中華:《中國文化概論》,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頁。
⑦張衛中:《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頁。
⑧湯學智:《新時期文學熱門話題》,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頁。
⑨邱華棟:《環境戲劇人》,《上海文學》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