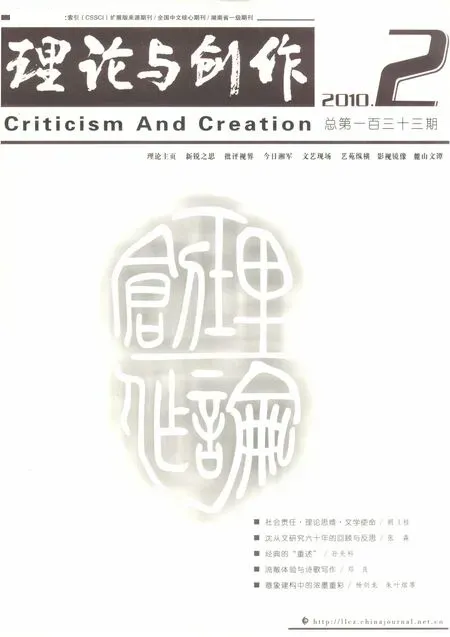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重返八十年代”與“十七年文學”研究?
■ 趙黎波
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及其研究的清理和反思顯然成為了當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熱點問題。顯然,這個問題已非始于當下,199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研究的升溫、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論爭、“純文學”概念反思和“底層寫作”的興起等思想文化事件中,一條反思1980年代的知識脈絡已經清晰可見。2005年“重返八十年代”這一命題的提出和實踐,更是將這一反思活動全方位整體展開,并上升到方法論高度和文學史反思的層面上來。
“重返八十年代”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它將1980年代擱置在一個開闊的文學場域,“嘗試通過將八十年代歷史化和知識化,探討何種力量以何種方式參與了八十年代的文學建構。”①通過對重要作家、批評家的走訪,對1980年代重要文學現象、作家作品、重要期刊和文學制度的分析,對核心概念的梳理,試圖還原出一個復雜的80年代,從而揭示“80年代文學”及我們今天的文學史是如何“形成”的。探尋80年代知識立場、文學成規、文學史敘述的形成,成為“重返八十年代”這一學術活動的核心層面。
正是在這個發生學意義的命題上,“重返八十年代”和“十七年文學”產生了緊密聯系。正如一位“重返”的研究者所言:“對1980年代文學的反思研究必須建立在對‘文革文學’、‘十七年文學’反思研究的前提下進行,只有重新發現‘文革文學’、‘十七年文學’的復雜建構才能‘理解’1980年代文學的復雜建構,這之間是一種同構關系。”②如果要從“起源性”的角度談論“新時期文學”的話,如何面對“當代文學”的“遺產”,如何認識“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不僅是“八十年代文學”首要面對的問題,同樣也是“重返八十年代”面對的重要問題。
一、“十七年文學”和“八十年代文學”的關聯性研究
在“文革”后至今的文學批評中,可能從沒有一個時期像80年代批評那樣熱衷于對行進中的文學進行主題概括和歸納。“人的發現”、“人道主義”、“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民族靈魂的重鑄”、“現實主義的復歸”、“反封建”等等,不一而舉,在新時期之初,這樣的總結顯然有它獨特的意義,就像劉再復所說,“新時期文學是在清除極左血污中開拓自己的道路的,它首先要贏得生存與發展的權利”,批評家的發現和吶喊“無疑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文化動力之一”。③但是,這樣急不可待的總結和吶喊除了使新時期文學“不憚于前驅”之外,本身還意味著一種姿態、一種心理、一種熱切的渴望,那就是急于顯示新時期文學的創作實績和新的特質,從而將其與之前的文學徹底劃清界限。
一切都是在對立中顯示出意義,為了發掘、建構新時期文學的“新質”,新時期之初的文學批評者采取的通行策略即是將它和“文革文學”、“十七年文學”區別開來。新時期文學被視為一種對“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清算、反撥、矯正和超越并向著“文學本身”回歸的文學形態。“新時期文學”正是以這種潛在的“進化論”觀念來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本質化的“50-70年代文學”,特別是“文革文學”,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和歷史價值。這就是當代文學史敘述的“斷裂論”,“十七年文學”也因此和“新時期文學”被人為地構成了一種非常緊張對抗的歷史關系。
較早關注“50-70年代文學”的洪子誠曾對這種“進化論”色彩的文學觀進行了反思,他認為,“這種不斷劃分階段,不斷把每個階段宣布為‘新的起點’,不斷掩蓋新的階段與過去關聯”的一清二楚的“斷裂”實際上掩蓋了文學史的“歷史性的關聯”(沖突、承繼、改造、轉化),這顯然極大地妨礙了五六十年代文學的深入研究。④1990年代末,不斷深入的“十七年文學”研究也越來越顯示出這一階段文學的豐富性和復雜面貌,同時,越來越多的文學史事實也在說明了“新時期文學”和之前文學史階段的復雜糾葛。
從“起源性”的角度談論二者的關聯性,昭示了“重返八十年代”嶄新的問題意識。它不再致力于發掘“十七年文學”的“文學性”或“現代性”因素,并以此來將之納入當代文學敘述的整體視野之中。而是探究“十七年文學”作為一種文學資源如何參與到“新時期文學”的建構中的。
“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導者之一程光煒在這方面做了相當的努力。他通過切入具體的文本和文學現象,清理出了一條80年代文學如何“不斷拒絕、重返、清理或挑選‘十七年文學’的復雜的歷史過程”。“新時期文學”在強調自身獨特性的同時,一方面拒絕、批判和排斥前者極左的思想思潮和激進性文學試驗;但同時又將“十七年文學”中被壓抑的因素吸收、消化和轉換到“新時期文學”中來。它建構起來的第一個文學經典——“傷痕文學”,就是直接從“十七年文學”中派生出來的。二者在文學觀念、審美選擇、主題和題材訴求等問題上,都顯現出同構關系。從作家王蒙、張潔、張賢亮等重要作家的題材記憶、寫作經驗和敘述方式中,也可以細查出十七年中所受的文學教育、接受的文學觀念的影響。這表明“十七年”作為一代作家的歷史經驗和文學記憶,在一定程度上實際上參與了“新時期文學”的想象與建構過程。“80年代文學”對“十七年文學”的態度也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化之中,1985年前后,它日益主動表現出與“十七年”歷史剝離的傾向。現代派、文學自主性等新的文學觀念的興起,“十七年”已經成為被刻意“遺忘”的對象,成為附著于政治的“非文學性”文學形態。⑤
伴隨著“十七年文學”和“八十年代文學”的動態關系的,是“八十年代文學”的知識立場、經典建構、文學觀念、文學體制等的不斷形成。新時期文學在樹立新的文學經典、建立自己的文學成規時,它需要恢復五六十年代文學中某些仍未耗盡的活力作為補充,但是它并不是“照單全收”的,而是有著自己的鑒定、甄別、排斥與肯定。⑥“十七年文學”對“新時期文學”的參與,是通過“改頭換面”的形式使自己“合法化”。⑦隨著“向內轉”、“文學的主體性”、“文化熱”、“現代派”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提出,“80年代文學”終于逐漸建構起了自己“去政治化”、“回歸文學自身”的主流文學史敘述。而這一建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強化“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的“政治化”和“非文學化”來得以完成的。
當然,在今天,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80年代文學”建構的知識立場和它的意識形態特征。但是,在當時,這些命題都是作為真理性的不證自明的命題存在的,這種帶有“啟蒙現代性”特征的文學史敘述作為一種話語霸權對其他文學形態起到了排斥和壓抑作用,這在1980年代現實主義的遭遇和先鋒文學的經典化中,體現得再也鮮明不過了。
這種關聯性的研究使得“重返八十年代”有效地揭示出了“80年代文學”知識立場和文學史敘述的形成。“80年代文學”也是經過復雜的沖突、經過對其他異質性的文學現象的壓抑和排斥才建立起來的,從建構方式上來說,它與“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并沒有什么本質不同。這種建構不僅掩蓋了80年代文學本身的復雜性,同時,也將“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本質牢牢地固定在了“政治”這個“文學”的“對立面”上,這兩個歷史階段的文化/文學在80年代的歷史敘述中被整合成為一個“整體性”的文學史事實,其復雜的歷史面貌在相當長時間內被有意無意地“遺忘”。正是從這些問題出發,程光煒的尖銳質疑才是有啟發性的:“也許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新時期文學’排斥、替代‘當代文學’的歷史性的‘豐功偉績’和某種‘進化論’的因素,而是1976年以前的‘當代文學’何以被統統抽象為‘非人化’的文學歷史?……假如說歷史性反省80年代與50至70年代文學的關系,是基于擺脫固有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深度干擾,使其呈現出更為豐富、復雜的研究維度,那么究竟該如何重新識別被80年代所否定、簡化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歷史/文學?它們本來有著怎樣而不是被80年代意識形態所改寫的歷史面貌?另外,哪些因素被前者拋棄而實際上被悄悄回收?哪些因素因為‘新時期文學’轉型而受到壓抑,但它卻是通過對歷史的‘遺忘’的方式來進行的?”⑧不僅如此,他又提出了“十七年文學”作為“重返八十年代”的參照系的說法,也就是說,只有重回“十七年文學”才能看清楚“80年代文學”和歷史到底發生了什么。我想這不只是對于80年代文學的評價問題,同時還是“80年代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的深入。
二、突破80年代“新啟蒙”文學史敘述
“斷裂論”之所以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史敘述,不能不說和80年代的“新啟蒙”話語有著直接的關系。作為對“文革”發生原因的一種闡釋,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論”成為了新時期的重要思想理論資源。既然五四“啟蒙”的任務沒有完成,那么“新時期”作為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使命就是繼續被中斷的“啟蒙”精神。作為八十年代的“元敘事”⑨,它也主導了80年代文學研究者理解、闡釋、敘述“新時期文學”的知識框架和批評立場。通過將“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擱置,80年代的文學批評在啟蒙的層面上將自己的理論資源、價值立場和五四文學接軌,從而形成了以反封建、人性解放和現代化追求為核心的啟蒙現代性價值觀念。在文學范疇內則衍生了一整套與此相關的核心概念、人道主義、主體性、向內轉等。“新啟蒙”思潮影響下的文學史敘述和研究顯然成為主宰“80年代文學”的評價體系,“80年代的文學史,是以‘新啟蒙’為中心的知識分子文學話語方式貫穿始末的”,是“精英文學(或說‘純文學’)對其他文學樣態的‘話語霸權’”。⑩
“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研究對“新啟蒙”文學史敘述話語霸權的顛覆是從解構制約80年代人文知識的“元話語”開始的。李楊認為,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論將“啟蒙”和“救亡”加以對立,實際上隱含其中的是“現代”和“傳統”的對立。這種論述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將50-70年代的歷史剔除“現代”之外,把“新時期”理解為啟蒙的復活。根據“現代民族國家”理論,李楊認為,“救亡”并不是“啟蒙”的對立面,而是“啟蒙”這一“現代性”得以生長的一個不可替代的環節。在這一意義上,“50-70年代”文學并沒有割斷“新時期文學”和“五四文學”的聯系。11在接下來討論的有關當代文學史寫作的一系列文章中,12批評者進一步解構了建立在這種“元敘事”基礎上的文學史“斷裂說”。不僅如此,它還從創作群體、文學建構、批評思維等角度,舉出種種例子來揭示“新時期文學”與“50-70年代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甚至提出了“沒有‘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這種具有鮮明針對性的問題。13
“新啟蒙”敘事不僅是一種知識框架,還是對80年代文學研究影響至深的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即是一種二元對立式的。它將八十年代理解為逐漸擺脫政治回歸自身的文學,將“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整體本質化為“政治性”的“非文學”,這不僅將“新時期文學”和“50-70年代文學”對立起來,將“啟蒙文學”和“左翼文學”對立起來,同時還派生出了一系列的諸如政治/文學、革命/審美、中/西、傳統/現代、文明/愚昧等二元對立結構。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是建立在“整體論”和“本質論”的基礎之上的,它不僅犧牲了“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同樣也簡化了“80年代文學”的復雜進程。
“重返”研究要解構的就是這種“高度本質化的二元對立”。在研究者看來,只有揭示出80年代文學的政治性,才能有效地化解這種二元對立:“如果政治對文學的‘規訓與懲罰’指的是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要求,規定作家如何寫和寫什么,那么,80年代針對文學的規訓同樣無處不在。”14通過對“純文學”、“現代派”、“先鋒小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等80年代重要的文學現象的分析,“重返”研究梳理了80年代文學現象的知識譜系,有力地揭示了其背后的意識形態特征。15
“重返”研究警惕的不僅是八十年代的研究思維方式,而是這種思維方式在90年代以至今天的延續,在他們看來,80年代文學研究的評價系統仍然在制約著文學研究界,這使得很多的反省并沒有有效地進行。今天的很多研究者仍然是在八十年代的知識框架來談論“80年代”、談論文學。“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實際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說,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觀念仍然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對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仍然是八十年代奠定的。”16“一些形成于80年代、未曾被充分意識和反省的思考框架/文化邏輯”仍然“制約著人們指認90年代社會現實的方式”。17
具體到19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研究,我們看到上述的“政治/文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仍然在很多研究中延續,不少成果仍然在重復著1980年代“新啟蒙”語境中產生的研究思路。這種研究大致順著這樣兩種思路在延伸,其一是固守80年代的啟蒙立場,整體上將“十七年文學”界定為“人”與“自我”的失落,18這種研究,顯然是將80年代“主體性”文學作為評價、衡量“十七年文學”的依據和標準,它的非歷史性特征非常明顯。其二,通過文本細讀、資料的重新發現,尋找、放大“十七年文學”的“文學性”因素,以此來證明它是有價值的。“民間”視角、“潛在寫作”概念和思路、“啟蒙文學”形態、“個體精神”碎片等等這些研究成果,19極大拓展了“十七年文學”的研究空間,發掘出了“十七年文學”中被壓抑的文學形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于“十七年文學”的認知。但是,這種研究,且不論它是否存在著過度闡釋的成分,就思維方式上看依然沒有走出80年代啟蒙文學史敘述的“價值預設”。在這些研究中,“十七年文學”的價值是依附于80年代文學而存在的,因為它同樣具有了符合80年代文學趣味和“個體性”、“啟蒙性”文學觀念。
由此看來,“十七年文學”研究如果要取得突破性進展,真正將它的復雜面貌、自身特征、文學史意義呈現出來,就必須在研究的方法論上有所更新,盡快揚棄這種產生于80年代但是至今仍制約著我們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這就是我們要談到的第三個問題,也就是“重返八十年代”的方法論啟示。
三、文學史研究方法的“整體觀”和“歷史化”
“重返八十年代”顯然有著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可以說“80年代文學研究”實際上包含了兩個面向,一是“作為問題的80年代文學研究”,另一個則是“作為方法的80年代文學研究”。20在我看來,這種方法論可以歸結到兩個相輔相成的層面:“整體觀”和“歷史化”。
在對于“十七年文學”和“80年代文學”的關聯性研究中,我們不難體察到“重返八十年代”學術研究的整體性視野和研究觀念。從學科史的角度來看,真正的文學史研究實際上已經暗含了整體性的觀念,缺乏“整體觀”的研究也很難說是一種有效的歷史研究。“重返八十年代”的這種整體視野致力于發掘文學史各個階段的內在聯系,有力地解構了文學史敘述的“斷裂說”。
這種“整體觀”和80年代的那種強調“宏觀研究”方法的整體觀是有區別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的整體觀”在當時用一種新的切入角度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進行宏觀的整體研究。這種“整體觀”作為一種研究范式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當下的文學研究界依然可以看到這種研究范式運用的普遍性。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很清晰地看到這種“整體觀”的研究并沒有真正解決現當代文學各個階段的“斷裂”問題,反而將這種斷裂進一步深化。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這種“整體觀”是有著潛在的價值預設和立場的,這種價值預設使它在進行文學史的整體觀照時是有取舍和甄別的,有學者曾戲稱為“撿好的拿”。21這種“排斥性”理解問題的方式把歷史整體性縮小壓癟,變成了一種狹隘的整體觀。22“重返”研究采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通過“重回八十年代”,以整體性的視野把“被‘新時期敘述’強行拆解、撕裂和斷開的若干個‘文學期’,在承認差異性的前提下尋找它們之間的關聯點,進而“重建各個文學期和文學現象的‘歷史聯系’”,23在對“十七年文學”和“80年代文學”關聯點的研究中,體現的就是這樣的充滿包容性和理解性的“整體觀”研究思路。
和“整體性”的研究思路并行不悖的,即是將問題放在“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的“歷史化”方法。在研究者看來,“始終沒有將自身和研究對象‘歷史化’,是困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24應該說,將“歷史化”這一帶有后現代理論色彩的的研究方法運用于當代文學研究并非“重返”研究者的首創,90年代末洪子誠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與寫作中就體現了將“文學歷史化”的意識,并認為這“不是將創作和文學問題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取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政治的、倫理的、審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考察。”25這種意識在“重返八十年代”中得到充分徹底的貫徹,并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
方法論意識形成的前提是對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存在問題的敏銳體察。“重返”研究者認為,當代文學研究“批評化”傾向和“當下性”特征是其沒有充分“歷史化”的重要原因。而“批評化”的形成和當代文學對“當下性”的迷戀又是分不開的。不斷變化的當下文化語境能夠激活已經“沉睡”的文學史問題的同時,也使得文學批評和研究很難擺脫當代文化語境的制約。尤其是在面對已經成為逐漸“經典化”的文學史階段時,這種過于強烈的當代意識,常常會干擾、阻礙甚至破壞我們對研究對象本身的認知和把握,從而陷入以今律古的迷津。如今不斷升溫的“十七年文學”、“左翼文學”研究中,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以當下的文化語境來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對象,這種作家作品“當下化”的問題普遍地存在于左翼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如從民間的、底層的角度將趙樹理再次經典化;從個人化、女性主義的立場對丁玲小說的褒貶;將孫犁從革命文學的精神譜系中剝離出來成為“多余人”;對郭小川詩歌中的“不和諧”因素的過分強調等等,這些研究在揭示這些經典作家“另一面”的同時,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既定的“經典”性結論的“顛覆”。程光煒通過對孫犁“復活”這一代表性現象的分析,認為,這種研究的“當下性”實際上是根據研究者自身的需要,把研究對象從“文學史”中“拎”出來以支持“當下”文學的構建。強調孫犁小說的“人性美”、突出他作為革命隊伍中的“多余人”形象、高度評價他的晚年寫作,這些都是將他從“革命文學”中剝離出來做法。但是,這種根據當下消費文化語境重新“定義”并給予積極評價的做法是否能夠更接近于研究對象的真實?對此,程光煒進行了質疑:“與‘革命文學’相‘剝離’也許并不出自孫犁本人的真正意愿……這種‘剝離’,在很大程度仍然只是文學史研究的需要……他們并沒有真正‘碰’到歷史的關節之處。”26這種研究歸根結底依然是80年代形成的“文學性”文學史觀念所致。
“重返文學現場、還原歷史語境”,將所有的文學史問題置身于其所處身的特定語境中去考察它的發生發展,“歷史化”的方法也能夠使我們警惕用一種恒定不變的“普遍性”的文學觀念去評價文學作品的方法,真正走出“文學/政治”、“文學/非文學”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80年代”的語境中談論“80年代文學”,同樣在“十七年”的語境中談論“十七年文學”。“重返”研究者不妥協地貫徹了“文學歷史化”的思路:“文學作品的好與壞常常并不由作品本身決定,而取決于評價作品的理論和方法,更取決于我們討論這些文學的語境。——如果我們因此承認‘個人性’本身并不是‘好文學’的理由,那么,是否我們也應當因此放棄將‘模式化’、‘公式化’的文學視為‘壞文學’乃至‘非文學’的偏見呢?”所以研究者“不應該把‘文學’剝離出具體的歷史進程和權力關系,而應該把‘文學’歷史化,——或者說將‘文學’作為話語對待。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不會再以是否與‘政治’有關作為判斷‘好文學’的標準,而是轉向追問這種文學表現的是‘何種政治’與‘誰的政治’。”27
如果說,今天的當代文學研究對“十七年”和“文革”時期文學的政治性有著足夠的警惕和反省,但是往往對“新時期文學”中形成的新的意識形態卻缺乏足夠的認知,“新時期”以來的研究者總是習慣于依憑著自己的文學史知識來評判之前時代的文學,而對自身所處身的文學語境缺乏自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浩然對新時期作家和批評家的憤怒:“有些人千方百計地糟蹋我。當前中國文壇野草雜生,妓女、土匪充斥書攤,他們認為理所當然,而且自己迷醉于描寫舊中國最落后最愚昧的女人裹腳纏足等等破爛貨的展覽,而對我寫的反映建國后農民運動、群眾斗爭的作品恨之入骨,不僅大動肝火,還‘以勢壓人’地對我大加討伐。對于這號所謂作家、實際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28參照系的確立也是相互的,在80年代的研究者眼里,“十七年文學”尤其是“文革文學”是根本沒有什么“文學性”的文學,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思考,在后者的眼里,“80年代文學”的價值又體現在何處呢?即便是“純文學”理想真的能夠得到實現,這種文學就一定是“好”的文學嗎?而為政治服務的文學就一定是沒有“文學性”的文學嗎?按照80年代進化論理念,是否個人化、主體性的寫作就一定比政治性的宏大敘事更進步?這也許很多新時期的作家從來沒有也不屑于思考的問題。
所以,“歷史化”并不僅僅是將研究對象歷史化——探尋它們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的不同意義,同時我們還要將自身“歷史化”,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自身研究也同樣處在“歷史化”過程之中,也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力地不斷對自己文學研究的知識框架、思維方式進行反思和調整,真正做到在“研究80年代”的同時“走出80年代”。
注 釋
①程光煒、李楊:《主持人的話·“重返八十年代文學”專欄之一》,《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2期。
②楊慶祥:《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學”》,《文藝爭鳴》2009年第2期。
③劉再復:《文學八年·序》,見閻綱:《文學八年》,花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④洪子誠、靜矣:《五六十年代文學的意義——洪子誠訪談錄》,《北京文學》1998年第7期。
⑤參考他的系列論文:《當代文學在“80年代”的轉型》、《“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革命文學的激活——王蒙創作自述與〈布禮〉之間的復雜纏繞》、《經典的顛覆和再建——重返重返八十年代文學之二》等。
⑥程光煒:《文學“成規”的建立———對〈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時候〉的“再評論”》,《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2期。
⑦程光煒:《革命文學的激活——王蒙創作自述與〈布禮〉之間的復雜纏繞》,《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⑧程光煒:《歷史重釋與“當代”文學》,《文藝爭鳴》2007年第7期。
⑨11李楊:《“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解構分析》,《書屋》2002年第5期。
⑩程光煒:《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頁。
12主要有《重返“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沒有“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為什么關注文學史——從〈問題與方法〉談當代“文學史轉向”》、《文學史意識與“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文學》、《文學史分期中的知識譜系學問題》等。
1316李楊:《“文學史意識”與“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文學”》,《江漢論壇》2002年第3期。
14李楊:《重返80年代: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80年代文學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訪談》,《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
15參看賀桂梅和程光煒關于“80年代文學”的知識譜系和意識形態研究的系列論文。
17賀桂梅:《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上海文學》2004年第5期。
18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9這一類研究在“十七年文學”研究中較為常見,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張光芒關于十七年文學中啟蒙碎片的發掘等,可以說是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20參看《文學、歷史和方法——程光煒教授訪談錄》,程光煒、楊慶祥,未刊。另外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80年代文學研究叢書中,程光煒將他的講稿命名為《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這都可以看出他們自覺的方法論意識。
21郜元寶:《批評五嗌》,《文藝研究》2005年第 9期。
22 23程光煒、楊慶祥:《文學、歷史和方法——程光煒教授訪談錄》,未刊。
24程光煒:《當代文學學科的認同、分歧和建構》,《文藝研究》2007年第5期。
25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26程光煒:《孫犁“復活”所牽涉的文學史問題》,《文藝爭鳴》2008年第7期。
27李楊:《“好的文學”與“何種文學”、“誰的文學”》,《南方文壇》2003年第1期。
28蔡詩華:《歷史是一面鏡子——浩然及其作品評價》,《文藝理論與批評》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