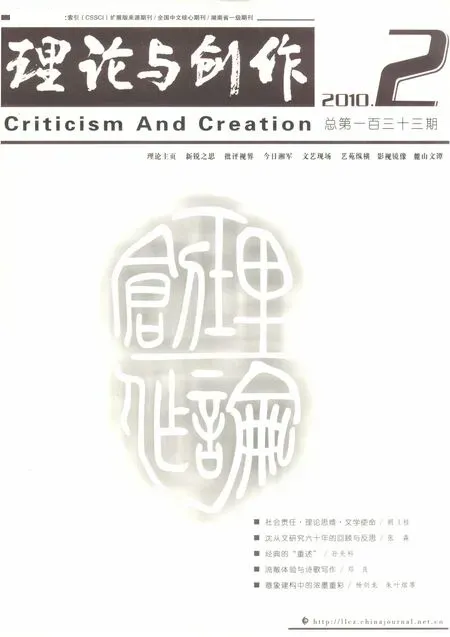人性的透視表現與現代國家民族想象——評張翎長篇小說《金山》
■ 王春林
我想,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經注意到了,在進入新世紀之后的中國文學界,一個十分令人驚喜的現象,就是所謂海外華人寫作群體的異軍崛起。如果突破國別的界限,只是從語言運用的角度來看,那么,當下時代的所謂漢語寫作,就應該被區分為以下的四個部分。首先當然是大陸用漢語寫作的漢族作家,其次是香港臺灣地區的漢語作家,然后是海外那些一直堅持用漢語寫作的作家,最后則是大陸使用漢語寫作的其他民族作家。在過去的研究視野中,我們往往不會注意到最后一個部分的存在,總是不約而同地把第四部分與第一部分的作家籠統地放在一起進行討論。現在看起來,這樣的一種理解區分方式還是存在一定問題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雖然這些非漢族作家同樣在使用漢語進行創作,但由于他們所處的文化背景與漢族作家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所以,他們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較之于漢族作家的作品自然也就具有著一種十分明顯的異質文化因素。關于這一點,我們在諸如阿來、扎西達娃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中,就有著突出的感受。因此,在我看來,把他們從總體意義上的漢語作家中剝離出來加以考察研究,也還是很有一番道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有以上四個部分作家的共同努力,所以新世紀以來的漢語寫作才呈現出了一種可謂是空前繁榮的可喜景象。這其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我們在文章開頭處已經提及的所謂海外華人寫作群體的異軍崛起。即以我自己非常熟悉的小說創作來說,包括嚴歌苓、張翎、陳謙等人在內的一大批海外華人作家,近幾年來,就已經在大陸的許多重要刊物上發表推出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優秀小說作品。別的且不說,最近幾年來由中國小說學會主持評選的,在海內外已經產生了廣泛影響的中國小說排行榜,海外的華人作家可以說是年年都榜上有名,而且,有的年份還往往是兩三位海外作家同時登榜,真的是相當引人注目。很顯然,一直堅持使用漢語寫作的這些海外華人作家,業已構成了一支漢語寫作的生力軍。他們正在以他們的積極努力,在與其他的漢語寫作群體一起,共同推進著當下時代總體意義上的漢語寫作。我們這里所主要關注著的作家張翎,就是這些海外作家中創作成就格外突出的一位。
張翎是一位寫作態度格外虔誠勤奮的作家,迄今不僅創作有長篇小說《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等數部,而且還有若干部中短篇小說集行世,其中的中篇小說《羊》和《雁過藻溪》,曾經被列入中國小說學會2003和2005的年度排行榜。但就我自己的閱讀感受而言,我以為,張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恐怕還應該是2009年上半年連載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的長篇小說《金山》。雖然說,《人民文學》雜志今日在文學界的地位,已經無法重現其當年“國刊”的重要性了,但說《人民文學》雜志依然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文學刊物之一,卻也還是無法否認的一個事實。近些年來,《人民文學》雜志雖然能夠打破陳規,開始完整地發表長篇小說,但所發長篇小說畢竟有限,一年也不過三、五部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張翎的《金山》能夠以兩期連載的形式發表在這個重要刊物上,就足見刊物編輯對這部作品的肯定與重視。具體來說,張翎的《金山》乃是一部以海外華人一百多年來的苦難與奮斗史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說。雖然長期以來也一直不斷地有表現海外華人艱難奮斗歷程的小說作品出現,但在同類題材的作品中,如同張翎的《金山》這樣具有相當深刻的思想內涵與格外精湛的藝術表現形式的長篇小說其實是極為罕見的。
閱讀《金山》,我覺得有兩個方面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其一,張翎以一種高度寫實的方式逼真地重現了海外華人飽蘸著血淚的艱難創業史。如果說,“十七年”期間的柳青曾經以他的不凡筆力成就了一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中國農民的創業史的話,那么,張翎所成就的則是海外華人一百多年來的一部同樣充滿著艱難曲折的創業史。或許是由于中外文化之間至今都依然存在著很大阻隔的緣故,長期以來,只要一提到海外華人(即華僑),我們最為本能的一種感覺就是這是一個富得流油的社會群體,似乎凡是海外華人就一定是腰纏萬貫的富翁。與之相伴的另外一個感覺就是,他們的富有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并不需要他們自己付出太多的努力,好像海外遍地都是黃金,因而海外華人的財富就都是唾手可得。對于這樣一種存在著明顯錯誤的想象性認識,張翎用她這一部刻骨真實的《金山》予以了斷然的回擊反駁。《金山》所集中展示的,是方得法家族幾代人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為了最終能夠在金山立足所付出的百般努力。實際上,也正是依托于對方氏家族幾代人拋鄉別土,遠涉重洋,在他們心目中的金山(即加拿大)所度過的艱難歲月的詳盡描寫,張翎將海外華人一部飽蘸著血淚的創業史,淋漓盡致形象生動地展示在了廣大讀者面前。由于受到了同村遠在金山討生活的紅毛的刺激啟發,更由于自己的家境特別艱難,所以年僅十六歲的方得法便跟隨著紅毛一起到金山去。只有在經過了多達一百多天的海上漂流抵達金山之后,方得法方才真正地明白了自己所面對的將是怎樣的一種現實。想象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竟然使方得法對于自然界的風都產生了異樣的感覺:“家那邊的風不是這樣的。家那邊的風是圓軟的一團,擦著碰著了,都留不下痕跡。金山的風長著邊長著角,刮著了,不小心就蹭掉一層皮。”只有到了金山之后,方得法方才真正明白,金山的生計其實一樣地艱難。如果不是生計艱難,不是找不著活兒干,這些遠涉重洋來到金山的中國人,又何至于要去修建不僅施工難度特別大,而且生命難以得到保障的太平洋鐵路呢?事實上,將方得法引領到金山來的紅毛的性命,也就葬送在了太平洋鐵路的工地上。可以說,小說中關于方得法他們修筑太平洋鐵路的描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如同方得法這樣的中國平民在金山所度過的艱難歲月的集中展示。
然而,被金山人稱為“豬仔”的方得法們,不僅要干那些金山人根本就不愿意沾邊的最低賤的活計(比如修筑太平洋鐵路),而且更得面對“豬仔”這樣一種稱呼后面的那樣一種強烈的種族歧視。因而,小說中的這樣一個段落描寫,就是特別意味深長的。“當阿法背著一長一短兩個布袋,穿越幾乎沒有人煙的荒林朝都市走來的時候,阿法不知道,在一個叫克拉克列奇的小鎮上,最后一顆道釘剛剛被砸進枕木。太平洋鐵路終于和中部東部的鐵路合攏,形成一條橫越過加拿大胸脯的大動脈。盛大的慶功宴席正在香檳酒的開瓶聲中拉開序幕……阿法也不知道,在所有的照片和新聞中,沒有人提起修鐵路的唐人。”“一個也沒有。”雖然中國人為了太平洋鐵路的建設付出了血的巨大代價,但他們的勞動價值卻并沒有能夠得到公平合理的評價與對待。這種現實遭遇,正是當時海外華人苦難遭際的一種真實寫照。事實上,只有當方得法有了這樣一番真切的人生經歷之后,他才確確實實地明白了在金山客表面上的風光背后所要付出的艱辛與屈辱。然而,金山的生存環境就是再艱難,也畢竟還是要比家鄉廣東開平要更容易些。這也正是方得法們雖然歷經艱難但卻仍然繼續呆在金山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方得法的兩個兒子錦山、錦河也先后來到了金山。他們父子三人雖然兢兢業業地不斷努力,但他們的家族式經營卻總是起起伏伏,始終沒有能夠取得想象中的成功。更為重要的問題在于,雖然他們事實上已經為金山當地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由于一種天然文化隔閡的存在,更由于金山當地社會一種種族歧視心理的根深蒂固,所以,在前前后后經過了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之后,一直到作為方得法第三代傳人的艾米·史密斯,才可以說真正地融入到了金山當地的社會之中。很顯然,張翎所濃墨重彩地描繪著的方得法家族在金山的人生遭遇,完全可以被理解為是幾代海外華人苦難經歷的一個形象縮影。
苦難人生的形象呈示固然很重要,但對于張翎所從事著的小說創作事業而言,與苦難生活的真實再現相比較,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卻是在展示表現苦難人生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對于堪稱豐富復雜的人性世界的深層透視與表現,因為小說畢竟是一種關乎于人性的語言藝術。通常意義上,在一部具有現實主義品格的長篇小說中,對于人性進行深層透視的結果,往往就是一系列具有相當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畫塑造。閱讀張翎這部現實主義色彩非常明顯的長篇小說,給讀者留下難忘印象的正是作家成功塑造出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或許因為作家張翎自身身為女性的緣故,雖然作家未必就在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上面下了過多的功夫,但從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成功程度而言,與方得法、錦山、錦河這些男性形象相比較,我個人覺得,張翎還是對女性形象的理解塑造要更加深入內在一些。無論是六指、貓眼、金山云,還是亨德森太太、方延齡、桑丹絲,甚至于包括那位令人倍感厭惡的區氏,這些女性形象都給讀者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首先當然是六指。應該說,這是一個性格特別堅韌、強悍的悲劇性女性形象。她的堅韌與強悍,最早是在她出嫁方得法的過程中得以充分體現的。因為方得法的母親麥氏本來已經替兒子選定了一個姓司徒的女子為妻,所以,盡管方得法一再央求母親自己要娶六指為妻,但母親卻以六指天生有不吉祥的六個指頭為由而執意不允,只答應六指可以給他做妾。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為了把握自己的命運,六指居然不懼死亡的威脅,用切豬刀將自己的第六個指頭砍了下來。就這樣,六指憑借著自我堅韌的強力意志,最終如愿以償地成為了方得法的妻子。六指堅韌、強悍性格的另一次充分體現,是在她和小兒子錦河一塊被土匪劫走而又一塊被贖回來之后。因為麥氏一直對方得法違背自己的意愿執意與六指結婚心懷不滿,所以,她的滿腹怨氣便借著這一難得的機會噴發了出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身為婆母的麥氏居然懷疑六指早已失身于土匪了。“麥氏把兩只瞎眼睜得天一樣的大,愣愣地盯著六指,許久,才狠狠地呸了一口,說誰和你是一家?你從朱四那里回來,你還敢說自己是方家的人?六指掙開麥氏的手,覺得地在她的腳下裂了一條縫。那條縫載著她一寸一寸越來越低地陷落到萬劫不復的泥塵里。”在那樣一個把女性的清白看得比生命都要重要的時代,一個女性的貞潔一旦受到懷疑,她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究竟會有多大,我們是完全能夠想象得到的。就這樣,在她的生命歷程中,六指又一次置身于難以擺脫的困境之中。怎么辦呢?六指第二次被迫以傷殘自身的方式來救贖自身。當婆母麥氏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之際,六指親手剜下了自己腿上的肉,燉湯救回了婆母的性命。“六指舉著刀,閉著眼睛剜了下去——朝自己的腿上。這一次她并沒有感覺到痛。她只覺得有些麻木,如螞蟻一樣地爬滿了全身。她試著挪動了一下腿,腿紋絲不動,仿佛已經從她身上脫落。”這是怎樣的一種生命堅韌啊!先后兩次以自殘的方式來達到自我救贖的目的,沒有強悍的生存意志者肯定是做不到的。面對這樣的一種具有十足象征意味的動作描寫過程,我們在感受到人物強力意志的同時,更多體會到的其實是一種悲劇式的獻祭意味。不知道作家張翎在設定這樣的故事情節時是否已經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反正我從小說中讀出的卻更多是一種無奈的悲涼感覺。
實際上,我對于作家在小說中展示著的六指與墨斗之間的關系,有著更為濃郁的興趣。他們之間雖然名為主仆關系,六指是明主,墨斗是義仆,但事實上卻有著更多復雜的情感糾葛。說他們之間存在著更多的情感糾葛,倒也并非是說他們已經突破了男女主仆之間的界限,發生了怎樣的不堪關系。我所強調的只是,在他們之間才可能存在著更多的精神交流與情感溝通。六指與方得法之間雖然有著夫妻的名分,但由于方得法遠在金山,所以他們實際上是聚少離多,除了依托于來往的書信傳遞信息之外,他們之間其實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交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六指與墨斗之間建立在精神相通基礎上的日常交往。雖然囿于時代道德規范以及他們之間現實主仆關系的制約,六指與墨斗始終都沒有在感情問題上越雷池一步,但我們卻不難發現,在漫長的日常生活中唯一能夠與六指進行精神、情感溝通的人,卻只有墨斗。這就說明,六指的性格雖然特別堅韌、強悍,但她卻也終歸是生活于一個具有強大男權傳統的現實世界中。在某種意義上,從她與墨斗的此種情感交流狀態,我們也完全可以看得出,其實六指也是一個處于情感枯寂狀態的被禁錮在某種無形的男權傳統中的“閣樓上的瘋女人”。我們之所以強調這一人物形象的悲劇性,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在六指這一人物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作家張翎犀利的人性解剖刀已經深深地探入了人物的人性縱深處。
然后是亨德森太太。雖然同樣是悲劇性的女性人物,但亨德森太太的柔弱、善良,卻與六指的堅韌、強悍,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因為亨德森先生在危難之時曾經幫助過自己,所以,當亨德森先生家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傭人照顧體弱的亨德森太太的時候,知恩必報的方得法就硬是逼迫著剛剛來到金山的小兒子錦河到亨德森先生家幫傭。但誰知這一來,錦河自己在進入一個陌生世界的同時,卻也為我們打開了理解亨德森太太精神世界的一個有效通道。按照小說中的交待,亨德森太太患有嚴重的關節炎:“疼痛像一只捉摸不定地游走在她血液里的蟲子,晚上睡下的時候還停在手指上,早上起來的時候已經走到肩上了。”為了緩解亨德森太太的疼痛,錦河就采納了錦山的建議,使用大煙汁為她止痛。但令錦河根本無法預料到的是,正是在他在亨德森家幫傭期間,亨德森太太居然以主動引誘的方式,和他發生了不正常的肉體關系。如果僅僅只是從這一點上來看,那么,亨德森太太無疑是一個精神上的變態者。為了留住錦河,亨德森太太不惜與女兒珍妮發生了尖銳的沖突,以至于瘋狂跑到大街上的珍妮居然因車禍而亡。然而,關鍵的問題在于,如此柔弱、善良的亨德森太太何至于有此出軌之舉呢?其中的原因,只有到了后文中才由亨德森先生親自揭破。卻原來,亨德森先生居然是個同性戀者:“從你到這里第一天起,我就喜歡你。可是她夾在我們中間,山一樣的,我爬不過去。所以我只好躲,我寧愿天天出差。我從來沒喜歡過她,這不是她的錯。我只是,不喜歡女人,任何女人。”亨德森先生自己是一個不喜歡異性的同性戀者,但他卻又偏偏要與身為異性的亨德森太太結婚,如此作為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對于亨德森太太的嚴重傷害了。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方才徹底理解了亨德森太太的一切變態行為,甚至于也理解了她身體上的嚴重疾病。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亨德森太太身體上的嚴重疾病,也理解為是其精神疾患的一種象征隱喻性表達。這樣看來,雖然導致她們被囚禁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亨德森太太卻與六指一樣,都可以被看作是“閣樓上的瘋女人”,可以被看作是對這一現代寫作傳統的進一步豐富。張翎在小說中雖然對于男性人物的人性世界有著同樣深入的觸摸和表達,雖然張翎在寫作之前所確定的寫作主旨中未必會有對于女性精神世界的透視與表現,但從文本的實際表達效果來看,作家對于諸如六指、亨德森太太這樣一些女性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和表現,卻的確給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這樣一種動機與結果或許悖反的創作狀態,再一次為“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句俗語提供了特別有力的注腳。不僅如此,長篇小說的所謂多義性或復調性也由此而得到了一種切實的證明。
其二,則是張翎在《金山》中通過對于以方得法家族為代表的海外華人的描寫,所突出表現出的國家民族想象的問題。按照中國社會的基本發展演進歷程,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想象,其形成出現的時間只能是在近代以來,也即是張翎小說所具體描述展示著的這一百多年時間。在此之前,中國人只有所謂天下的概念,而根本不知道在中國之外還有一個極其廣闊的世界存在。既然只知道天下,不知道世界,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明確的民族國家概念的形成了。說到底,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是晚近以來伴隨著所謂現代性的出現而逐步形成的。長期以來,一直有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文學創作的形式探究表現著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產生的問題。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是因為海外的華人作家置身于異國他鄉,對于所謂國族的身份問題有著感同身受的強烈感覺的緣故,我們往往能夠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明顯地感覺到有對于民族國家問題的思考與表達。張翎的《金山》很顯然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我們雖然無法確證張翎的創作動機中就有著對于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問題的自覺思考,但最起碼因為《金山》乃是一部表現一百多年來海外華人艱難奮斗史的長篇歷史小說,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對于所謂民族國家問題的探究與表現。
說到《金山》中的國家民族想象,就需要特別注意張翎在小說中始終沒有中斷的這樣三條線索。一是關于歐陽家族的描寫。與小說所重點描寫表現著的方得法家族的幾代人相對應,張翎也先后進行過關于歐陽家族三代人的描寫。第一代是對方得法本人曾經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歐陽明先生。因為父親方元昌曾經得到過一筆意外的橫財,所以方家也曾經一度有過中興的日子。因為日子好過了,所以方元昌便把自己的兒子方得法送到歐陽明先生那里去讀書接受教育。方得法最早的民族國家意識,就是從歐陽明先生那里得來的。這一點,從他向阿爸轉述的歐陽先生的教誨中即可得到確切的證明。“阿爸,歐陽先生說夷人賣給我們煙土,就是想吃垮我們的精神志氣。民垮了,國就垮。”不僅如此,即使是家道敗落之后方得法最終決定遠走金山的主意,也是歐陽明先生幫著拿定的。當然,歐陽明先生對此自然有他自己的考慮。“這邊的日子是黑到底了,那邊的日子你至少還可以拼它個魚死網破。歐陽先生的一句話,一下子將那個不成團也不成形的模糊想法捏成了團,揉成了形。阿法就有了主張。”事實上,也正是在歐陽明先生的大力肯定之下,方得法才最終拿定了遠走金山的主意。于是,也才有了整部《金山》描寫表現著的全部故事。第二代是對方得法的女兒錦繡及女婿阿元曾經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歐陽玉山先生。與歐陽明先生相同,歐陽玉山先生出演的依然是思想啟蒙者的角色。“阿元讀過許多兵器的書,都是歐陽玉山先生借給他看的。歐陽先生說中國好比是一頭獅子,身上長了一個巨大的毒瘡。這毒瘡一天不清除,獅子一天就站不起來。”第三代歐陽先生的身份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位名為歐陽云安的先生,在繼續承擔啟蒙者使命的同時,也成為了小說中作用特別重要的情節線索導引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張翎的這一部《金山》采取的是一種由現在而不斷地返回到過去,現在過去不斷地互相交織,而又以既往的歷史為主要透視表現對象的敘事方式。雖然現在并不是小說的主要表現對象,但這樣一個敘事視點的重要性卻是無可置疑的。很顯然,正是因為作家占據著這樣的一個敘事制高點,所以她對于既往歷史的思考與表達才會呈現出如此一種面貌。雖然小說采用的是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方式,但卻依然有很重要的視角式人物存在。具體來說,這人物不是別人,一個是作為啟蒙者的歐陽云安,另一個是作為被啟蒙者的艾米。艾米出演的是一個尋根問祖者的角色。很顯然,在她的成長歷程中,或許正是出于自己由于特別的出身而曾經在金山(加拿大)備受歧視的緣故,她的母親方延齡并沒有把她的身世來歷講述給她聽。因此,對于自己的血緣家族譜系,身為社會學系教授的艾米,始終處于被遮蔽的狀態,一點都不知情。只有在來到中國,與肩負民族國家啟蒙重任的歐陽云安結識之后,在歐陽一再反復的積極努力之下,被蒙蔽多年的艾米才對自己的家族歷史有了一種清晰地了解和認識。在某種意義上,艾米如同我們一樣都屬于小說中所表現著的這一百多年歷史的局外人。張翎藝術設計的絕妙之處就在于,艾米的好奇心,實際上也正是我們作為局外人的讀者的好奇心。當她頗有敘事耐心地將一幅漫長的歷史畫卷慢慢拉開的時候,所滿足的就既是艾米也是我們自己的好奇心。這樣,張翎也就很好地調動起了讀者的閱讀主動性,使讀者積極地介入到了小說意義的建構過程之中。
二是與歐陽家族的啟蒙式影響有關,作家張翎所特別設定出的方得法家族與國家民族之間的種種牽系。其一表現為晚清重臣李鴻章到金山訪問時,方得法對于李鴻章講的那番話:“稟報中堂大人,我們在這里過得不好。官府的大營生,我們都不能沾邊。我們只能做白番不肯做的爛活,工錢只有白番的一半。”當方得法一再強調我們與白番之間的區別的時候,所表現出的自然也就是一種強烈的國族意識了。事實上,正因為接受過歐陽明先生啟蒙教育的方得法具有強烈的國族意識,所以在親耳聆聽了梁啟超的金山演講之后,他才毅然決然地出賣了自己其實經營得很好的竹喧洗衣行,并且把其中最大的一份寄給了北美的保皇黨總部,以示對康梁的堅決支持。其二表現為錦山在聆聽了孫中山的演講之后表示愿意加入洪門時發辮的被剪掉。真可謂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方得法聽到的是梁啟超的演講,而金山聽到的則是孫中山的演講。梁與孫均是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走向產生了巨大影響的重要歷史人物。在一部表現海外華人百年苦難命運的長篇小說中,一再地把如同梁、孫這樣真實存在過的重要歷史人物穿插進來加以濃墨重彩的描寫,所充分凸顯出的首先正是作家張翎身上一種極其強烈的國族意識。其三則表現為抗戰期間錦河不僅捐出四千加元用以購買飛機,而且還參加了加拿大軍隊并最后為二戰的勝利英勇捐軀。關于錦河的這些事跡,方得法的家譜里有明確的記載:“民國二十九年方錦河向廣東國民政府捐贈四千加元用于購置抗日飛機,獲愛國紀念勛章。同年方錦河加入加拿大軍隊,以特工身份在法蘭西南部一鎮收集情報并培訓地下抵抗組織。民國三十四年盟軍勝利前夕身份暴露,為國捐軀。”從方得法最早接受歐陽明先生關于國族問題的啟蒙教育,一直到錦河以自我獻身的方式致力于國家民族的解放事業,方得法家族與國家民族問題之間的牽系,可謂是貫穿了張翎《金山》的始終。作家對于國族問題的強烈關注與深入思考,由此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三是一直貫穿于小說始終的中國勞工在金山(即加拿大)所必然遭受的種族歧視。所謂海外華人一百多年來的艱難創業史,除了他們不得不在金山干那些金山人根本就不愿意沾邊的苦活累活之外,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們的精神世界還必須得同時承受來自于金山人本能的一種種族歧視。這一點,雖然在方家的幾代人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在艾米的母親方延齡身上卻體現得特別明顯。應該注意到,艾米曾經對歐陽云安講過這樣一番話:“其實,方家的故事一代不如一代精彩,到了我這一代,幾乎有些落俗套了。無非是一個遭夠了白人白眼的單身中國母親,想把她的女兒從地上拔起來,送到天上的故事。這個媽媽在賭場一直工作到退休,一生用她并不豐厚的收入,孜孜不倦地打造女兒成為一個上等社會的白人。”很顯然,方延齡之所以會在女兒的成長問題上如此地耿耿于懷如此地固執,正是因為她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在金山備受冷眼欺辱的緣故。雖然我們無法得知作家張翎在異國他鄉有過怎樣的屈辱體驗,但實際上,在她對于諸如方延齡這樣的中國人海外受辱的情節展示過程中,卻非常明顯地有著自身生存經驗的曲折投射。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樣一種強烈的來自于異國異族的歧視性看法,往往會強有力地激發出如同方得法他們這樣的中國勞工更加強烈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愿望。雖然由于受到他們思想文化水平的限制,他們根本不可能在思想認識的層面上真正地理解民族問題的內在原理及其重要性,但他們卻可以憑借自己的本能感受來體現出自身一種強烈的國家民族的想象認同情結。
總之,海外華人苦難命運展示過程中人性的透視與表現,以及滲透于故事情節之中的現代民族國家想象,正是我從張翎的《金山》中讀出的最值得引發我們深入思考的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之所以能夠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藝術表現,我覺得,與作家對于一種特別的小說結構方式的設定,與作家對于多種文體形式的雜糅運用,同樣存在著十分緊密的關系。規劃設定怎樣的一種藝術結構,對于長篇小說而言本來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而對于張翎的這樣一部要在三四十萬字的篇幅內講述海外華人長達一百多年的傳奇性歷史的長篇小說來說,采用怎樣的一種結構方式,就自然是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了。張翎在這一方面很顯然花費了很大的心思。從這個角度來看,艾米和歐陽云安這兩位結構串聯式人物就顯得特別重要了。這就是說,這兩位人物,既是小說中的方氏家族與歐陽家族中的重要成員,同時也是對于小說的結構而言十分重要的功能性人物。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兩個結構串聯式人物,張翎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對于故事情節順時序的平鋪直敘,才能夠對于一百多年來的人與事做出符合自己敘事意志的有效篩選。哪些事情可以進入自己的敘事視野之中,哪些事情應該以極充分的筆墨展開詳盡細致的描寫,而哪些事情只需簡略地提及一下即可,諸如此類的一系列問題,張翎都能夠憑借這樣的一種敘事結構方式做出自如的選擇。同時,借助于艾米和歐陽云安這兩位結構串聯式人物,讀者也可以有充裕的空間對張翎的小說文本進行深度的再思考與再創造。然后,就是多種文體形式的雜糅運用。小說中,除了借助于特定人物視角的常規敘事之外,張翎還同時穿插運用了諸如書信、報刊報道、族譜記載、通報、廣告等多種文體形式。這些文體形式的運用,一方面使得小說的篇幅大大縮短,另一方面也幫助作家張翎更好地實現了自己的創作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