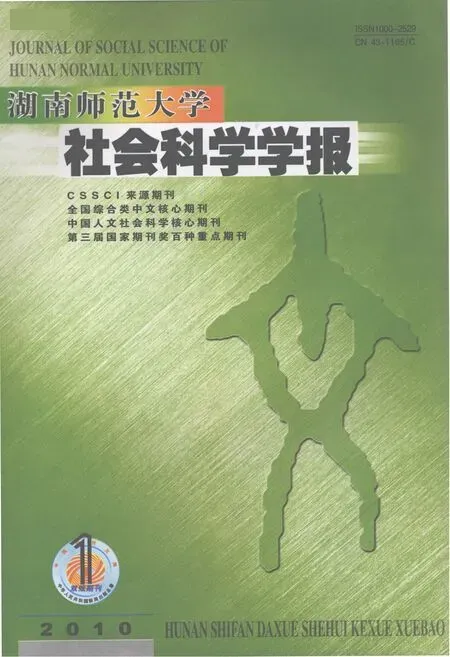基于協同的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研究
曹曉鮮
(中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吉首大學,湖南 吉首 416000)
基于協同的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研究
曹曉鮮
(中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吉首大學,湖南 吉首 416000)
針對當前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研究的不足,我們運用文化生態理論、區域品牌資產理論和協同理論,分析了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內涵、特性及其構成體系,并結合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創建的內部沖突,基于協同的視角提出了調整政績考核機制、建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管理委員會和民族文化旅游發展利益共享機制的三條品牌資產提升建議。
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協同
一、問題的提出
湖南西部地區不僅有著“世界自然遺產地”之稱的張家界自然山、水、洞等自然景觀,也有著以古城鳳凰為代表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人民在長期生態環境適應過程中所創造的民族文化資源。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相對于自然景觀而言,民族文化資源由于其獨特性、體驗性、原生態等特點日漸成為更富內涵和價值的旅游資源。不過,伴隨民族地區旅游資源的開發,傳統的民族文化正日益被侵蝕。民族文化的同質化、庸俗化、商業化、價值觀的退化和遺失已經嚴重威脅著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如曾經古樸的麗江、鳳凰由于過度的商業化已使其旅游品牌價值大幅下降。
如何在開發中實現民族文化的保護,學者們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理念。良警宇(2005)、蔣麗芹(2005)、趙麗麗等分別從民族文化的挖掘、再造和展現,以及民族認同感和當地群眾商品意識強化等方面肯定了實現民族文化的傳承和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是西部民族地區旅游開發要解決的當務之急。同時,他們強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開發在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意義,并充分肯定了對實現以民族文化和生態旅游資源的永續利用為目標的可持續發展的“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觀[1]。而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具體開發模式上,黃萍(2005)、余青(2000)[2]和劉旭玲等(2005)則提出了創建文化生態村和生態博物館的持續旅游發展模式。在實證研究方面,賴斌等(2007)通過建立模糊因子分析模型的方法研究了民族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測度問題。[1]
顯然,上述研究已表明學者們對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高度重視,也從“旁觀者”的角度進行了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戰略思考。不過,這種不從旅游開發的“當局者”出發來設計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開發模式,難免忽視“當局者”的動機和行為模式。而且,民族文化生態的公共物品特性不可避免地使“當局者”存在過度開發的動機。為了避免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源的“公地悲劇”,本文嘗試運用生態旅游理論、品牌資產理論和協同理論從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價值維護和提升的角度探討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源的有效保護和開發問題。
二、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內涵及其構成體系
“文化生態”是指文化的生成、傳承、存在的生態狀況,是指將文化納入生態視野,使人們獲得對文化的新認識。“生態性”是文化生態的重要特征。而民族文化生態就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成的結構系統以及它們與自然地理、社會環境的關系。[2]一般而言,其外化形式為獨特的建筑形式、服飾、飲食、慶典節日、風俗習慣等極具吸引力和體驗性的資源。
1.民族文化生態旅游
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是應民族地區文化生態保護和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從我國民族地區的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實踐來看,各民族地區通過將其傳統文化展現于旅游者面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外來游客及其現代文明的影響,傳統的民族社會文化也在迅速地發生質變。針對民族文化的這種脆弱性,引入生態旅游的概念,強調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
因此,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可以被界定為是指以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為研究對象,在最大限度滿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和減少對旅游目的地文化進程發展的影響的前提下,將生態旅游理念貫穿于整個旅游系統,并指導其形成有序發展的可持續開發模式。
2.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內涵及其特性
品牌資產是上個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指一個既定的品牌賦予產品的附加價值。這種附加價值是除產品的功能利益外的價值,可從公司、交易、消費者等層面加以衡量。一般而言,品牌資產被理解為品牌的營銷效應和社會效應。其中,營銷效應指品牌在市場上所產生的效果和反映,包括給經營者帶來的效應,如利潤、規模、無形資產、管理、文化效應等;而品牌的社會效應則包括示范、優化和國力效應。
顯然,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公司品牌資產,是一種區域品牌資產。而所謂區域品牌資產,蔣廉雄等(2005)認為是在滿足外部消費者的需要、實現內部營銷主體目標一致的基礎上,增加區域品牌的消費者影響力、市場競爭力和區域品牌的社會影響力,以提高區域品牌的營銷效應和競爭能力,為區域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區域居民創造最大的附加值,以促進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目標的實現。[3]據此,我們不難將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界定為:在滿足外部游客的需要、實現內部旅游開發者(含文化載體的居民本身)目標一致以及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質(封閉性)的自我發展(包容性)基礎上,增加該地區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游客影響力、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以提高該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的營銷效應和競爭力,為民族地區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居民創造最大的附加值,以促進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目標的實現。
從上述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內涵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發現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具有以下特性:
(1)公共物品特性。一般而言,同時具備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兩個條件就是純公共物品。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一旦創建成功,該區域內任何旅游開發主體都可以使用這一品牌低成本或無成本地享受其帶來的收益,同時,任一主體的使用并不阻礙其他主體的使用。顯然,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就具備了公共物品的特性,是一種區域性公共物品[4]。
(2)品牌資產構成的復合性。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作為一種區域品牌資產,一方面,它涵蓋了民族地區文化生態的物質、精神、制度諸層面及它們與自然地理、社會環境的關系;另一方面,它應包括民族文化產品、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服務、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產業、自然地理、文化、社會系統等不同的產品層級。因而,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具有多層次和復合性。
(3)品牌資產價值創造主體的多重性。由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復合性可知,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產價值的創造必須由不同的主體來共同創造。比如,民族文化的創造和承載者——民族地區居民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生成是品牌資產價值最根本的創造者,而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主要開發者——旅游開發公司則是品牌資產價值的提升和直接實現者。
3.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構成體系
根據上述對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及其品牌資產內涵、特性的理解,借鑒區域品牌資產的構成體系,我們結合文化生態及品牌資產理論將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解構如下:
(1)民族文化生態物質品牌資產。民族歷史遺存遺跡、民居建筑、服飾、飲食、生產生活用具及工藝品等物質形態,是民族文化的一般物化表現,在平凡中透視著民族文化品格,具有普遍存在性。這些物質的民族文化遺產屬于民族文化生態的認知層面,是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的最基本構成。其游客吸引力、市場競爭力、社會影響力及其相互協調性影響著該品牌資產價值的大小。
(2)民族文化生態精神品牌資產。民族精神理念、價值觀念、心理素質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形態,是民族文化的源頭與本質,也是民族文化生態的感知層面,一般外化為民族禮俗、民風、民俗、行為舉止及宗教儀式等行為形態。其中,以反映民俗、民風等為主題的影視作品、文學繪畫作品、民歌民舞,甚至民族地區藝術家本身等都是民族文化生態精神品牌資產的具體構成。其強大的體驗性、感染力和名人效應是品牌資產測度的重要指標。
(3)民族文化生態制度品牌資產。除了外在化、生活化、具體化的民族文化生態物質形態構成和反映民族精神理念、價值觀念的精神層面構成外,還存在具有一定強制性的民族文化規范化表現形式,即民族宗教制度、宗族制度、道德及約定俗成的規范等制度形態。它和民族文化生態精神形態一起作為一個民族的“原本精神”所在,是民族文化的內在運轉機制,保證了民族文化的歷史傳承與延續。其中,制度形態的約束力、內生性、包容性是測度品牌資產的重要維度。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構建表1所示的民族文化生態品牌資產構成體系。

表1 民族文化生態品牌資產構成體系
三、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創建現狀與內部沖突
湖南西部地區為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隨著“大湘西旅游圈”的進一步推進,該地區民族文化旅游開發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但不容忽視的是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中忽視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已導致民族文化衰退和變異現象嚴重,威脅著湖南西部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續發展。雖然,目前該地區正在積極嘗試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模式,但由于對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缺乏科學認識和有效的內部沖突協調機制,民族文化生態旅游仍面臨發展的桎梏。
1.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現狀
近年來,湖南西部民族地區一方面通過大型電視節目“走近湘西”、“神秘湘西”、“走玩湘西”以及舉辦各種大型活動如“南長城國際圍棋賽”、“鳳凰國際音樂節”等加大民族文化旅游的宣傳力度;另一方面,通過挖掘、整理、聯合開發打造了一大批民族文化旅游產品,如夜郎文化遺跡、里耶古城、鳳凰古城、南方長城,土家族的“擺手舞”、“打溜子”,苗族的“接龍舞”、“猴兒鼓”,侗族的“長龍宴”以及這一地區廣為流行的巫、儺文化、巴楚文化等。[4]基本上形成了以民族文化遺存遺跡、民居建筑(如鳳凰古城、芙蓉鎮、里耶古城)為中心,以民族風情村寨(如德夯苗寨、臘爾山苗寨等)為輻射點,以民族歌舞、習俗、服飾、工藝品、特色食品為載體的立體開發模式。不過,隨著景區知名度的提高,游客數量急劇增加,本地居民商業意識增強,再加上行政隸屬上的各異,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各旅游開發點相互攀比,彼此模仿,內容單一,檔次不高,缺少實質性的創意,缺乏統一規劃和全面統籌,從而表現出明顯的開發無序性。而在核心景區(如鳳凰古城),為了追求短期經濟效益最大化,過分地商業化不僅導致了民族文化資源的濫用,而且破壞了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嚴重威脅到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永續利用。
2.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總體評價
依據第二部分所構建的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構成體系中的構成層級及相應的測度指標,結合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的現狀,我們可以對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作一簡單的定性評價。①首先,從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物質層面看,千年古鎮——鳳凰、美麗的王村——芙蓉鎮、南方長城、夜郎文化遺跡、里耶古城,苗族、土家族服飾、銀飾,酸辣食品,水車,湘西蠟染等都是具有較大的游客吸引力、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的品牌資產。但在開發過程中,由于過度的商業化出現了與民居建筑不協調的現代建筑、設施與經營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質品牌資產的價值。其次,從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精神層面看,獨特的苗族“邊邊場”、“接龍舞”、“猴兒鼓”,土家族“哭嫁”、“攔門酒”、“擺手舞”、“打溜子”、“茅古斯舞”,侗族的“長龍宴”,以及“上刀梯,下火海”等風俗、歌舞和宗教儀式都具有很強的體驗和互動性;而反映湘西民族文化的影視、文藝作品《血色湘西》、《邊城》以及歌舞《小背簍》、《辣妹子》等都具有相當的感染力;同時,人才輩出的湘西也擁有極具名人效應的藝術家,如沈從文、黃永玉、宋祖英等。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民間藝人正在興起。不過,由于年輕一代外出讀書、入城打工的緣故,很多傳統風俗、工藝制作出現后繼無人的尷尬局面,這不利于民族文化生態精神資產的傳承。再次,從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產品牌價值的制度層面來看,湘西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宗族制度以及道德規范都內化于各種祭祀儀式中,如對自然、祖先、神靈的崇拜,“忠君”與“崇祖”,求子與喪葬儀式等等。②由于這些宗教、宗族儀式不僅體現了湘西民族文化的信仰、德性、人倫與生命意識,而且各種儀式具有極強的藝術性、觀賞性。特別是土家族的喪葬儀式、巫術征戰儀式、“斗龍”求雨、“鞭石”求雨、驅邪逐魅儀式等。其中,湘西民族文化人倫意識中的包容開放精神使該地區民族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其信仰和強烈的生命意識則使其文化具有較強的內生力和約束力。
綜上所述,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三個層面都具有較好的基礎和較大的開發潛力。現存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物質層面的協調性有所破壞,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還很有限;精神層面的體驗形式較單一、較粗糙,感染力有待加強,民族傳統文化名人后繼無人;制度層面傳統的宗教、宗族信仰、儀式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開發,其約束力、內生力都有減弱的趨勢。
3.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創建中的內部沖突
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作為一種區域品牌資產,由于其自身公共物品特性、品牌資產構成的復合性以及品牌價值創造主體的多重性,不可避免會出現品牌資產創造的內部沖突。具體表現為三方面:一是品牌資產創造時的“搭便車”行為,各品牌價值創造主體都寄希望于其他主體作出努力,而自己不愿意承擔成本,結果造成品牌價值創造投入不足,制約了品牌資產的生成和提升;二是品牌資產構成的復合性導致的在品牌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彼此不協調;三是品牌資產一旦創建,由于其公共物品特性,各品牌價值的使用者會忽視其使用品牌資產的外部成本,從而濫用品牌資產,釀成品牌資產的“公地悲劇”。目前,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創建中的內部沖突已成為該品牌資產價值提升的重要障礙。首先,該地區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隸屬于湘西自治州、張家界、懷化三個不同的行政區,由于現有政績考核方式的局限,三市(州)缺乏共同打造“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激勵,相反,各自為政、彼此競爭、同質模仿,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浪費,而且有損于該品牌資產的現有價值。其次,即便在同一行政區內,由于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各旅游資源開發主體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視彼此之間的協調和長遠利益。有的旅游資源開發主體甚至在惡性競爭中不惜歪曲、庸俗化民族文化,直接損害品牌資產價值。再者,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中,由于開發者多為外來投資者,大多數民族文化的直接傳承者、載體——當地居民并沒有得到旅游開發所帶來的實惠,從而挫傷了他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積極性,致使除了那些純粹為了旅游而表演的民族風俗、歌舞以外,更多的、真實的民族文化正在悄然失去。而這種民族文化的丟失是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提升的最大障礙。除此之外,還有居民與游客之間的沖突以及文化保護部門與旅游開發部門之間的沖突都是重要的阻礙因素。因而,要成功打造和提升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價值,協調上述沖突,實現協同發展乃是當務之急。
四、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提升策略:基于協同發展的視角
協同理論(synergetics)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多學科研究基礎上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是系統科學的重要分支理論。該理論認為,千差萬別的系統,盡管其屬性不同,但在整個環境中,各個系統間存在著相互影響而又相互合作的關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會現象,如不同單位間的相互配合與協作,部門間關系的協調,企業間相互競爭的作用,以及系統中的相互干擾和制約等。而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把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創建和提升看作一個由多個子系統形成的復雜系統工程。為了克服品牌資產創建過程中的沖突,實現協同效應,將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由無序變為有序。基于協同發展的視角,特提出以下建議。
1.調整政績考核機制,納入“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貢獻評價因子
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級行政區域是一天然的經濟發展系統。而政府在該系統中發揮著最直接的作用,在以經濟增長速度作為核心考核指標的政治升遷制度背景下,各級政府只關注任期內本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當然,在一定程度上,該制度促進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競爭,也使政府自覺限制“掠奪之手”,積極實施“援助之手”,保護地區內的產權,引導和資助地區內企業發展。同時,也因為該制度以絕對的行政區內經濟發展業績作為嚴格的考核界線,各行政區系統之間缺乏彼此協作的真正動機,即使在外力的推動下,勉強實施合作,也會因為“外部收益內在化,外部成本外部化”的私人理性而導致集體不理性,陷入“囚徒困境”。目前,“大湘西旅游圈”概念早已提出,但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原因就在于此。因而,在實質性推動“大湘西旅游圈”和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創建過程中,要讓三個以各自政府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系統相互協調,就必須將他們各自對“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貢獻率作為考核其政績的重要評價因子。使三市(州)將協調打造“大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的努力內化到各自追求政治升遷的動機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測度各政府對“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貢獻率時,必須將“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作為一個嚴格的整體來看待,以避免進入新的無序競爭與發展。
2.建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管理委員會,負責品牌資產保值增值
由于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構成的復合性,以及品牌價值創造主體的多重性,要實現品牌資產各層級的相互協調以及各品牌價值創造主體之間的合作,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協調與管理機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管理委員會。該管理委員會由一名正職和三名副職及相關辦事人員組成,其中,委員會正職由省旅游局相關領導擔任,其他三名副職則分別由三市(州)旅游局長兼任。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協調三市(州)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規劃,統籌三市(州)內的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根據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構成,實現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物質、精神、制度層面的協調一致;引導、鼓勵、監督各旅游資源開發主體的經營行為,嚴懲有損區域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價值的經營行為;通過稅收和財政補貼渠道籌集資金,實施意在擴大區域影響力、競爭力和樹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形象,打造統一大品牌;定期(一般為一年)對“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價值進行評估,制定年度品牌資產價值增值計劃;負責該地區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招商引資,以及督促當地旅游管理機構對旅游資源開發經營主體的監管;考核該地區三市(州)政府在“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創建中的貢獻,并將其作為考核各政府政績的一重要評價指標報送省政府。
總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管理委員會作為一個駐扎在湖南西部的副廳級常設機構,全權負責“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區域旅游協調工作。
3.與民共享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實惠,提高民族地區居民傳承和創造民族文化的積極性
貧窮落后不是特色,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創造不可能像保存文物一樣原封不動地封存,追求日益提高的物質文化需要也是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權利。如果不能很好地滿足他們的這種需要,可能迫于生計,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將消失得更快。目前,大量民族地區的年輕人外出打工、求學,而不愿學習和繼承本民族的傳統禮儀、工藝,不愿意穿戴民族服飾,已經構成了對民族文化旅游持續發展最大的障礙。究其原因在于民族地區居民并沒有隨著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而得到真正的實惠,民族文化的認同感、自豪感甚至被巨大的貧富差距所質疑。少數民族居民缺乏繼承、發揚和創造民族文化的動力。
民族文化具有封閉性和包容性,不同于其他的旅游資源,它本身具有生命力,是動態和發展的。雖然,目前已提出了“文化生態村”和“民族文化博物館”的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模式,但這并非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的最佳模式。這就仿佛為了保護珍稀動物而建立的動物園一樣,雖然我們看到的是這些動物,但這些動物已與大自然中的該類動物相去甚遠。因而,讓民族地區居民在發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同時,確確實實地得到發展帶來的實惠,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感受到他們的文化受到尊重,產生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感、自豪感和責任感,這樣才能使他們自覺地維護、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并在發展中實現民族文化的保護,實現民族文化生態旅游。
因而,建立民族地區居民的民族文化旅游發展利益共享機制,協調民族文化的傳承者、載體與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開發者之間的利益,是提高民族地區居民傳承和創造民族文化的積極性和提升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關鍵。
注 釋:
① 當然,為了更精確地對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的評價,我們可以進行更細致的定量分析,比如通過確定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資產構成體系中各層級及各層級內部各測度指標的權重,然后通過專家打分法得出各測度指標分值,進而可得出該品牌資產的評分。這將在后續論文中進行研究。
② 關于湘西地區民族文化的宗教、宗族制度、文化精神的詳細了解可以參閱胡炳章著的《土家族文化精神》一書,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賴 斌,楊麗娟,方 杰.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測度研究[J].生態經濟,2006,(11):99-101.
[2]趙麗麗,朱創業.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源開發芻議—兼議“攀西大裂谷”格薩拉旅游區旅游開發[J].生態經濟,2005,(6):93.
[3]蔣廉雄.區域競爭的新戰略:基于協同的區域品牌資產構建[J].中國軟科學,2005,(11):107.
[4]鄭必清.生態文明的時代性與水環境建設[J]消費經濟,2008,(1):16.
(責任編校:文 心)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Culture Eco-tourism Brand Property of Western Hunan with the View of Coordination
CAO Xiaox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In view of current national cultur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es’insufficiency,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cology,the region brand property and the theory of coordination to analyze national culture eco-tourism brand property’s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 and constitution system,combining the internal conflicts which generated during the national culture eco-tourism brand property founding in western Hunan.The article then proposes three brand property promotion suggestions from the view of coordination as follows: (1) to adjust the local government’s achievements inspection mechanism,(2) to establish the“Big Western Hunan”national culture eco-tourism brand asset management committee,(3) to share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veling development with the residents.
national culture;eco-tourism;brand property;coordination
F590
A
1000-2529(2010)01-0099-05
2009-09-15
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態旅游資源保護與利用”(08zdb051)
曹曉鮮(1964-),男,湖南桑植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