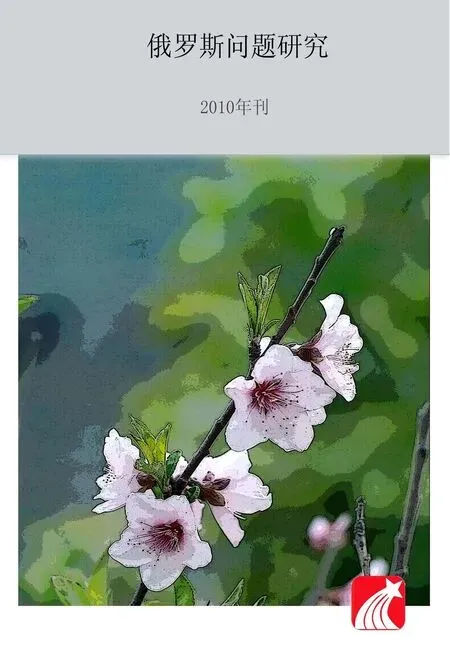俄羅斯的現代化之路:迷霧中的困境
門小軍
俄羅斯的現代化之路:迷霧中的困境
門小軍
俄羅斯的強勢“回歸”引發西方社會專政復興主義理論的鵲起,該理論認為俄羅斯的專制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新的制度選擇。與西方社會的認識不同,民主激情過后的俄羅斯國內社會對秩序和穩定的渴求遠勝于對民主的熱情。基于民意支持而成型的主權民主論雖為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卻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普京體制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俄羅斯國內自由主義復興的機會微乎其微,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專政復興與鐵腕治理在實現秩序和穩定之時所面臨的困境。迷霧之中,“沒有目的地的轉軌”仍將主導俄羅斯政壇很長一段時間。
俄羅斯強勢崛起的西方映像——專政復興主義
20世紀原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陣營轟然倒塌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俄羅斯并未朝著單一的自由民主政治走向“歷史之終結”,許多西方觀察家和思想家在俄羅斯身上看到了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現代化的不同道路:專政政治體系也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以色列歷史學家阿澤爾·蓋特在其2007年發表的《獨裁大國的回歸》一文中指出,俄羅斯的崛起標志著“獲得資本主義經濟成功的專政大國的回歸”,并“代表了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新的制度選擇”。*[美]丹尼爾·杜德尼、約翰·伊肯貝里:《專政復興主義理論評析》,載[美]《外交》雜志2009年1/2月號。專政復興主義就是近些年來西方社會某些學者對俄羅斯政治現狀的一種最新解讀。
美國共和黨新保守主義思想的理論大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其《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一書中也認為,世界面臨反自由主義思潮的挑戰,西方民主陣營和專政陣營之間的激烈對抗將再次籠罩全球,而俄羅斯乃是專政復興主義思潮盛行的典型例證: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政府不僅拋棄了業已取得的民主成果,還實行鐵腕政治,變得愈加專政,“俄羅斯毅然決然地從尚未完成的自由主義轉向了專制主義”。*[美]羅伯特·卡根:《世界分裂,民主遭圍攻》,載[英]《泰晤士報》2007年9月2日。
然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丹尼爾·杜德尼和約翰·伊肯貝里在《外交事務》雜志2009年1/2月號撰文指出,如今的專政復興主義浪潮同冷戰結束時西方媒體大肆鼓吹“歷史之終結”一樣,僅僅是學術界的夸大其詞而已:它的許多理論觀點都很模糊,比如認為專制制度已重新煥發青春與活力,并逐步成為當今資本主義體系中另一種可行的政治選擇;再如認為同過去相比,如今的專政國家在各方面都有長足進步,且更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兩位學者進一步指出,這些專政國家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這也并不能成為批駁自由民主派觀點的例證:它們的經濟成功并非基于統治階層的聰明才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現行國際秩序,并嚴重依賴國際經濟的投資與貿易往來。最為重要的是,專政復興主義國家并非試圖放棄或退出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是重新定義和鞏固它。
專政復興主義理論認為,冷戰的驟然結束和政治經濟制度的劇烈變革使人難免對未來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隨后而至的失望心理讓專政復興主義思想乘虛而入;目前專政在俄羅斯的盛行也有其特定原因,其在歷史上曾遭受外敵入侵,且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實際上,專政復興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特征就是承認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在特定條件下的不同步性,集權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的社會模式并不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而是對弗朗西斯·福山所謂的西方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結合的社會模式的一種有效替代,世界民主發展的前景黯淡。與專政復興主義的此種論調相左,丹尼爾·杜德尼和約翰·伊肯貝里認為沒有跡象顯示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經濟已與專政政權達成某種穩定平衡,并成為一種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新型社會模式;民主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固然會因不同國家的歷史和經驗差異而有所不同,但專政并不是一條現實的現代化之路,它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俄羅斯雖稱不上是民主國家,但與從前相比已經民主很多了,并且許多實現民主政治所需的必備條件業已逐步形成。*[美]丹尼爾·杜德尼、約翰·伊肯貝里:《專政復興主義理論評析》,載[美]《外交》雜志2009年1/2月號。
政績合法性——秩序和穩定也是政績
逝去的前總統鮑里斯·葉利欽照搬西式民主,進行脫離國情的政治改革,導致社會動蕩、信念喪失、民族失去凝聚力、國家失去前進方向、民族分裂主義和地方分離主義猖獗。一言以蔽之,失序的民主和失控的市場乃是葉利欽執政時期的真實寫照,用普京的話說就是:蘇聯解體后頭十年是“俄羅斯三百年來最黑暗時期”*宋魯鄭:《西式民主得了什么病》,載《北京日報》2009年4月20日。。失望情緒彌漫的俄羅斯在普京的鐵腕治理下,終于走向了秩序和穩定。而與此同時,普京的鐵腕治理也被西方貼上“專政”的標簽。
為何國內外反差如此巨大?在發展中國家享有盛譽的已逝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強大政府論可謂是見解獨到。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會引起動亂和不穩定;而要消除這種不穩定,首先必須建立起強大政府,必須強化制度化建構。*張桂琳:《民主與權威的平衡》,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3期。俄羅斯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但由于其現代化尚未完成且存在動亂和不穩定隱患,因而亨廷頓的理論對俄羅斯來說也具有很大的解釋力:蘇聯解體后前十年和后十年的發展對比乃是亨廷頓強大政府論的最好注腳。然而,亨廷頓同時又認為,強大政府若想存續下去,就必須有意識形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政績合法性的三重支撐,其中尤以政績合法性最為重要,一旦政績出現問題,民眾就會質疑這個政權所賴以建立的價值基礎(即意識形態合法性)和這個政權在建立過程中所依據的程序(即程序合法性)。
民主是個漸進的過程,需要社會的成熟發展作為根基,更需要財富的積累和秩序的維持。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所說,“不公平”還比不上“脫序”糟糕,因為即使出現不公正,影響的只是某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而“脫序”會導致全盤崩潰,正所謂“國將不國”,民主何存?“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卻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秩序與無政府之間的分野比民主與獨裁之間的分野更為根本”,亨氏語錄仍擲地有聲,對于俄羅斯來說,秩序和穩定乃是俄羅斯當前政治體系的最大政績。
亨廷頓在其1968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斷言:“國家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區別不是它們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與其看它是民主還是專制,不如看它是否體現了共識、合法性、組織、效率和穩定。”*[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耶魯大學出版社,1968年。若以此視角來觀察俄羅斯的國內現實,普京的鐵腕治理已然實現了穩定和共識(秩序優先于民主),政治架構(組織)也在選舉政治(合法性)的磨礪下逐步成熟起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效率)也使政府解決社會矛盾的信心大增。
與西方社會關于俄羅斯專政復興主義論辯的熱鬧氣氛相比,俄羅斯人民對西方民主已不再狂熱和盲目迷信,民主激情燃燒過后的普通老百姓對秩序和穩定的渴望之情溢于言表。為回應西方國家對目前俄政治體制的指責,基于“民眾對普京的高支持率”,俄國內“主權民主論”開始成型。該理論認為,民主和主權同等重要,民主原則和民主標準不應導致國家解體和人民受窮,而應使國家更加安定團結,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達成民主政治屬于一國內部的自決事務,要根據本國歷史、地緣政治、國情和法律由本國人民自主決定民主的模式和實施路徑。*范建中、徐宜鵬:《俄羅斯的“主權民主”:由來、爭議及前景》,載《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4期。
俄羅斯未來怎么辦——沒有目的地的轉軌
普京雖將主權民主論作為政府的主導意識形態,但也面對外界“極權民主”的詬病。為此,普京不得不再三表明他并不打算追求所謂“俄國式的民主”,俄羅斯接受所有文明世界都接受的民主原則,“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培植與鞏固民主不會使民主概念本身遭到玷污”。*馮紹雷:《俄國式民主》,載《東方早報》2005年2月28日。可見,普京通過不否認民主具有普適性而小心謹慎地給民主在俄羅斯的“獨立”發展留下空間。俄現任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也表示,21世紀俄羅斯現代化將以民主的價值觀和體制為基礎。*梅德韋杰夫:《俄羅斯現代化基礎是民主價值》,http://gjgy.1949w.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6主權民主論固然符合俄羅斯的傳統文化,且適應轉軌時期俄羅斯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普京奉行主權民主論的目的很明顯主要不在于鞏固個人權力,而在于為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造創造有利條件,而其背后則體現了俄羅斯當局深刻的憂患意識:在國際競爭中俄羅斯已經落伍并面臨嚴重危機,唯有放棄不切實際的民主幻想,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并使之成為“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成為“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這也就是說,普京的主權民主論在理論和實踐當中都帶有過渡性質,而最終的發展目標仍不可知。
其實,即使是讓俄羅斯當前的政治秩序持久存續下去至少也面臨兩大挑戰。其一,一旦上文提到的大規模社會改造付諸實施,普京執政集團面臨的風險將隨之增大:社會改造必然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他們會質疑政權的合法性并起而反對。其二,俄羅斯當前政治體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極度依賴普京的個人威信,在許多俄羅斯人的眼中,普京代表了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有資力和能力重新維護長期處在西方陰影之下的俄羅斯國家利益。這種信任是維持一個脆弱國家并使社會團結凝聚在一起的關鍵因素,一旦失去這種信任,就可能會引發社會騷動。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蘇聯問題專家安德斯·阿斯倫德還注意到,普京的一些“治國方略”也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特點,其實也缺乏可持續性。
普京體制的存續依賴民意的支持,俄羅斯執政集團向民眾提供一定水平的“豐衣足食”來換取他們的忠誠,這實質上是建立了一種社會契約關系。*[美]利昂·奧隆:《俄羅斯21世紀的違禁言論》,載[美]《外交政策》雜志2009年7/8月號。普京社會契約的瓦解固然現在還看不到任何跡象,但即使此種社會契約瓦解了,自由主義復興的機會也非常渺茫。正如在押的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所說,令人不安的真相是:普京“比70%的人更自由化、更民主化”。*阿卡迪·奧斯特洛夫斯基:《財富的逆轉:俄羅斯何去何從》,載[美]《外交政策》雜志2009年3/4月號。俄羅斯民意測驗機構“列瓦達中心”2008—2009年的調查顯示,認為國家處在正確軌道上的人一年來從59%下降到41%,而認為俄羅斯方向錯誤的人則從27%上升到39%,*[美]利昂·奧隆:《俄羅斯21世紀的違禁言論》,載[美]《外交政策》雜志2009年7/8月號。但這在美國企業研究所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利昂·奧隆看來,可持續的自由主義化的前提條件在俄羅斯可能更難鑄造,打破普京體制創建自由主義化的基礎條件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復雜而冒險的工作”,單純的經濟改革遠遠不夠,必須要有一個突出市民社會培育、注重保障個人政治自由的新社會契約的創建。利昂·奧隆認為這雖然不可能是俄羅斯政府的首要任務,但俄政府也的確“忽視”了此種選項民意支持過低的現狀。英國《經濟學家》雜志駐莫斯科辦公室主編阿卡迪·奧斯特洛夫斯基更是指出,一旦普京體制瓦解,俄羅斯面臨的情況可能會更糟。
總之,俄羅斯雖放棄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而步入市場經濟軌道,但堅決排斥來自外部的“目標管理”模式。當前的普京體制面臨執政風險加大和普京個人威信下降的雙重挑戰,政府的主導意識形態主權民主論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而俄羅斯國內自由主義復興的機會也非常渺茫,“沒有目的地的轉軌”可謂是俄羅斯未來一段時間發展前景的唯一可能路徑。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