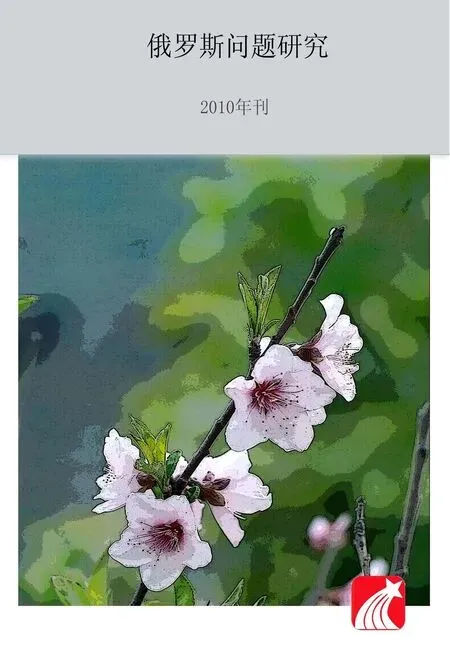俄羅斯和中國發展路徑的新模式
彼得·拉特蘭 著 王新穎 編譯
俄羅斯和中國發展路徑的新模式
彼得·拉特蘭 著 王新穎 編譯
本文是美國衛斯理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彼得·拉特蘭于2008年11月提交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全球化與歐亞”研討會論文的最后部分,論文題目是《后社會主義國家與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演變:俄羅斯與中國的比較》。
作者對比了俄羅斯和中國在過去20年的經濟體制演變,分析了兩國改革的初始條件、領導人的政策選擇和改革的路徑,發現在政治轉型和經濟改革中,兩國經驗的不同之處遠多于相似之處。但是,俄羅斯和中國作為向全球資本主義轉軌的大國,都沒有完全采納“華盛頓共識”的價值觀和機制,而是逐漸在一種可以被稱做“北京共識”的模式中趨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趨同和模式?它對于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發展將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篇論文的最后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
俄羅斯和中國不同的軌跡說明,全球化對單個國家的影響是不可預測的。兩國雖然都面臨著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但是領導層的選擇和歷史演進的偶然性還是起著作用。中國和俄羅斯為全球化理論家提供了一條普遍的經驗,那就是,世界并不是“平的”,強大的國家可以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中找到合適的角色。
兩個國家現在看來在一種受規制的市場模式(a regulated market model)中趨同,在這一模式中,市場多元化因素被嵌入到后共產主義、權威主義的制度和實踐中(這有時被稱為“北京共識”)。這種新的受規制的市場模式有哪些要素呢?
(1)領導人致力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認同的統一,這就意味著防止外國領導人和機構強迫俄羅斯和中國政府作出政治和經濟決策,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不能要求以國家主權作為交換。批評意見認為,這種對主權的堅持僅僅是證明領導人控制權力的正當性的一個幌子。而辯護者認為,這是一種基于對本國人民的福祉的關切的原則性姿態,他們的歷史已經證明容許外國人侵入領土的可怕后果。
民族主義是領導人的修辭,但是他們并不想讓它失去控制而引發破壞穩定的群眾運動,或威脅到與重要貿易伙伴的關系。在俄羅斯和中國,隨著兩國向國際市場的不斷開放,民族主義看來都明顯加強,這與全球化必然引起“身份和制度的不斷破碎”的觀點正好相反。
(2)領導人把經濟增長視為主要目標。在其他意識形態方面的正當性辯解遭受侵蝕的時候,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國家安全、提升制度的合法性。增長也擴大了領導干部個人致富的機會,同時也令人遺憾地把他們的注意力從人的發展的問題上轉移開。
(3)不論是國內經濟還是國際經濟,市場機制都是經濟增長最有效的工具。國際貿易對所有參與者都是一種雙贏的局面。每個國家都必須接受比較優勢的邏輯,在國際分工中尋找到最合適的位置。在中國,這意味著通過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剝削大量廉價勞動力。在俄羅斯,這意味著出售國家的礦產資源。兩國領導人都希望通過發展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走向食物鏈的上游。在接受全球化邏輯方面中國超過了俄羅斯。中國甚至比美國的老盟友日本更愿意降低貿易壁壘。
(4)市場有其局限,必須受到國家監管。那些侵蝕國家合法性和能力、激發不受控制的社會抗議的市場力量必須得到糾正。國家必須出面提供公共產品——從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對改革失意者進行補償,一直到制定規制框架。政治精英對經濟行為者的思想脫離自己的控制感到不安。所以,出現的政治經濟體具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雜交的特征。這或許沒有政治和經濟相分離更為有效,但是它的好處(對領導人來說)是保證政治階級不可或缺。
(5)自由民主并非最適宜的和最必要的,執政政治精英之間的公開對抗要保持在最低限度。中國領導人毫不含糊地反對自由民主范式,正如黎安友指出:“民主化、自由和人權會導致一種更真實的穩定的論點——正如世界上的民主人士所確信的——對于中國領導人來說已經沒有吸引力。”他們甚至有膽量發布批評美國人權的報告來回應美國國務院的中國人權紀錄報告。俄羅斯的立場更加微妙:領導人正式接受民主價值,它們被寫進1993年憲法。但俄羅斯的實踐明顯偏離民主理論。克里姆林宮的思想家們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這一點,提出了“可控民主”和“主權民主”等說法來彌合俄羅斯實際與西方理念之間的差距。
(6)經濟繁榮所造就的中產階級是這個受規制市場體制的一個社會基礎。這與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期望相反,他們在傳統上把中產階級視為民主的可靠旗手。傅士卓認為1989年之后中國社會契約的基礎是“以政治停滯來交換經濟繁榮”。埃德·弗里德曼認為“中國城市新的中產階級往往會把民主想象成一種賦予大多數人——農村窮人——權力的制度”。中國的中產階級也被蘇聯解體后的混亂嚇壞了,因此更愿意支持權威主義的技術官僚領導人。
在俄羅斯,正如民意調查和選舉結果證明,職業人士受到1990年代經濟休克的創傷,歡迎普京的鐵腕所帶來的穩定。在中俄兩國,中產階級已經徹底接受消費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并將它與汪暉所說的“消費民族主義(consumer nationalism)”中的政治融為一體。
這種“受規制的市場”路徑真的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理論上和實踐上前后一致的范式嗎?或者,它是一種思想和政策的矛盾混合體,是不同趨勢的一種暫時重合,而在未來幾年就會分岔?
20世紀60—80年代從巴西席卷東亞的上一波權威主義發展浪潮于90年代平息。這波浪潮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不論是國際上(全球共產主義),還是國內(強大的工會),都存在一種真正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威脅。國家需要保護市場抵御市場的反對者。當冷戰結束這些反對者的力量受到削弱時,權威主義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但是受規制市場的模式根植于一種不同的世界秩序中,根植于不可能很快消失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國家的作用被視做為市場力量履行其職責提供政治穩定,規制性的干預需要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有利于東道國,而不僅僅是外國伙伴。在冷戰后這兩個前社會主義大國的迫切生存需要中,受規制的市場似乎體現了一種切實可行的組織上的反應。
這種現象為全球發展的新階段打開了大門,在這個階段游戲規則可能并不為西方強國獨斷。俄羅斯和中國希望在國際舞臺上成為規則的制定者,而非僅僅是規則的接受者。但是兩國的發展道路是可持續的嗎?如果是可持續的,它們是否可以與其他大國就一套與現行價值觀不同、將塑造下一個十年全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新價值觀達成一致?巴西、印度、南非、印尼等國也在接受國際融合,并經歷著快速的增長。但是與俄羅斯和中國不同,它們是穩固的民主國家。所以,全球化了的世界并不是“平的”:這里有多種多樣的、切實可行的模式在應對其挑戰中出現。
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俄羅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