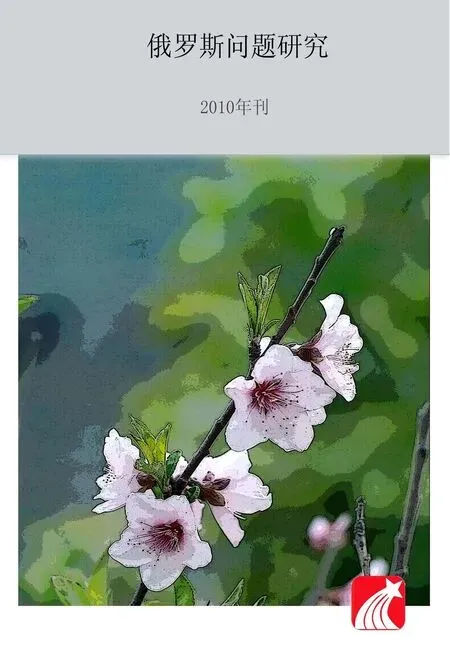1989年后匈牙利自由主義夢想的終結
亞當·法布里 著 張瑞花 編譯
1989年后匈牙利自由主義夢想的終結
亞當·法布里 著 張瑞花 編譯
2009年11月是柏林墻倒塌20周年。20年前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統治東歐國家的一黨專政政權幾乎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許多評論者認為只有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在中東歐才能行得通。斯大林主義的垮臺被認為是“整個體系失敗”的象征,是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的市場優于行政計劃的最好證明。社會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和人類發展的一種方案,只淪為對過去的回憶。但是,20年過去了,作為該地區一度的領跑者、轉型優等生匈牙利,其新自由主義夢想實現了嗎?《國際社會主義》雜志2009年秋季刊第124期刊載了英國布魯內爾大學中東歐問題研究學者亞當·法布里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后,中東歐進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政治改革與經濟快速自由化的結合不僅會帶來更大的個人自由,也會給該地區危機四伏的經濟帶來繁榮及更高的生活標準。匈牙利作為蘇聯集團中市場改革的領跑者,被一致認為是該地區未來成功轉型的典范。
然而,20年過去了,匈牙利轉型期的調整結果遠不盡人意。新自由主義對匈牙利社會的影響更多時候可以說是毀滅性的。國家的經濟產量急劇下降,失業率暴增,多數人生活水平下降,社會不平等加劇,漸趨貧困化已經成為匈牙利的標志。這種局面遍及東歐其他國家。
同時,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使得匈牙利的經濟危機正在迅速轉變為政治危機:處于執政地位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盟一片混亂,近期的歐洲議會選舉也證實了極右勢力正在興起。
國家資本主義與市場之間
對于1989年后匈牙利自由主義夢斷的原因,我們必須從近年來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中去探尋。
從整個地區看,柏林墻倒塌前,隨著20世紀70年代早期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顯現和戰后長期經濟繁榮的結束,全世界的領導者們都面臨著投資回報低和大量失業再次出現的問題。然而,柏林墻兩邊應對經濟危機的措施卻截然不同。
西方領導者摒棄了從20世紀40年代末就采納的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凱恩斯主義”,取而代之以“全球市場原則”。
東歐國家的最初反應是抗拒來自國際市場的壓力。然而,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只能使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缺陷逐漸暴露無遺。從內部來說,指令性經濟結構主要偏重于工業生產而不是產品和服務的專業化。從外部而言,屈服于蘇聯利益的壓力不僅意味著東歐經濟與國際市場的一體化進程依然受到限制,同時表明這種一體化模式從根本上存在缺陷。到70年代末,世界經濟衰退的影響愈加明顯。由于擔心民眾不滿加劇,一黨制國家的領導者試圖尋求變通,最終他們選擇更深地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即通過從西方進口高科技產品,出口工農業產品這一政策來達到目標。以前匈牙利就是這個區域的領跑者,它從西方進口產品速度之快遠遠高于其他蘇聯集團國家。但問題是:這種不斷增長的貿易如何買單?
東歐各國政府試圖從西方國家、銀行和國際組織的可兌換貨幣中尋求貸款來克服這一困難。因此,它們的債務負擔從70年代開始大幅增長。匈牙利做了反面教材:到1978年它的可兌換貨幣貿易逆差已經達到30多億美元。從整個東歐地區來看,這一被動局面從80年代開始就沒有出現過減緩的跡象。
世界經濟的外部壓力及內部當權官僚集團和反對派的改革要求,使一黨專政的領導者們陷入困境。1985年開始,戈爾巴喬夫試圖運用“公開性”和“重建”政策對計劃經濟進行根本性改革。這一設想意味著允許更大的政治自由。同時試圖在經濟領域引進市場激勵措施來鏟除腐敗。然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卻為蘇聯官僚統治階層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面對國家不斷攀升的債務問題,匈牙利執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不得不在1985年和1986年進行經濟改革:在雇用和解聘工人方面給予國有企業管理者更大的自由,頒布了破產法和失業保障法。然而,隨著改革的失敗,要求對全社會和社會主義工人黨實施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響。1989年秋天,議會通過了匈牙利轉型為議會民主制國家的法令,從10月23日開始,這個國家就不再是“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了。
經濟改革之邏輯
一黨專政政權結束的最初幾年里,匈牙利人普遍情緒樂觀。人們相信有可能享受到和他們的西方鄰國一樣的自由和生活水準。一些國家新選舉的領導人大肆鼓吹在不久的將來和西歐一體化的可能性。
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國際主流經濟學家、決策者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組織對此作出了回答。他們認為只有通過一種快速而激進的經濟改革才會趕上西方,即“創造性毀滅”,重點是盡快擺脫對經濟的束縛,實現市場化和私有化,鼓勵政府繼續實行眾所周知的“休克療法”。這種改革模式在經濟范疇內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國家角色觀點,這與凱恩斯理論所設想的“管制型國家”的觀點完全不同。
西方專家普遍預言,匈牙利作為市場改革的先行者會發展成為未來本地區政治經濟成功改革的典范。然而,事實證明現實與新自由主義的夢想截然不同。
缺乏創造力的“創造性毀滅”
20年過去了,這些為適應全球資本所進行的調整打通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通往全球資本之路,但結果卻十分糟糕。整體來看,這個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重建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產量暴跌。即便是世界銀行也不得不承認,“對于所有國家來說,轉型期經濟衰退的強度和持續時間比得上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情況甚至更糟。”
對于匈牙利經濟來說,20世紀90年代從某種意義上講變成了迷失的十年。直到2000年,經濟才開始復蘇,至2006年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始終保持在4%。但當前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結束了先前這種微弱的增長。
隨著生產的急劇萎縮,長期失業演變成了匈牙利經濟的一個象征。官方失業率目前是9.6%。全球經濟危機更使失業率不斷攀升,實際工資收入持續走低,而政府打算進一步削減社會開支。根據2003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所作的一份調查:2003年,匈牙利人實際工資只達到80年代的水平,貧窮人數高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近300萬人)。
轉型后經濟的低迷狀態加深了階層、種族和地區間的不平等。全國家庭中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之間的差距從1992年的7.5倍上升到2003年的8.4倍。經濟轉型的主要受益者是人口的一小部分(10%—12%)。另外,還存在著一個大約占全部人口的30%的中間階層。對于中間階層,轉型在某種意義上是喜憂參半。
貧窮在匈牙利也有種族方面的原因。經濟轉型在吉普賽人中引起了災難性的后果。吉普賽人就業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從75%下降到30%。吉普賽人的貧窮率幾乎是其他人群的7倍。今天,吉普賽人不僅面臨失業和貧窮的危機,而且面臨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生命的威脅也與日俱增。
最后,地區差異也在加劇匈牙利境內的不平等。自1989年以來,布達佩斯和與西歐接壤的西部地區獲得了大部分外資投入,而其他地區則少得可憐。尤為嚴重的是,1989年后不久,北部和東部地區遭受了重工業和礦業崩潰所帶來的劇烈沖擊。匈牙利的這些地區,其失業率、貧窮和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也達到了最嚴重的程度。
結 論
1989年后匈牙利在發展中所衍生的矛盾,需要借助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來解讀,這些變化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向跨國資本主義進行轉變的過程。這種變化促進了全球貿易和金融市場的成長,也帶來了跨國公司的崛起。同時,“競爭性放松管制的邏輯”凸顯資本主義的矛盾。
匈牙利自1989年以來的坎坷道路,并不是“錯誤政策”(以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形式出現)或“腐敗政府”(盡管這些因素無疑加重了匈牙利的困境)的結果,而是基于一般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以及帝國主義競爭必然存在的特點,“本身是內在擴張傾向和集中傾向的副產物”,其發展趨勢是加劇“落后國家”的負擔。
當前的經濟危機毫不留情地使這一情況更加惡化,它使中東歐的小國及脆弱的經濟體成為“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工人階級被遺忘,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發言權,在統治階級的進攻面前不堪一擊。
怎樣才能找到可選擇的反制力量?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似乎是尤為正確的選擇。根據卡爾·馬克思、托洛茨基以及傳統理論中其他人的觀點,我們不但能夠剖析匈牙利自1989年以來發展不平衡的原因,而且還要喚醒工人階級,用托洛茨基的話說,他們仍然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譯者單位:陸軍航空兵學院基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