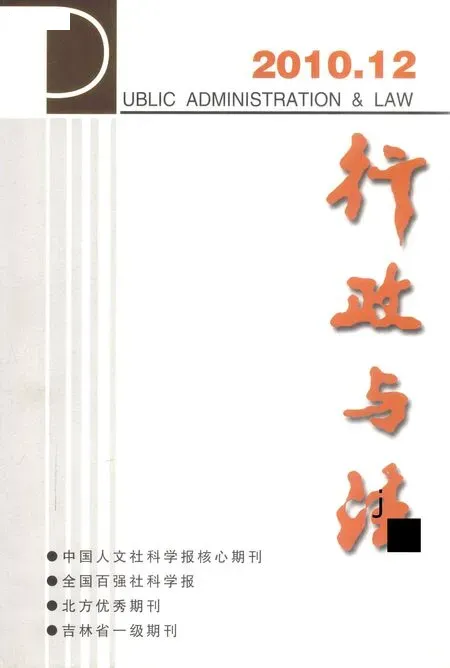我國城市社區自治建設研究
□ 汲立立,李澤霖,宋雄偉
(燕山大學,河北 秦皇島 066004)
我國城市社區自治建設研究
□ 汲立立,李澤霖,宋雄偉
(燕山大學,河北 秦皇島 066004)
我國的城市社區自治是在政府職責與城市基層社會有效銜接過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發揮著主導作用,社區組織和居民參與是社區自治的主體,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動模式。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城市社區自治也經歷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并在實踐中形成了許多具有鮮明特色的城市社區自治建設模式。
社區自治;基層民主;和諧社會
“社區”一詞是基層政治研究的基本概念,它最早出現于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騰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區與社會》一書中。騰尼斯認為,“社區是由具有共同習俗和價值觀念的同質人口組成,是一種關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及富有人情味的社會團體。”自從1933年費孝通等一批燕京大學的學生將“社區”概念引入中國,我國學者開始嘗試進行獨立的研究,并從不同的視角對社區概念進行界定。徐永祥認為,“社區是指一定數量居民組成的具有內在互動關系與文化維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體;地域、人口、組織結構和文化是社會構成的基本要素。”[1](p33-34)周沛認為,“所謂社區是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由具有相互聯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會群體、社會組織所構成的一個社會實體。”[2](p6)2000年11月,我國民政部頒發的《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指出,“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3](p52-57)“自治”是與社區緊密相關的概念,它的全稱是“自組織治理”,最早出現在希臘語中,表達一種自我治理和自我做主的狀態。
一、我國城市社區自治建設的歷史回顧
社區自治建設創建于新中國成立之后,它的成長是與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變革緊密相聯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城市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我國社區自治的主要載體,是居民會議或居民代表會議的常設機構。因此,居民委員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也就是城市社區自治成長的主要標志。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舊制度的滅亡。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新基層組織制度的創設成為城市組織和管理的重要問題。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上城上羊市街成立了全國首個居民委員會,拉開了全國范圍內城市社區建設的序幕。但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城市居民委員會的職能被嚴重扭曲。居民委員會由群眾自治組織變成了群眾性的革命組織,它的功能、職責、組織結構都發生了質的改變,單位不僅可以解決個人的就業問題,也負責管理衣食住行等生活福利問題。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社區居民委員會開始逐步進入恢復、調整和快速發展時期。1980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重新頒布1954年通過的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有關居民委員會的法律文件,明確將城市街道辦事處的工作劃歸民政部統一管理。“在單位社會全面形成的時候,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就淪為了管理單位以外的無業居民(或稱‘邊緣人’)的主要機構。但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度外的居民數量還相當少。所以,街道居委會制度在城市社區中并不占主導地位,只充當一個 ‘拾單位之遺,補單位之缺’的角色。”[4]
在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居民委員會的性質、組成方式、組成架構、基本功能和主要作用。1989年12月26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首次將“開展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活動”列為居委會的一項主要職能,標志著居民自治和居民委員會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系列法律法規為居民自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1999年,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探索推進社區建設的工作思路和運行模式,開啟我國社區自治的新階段,國家民政部開展了“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工程,確定在北京、上海、杭州、青島、南京、武漢等10個市11個區為全國城市社區建設實驗區,并在同年制定頒布了《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工作實施方案》。2000年10月11日,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加強城市“社區民主建設”的目標。2001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對社區建設的發展目標和任務作了完整的闡述。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重視和諧社區建設,要將“共建共榮”理念貫穿于和諧社區建設的始終,調動一切社會力量參與和諧社區建設,讓廣大人民群眾在共建中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社區社會組織作為我國社會組織的一部分,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背景下,是組織居民參與和諧社區建設,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和探討社區社會組織參與和諧社區建設的具體途徑和方式,對于大力推進和加快和諧社區建設的進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我國城市社區自治存在的問題
⒈社區法制體系不健全,自治法律保障缺位。一是城市社區自治立法空白。在社區服務方面,還沒有適合全國范圍的社區服務法律。二是社區管理缺少綜合立法,許多工作只能靠政策規定和行政手段強制推行。三是社區社會工作立法空白,影響專業社區工作機構和工作者的培育與發展。相關政策法規的缺失,極大地限制了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的領域與效果。以社區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為例,其中規定社會組織成立必須具備的資金、場地、人員等要求,對社區中的絕大多數社區組織而言都是難以克服的困難,使許多社區社會組織沒有資格正常參與許多社區的社會事務與管理。而當地政府又因為社會民間組織尚未納入登記管理軌道,對社區社會組織也缺乏規劃、引導、激勵和保護。
⒉社區自治體制不完善,行政化傾向嚴重。由于長期受到原有社會管理體制和模式的影響,社區居委會往往被視為街道辦事處的下級單位,有著濃厚的行政色彩。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各職能部門在認識上存在偏差。將社區居委會視為基層工作機構,將自身工作下移。“首先,社區人員的工資、經費都由財政負擔,造成了社區對政府的依賴;其次,一些社區服務組織如志愿者隊伍,既需要政府的財力支持也需要政府部門的參與,形成了對政府的依賴;另外,在財政安排上的某些‘過度投入’,如社區服務中心、社區圖書站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完全可以招募志愿人員來充任,而現實情況卻多為在編的事業性單位職工,造成了政府有限財力的過度性投入。政府一方面扮演社區自治的指導者,同時又慣用單純的行政手段控制,約束甚至是代替社區自治組織的某些工作,這將嚴重阻礙社區自治組織的發育和社區自治建設的發展。”[5]
⒊社區資金缺乏,自治的經濟基礎薄弱。社區居委會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市、區兩級財政撥款,由街道辦事處統管,辦事處根據年度考評結果予以撥付。社區自身的融資渠道狹窄,硬件建設的投入完全依賴政府的財政支持,舉辦的文體活動依賴于駐社區單位的支持,社區自身沒有形成自我的財力支撐體系,財力緊張在社區管理和運行中普遍存在。“長期以來,城市社區居委會處于既無財力、又無財務自主權的生存狀態。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居委會獨立地行使自治權力,同時也影響居委會開展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活動。”[6](p88)社區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社區財政的角色模糊,特別是許多經濟不發達的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缺乏資金來源的問題更加突出。
⒋社區自治意識缺乏,居民參與的積極性不高。“社區居民參與問題已成為目前政治輿論的重要話題,從總體情況看,仍處于弱參與的階段,自主性差,整體發展不平衡。”[7](p163)參與不足主要表現為:城市居民和單位社區參與水平低;社區居民參與意識薄弱,以被動型參與為主;參與主體不足且結構失衡,主要是低保居民、下崗失業人員、離退休黨員和老年人;社區居民參與大部分是以活動參與為主,只有少數居民參與過社區管理、決策、監督等,參與社區政治內容涉及面窄;回報性參與多,奉獻性參與少,文體型參與多,政治型和服務型參與少,參與的內在動力多是基于人際關系,公共參與精神尚未形成。目前,社區參與不足是我國社區建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如果廣大居民和社區單位不能通過健全、通暢的基層體制參與社區管理,居民的自治活動如果得不到有效組織,社區就會缺乏基本的社會凝聚力,社會資源就不能實現共享和整合。
雖然我國社區自治歷經波折,但現已逐步成長壯大,上海模式、青島模式、江漢模式、北京模式等都是各地在不斷嘗試之后的成功經驗,不容忽視的是城市社區建設中仍存在政府與社區間權責不明、轄區不清,社區自治能力與居民參與意識都處于較低水平的問題。如何克服這些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是我們未來一個時期內應重點考慮的問題。
三、中國特色城市社區自治制度建設的路徑
我國城市社區自治建設已有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其間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社區法律的改革與創新卻沒有體現出改革開放以來新的時代要求。諸多法律法規始終沒有做出相應調整和改變,社區自治體制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都無法突破原有法律法規的界限。因此,根據已經發展了的社會現實,總結社區自治的成功經驗,修訂或重新制定相應法律法規十分必要。胡錦濤總書記曾明確指出,一旦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制度的運轉有了法律保障且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其應有的制度活力就一定會迸發出來。當地政府在不違背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可根據本地的特點及情況,制訂適應本地實際的社區管理條例或實施細則,以便更好的指導社區建設。
⒈轉變政府職能,真正實現社區自治。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進一步剝離市、區政府現有的權力,把社會可以自我調節和管理的職能交給社會中介組織,把群眾自治范圍內的事交給群眾自己依法辦理,形成 “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格局。市、區政府職能部門應進一步改革行政運行模式,由向社區下派工作變成工作進社區,主動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各級政府應充分利用社區服務中心直接服務于社區需要。真正實現政府部門和街道對社區居委會給予指導而不是進行行政干預,提供服務而不是插手社區事務。政府發揮協調作用,整合區域社會所有成員和資源力量,協調社區各種群體的利益關系,并服務于各種群體。政府必須依據國家相應法規,管理和指導社區依法建立自治組織,建立起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社區建設投入體系,為社區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改善社區環境,升級社區服務水平。
⒉社區居民在對自身權利、義務和追求目標理性認識基礎上的自愿、自主性的參與,是建立、完善政府和社區群眾性自治組織良性互動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在構筑新型社區治理模式過程中,應將促進居民參與放在首要的位置。“建立和健全有關社區居民參與的各項制度,完善社區居民參與機制,把知情權、表意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等權力還予社區居民,把社區居民是否知情,社區居民是否參與,社區居民是否滿意作為衡量社區發展的標準。”[8](p57)社區自治能力的提高離不開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居民參與是社區建設的內在動力,參與的規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直接關系到社區發展的整體變化和目標管理。在實踐中培育社區居民的參與精神應切實做好以下幾點:一是通過整合社區各種利益并有效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的意見和要求,開放和利用社區各種資源,提供優質高效服務,可以有效激發社區成員的參與熱情。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達自身利益的渠道,及時了解廣大群眾對社區發展及重大方針政策的看法。三是建立社區居民選舉、社區民主決策、社區服務承諾及社區工作評議等制度,保證群眾對社區事務享有充分的知情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
⒊充足的財政資源是保證社區治理各項工作正常運轉的生命線。目前,我國社區自我管理機制很難運轉的關鍵在于沒有充足的財政基礎,沒有實現政府管理和社區自治有效銜接的城市社區治理機制來提供充足的財政保障。為進一步加快社區經濟建設步伐,穩步推進社區經濟發展,幫助居民解決實際困難,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努力實現社區經濟健康穩步發展,應積極主動整合社區的內部資源,深挖社區經濟發展的優勢潛力,鼓勵和提倡駐社區單位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經濟發展。通過“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駐共建”的形式,發揮駐社區單位經濟實力強、聯系業務廣泛、信息靈通的優勢,為社區經濟發展提供廠房、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持。這樣,即可以創造社會效益,又可以創造經濟效益,從而把社區資源優勢與市場建設結合起來,依托資源辦項目,不斷壯大社區經濟實力。只有社區經濟實力強大了,才能為社區履行各項自治職能提供經濟保障和財力支持。
總之,城市社區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需要政府與社區自治組織努力改革創新,精心謀劃發展,通力配合、分步實施。因此,要加強社區黨的領導,為社區自治提供堅強的思想和組織保障;完善社區自治的法律保障,推進依法治理的進程;規范發展社會力量,建立社會化的社區事務管理運作機制;營造良好自治環境,培育公民參與意識。只有這樣城市社區建設工作才能不斷規范、拓展、創新,才能建設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健康的和諧社區。
[1]徐永祥.社會發展論[M].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
[2]周沛.社區社會工作[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3]斐迪南·騰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
[4]謝中立.城市居民自治:實際涵義、分析模式與歷史軌跡[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2,(03):69.
[5]張韡.城市社區自治問題探析[J].青年科學,2009,(10):107.
[6]吳忠民,劉祖云.發展社會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吳鐸.城市社區工作讀本[M].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9.
[8]李惠斌,楊雪東.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王秀艷)
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
Ji Lili,Li Zelin,Song Xiongwei
Autonomy of the urban community and city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in an effective grass-roots communit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gence,which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government,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body,the three together form the government agency cooperation,positive interaction mod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the immature to mature,an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any urban communitie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self-building mode.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grassroots democracy;harmonious society
D630.1
A
1007-8207(2010)12-0016-03
2010-09-20
汲立立(1985—),吉林通化人,燕山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實踐;李澤霖(1982—),廣東揭陽人,英國倫敦金斯敦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公共信息管理;宋雄偉(1983—),山西介休人,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政策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