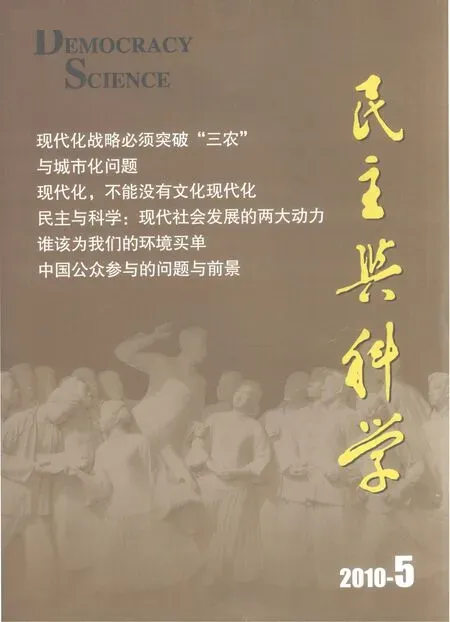民主與科學:現代社會發展的兩大動力
■張宣三
民主與科學:現代社會發展的兩大動力
■張宣三
民主與科學不但是推動現代社會的實現和發展的兩大支柱和基礎,而且是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的兩大動力。
師昌緒先生在他的一篇短文《談科學和民主》中說:“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支柱。”(《民主與科學文集》第181頁)這句話是正確的。甚至我們還可以把這句話加以引伸,如果沒有民主和科學,就沒有歷史。因為沒有民主與科學,只有專制制度的民族,歷史就是停滯的,幾千年也沒有變化,中國的封建時代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中國從西周到清末,三千多年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統治一直延續不變,民主是人民所不敢想望的。雖然我國已經有了科學,但是真正的科學時代并沒有到來,我國仍然處于仿制和改進的時代,基礎科學的發展,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仍與我國無緣。沒有基礎科學的發展,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大國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說,中國沒有民主,中國在歷史上卻是科學發展的大國,李約瑟研究中的科學史,挑選出對人類歷史有重要意義的300多種重要的科學技術發明,中國的發明占70%以上。另一位西方的科學家挑選出100種重要的科學技術發明,中國也占70%以上。特別是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大發明是西方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技術基礎,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真正現代科學的出現是在西方,基礎科學的發明無一是來自中國,沒有基礎科學的發明和建立,一個真正的科學的時代就不可能出現,使一個國家成為科學大國的是基礎科學的發明和建立。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雖然有不少技術和應用科學的發明,但并沒有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產生過任何積極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中國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大帝國,封建專制的制度及其文化和禮教壓制了人民的思想,不但壓制了真正的科學的產生,而且也壓制了任何制度的改變,即使有了科學的發明,也不能發揮作用。
我國歷史上的學術發展是完全在專制統治下進行的,從西漢章帝召開的白馬觀會議以后就已確定了方向,以后就沿著這個方向發展,這是眾所周知的。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也出現過著名的書院,如南宋的四大書院,貌似獨立講學,實際上是圍繞一個中心各自發揮,那就是定于一尊的以君為總綱的三綱哲學的各自發揮。中國的學術發展,一千多年來,自從朱熹把三綱定為天理,不論在朝在野,學術研究都跳不出這個總綱。
明末清初,出現了一批忠于明代的遺民學者,發表出一批對專制統治和綱常批判的學說,例如黃梨洲對家天下的尖銳批判。帝王“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大,于兆民萬姓之中,豈私其一人乎”。(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摘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戴震也激烈反對理學,他認為:“所謂理者同于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公然反對理學。
朱熹鼓吹理學,認為人欲是人之大惡,天理和人欲是絕對對立的,“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因此朱熹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戴震進行了徹底的批判,認為“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同上,梁啟超《中國學術近三百年史》)戴震公然為私欲辯護,認為個人利益不能侵犯,必須受到尊重。
對于明末清初所興起的這種批判理的思潮恰與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大體在同一個時期,因此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然而中國的文藝復興只不過是少數學者私下的言論,雖然出現了思想的火花,但是他們的言論不能公之于大眾,他們所寫的著作不能公開刊出發行,只能藏之于秘笈,根本不能形成運動,對社會可以說沒有產生什么影響。相反地,清朝的文字獄造成的大批屠殺,使學者不能不謹小慎微,而且轉向訓詁之學,即校勘古籍,使學術的研究脫離時代,以避免飛來橫禍。中國的傳統社會并不像仲先生所說的,我國的傳統社會就有學術自由的空間。西方從十二三世紀就開始產生各種自由思想,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四百年中,就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一個一個的革命運動,接連不斷為現代社會的到來準備了條件,十九世紀就開始進入了民主與科學的時代。在西方以加快的步伐前進時,中國的社會是一潭死水。
但是科學是對未知的探索和發現,在科學的探索中任何新奇的思想都可能發生,任何想像不到的現象都可能成為現實,科學的真理永遠處于證偽之中,新的發展推翻已有的理論和規律,是科學研究常見的現象。因此科學需要民主,民主和科學是不可分離的。
竺可楨在抗戰以前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說,三年前國聯派代表來中國考查,在他們的考察報告中說,“一般人認為歐美社會的文明統統是科學造成的”,“但實際只有歐洲的社會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學”。在2010年第一期《民主與科學》中登載熊衛民先生訪問沈善炯先生的文章《科學離不開民主,民主離不開科學》的最后說:“我們向西方引進了科學的種子,卻沒有把科學創新的土壤引過來。”沈先生的這個觀點和竺先生的觀點是一致的,竺先生所說的能夠讓科學發展的社會,沈先生所說科學能夠創新的土壤就是民主。只有當我們有了民主的土壤,科學的種子才能生根發芽。“五四”先驅在引進民主和科學救中國,把民主放在科學的前面,說明“五四”先驅真正理解民主對科學的重要意義。
張千帆先生從法學的角度提出,“只有人民成為決定自己命運的主人,才能獲得健全的政治人格,獲得完全意義的道德尊嚴”。(張千帆: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民主與科學》2009年第6期)只有這樣,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才能實現,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實現這樣一個有人的道德尊嚴的民主社會,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一個發芽滋長的土壤。因此,在今天我們繼續當年“五四”先驅所提出的請德先生和賽先生前來我國的歷史任務,讓民主與科學精神根植大地,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