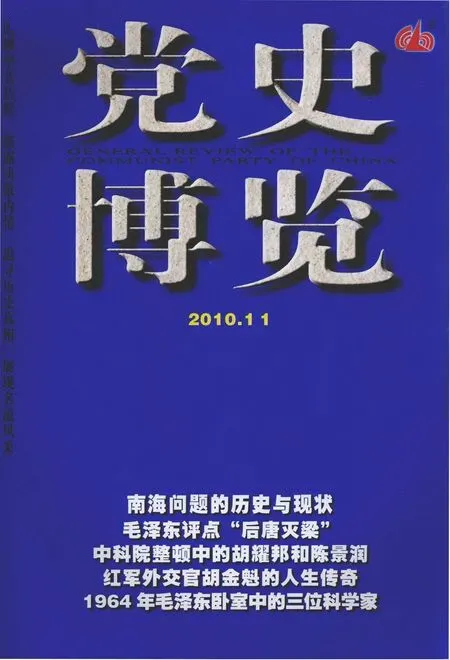于會泳浮沉錄
艾英旭
從一個有音樂天賦的少年到音樂專家
于會泳,1926年6月生于山東乳山縣海陽所鎮西泓于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于會泳從小喜愛音樂。家里雖然窮,但父母仍然拿出家里的積蓄,讓他念書。讀到中學時,因家中貧困,輟學回家。回到家鄉后,被當地聘為小學教師。在此期間,他讀了不少宣傳共產黨主張的進步刊物。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膠東地區黨組織,講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參加革命的決心,隨即被安排到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工作團工作。
1949年10月,組織上送于會泳去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音樂專修班進修學習,時間為一年。在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于會泳很快就掌握了樂理、樂譜、演唱等音樂基礎知識,并且很快學會了作曲。他選擇民歌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動傳神,曲調優美,這引起了院長賀綠汀的注意。
1949年11月,于會泳還在上海學習期間,中共膠東文工團黨支部經過討論,發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9月,于會泳結束了在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音樂專修班的學習。經院長賀綠汀舉薦,于會泳留在音樂工作團搞創作工作。此時,該學院已更名為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后改名為上海音樂學院)。
在上海音樂學院期間,于會泳創作了大量作品。入學不久,于會泳就比照著在文工團常用的創作方法,創作了小歌劇《夸女婿》,受到學院教師們的稱贊。他編寫出版的《山東大鼓》很有影響。他寫的《陜北榆林小曲》、《單弦牌子曲分析》等音樂作品,反響也不錯。他還與人合編了《膠東民間歌曲》專集。他撰寫的《民間曲調研究》、《腔詞關系研究》成為上海音樂學院本科和專修科的必修教材。他先后發表的《女社員之歌》、《幸福花開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黨的恩情長又長》等歌曲,在當時也受到好評。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系研究》一書,有較高水平。依靠這部專著,于會泳得以躋身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專家行列。
被江青看中
1965年初,江青來到上海抓京劇革命,想要“促進”一下上海搞京劇現代戲。她把此前不久在北京搞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中最受好評的《紅燈記》劇組調來,在上海演出多場,一時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文藝界許多“筆桿子”紛紛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對《紅燈記》進行評論。這些評論文章,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從政治上進行贊頌的,一類是從藝術角度贊頌的。于會泳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 《從 〈紅燈記〉談開去——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文匯報》很快就發表了這篇文章。于會泳在這篇文章中認為,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調已不能適應現代戲的內容。他建議,每一出京劇現代戲都要為它設計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廣泛流傳。這篇文章與其他文章的不同之處,一是從音樂、唱腔方面談的,二是提倡改革,而不光是贊頌。不久,他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郭建光的唱腔音樂設計》一文。
江青對于會泳的文章非常贊賞,開始對于會泳這個人感興趣。
有一天,江青問張春橋:“于會泳是個什么人?你去了解了解。”張春橋通過組織部門到于會泳所在的上海音樂學院,了解了于會泳的經歷和表現,又調來于的檔案認真看了一遍,然后到江青住處去匯報: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出身貧苦,1946年參加革命,長期在膠東文工團工作,有音樂天賦,被組織上送到上海音樂學院培養,后留校工作,工作積極,是共產黨員,在民歌創作方面有成績,還寫有專著。江青一聽于會泳是個“根正苗紅”的專家,馬上提出要見于會泳。張春橋立即安排。第二天,于會泳被通知到錦江飯店小禮堂,說有一位領導同志要和他談話。于會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來要見自己的是江青。談話中,江青當面稱贊他:“你的文章我看過,應該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想法還是一致的。”江青還當著于會泳的面對張春橋說,今后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于會泳同志。江青的話,使于會泳受寵若驚。
成為江青搞樣板戲的“臺柱子”
這次與江青見面之后,于會泳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變化。不久,張春橋將于會泳調到上海京劇院,讓他擔任重點劇目《海港》劇組的音樂設計組組長。于會泳在上海音樂學院的職務仍然不變,編制還在該院。
于會泳把《海港》中全部樂曲都認真分析了一遍,找出劇中樂曲中的問題,然后尋找改進的辦法。為了改進樂曲,他對當時中國京劇所有流派的唱腔進行了透徹了解,分析各自的優點和不足,然后結合《海港》的劇情,對唱腔進行了重新改造和設計。他在設計《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時,更多地將京劇程派的唱腔加入進去,充分發揮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點。在戲中,當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黨”這一段時,運用程派唱腔,將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激情,表現得十分到位。當方海珍唱“有多少烈士的血滲透了這碼頭的土地”這一句時,唱腔既低沉又厚重,讓人聽了,有一種蕩氣回腸的感覺。上海京劇院把全劇的演唱錄音后,于會泳立即將錄音帶送給江青聽。江青原來就特別推崇程派唱腔,聽了錄音帶后,非常高興。
于會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為搞樣板戲的“臺柱子”。很快,于會泳被調到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負責全劇唱腔設計工作。于會泳把全部心思又投入到這出戲的唱腔改造中來。他把中國傳統京劇中最響亮、最高亢的唱腔進行分析選擇,然后將其中精華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劇的唱腔中,還對全劇音樂進行了藝術加工,加進了西洋音樂的一些元素,使改造后的唱腔和音樂十分和諧。如在該劇“打虎上山”這段唱腔中,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圓號的渾厚交織在一起,并且和楊子榮的唱腔結合得天衣無縫,把楊子榮滿懷激情打馬上山,頂風雪入虎穴的壯志情懷,表現得十分充分。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驗”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編樣板戲音樂上的于會泳對運動并不太了解。可是,運動的發展,讓他不能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正在北京隨《智取威虎山》劇組演出時,他接到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個電話:上海音樂學院造反學生送到市委宣傳部一紙勒令,于會泳必須立即回到音樂學院接受群眾批斗、審查。
于會泳此前發表的文章和專著較多,造反派把這些作品找出來,挑毛病,斷章取義,給他羅織了不少罪名。造反派抓住于會泳文章、專著中較多的“問題”,認定他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造反派指責于會泳有“資產階級名利思想”、“走白專道路”,等等。造反派還說,于會泳長期不在音樂學院上班,是逃避“文化大革命”。得知于會泳是被上海市委宣傳部調走的,便把這紙勒令送到市委宣傳部,并且強烈要求市委宣傳部不得保于會泳。
于會泳找到張春橋,問怎么辦。張春橋回答說:“《智取威虎山》劇組的演出已經結束了,你回去吧。不要怕,我們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將站在一起。”
于會泳聽后,長出了一口氣。他特別記住了張春橋這樣一句話:我們信任你。因為此時的張春橋,已經是受到毛澤東信任的人。這一點,于會泳是知道的。
于會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樂學院,主動找到學院紅衛兵各主要戰斗隊的頭目,非常虛心地征求紅衛兵的意見,并且主動作檢討。
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也讓手下人到上海音樂學院做紅衛兵的工作,講:于會泳是革命的,他被調來參與搞樣板戲,是張春橋通過市委宣傳部辦的。他搞樣板戲有功,受到江青同志的表揚,等等。此后不久,江青在一次開會時,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轎車去接于會泳。還有一次,江青在于會泳陪同自己觀看樣板戲后,又特意拉于會泳和自己一起上臺會見演員。江青此舉,立即傳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們得知后,不再揪斗于會泳,反而認為他是革命教師的代表。
緊跟江青
于會泳受到江青的青睞,工作更起勁了。即使是他當上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后,仍然整天在排練現場,一絲不茍地過問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他參加了《杜鵑山》、《平原作戰》、《龍江頌》等樣板戲的音樂創作。這些樣板戲中的每個字,每個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于會泳年輕時就愛好寫作,也有一定理論功底。他仔細研究江青講話時強調的重心,然后寫成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傳一時并且曾經指導“文化大革命”中文藝創作的“三突出”理論,就是于會泳根據江青幾次談話的意思概括而成的。
1968年,《文匯報》上發表了于會泳寫的文章《讓文藝舞臺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這篇文章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論。于會泳在文章中寫道:“我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個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人物即中心人物。”
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稱贊,說:于會泳的文章寫得好,“三突出應該成為文藝創作的根本原則”。甚至還說,“是不是搞三突出,是革命文藝路線和反革命文藝路線的根本區別”。
為報答江青對自己的賞識,于會泳到處贊頌江青。他在指導演員演戲時,常說的話是:“對江青同志的話,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緊跟,‘樣板團’的人員,要永遠銘記在江青同志領導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榮……”在中共九大召開期間,《智取威虎山》作為首場樣板戲,在京西賓館禮堂上演。于會泳在演出的開場白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為培育樣板戲嘔心瀝血,她實際上是這出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江青似乎也受不了這番奉承,她站起來說:“會泳同志,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我可要離場了。”
由于受到江青的重視,加上搞樣板戲有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于會泳就擔任了上海市文化系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4月,他作為上海的黨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中共九大之后,他擔任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
也曾受到江青的猜疑
江青是個喜怒無常的人,對于自己的親信也常常是今天信任,明天又猜疑。她對于會泳也是如此。
施光南是于會泳的老師,“文化大革命”之前,對于會泳很是賞識,并著意培養。“文化大革命”中,施光南受到批斗。于會泳被迫參加批斗恩師施光南時,卻遲遲不發言。張春橋對此很失望。
賀綠汀是于會泳的恩師,“文革”中受到批斗。于會泳想利用自己的影響,把賀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加以“解放”,卻被張春橋斥責為有“糊涂”觀點。張春橋還特意安排于會泳主持第二次批斗賀綠汀的“電視斗爭會”,全市轉播,張春橋則坐在辦公室里觀看批斗情況。于會泳主持這次批斗大會時,說話很軟弱,而賀綠汀則在會場上頑強抗爭,批斗會以失敗告終。
1974年底,長春電影制片廠將拍攝的故事影片《創業》送國務院文化組審查。于會泳覺得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報告向江青等人推薦這部影片在1975年春節公映。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閱同意。就在于會泳下令發行時,突然被江青叫到釣魚臺,她當面指責于會泳:“《創業》這么糟,你為什么批準發行?這部影片明目張膽為劉少奇鳴冤叫屈,替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老家伙評功擺好。”江青下令:長影廠要“修改”《創業》,于會泳要寫檢查。于會泳不敢不執行,立即以文化部的名義下令停止發行《創業》。除自己寫檢查外,還根據江青、姚文元的意見,寫出文化部對《創業》的“十條意見”,上報中央。不料,當年7月毛澤東在《創業》編劇張天民的來信上批示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后,“四人幫”一方面攻擊張天民告刁狀,另一方面把責任推給于會泳,要他和文化部承擔責任。于會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黨組成員共同寫出檢討呈送毛澤東,并在文化部的司、局級領導干部會上作了公開檢討。
此后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又與江青等人在電影《海霞》問題上發生矛盾。此時,于會泳恰恰被醫生查出因長期營養不良患有代謝性肝炎病,醫生意見:于會泳必須住院臥床休息。但江青等人認為,于會泳這是在逃避“斗爭”。
1974年、1975年,“四人幫”搞“批林批孔”,矛頭指向周恩來。于會泳明白這一點。他當上文化部部長后,與周恩來有過工作接觸,對周恩來的品格和風范十分佩服;周恩來也稱贊過于會泳。因此,他不愿意參與江青旨在攻擊周恩來的斗爭,對江青布置的“批林批孔”只是敷衍、應付。江青認為于會泳陽奉陰違。
幻想破滅后自殺身亡
盡管如此,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于會泳還是緊跟江青的。1976年初“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于會泳緊跟“四人幫”,全力以赴。因此,他仍受到“四人幫”的信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央查獲了“四人幫”所擬定的他們打算在上臺后“組閣”的中央領導班子中,于會泳被列為副總理人選。
10月中旬,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文化部。隨之,于會泳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在被隔離審查期間,于會泳對于自己緊跟“四人幫”十分悔恨,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當時,于會泳對自己今后的出路還比較樂觀。他覺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干過什么壞事,還做過不少如保護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自己跟隨江青等人辦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不辦也不行;自己有錯誤,沒大罪,自己參與搞的樣板戲,毛主席、周總理也是喜歡和肯定的;周總理還稱贊過自己……他認為,隔離審查結束后,會給自己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文化部部長是不能再當了,但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即使回不了上海音樂學院,還可以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當一名普通干部,搞搞文藝工作。
于會泳確實過于樂觀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于會泳感到如五雷轟頂。當天晚上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專案組談話,在表示認罪服罪的同時,請求要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期望這位組長能聽聽自己的意見。然而,他得到的答復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當看守人員向上級報告于會泳神志恍惚,有異常表現時,上級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沒有對于會泳采取其他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在院子里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著足以使人穿腸爛肚的“來蘇水”,便趁看守人員不注意時,將這只瓶子挪到自己經常洗臉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后,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了自己的房間。入夜,于會泳提筆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遺書中有這樣的話:“我跟著 ‘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只有一死(后將‘一死’改為‘長期’)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希望你們永遠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革命到底。”晚8點左右,他決然地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當他被人發現時,已經處于昏迷狀態。他被送到阜外醫院搶救。醫院采取了搶救措施,仍然沒有挽回他的生命。
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年度學刊)上發表了于會泳的作品《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系研究》。作為音樂家,他仍然被人們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