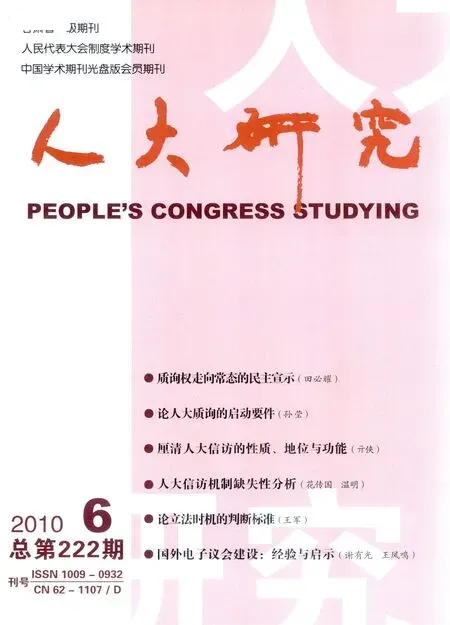詢問是人大實施監督的有力方式
——對監督法第三十四條的研讀
□ 丁益民
詢問是人大實施監督的有力方式
——對監督法第三十四條的研讀
□ 丁益民
監督法第六章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議案和有關報告時,本級人民政府或者有關部門、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派有關人員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筆者認為,這一條關于詢問的規定,是地方人大常委會監督工作的一座“金礦”,極具開采價值。用足用好詢問這一監督方式,對于加大人大監督力度,提升監督水平、維護監督權威,作用不可小視。
設置詢問的深刻含義。監督法第三十四條有關詢問的規定,是從立法上賦予各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以詢問權。詢問即對話,通過對話以權力制約權力,促進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維護社會穩定和諧。詢問不同于一般的審議發言,詢問針對的多是熱點、焦點或敏感性問題,會對被詢問者產生一定壓力。但詢問又不同于質詢,不需要經過聯名提出議案等法定程序,運用比較靈活,影響面小于質詢。如果常委會對詢問回答不滿意,則詢問有可能成為質詢的前奏,因此詢問在一定條件下也能起到質詢的效果。在立法上對詢問這種進退自如的監督方式的設計,給人大常委會監督工作留下了較大的空間。
此前地方組織法在第二十九條規定了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議案的時候,代表可以向有關地方國家機關提出詢問,由有關機關派人說明。地方組織法由于規定得比較寬泛,代表在大會期間的詢問實踐中少有發生。而監督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各級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議案和有關報告時,組成人員有權提出詢問,“一府兩院”必須派出負責人員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監督法將詢問與質詢同歸在一個章節,可見詢問不是一般對話,而是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與“一府兩院”有關負責人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的對話。監督法規定的詢問含義更加深刻,它是在常委會會議審議時提出,由于常委會在審議議案和報告之前已經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包括議題的提出、調研和初審,常委會成員的詢問多是有的放矢,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一府兩院”對待詢問也不一樣,地方組織法只是一般規定派人說明,而監督法則規定應當派出有關負責人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監督法如此規定,對于人大常委會加大監督力度,提高審議意見的質量和分量具有深刻含義,對于保障委員的知情權,增加權力運作的公開性,促進民主和諧具有積極意義。
詢問的若干特性。一是主動性。即我問你答,區別一般發言泛泛而談,凸現監督者主導地位。二是強制性。即有問必答,而且必須是有關單位負責人在會上給予明確的回答,強調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權利、義務。三是針對性。詢問提出的問題多是經過議題準備,或是社會反映的熱點、焦點問題,不同于一般的意見、建議,它針對性強,對被詢問者有一定壓力,即“監督在點子上”,能產生實質性效果。四是連續性。監督法沒有限定常委會詢問的次數,一次會議回答不上,二次甚至三次會議可以繼續詢問并回答,保證了常委會監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連續性。五是靈活性。監督法把詢問和質詢歸在同一章節,又把詢問單獨作為第三十四條,可靈活運用,進退自如,體現了立法的智慧。
關鍵在于正確把握詢問權的運用。一是選題要得當。法律在制度上為人大常委會成員設立了詢問權,但并不意味就此高人一等,隨心所欲想問就問。因為詢問位于質詢同一章節,是一種比較嚴肅的監督方式,詢問要有針對性,要有質量、有分量,宜選社會關注的民生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二是詢問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從監督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看,詢問沒有限定人數、次數和內容。筆者理解,常委會會議審議期間,擁有詢問權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個人可以提出詢問,也可以聯名提出詢問,列席會議的代表和旁聽市民則無權提起詢問。報告工作的“一府兩院”負責人可以即席回答,可以在會議期間回答,但不宜以常委會閉會期間向詢問者作出的答復或說明來代替會議上的回答。如果詢問涉及非報告單位的問題,也應通知有關負責人到會作出回答。關于詢問的方式,常委會組成人員要有明確的意思表示,可以書面也可以口頭提出詢問的要求,包括被詢問機關、詢問的事項、回答的時間、方式等,對回答不滿意的可以再次詢問。詢問要作為特別程序,當常委會會議進入審議時,主持人要征求與會成員有無詢問要求,并記錄在案。監督法附則第四十七條規定,省級人大常委會可以根據監督法和有關法律,結合實際制定實施辦法,這就給地方立法留下了空間。各省級人大常委會在制定實施辦法時,可以結合實踐對詢問規定進一步細化,并制定相關程序,以利于監督法在本行政區域更好地貫徹實施,進一步完善人大監督制度,切實增強人大監督實效。
(作者單位:安徽省安慶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