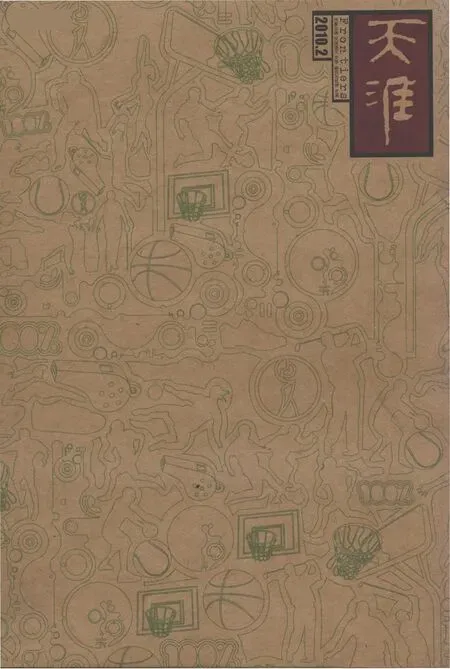哥特蘭島上的追尋
王家新
2009年8月下旬,我和其他幾位中國詩人應邀參加由瑞典哥特蘭島作家和翻譯家中心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國際詩歌節。這是我第一次前往北歐,前往由斯堪的納維亞山脈嚴峻的冰雪與溫暖的波羅的海相互映照的北歐。
哥特蘭為瑞典最大的一個島,位于瑞典東南端的波羅的海,全島一百多公里長,人口約七萬,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我們從斯德哥爾摩坐大巴出發,然后再乘船三小時,一下船,向上邁入它的首府維斯比(在歷史上它曾是漢薩王國同盟城,現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古老城門時,我們便被它的美驚呆了:那毀棄的或仍在高高屹立的城堡和教堂,那四周布滿店鋪和露天咖啡館的誘人的小廣場,那一道道被磨亮的老街、砂巖拱廊和童話般的房屋……待登上山坡上我們的住地時,山坡下那錯落有致的古城和彤云迸放、波光如鏡的大海便全然展現在我們面前,大家幾乎都要歡呼起來了。
還寫什么詩?在這里,寫一首就是多一首。大口呼吸吧,為了這世上最清澈的空氣!拍照吧,不僅是為了“留念”,更是為了把黃昏時分那金子一樣鍍亮山巖、屋頂和我們額頭的光留下來……
然而,深深吸引我的,不僅是島上風光和那童話般的美,還有兩位藝術大師在這里留下的一切。詩歌節的朗誦每天主要在維斯比市中心一個廢棄的大教堂內進行,我和藍藍一進去就有點愣了,我們在互相問:這不就是塔可夫斯基《鄉愁》中的場景嗎?那古老的高大廊柱仍屹立著,猶如精神的不死的骨架。在電影《鄉愁》的最后,塔可夫斯基正是在這樣的大教堂廢址內置入了霧氣洋溢的樹木和俄羅斯房舍,以此構成全新的庇護和啟示性景象。他所做的,真是一般人想都想不出來的啊。
當然,《鄉愁》并不是在哥特蘭島而是在意大利拍的。這位前蘇聯著名導演在哥特蘭拍的,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杰作《犧牲》。多年前看《犧牲》,使我最受震動的是主人公最后燒掉自己的房子追隨“女巫”而去的情景,那沖天而起的火光,那劈啪爆裂的聲音,曾使我久久不能平靜;另外,就是穿插在影片中的樹的意象:一個不知名的少年每天吃力地提著兩大桶水去海灘上澆一棵枯樹,到電影的最后,在我們目睹亞歷山大的房子被燒成灰燼后,這棵樹居然復活了——多么動人啊,風吹動著那樹上的每一片簇新的葉子,巴赫的音樂響起……
這也就是塔可夫斯基會深刻影響我們的最根本原因,“我想做的,乃是提出質疑并對深入我們生命核心的諸般問題有所論證,從而把觀眾帶回到我們存在的隱伏、干涸的泉源”(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這也正是他之于我們的不可或缺的意義。而這次來,我也從其他詩人那里感到了這種精神的回響。我驚喜地看到丹麥著名女詩人Pia Tafdrup這次帶來朗誦的詩集就叫《塔可夫斯基的馬》,其中的同題詩敘述她在父親去世后怎樣長久悲痛地說不出話,直到一次在從柏林坐火車歸來的旅途上,在臨近一片海灣時,她“看見”了那多次在塔可夫斯基電影中出現的馬,然后她哭出了聲來……
不僅如此,在特地來哥特蘭島為詩歌節拍照的瑞典攝影家Cato Lein的攝影集中居然也有一棵“塔可夫斯基的樹”!它就出現在一些諾貝爾獎獲獎作家諸如帕慕克和其他作家、藝術家的肖像中間。的確,這也是一種精神的肖像:那不屈不撓的孤絕身姿,那投在地上的深邃影子……我問Cato拍攝這幅作品是不是受到塔可夫斯基的啟發?他回答說是的,不過那棵樹已不存在。它只是為了那部電影而存在。
是嗎?我不甘心似的問道。從此,仿佛一顆種子落下了根,那幾天在島上漫游時,我就一直在尋覓著什么。是的,那棵樹!那棵在塔可夫斯基的世界中出現的樹,那棵孤單、倔犟而又仿佛是從我們的血肉中長出來的樹,那棵在巴赫的音樂中奇跡般復活的樹……
為此我們去過無數的海灘。成片的松林在海風中起伏,但卻很難找到一棵兀自挺立的樹。我們感嘆:在這里,要發現一棵孤單的樹可真難啊。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脫離了群體的樹在海邊很難存活。
但在這世上,總會出現一些特立獨行者。塔可夫斯基是這樣一棵“孤絕的樹”,伯格曼也是——在某種意義上更是!這次來之前,詩人、翻譯家李笠在信中就特意告訴我哥特蘭島是這位電影大師中、晚年生活的地方。來后第二天,我們就開上了從哥特蘭大學謝老師那里借來的車,長驅五六十公里,去哥特蘭最南端的費羅島(它與哥特蘭主島隔一個小海灣,還需乘渡船),去尋訪伯格曼那神話般的住所。
然而,那地方很不好找,沒有任何指示路標,臨近目的地時,我們繞來繞去,不得不停車好幾次問路,其間還被一個從屋里出來的女人咒罵了一通。我們真不明白她為什么要跳起腳來罵?是被打擾了嗎?還是她已完全瘋了?不過這樣也好。這會加深我們對伯格曼那鬼影憧憧的世界的理解。
那詛咒聲,我們“逃”了大半公里仍能隱隱聽到。
據傳記材料,伯格曼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移居到這里的。他親自設計了這個面向大海,掩映在森林中的住所兼工作室。他后期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這里寫作、拍攝和剪輯的。這里是他晚年唯一的家,據說戛納電影節五十周年大慶把終身成就獎授予他時,他也懶得出門,只讓他的女兒前往代領。到了他最后一部電影《芬妮與亞歷山大》(1982)拍攝完畢后,他便完全在這里生活,直到前年夏天在這里謝世。
現在,這個一代大師的居所已空無一人,成為一片由密林和寂靜守護的禁地,周圍還設有禁止入內的標志。但我們已顧不上那么多了,輕輕推開森林小道邊的木柵門,便躡手躡腳進入了這個我們早在《野草莓》等電影中窺見到的神秘世界。我們是從后門溜進去的,一進去,便驟然被那滲透林間的寂靜所控制。樹蔭下,伯格曼那輛深紅色的奔馳牌舊車還在,好像仍在等著它那高大、佝僂著腰的主人似的。我在心里不由得感嘆:一個人要長年生活在這里,需要怎樣的勇氣!
沿著布滿青苔的石頭壘成的長長圍墻,我們在后院里開始拍照了。這個只有一層、長約五六十米、用木頭和石塊建成的簡樸住所,與其說是一個“詩意棲居”之所,不如說是一個“秘密工作間”,而我們無法進入。我們在這里又能找到什么?不過,我多么愛這些累累的無言的石頭!待繞到屋子的側面時,那從松林中透來的海風更是使我精神一振:這就是一個人的晚年獨自為伴的大海了(伯格曼夫人比他早逝十一年)。我們去時,正值正午,那寬大的起居室窗戶面對的大海一片波光粼粼,真使人“猶在鏡中”(伯格曼一部電影的名字)。不過,到了冰天雪地、寒風刺骨的嚴冬又怎么辦呢?
后來我才知道,伯格曼為他這個住所親自設計了一個俄國式的帶熱炕的壁爐,冬天他就躺在那里讀書、思考,聽著那架古老的掛鐘在寂靜中發出的深邃轟響。這使我想起我曾訪問過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黑森林山上的小屋,是的,“嚴冬的深夜里,暴風雪在小屋外肆虐,還有什么時刻比此時此景更適合哲學思考呢?這樣的時候,所有的追問必然會變得更加單純而富有實質性。那種把思想訴諸語言的努力,則像高聳的杉樹對抗猛烈的風暴一樣”(海德格爾《人與思想者》)。
那些終生投身于精神勞作的人會理解這一切的!正是來到這里,我知道了自己“孤獨得還不夠”。我們獻身的勇氣也還遠遠不夠。在這無言掩映在松林邊的房子一側,在那無垠展開的波光如鏡的大海前,我們都靜默下來了。我們變得像幾個游魂。我們靜得甚至已聽不見自己的腳步。
一代大師去了,他就安葬在當地小教堂的墓園內。我們去看了那墓園。沒有高大的墓碑,只是在一方朝向大海的樸拙石頭上刻著他的名字及生卒年份。“多好的酬勞啊,經過一番深思/終得以放眼遠眺神明的寧靜”,這是瓦雷里《海濱墓園》中的名句。伯格曼會這樣寫嗎?不會的。他進入的是一片更不可追問的沉默。他一生留下的四十余部電影及多部戲劇,從某種意義上,正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從被給予的信仰(他父親即是一位嚴厲的牧師),到“被揭露的確信”并最終到“上帝的沉默”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艱難歷程。當然,在他作品中也有安慰、凈化,但他留下更多的,是那黑暗的謎。即使在他晚年拍下的《芬妮與亞歷山大》中,他也沒有中止對靈魂世界的無畏探索,他帶領我們“躍入”的,是那“童年的深淵”!
相比之下,中國的一些藝術家、作家、詩人、導演……是多么容易陷入世俗的滿足啊。也許,這樣說還是輕的。他們一生追求的,不正是這個嗎?
這也就是哥特蘭——費羅島之旅之于我們的意義。它不僅使我們感到一個超越一切現實虛榮、平庸和懦弱的藝術大師是怎樣把對生命的追問一直帶入他的晚年。它使我們自省。它為我們再次顯現出存在的光亮和尊嚴。它把我們“帶回到我們存在的隱伏、干涸的泉源”。
歸來,又是黃昏。多美啊,哥特蘭!那海之光,那黃昏之光,再一次鍍亮了旅途、車窗和我們的額頭。我們豈止是陶醉了,我們的靈魂(它僅僅屬于我們嗎?),在深深地經受著光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