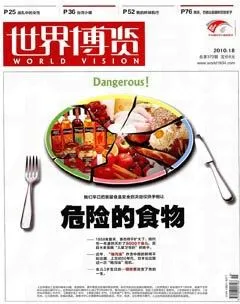“瘋子”免刑難在觀念障礙嗎?
此案中,潮州市的司法人員與政府官員的表現值得崇敬和贊美,而這樣的判例何以罕見更值得檢討。
精神病人(俗話叫“瘋子”)在精神病發作期間,不能辨認和不能控制自己行為而產生的危害行為,經過法定程序鑒定,不負刑事責任,應該說是現代文明常識,中國刑法早就對此有明確規定。可是,實行起來為什么會十分艱難呢?
9月9日《南方周末》以《“瘋漢”殺人的艱難免刑》為題,頭條位置報道了發生在廣東潮州的一起精神病人殺人免刑的案例。編者按說:“這是一個全國罕見的案例……法院能作出這樣的判決,是法律理性精神的勝利,更彰顯了中國司法在人權保障上的進步。”
文中更強調觀念轉變之難:“這是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數十年來第一起精神病人殺人被判‘無罪’的案件,在廣東乃至全國,這樣的判例也極其罕見。這一判決背后,是中國司法系統在‘少殺慎殺’與‘殺人償命’兩種不同司法理念的博弈,前者最終勝利,但過程卻極其艱難。”
從全國數十年辦理精神病人案例來說,總體上看大約是這樣的吧,所以編者為這篇報道配了一篇專家文章《肇禍精神病人為何不能殺》,進一步宣傳這種司法理念。不過既然免刑責條款寫進刑法,必是司法界和立法者的共識,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就更應該知道且認同這個司法理念。
之所以“免責”難,難在執法者、主事者有無社會責任感和人道精神,國家有無相應的保障精神病人權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安排。這篇報道的細節就可以支持人們做出這一判斷。
潮州中院強調,這一結果是公、檢、法三家共同促成的結果。但公、檢、法只要有一個環節的司法人員缺乏責任感,缺乏基本的人道精神,本案中的精神病人劉寶和就被肯定被“草營”而不聞聲。辦案警察不厭其煩如實記錄“瘋漢”劉寶和顛三倒四殺人動機的“供述”,為法官閱案發現疑點提供了條件。
法官不僅知道“免責”理念,還花心血比對供述查疑點,而不是接受公訴方的結論了事,這對他有什么“好處”?而且,如果尷尬的檢察官不是秉持“人命關天”的信念,把公訴方的面子看得比人命還重要,與警方聯手,提請政法委的三家聯席會議討論,以二比一否定法院的意見不是很合時下辦案的常規嗎?
比辦案人員素質更重要的是經濟困擾。刑法規定,劉寶和被釋放后,或由家人看管,或由政府強制醫療;然而,由于其父母均年事已高且家境貧寒,拒絕將劉寶和接回,甚至要求將劉寶和槍決了事,以平民憤。
幸好當地父母官開明,經潮州市中院游說后,責成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和劉寶和所在鎮政府召開協調會,確定劉寶和要送精神病院治療,治療費用由鎮政府墊支后向縣財政、民政申請補充經費。
換言之,國家還沒有制定關于精神病人免費治療的公益性的強制性的明確規定,精神病人能否得到救治取決于家庭或地方政府的經濟能力和意愿。這也是大街上經常能看到精神病人流浪、時聞精神病人殺人的緣故。
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明程度,可以看這個地方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即是否存在“以眾暴寡”現象,以及如何對待困難群體,即看鰥寡孤獨和精神病人能否得到幫助。經濟上沒有制度保障,進步的司法理念就難落實。
而按當下流行的所謂“維穩”思路,上訪者被關精神病院的并非個別。劉寶和最終被法院判決賠償遇害家屬18萬元。而劉寶和一不償命,二不賠錢(無力賠償),當地政府有理由擔心,遇害家屬以此向政府施壓,并引發群體性事件。
(遇害者所在村,90%以上都是同族)。斃掉了劉寶和,許家就少了向政府施壓的理由。在這種情形下,地方官員通常不惜以精神病人之命換取“穩定大局”。最終潮州地方政府選擇了“人命為重”。
顯然,與其說這個罕見的判例是現代司法理念的勝利,不如說是人道主義精神和執政為民理念的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