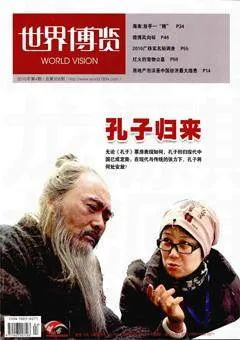讀者圓桌
《阿凡達》無疑是誘人的,創紀錄的票房就是證明。而且據我觀察,似乎周圍的女性更是狂迷“阿凡達”。向來據說最物質最現實的的當代女性,在面對《阿凡達》的時候,又如此迷戀片中的原始仙境,迷戀勇士與土著少女的愛情,并因而憎惡對這神話的暴力摧毀,看來只有感性能告訴我們真正的內心渴求。但是為什么有人批判卡梅隆是“反人類”的呢?現代人真是糾結——美國是令人羨慕的,所以發展是美好的,納美土著是原始落后的,而征服者是先進。似乎這一切都成無法反駁的共識,這種進步與落后的直線型二元對立思維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因為發展中國家看著發達國家,窮人看著富人,欲望被撩撥而不能自拔,更嚴重的是,財富成為一種價值暴力。
楊奎松教授從電影《阿凡達》人手,反思現代化,指出了其中的吊詭——盡管我們活得如此痛苦,環境污染但在氣候問題上爭持不下,資源愈來愈匱乏仍爭得頭破血流。對于個體來說,都能感到殘酷競爭、工作壓力、不確定和不安全等等。為什么我們生活在現實的痛苦中,都執迷于現在的價值邏輯所虛構的那種幸福?因為發展確實帶來了好處。因為我們被“溫水煮青蛙”之后,基本喪失了對幸福的判斷能力。可悲的是,今天誰也不敢輕易斷言放棄發展。 “納美人”生活,依然是和批判和反思之后的神話而已。
那么多女人喜歡《阿凡達》,真是這種糾結最現實的附體。
上海 丁梵谷
每逢經濟危機,市場女神就復蘇,其實不外乎是沒什么想什么的心理。政府調控力度加大,人們就歌頌市場;市場造成了貧富不均,人們又期望政府出面解決。正因為蘭德本人有過在集權時期的蘇聯生活的經驗,她才能如此赤裸的把“自私當美德”來歌頌。
在中國長大,天天聽見人批評計劃經濟的害處,“小政府,大社會”似乎成了所有知識階層追求的目標。留學到了加拿大,卻往往遇見激進的知識份子揭露市場化的丑惡。教授們的聚會上,總能聽見對“政府干的太少了”的批評。
曾經碰到過一位意大利的同學,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斗士。聽說我是中國來的,馬上向我痛陳了一翻他對毛澤東時代的向往及對中國“市場化”的失望。
沒什么就想什么,重要的是別失去選擇的意識和權力。
加拿大 Linda
地球到底怎么了?2009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疑是全球變暖的哥本哈根會議,各國的政治領袖們最終也沒能達成拯救地球的共識,說不準某天“暖球”就變成了一個熱氣騰騰的“哈雷彗星”,不過那些決策者是不會在意的;而在貴刊2010年第3期,我又了解到了另外一個全新的地球,那就是一個被全副武裝了地球——傳感器、攝像頭、網線、信號塔……一個所謂“智慧的地球”。我覺得,該文章最后的部分令人深思,所謂地球到底是“蓋婭”還是“勾勒姆”,正是我們現代人類必須考慮的一個大問題。
試想一下,假如說IBM公司成功地實現了“智慧地球”的理想,那地球的一切秘密不就掌握在某些少數人的手中了?這將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科技所創造的一切驚人的奇跡,為人類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是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另外,我是貴刊的一位忠實讀者,以前也給貴刊寫過一些信件,不知道編輯們有沒有收到?看到新年的封面設計發生的變化,感覺變得更舒服了;里面的欄目設置也做了調整,想必貴刊正在順應時代潮流,時刻調整著、發展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希望貴刊越辦越好!
咸陽老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