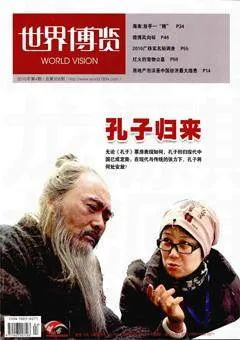構筑中日共同的歷史記憶
中日歷史問題的癥結與兩國國民的教育現狀、情感沖突、現實政治和外交乃至世界政治框架連在一起,并非少數學者短期內能說得清的。
持續3年多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第一階段宣告結束,中日兩國的媒體、社會都靜靜等待著它的成果。畢竟這是兩國學者第一次坐下來,試圖理清兩國糾結的歷史癥結。而這歷史癥結又與兩國國民的教育現狀、情感沖突、現實政治和外交乃至世界政治框架連在一起,并非少數學者短期內所能說得清的。于是,坐在一起設立共同課題本身,就是一個前進。在此基礎上,達成一些階段性的共識,減少今后交流上的障礙,有利于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
正如共同報告所指出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是學術研究,每一篇論文的觀點是研究者個人觀點。既然是學術研究,就允許各種觀點共存;既然是個人觀點,就要承受不同觀點的批判。或者,研究報告書全文的發表,才是評價與批判的開始。但也因為是學術研究,用簡單的感情論是無法辯駁的,共同研究作為一個開端,相信會促進雙方研究和史料搜集利用的進程。
史實和解釋之間
人們注意到,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全體研究者的4次會議中,第一次會議雙方代表會上的致辭和會后的發言,頗有值得玩味和推敲的地方。而在那之后,雙方的發言漸趨一致。
在第一次會談后,據日本媒體公布,日方首席委員北因伸一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歷史事實只有一個,但對其解釋可以有幾個。”這句話當如何理解呢?
在歷史解釋方面,就一國的范圍來說,至少存在著政權的歷史意識、歷史教育、歷史學研究這幾種層次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以本國為中心解釋歷史的傾向,各國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介入歷史教育。歷史研究水平固然是解釋歷史的基礎,但絕不是唯一的解釋途徑。但當幾個國家歷史在某一段時期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對歷史的解釋不同會對相互交流形成妨礙。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和亞洲都有發生,因此才會有共同歷史研究的必要性。只有在雙方交流緊密化、歷史認識影響互相溝通的時候,才會出現達成歷史共同認識的必要性。
對于歷史事件和人物行為的解釋,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從國家的歷史教育來看,教課書對歷史事件的解釋,是學生獲得歷史認識的第一步,不同的解釋對受眾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因而也會對整個社會的歷史認識造成影響。對歷史研究來說,持不同方法論的人對同一個歷史事件或人物會做出不同的解釋,而主要歷史研究方法論受政治的影響非常大;除了方法論之外,對某一歷史事件或人物客觀的評價,還取決于基礎史料狀況、實證研究積累、與其他平行人物或事件之間相關性分析的進展,在這些要素不充分的情況下,也會難于全面評價其作用和意義。
看看戰后日本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的歷程,也許有助于理解“事實”與“解釋”的關系。
剛剛戰敗的日本,脫離了教育敕語體制,教育民主化的機會有很多。但很難下結論說,以1945年8月為分界各個領域都進行了大變革,因為從戰時開始的舊體制頑固地保留了下來。
日本戰敗后,美軍占領政策隨著冷戰的需要發生了轉變,最開始要日本進行徹底的民主改革、根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后來隨著冷戰的發展,采取了扶植保守勢力、對抗左翼革命的方針。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和官僚體制相結合的政治制度被保ziL8RPS0+tm5NqyjshTvZCsEvxTWSOnwcIvGjyERlTU=留了下來。戰前日本抵制社會進步的意識形態也被貼上現代民主制度的標簽,獲得了合法性。
1955年以后,文部省以布告形式公布的“學習指導要領”的指導性加強了,最后發展到逐字逐句的對教科書進行審查。不僅如此,從1955年和80年代初,日本社會還出現過依據文部省行政命令和右派意識形態對現行教科書的批判,實際上是政府在運用右派壓力抵制進步輿論。
對此,日本的教員們也進行了堅決的抵制。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原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曾三次提出對教科書審查的訴訟,還有橫濱教科書訴訟案,這些事件在反擊右派批判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在歷史教育中,不僅僅把日本看作戰爭的“被害國”,對其作為“加害國”的認識也深化了。至此,在教育中,日本在近現代史中的“侵略性”才終于被立體地顯現出來。但到了1995年,當日本的歷史認識和教育剛剛向健康的方向進展時,右派們又一次舉起“民族主義”的旗號跳了出來。而文部省也以強制“日章旗、君之代”與之相呼應。進入2l世紀以后,小泉政權則通過參拜靖國神社、鼓動民族對立,把這種冷戰時代的方法論推到了極致。
1997年和2001年之間,為了抵制日本社會中右翼集團編寫美化過去的歷史教科書,一些日本教科書研究者,曾經搞過一個日本與世界各國教科書的對照研究。其中對日本教科書的特點作了一些描述,就此能看出文部省審定教科書的問題所在。
1946年的小學國定教科書這樣描寫“太平洋戰爭”中的戰敗:“昭和20年8月,原子彈落了下來,蘇聯攻了過來,天皇發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詔書,并且命令政府和大本營投降。”接下來,“我們的國家敗了。國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受了很多苦,是軍部迫使國民、勉強從事戰爭從而引起了如此的不幸”。在這里,所有責任都推給了軍部,根本沒有追究體制和天皇戰爭責任的余地。日本很多的歷史研究成果都證明,以絕對主義天皇制為頂點的政治體制,對于戰前鎮壓民主運動、發動侵略戰爭有著無可推托的責任。但在教科書里,無論結束戰爭,還是戰后走向和平民主,皆出于天皇的“圣慮”。當然不可能是追究戰爭責任的對象了。也就是說,戰后日本政治家們,充分利用美軍保存天皇制的意向,趁機將一些東西劃成了禁區。
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日本教科書,只提到了日本在戰爭中的受害問題,卻不提加害和侵略別國的問題。教科書中開始有侵略別國的內容是80年代以后的事,例如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載,80年代的日本歷史教科書20余種中,只有4種提到,而且還不是在正文中,只是在腳注中提到。1982年受到亞洲各國批判后,日本各歷史教科書中才開始全部加入相關的史實描述。關于從軍慰安婦的問題,到了1994年以后,所有的教科書才開始都有記載。
現在日本的教科書中,也有一些談及戰后補償的問題。并指出日本并沒有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戰后補償。日本的戰后賠償只支付了10多億美元就終止了,而德國在戰后直到2030年包括對納粹罪行犧牲者和遺屬的補償總額將達1200億馬克。雖然日本與德國在戰后的歷史進程、國際狀況都有所不同,但作為一種反省歷史的姿態,形成絕好的對照。
戰后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對歷史事實的政治解釋!掩蓋歷史真實的教科書審定,是保守政治的需要,這對造成兩國歷史認識差距是有責任的。
教科書與歷史研究
有關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特點,據專家概括有下述幾個方面。有些問題看似無關緊要,卻對學習者的歷史觀、甚至世界觀有著重大影響。
單線型歷史描述:日本的歷史教育從明治維新以后一直教授天皇從古至今君臨天下的歷史觀。戰后盡管實施了民主化,這一單線型的內容并沒有變。但日本民族的形成是一個多民族融和的過程,日本天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不掌握政權。這樣的歷史教育會給人留下天皇萬世一系、日本是單一民族的假象,使學習者缺乏與其他民族交流與共生的理念。
歐美中心史觀:歷史教科書將資產階級革命絕對化。將拿破侖戰爭解釋為推廣法國文明,而不管受侵略民族的感受,這是啟蒙主義的近代文明史觀,無疑是為侵略張目的。同時,將世界資產階級革命與明治維新連起來,明治維新就成了改革,成了絕對正確的東西。只強調明治政府各項改革的強國效果,而不管民眾生活和強制現代化帶來的痛苦,不說明犧牲人命積累財富的資本原始過程的實質。傳遞了一種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史觀,那么對于亞洲民族的欺凌和侵略就都可以順理成章了,亞洲各國的現代化也只有以日本為摹本了。
其三美化殖民政策:盡管歷史研究早已證明,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已久的將朝鮮占為殖民地的戰爭。但日本的一些教科書還是將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目的,故意寫成好像要幫助朝鮮獨立似的。
其四戰爭責任問題不明確:很多教科書只是敘說在戰爭中發生的事,并沒有界定日本的戰爭責任和對其他國家的危害。
其五對于歷史過程分析不充分:有專家指出,南京大屠殺、在亞洲地區的殘暴行為、數量驚人的強制關押和強迫勞動、抹殺民族文化等,僅僅羅列事件是不夠的,對前因后果不加分析,并不能完整把握事件相互聯系和演變的歷史定位。日本并不是從某天開始突然對亞洲有了加害行為,而與其開始前的歷史“助跑”過程有關。忽略了聯系就等于隱去了動機,當然會引起理解上的問題。
除了教科書本身的問題,還有授課老師的問題,有的人受“自由主義史觀”影響,寧愿去搞浪漫化的歷史。把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作為歷史事實來接受。更為重大的問題是,教科書是與社會歷史認識緊密關聯的。初學者似乎沒有太多的選擇,死記硬背教科書是學習歷史科目的方法之一,內容上也只能認為教科書所寫的都是真實的、是唯一解釋。再與大學考試聯系起來,教科書上記載的內容就更被絕對化了。
一般來說,教科書中的大部分內容是參考史學研究論著編寫的。那么,日本的歷史研究是什么樣子呢?這里,重要的關鍵詞是學術自由。人們有自由探討史實的自由,但這個研究究竟是否被社會接受,成為歷史認識的一部分?卻很難說是由學術判斷作主的。經驗證明這很大程度上與日本政治體制以及保守社會輿論相關聯。只要執政黨死抱著冷戰思維不放,日本與亞洲各國間在歷史問題上的對立就會不斷上演。
就以有關中國東北的研究為例,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出版了大量從中國遣返者的回憶錄、遣返記錄,一些曾在偽滿任職的人、甚至是遠東軍事法庭定為戰犯的人后來成為政治家、官僚、企業家、研究者、雜志編輯,不僅出版書,還接受報紙、雜志采訪,發表言論,形成了一種巨大的輿論。而這段時間,也正好是日本殖民地統治史研究的空白期。
到了70年代以后,歷史研究者才開始從學術上探討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但歷史學界正式將殖民統治研究提上日程,未必會對市民的認識產生影響。因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五六十年代,日本社會將戰前日本進行殖民統治的經歷,封存在了記憶底層。
蘇聯、東歐解體,冷戰結束后,日本與東亞各國經濟、政治交流日益緊密。20世紀90年代,圍繞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歷史認識差別問題,才像蓄積已久的火山噴涌而出。所謂日本的“新教科書問題”,還有小泉政權期間日本與中國、韓國之間圍繞歷史問題的對峙,都起因于這種認識差別。
一方面,雙方交流的密切促成了歷史認識的碰撞,另一方面,交流的密切化也要求構筑共同歷史認識,以消除維持、擴大交流的障礙。
研究成果與史料
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學者團隊組成之后,日本國內有聲音指責日方近現代史學者團隊專搞史學研究的學者很少,多為政治學者、外交史學者。這當然是一種貼標簽的看法,但是史學研究成果的繼承的確是個重要問題。
共同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中日戰爭的問題。在中國學術界,有以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的八年抗戰研究,也有從日本派兵鎮壓臺灣牡丹社開始的中日關系六十年的史料長編;在日本史學界,有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的十五年戰爭史研究;更有以偷襲珍珠港為起點的太平洋戰爭史研究;此外還有外交、政治、經濟各專門領域、各專題的研究。
涉及中日戰爭史的部分,政治、經濟、外交等各種因素交錯,人物事件線索繁多,有賴于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部分甚多。尤其是中日戰爭開始前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狀,各列強侵略、瓜分中國領土以及劃分勢力范圍的過程,與中華民族覺醒形成民族國家的過程相重合,各列強在中國的利益互相沖突、勢力互相制約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程相交疊,決定了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相聯結的特點。這一特點,決定了中日戰爭舞臺上中外各種勢力和人群復雜關聯,增加了歷史研究中對中日戰爭期間各種事件和人物評價的難度。
另一方面,有關日本策劃侵華戰爭的進程和日本軍部法西斯勢力膨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國內政治史研究的進展,如日本政治體制和決策方式的演變、日本議會政黨政治的失敗和軍部內閣的登臺、近代天皇制與元老組合的獨裁、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參謀本部與大本營、統率權獨立問題、派遣軍與大本營在侵華中各自扮演的角色等問題,都有賴于政治史和軍事史研究的進展。日本對華的經濟滲透、不平等條約與在華權益、移民問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阻撓、日本的戰爭依賴型經濟的形成等問題,又有待于日本經濟史的研究。
在史料保存利用方面,由于日本在宣布投降后至美軍占領前的兩周內,徹底地銷毀了政府各部門、外交、軍方涉及追究戰爭責任的資料,再加上美軍占領后沒收日本資料過程中涉及中日戰爭外交關鍵史料的丟失,都對中日戰爭乃至日本近現代史史料造成了極大損害。盡管遠東軍事審判中戰犯的供述和后來搜集的當事人訪談彌補了一些空缺,但相關史料依然存在很大的空白與缺口。而且,天皇家保存的史料并未被美軍沒收,迄今也未公開。史料學家認為,這些史料若能公布,將對中日戰爭史和近代政治史產生重大影響。
較為全面地評價和繼承兩國史學研究的成果,才能做到對中日戰爭史比較全面和中肯的評價。但要做到這一點,恰恰需要兩國史學研究者長期努力才能做到。這也許是中日雙方相約今后第二期研究的意義所在。
(高宇,日本立教大學講師、山西大學兼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