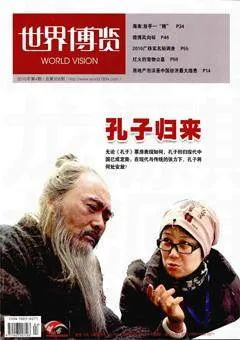政治\\學術與民眾感情
雙方學者坐下來交流,與以前各說各話相比已經是非常大的突破。這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這一步后,我們才有可能對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突破。
開始于2006年10月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經過雙方學者的努力,于2010年1月31日公布了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這份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書,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現代史”部分的中日雙方學者的各13篇文章。就3年多來首次公布的研究成果,我刊采訪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員步平教授。
《世界博覽》: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開始的過程中,有些日本媒體認為這次中國選擇的是社科院和北大組成的黨指導下的研究集團,日本選擇的是靠近自民黨的政治史、外交史學者為主的集團,共同研究的學術價值很難認定。您如何評價此次共同研究的學術性?
步平:有些日本媒體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包括中國的學術研究。不過,我們可以看一看報告書發布之后,日本一些偏重實證研究的學者關于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評論,比如《日中戰爭史》的作者秦郁彥說:“中方報告始終引經據典根據史實關系記敘,比起以前那種始終譴責日本的誘導輿論意味很強的歷史論文比起來,感覺有了很大變化……中國的歷史研究和公開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這個問題也可以用日本人自己的話來回答。
我一直強調中日歷史問題是政治判斷、學術研究和民眾感情三個層面交錯的問題,這三個層面既不完全分離也不完全重合,學術研究問題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但學者更主要是從學術角度來討論問題,需要遵循學術規范,這次報告書的結果證明大家是從學術角度來研究的。這一點與來自北大或社科院似乎沒有關系。
《世界博覽》: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只有近現代史的研究,古代史研究方面相對薄弱,這種情況在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里有表現嗎?
點評:我們的文章都已經發表了,大家都可以看,不能籠統說薄弱。應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
《世界博覽》:我國的古代史研究相對近代史來說顯得薄弱嗎?
步平:我個人認為不存在這種情況,中日學者之間這樣深入交流的機會并不多,這次和以前都存在的問題是一開始我們的對話沒在一個層面上,但并非哪一層面高或哪一層面低的問題。深入的對話,需要長一點時間的磨合,比如說,我得了解對方的話語體系,對方也得了解我的話語體系,這樣才能對話,否則的話可能就是各說各話,我覺得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古代史也是這種情況,不能判斷說誰的更高,誰的更學術。除非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
《世界博覽》:我們有很輝煌的古代史,對日本的影響又那么深遠。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我們要不要強調這一面呢?
步平:我不覺得需要特別強調,因為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自身發生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外來的影響,同時又有自身的獨特性,這是一個國家形成的基礎,日本和中國都是這樣。當然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漢字、儒教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影響,回避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亞流”也不科學,日本學者不贊成這個觀點,實際上我也不贊成,我們也沒必要用這樣的觀點來判斷中日之間的關系,我們要尊重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但是,換個角度,如果日本過分強調獨特性而否認中國的影響,這也是不對的。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強調我們的文化如何影響日本,“灌輸”方式效果并不好。我覺得日本人自己意識到這一點可能更好。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存在天然的感情,倒退到一百年前,不懂日文的中國人照樣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可以用文言筆談。那一時代日本人的文言水平相當好,那不就是中國文化的影響嗎?尊重與重視中國文化影響的傾向,這些年確實有些變化,日本人開始強調自身的獨特性了。這部分原因是因為中日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近代以來,日本比中國強勢,習慣于居高臨下地看中國,所以他們不覺得承認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有什么問題,因為日本處于優勢地位。現在面對中國的崛起,一些日本人感到有壓力,有一種很焦慮的心態,所以擔心如果總強調中國的影響,而不強調日本的獨特性,日本人就越來越沒有自信心。這也是近年來日本國內的“自由主義史觀”、歷史修正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抬頭的社會背景。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扎扎實實研究歷史的話,日本人會注意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近代的情況是日本文化對中國很有影響。在我們這次近代部分的研究中,我們特意設了一個題目: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和中國近代留日熱。甲午戰爭之后,中國很多人去日本留學,因為離得近、花費少、文字上有相通之處。我們近代用的很多語言實際上都是從日本過來的,比如民主、自由、反省、覺悟等詞。漢語外來語詞典中,可能超過一半的近代詞語是從日本傳過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是通過日本到中國,日本是中國革命者接觸馬克思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對于我們在近代部分列了這樣一個題目。有的日本學者非常驚訝,也很感動。我們應該承認這段歷史。不管古代也好,近代也好,歷史研究就要尊重歷史事實。
《世界博覽》:雖然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是兩國政府委托進行的。但還是學術上的研究,那在具體的學術問題上經過這幾年的共同研究有什么突破嗎?您能舉出具體事例嗎?
步平:這次的共同歷史研究不是要追求學術上多么大的突破。以前兩國有爭論、有爭吵,現在兩國學者首次坐到一起來研究,坐到一起之后首要的問題是把各自的主流觀點整理清楚了,告訴對方。所以我們首先確立了共同題目,各自寫了文章,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主流學者的觀點。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互相交換了論文,讓各自了解。就各自的論文來說,談不到特別大的突破,但是我認為最大的突破是雙方學者坐下來的交流。現在我們發表的論文,實際上是我們雙方經過了幾個回合的交換論文、聽取意見并修改后提出來的,部分采納了對方的意見。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這比以前各說各話已經是非常大的突破。這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這一步后,我們才有可能對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取得突破。
《世界博覽》:在學術交流過程中,您覺得中日學者在方法論方面有何異同?
步平:實際上中日學者遵循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歷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要尊重史實,用事實說話,這一點中日學者都沒有什么分歧。在具體的問題上,我可能用我掌握的史料來說話,對方可能使用對方掌握的史料來說話,可能不一定立即達成一致意見,需要慢慢來解決,如交換資料,交流認識,以后才能達成共識。
另外,方法論的差異還表現在對史實的判斷上。史實只有一個,但你從你的角度看,我從我的角度看,這就涉及到觀察方法。有的學者可能注重對具體事件過程的分析,有的把所有事件聯系起來之后,研究它們之間的聯系。比如我們研究近代以來的中日關系的時候,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結合日本早已經劃定的生命線和利益線,我們會認為近代日本一步步走向侵華的道路,是其實施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這是我們的觀察方法。而日本學者雖然承認這個過程,但是他們會比較關注事件的具體過程,比如“九·一八事變”確實導致侵占中國東北的結果,但是他們關注當時日本的各種聲音,比如外務省與軍部的觀點不同。我認為:首先需要承認基本事實,對于具體事件的判斷不一致,并非都是中日學者間的分歧,其實在中國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看法,日本國內也是如此。我認為這種不一致可以長時間存在,有的涉及歷史觀的問題。從國際學術交流的角度看,我們不一定要強求歷史觀的一致,實際上也不可能存在唯一的一種觀察方法,我們可以通過長時間的交流,相互了解或理解對方的觀察方法,也許會長時期存在一種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狀態。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歷史事實的確認。
《世界博覽》:既然都尊重史實,那這次雙方的主要爭論點在哪里呢?
步平:這次報告出來之后,你看看雙方的文章會發現,雙方的爭論點其實有許多,并不容易簡單歸納,有些媒體抓住某些表面上的差異做文章,其實并沒有抓住真正的問題,缺少冷靜的,客觀的思考和報道。我們用那么多的時間,經過反復討論寫出論文,而有些人用還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看過之后就給出評論,這樣的態度是不可取的。我希望大家仔細看看。
在南京大屠殺的數字這個問題上,中方學者列舉了南京審判和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上的數字,即30萬以上和20萬以上。日方學者還列舉了日本學者的研究結果,包括幾萬到十幾萬這樣的數字。日本的一些媒體有意抹殺雙方學者就“大屠殺是存在的”這一點達成的共識,也不報道學者關于大屠殺產生的責任和原因的追究,偏要把數字問題提出來,這是為什么呢?這是有歷史背景的。因為以前日本的右翼就想證明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在沒辦法否認基本事實的情況下,就故意在數字準確性上做文章,其邏輯是:數字不精確,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就是虛構的。這樣的邏輯其實是設置了一個陷阱,應當警惕。當然,強調某些數字是無可置疑的也不是學術研究層面上的科學論斷。我們的共同研究報告希望引導大家去冷靜思考,為思考歷史問題提供一個平臺。如果我們能夠根據學術研究的基礎來調控自己的感情的話,對話與相互理解就容易一些,也就能增進雙方的理解。學者不能說是先知先覺,但至少在歷史資料的掌握上有一定的優勢,其責任就是給大眾的歷史認識提供科學的依據。
《世界博覽》:有人指責日方團隊有幾位學者實際上是自民黨的智囊,對一些歷史問題的看法主要從政治上考慮,而非學術的。您怎么認為?
步平:這和第一個問題有聯系,學術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有一定的關聯,不能說學者沒有政治態度,但共同歷史研究要求學者以尊重歷史事實為基本前提,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我覺得政治背景的問題不宜強調。現在文章都已經發表了,我認為需要就文章的內容來討論,日本有的媒體也說中方的學者是政府選擇的,沒有自己的見解,故意把政府和學者對立起來,好像反政府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學者,這是什么邏輯呢?政府不是學術機構,其學術判斷來源于學者的研究,也依靠學者的研究,是學者拿出研究結果。
《世界博覽》:中日學者的學術背景也有差異?
步平:學術背景的差異表現在我們的學者大部分是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學者,日方學者中有從事政治學的、法學的學者。中日雙方學者在學術背景上有所不同,我倒覺得這種差異無可厚非,這段歷史本來就是和政治有關聯的,也和法律有關聯,觀察問題的角度更寬一些并非壞事。但研究歷史問題,歷史學者的觀察角度與立場是最基本的。雙方都在10名委員之外聘請了一些“外部執筆者”,這是為了彌補知識結構上的缺陷。
《世界博覽》: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遇到的真正問題是什么?有人說其一來自社會制度和現代化過程之差,其二來自歷史學方法論。您怎么看。
步平:真正的問題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斷。提出這樣的問題之前,首先要研讀雙方的研究報告。另外,現在的研究報告是“各自表述”,并不要求建立同一的認識,畢竟是學術研究,需要尊重學術規范。
《世界博覽》:這次研究涉及到很多政治問題,前面您也說過當兩個國家的國家地位和實力發生變化的時候,國民意識和考慮問題的角度也會發生變化。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也體現出當前中日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的現實嗎?
步平:學者的學術研究對歷史局限性是要有所超越的,我覺得我們是有所超越的,包括超越自己。比如我們主動提出近代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和留學熱,日本學者也會注意到中國文化特別是古代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學者不應該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去研究歷史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我一直強調應當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
《世界博覽》:說到感情色彩,在這次學術研究中,日方學者中是否存在歧視亞洲國家的傾向?
步平:在這次共同歷史研究中沒有。近代以來,中、日、韓和其他亞洲國家是同時起步的,大家都面臨西方列強的壓迫。不過日本最早擺脫了被動地位,通過明治維新、甲午戰爭、特別是日俄戰爭成為了亞洲強國,這讓日本人自信心膨脹,不斷強調日本的所謂“優秀”,形成了“民族差別意識”。日本戰敗之后,日本國內不斷反省走向戰爭道路的原因在哪?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民族差別意識”。相當多的日本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有意識地推動日本反省這個問題。日本戰后的確是反省了。首先反省日本為什么戰敗了,進而反省為什么走向戰爭道路了,再進一步反省為什么不能早日結束戰爭。但是這樣的反省是有問題的。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社會才開始反省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角色。而在這之前,日本人反省的角度是自己在戰爭中的受害,比如東京空襲,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越南戰爭升級之后。日本人發現,美國轟炸越南造成那么大災難,與當年日本給中國、朝鮮造成的傷害沒有區別,所以,日本應該也是加害者。日本作為加害者的反省到現在還沒完成,沒形成社會的整體意識。但是這次日本學者的文章,對加害者的問題還提到并強調了。當然不能說“民族差別意識”已經完全被消滅了。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實力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些偏見遲早會被徹底拋棄。這不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遇到的主要問題。
《世界博覽》:在這次共同研究中有沒有遇到資料的問題呢?中日雙方在使用資料上有沒有什么偏頗。如何在資料短缺的情況下再現歷史的真相?
步平:現在雙方在史料的使用上,還是有一定差異的。
戰后日本資料的毀壞和銷毀這部分是客觀存在的,比如日本731細菌戰部隊的資料,比如說戰爭期間使用化學武器的資料等,這些方面的資料日本學者也正在要求日方公布,但是日本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還不知道,目前我們在他們的檔案館里很少能找到。被美國拿過去的那一部分資料,還是開放的,現在這些資料有的在美國,有一部分已經返還給日本,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最成問題的是日本戰后或者是戰敗時銷毀的那一部分。如果在中國戰場上的和在日本國內的資料都毀掉的話,那就再也看不到了,這部分史料確實是問題,但對第一階段共同歷史研究還沒有形成特別大的問題。
《世界博覽》:中國學者使用日本方面的史料很多嗎?
步平:我們的學者用了很多日本方面的資料,相對來說,使用那些資料還是比較容易的。但日本方面使用中國的資料有限。一方面有語言方面的問題,但與我們檔案資料的開放程度有很大關系,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的檔案開放還是有問題的,非常落后,不要說外國學者使用,就是本國學者使用也還有許多不便之處,急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