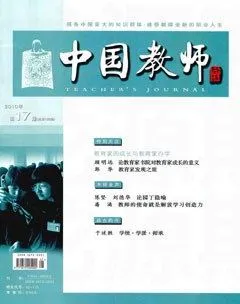在實踐中發揮教師的道德影響力
一、教學是“以善致善”的實踐活動
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教學本質上是一種“以善致善”的實踐活動。它以善的行為、善的內容來鍛造善的心靈、實現善的目的,為善之行、趨善之的是其根本特色。教學的根本目的在于學生、在于學生的發展,因而在當前,推動人道教學、追求教學公正、實現學生創造性生活、促進學生幸福就是教學活動的根本道德目的、根本的“目的善”。我們很難想象,教學能夠通過惡的手段來達致善的目的,或者說教學手段惡劣、教學結果卻優良。我們堅決不相信,魔鬼訓練、體罰心罰、摧殘虐待、知識剝奪,等等,可以換來學生幸福;我們也堅決不相信,現成的、規訓的工具性生活可以養成學生高貴的德性;我們更堅決不相信,通過充斥著不公正與種種歧視、對學生實行“獸道”管理與自由剝奪的教學,最終卻能實現學生的創造性生活……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上述種種手段真的能最終換來所謂的學生幸福,那么我們寧可不要那種幸福。
由上看來,實現學生幸福這一善的目的,必須采用善的手段。正因如此,有論者強調提出,“純粹的教學不但以追求生活幸福為終極目的,還講求‘以善致善’的方式獲得這種目的,不會以壓抑、扭曲、規避當下的師生生活為代價換取未來的幸福”[1]。然而可悲的是,在我們當前的教學過程中,教學惡行卻屢見不鮮,比如,目前種種教學暴力、體罰心罰、感情冷漠、師愛淡薄、師德淪喪等惡劣行為,不斷見諸媒體,社會公議不絕于耳。試問,這樣的教學手段,何以創造學生的德性生活,又何以實現學生的最終幸福?
因此在當前,在強調教學的“目的善”的同時,強調教學的“手段善”,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迫切課題。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種種的“手段善”——包括善的教學內容、善的教學行為、以及其他達致教學目的善的所有教學條件,它們當然都很重要,但其中最為關鍵的手段善,則無可辯駁地是教師本身。因此,下文將教師、教師德性作為一種手段善提出來重點討論。
二、教師德性是具有重要實踐影響的手段善
那么,為什么說教師、教師德性是最為關鍵的手段善呢?我們知道,一切手段,歸根結底都要通過作為道德主體的人來發揮作用。顯然,在教學中,有教師與學生這樣兩類人,兩類道德行為的主體。盡管他們都發揮著重要的道德主體性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教學過程指導者、教學生活引路人的教師,在其中卻發揮著更大的、更為關鍵的作用。這是因為,較之于教師來說,學生總是相對“無知”、相對“無德”的。學生知識的增長、智慧的生成與道德的完善,都需要具有相對較高知識、智慧與道德水準的教師,通過有道德的教學來完成。這就是為什么教師是教師、學生卻只能是學生的基本道理。我們總是強調,性格要靠性格來塑造,道德要由道德來完成,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作為手段善的教師,在學生發展的目的善中意義重大。
不僅如此,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其他種種手段善,如善的內容、善的行為、公正人道等善的教學原則,離開了教師這一主體,也都成了無本之木,無從發揮其作為手段善對學生成長與發展的作用。因此,從整體上來說,教學目的善的實現,很大程度上跟教師的道德水平息息相關。可以這樣說,有什么樣的教師,就會教出什么樣的學生;有什么樣的教師,就會形成什么樣的教學道德;教師具有什么樣的道德水平,也就決定了教學道德能達到什么樣的實踐境界。正因如此,國內教育倫理學研究專家王本陸教授認為,“教育的善惡,和教師有內在的聯系。好的教師能弘揚教育善,壞的教師則可能導致教育惡”[2]。
更進一步說,在教學活動過程中,教師的德性不僅不能“缺席”,而且必須是首先“在位”的。“正是在教育關系的意義上,教師才會反思性地而非毫無思想地、教條地或者偏執地和孩子們交往。而且,教師作為教育者(pedagogue)決定其養育興趣的出發點是對孩子們的成長和幸福感興趣。換句話說,教學不僅僅受效率原則支配,而且還有特殊的規范、倫理或愛的考慮。簡單地說,教師是用全身心來教學的,在和孩子們永遠變化的交往情境中,教師必須從情感上知道做什么合適,無論把他們看做集體,還是看成獨立的個體”,“確切地說,優秀教師學者向孩子們展示的教育智慧取決于內化的價值、身體化的品質、關切的習慣,這些構成了教學的德行”。[3]無疑,教師與學生同處于教學這個“場域”之中,但教師是必須提前“在位”的。他需要激發學生創造,全情投入過程,展示教學智慧,進行教學反思。如此這些,構成了教師的道德綜合素養,或者說教師的教育倫理素養。可見,教師德性作為教學手段善,具有至關重要的實踐影響,在教學道德目標的達成過程中意義重大,由此,它也就上升成了教學優良道德實踐的重要機制。
總之,“就教師而言,應該說,教學道德的提升與教師的業務知識素養有著密切的聯系,現實教學的平等、人道、自由等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教師的創造性教學,可以說,沒有教師的創造性教學,教學的道德是很難臻于完善的”[4]。
三、發揮教師德性的實踐影響力
那么,教師究竟應該具備何種德性品質?這些德性品質又如何在教學優良道德的實現過程中發揮“以善致善”的作用呢?據現有研究資料來看,人們在教師德性方面已展開了豐富的探討,目前也提出了觀點各異、豐富多樣的主張。筆者嘗試提幾條具有共性的教師德性來作些粗略討論。
一是教學使命感。教學使命感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地區的教師都首先必須具備的德性品質。沒有教學使命感的教師,當然不可能實現教學的使命。一個對教學事業麻木不仁、毫無使命感的人,根本就不配做教師,更不要奢談什么其他教師德性。中國儒家傳統對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教師提出,作為儒家君子、天地大丈夫,應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足見其高遠的人生境界與厚重的歷史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體現在教學上,至少應有三點。其一,要有教書立人的使命感。教師要把教學當做一種教書育人的德性事業來看待,而不是當做自己養家糊口的一個職業來敷衍。在這個意義上,教師德性是一種“事業道德”,而不是“職業道德”。惟其如此,教師才會充分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重視學生的生活幸福。其二,要有傳承文明的使命感。教師要把教學視作為一個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延續過程,它承載著重要的文化使命。惟其如此,教師才會科學合理地處理好教學目標上社會目的與個人目的的關系、教學過程中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教學方式方法上授受與建構的關系等,實現人類文明的存續、發展與創新。其三,要有分享文化的使命感。在有教學使命感的教師眼里,教學是一個人們通過公平競爭機會實現社會階層流動、身份再造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打破文化獨享與知識壟斷、促進文化分享的過程。惟其如此,教師才會努力打破學生階層、群體、資質、文化與心理差異等方面的束縛,消除歧見,公正公平地對待所有學生,以促進所有學生公平發展為己任。
二是教學良知。教學良知也叫教學良心,它也是教師必不可少的德性品質之一。康德對良知問題曾有很好的論述:良知是“任何人作為道德存在物生來就具有的”“是所有的自由行為的內在法官”“是人(在他心中的各種念頭互相控辯以前)內心的一種審判意識”,“良知必須被看做這樣一種主體原則:在上帝面前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5]只有具有教學良知,也即這種內在的審判意識、對自己行為負責的特殊道德責任感,教師面對學生時才會“把人當人看、使人成為人”,將此原則完整地貫徹到自身教學實踐中去,才會努力消除“神道”“霸道”與“獸道”,貫徹教學的“人道”,才會真正關注學生的發展與成長,賦予學生創造性自由。不僅如此,理學大師王陽明提出,良知作為一種德性,它既與自我存在融合為一,又構成了主體行為的動力因——從知善到行善的轉換。它既體現為主體對自我的內在要求,又體現為對行為外在強制的揚棄。[6]因此,一位具有教學良知的教師,就會自覺地化德性為德行,去履行自己的道德承諾,實踐教學的道德理想與倫理使命。作家三毛說得好:“教師不是飛蛾撲火的浪漫烈士,教師是骨子里有良知的生意人”(三毛:《送你一匹馬》)。筆者的理解是,一個有德性的教師骨子里是富有教學良知的,他必定是以自身德性與德行去喚醒學生良知、營造學生幸福的“經營者”。這種良知,是深入骨髓的良知,是明明知道生意要賠本卻依然扛著做下去的良知。因為這種良知,教師注定要成為單單生意都虧本的“烈士”。這,也許就是教師教學良知的生動寫照。
三是教學責任倫理。責任倫理是傳統德性論與現代權利論、義務論、目的論等融合重構的結果。它作為一種與當代教師所面臨的特定價值處境相適應的道德立場,在當前顯得越來越重要而迫切。教師究竟應該具備何種責任倫理?目前,論者從不同方面對此展開了豐富的研究,比如有人提及價值啟蒙、敬畏生命、政治責任、育人責任、道德責任,等等。角度不同,主張自然也就各異。從學生幸福目的論的角度來說,教師最基本的責任倫理,就是應該基于學生幸福,學生幸福目的應該成為教師教學責任倫理的最基本考量。具體表現在于,其一,要對學生生理幸福承擔責任。即教師要關注學生的身體健康,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同時也有保障他們安全與生命不受侵害的義務。從這個角度看,汶川地震中“范跑跑”作為教師搶先逃離危險,就不符合生存秩序與教學責任倫理。其二,要對學生心理幸福承擔責任。即教師要承擔“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責任,引導學生增進知識、增長智慧、陶冶情操,凈化心靈,培養健康的知情意行。如果教師在此方面缺位,那就會造成責任倫理的缺失,教師的角色也就變得黯淡無光。其三,要對學生倫理幸福承擔責任。即教師要賦予與保障學生創造性發展的自由,為學生在創造性的德性生活中走向具有多種發展可能的“可能生活”提供有效的保障。
總而言之,教學是一項“以善致善”的道德實踐活動,而教師德性作為至關重要的手段善,在教學實踐活動中產生著重要的道德影響。在教學過程中,只有發揮諸如教學使命感、教學良知、教學責任倫理等在內的教師德性的綜合影響力,才能真正達致教學的道德目的,實現學生的創造性發展與幸福。
[1]劉萬海.重返德性生活——教學道德性研究[D].上海:華東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