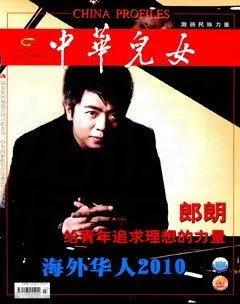單秀梅:布藝中傳達的新疆民族文化符號
2010年10月26日,烏魯木齊7坊街文化節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開幕。帳篷式的展區,一踏進去,濃濃的西域風情似乎就裹挾著風沙與果香撲面而來。種類各異的展品中,—對維吾爾族老夫婦造型的布偶被放在展廳門口的展臺上,格外引人注目。
老夫婦—人捧著花皮西瓜,—人舉著剛剛烤好的馕,上面還撒了芝麻……濃烈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這是單秀梅的作品。這個看似單薄柔弱的女民間工藝大師,用雙手一針一線通過布偶,告訴世界新疆的美好。
在一針一線中傳遞出新疆的靈魂
單秀梅是新疆人,回族。
作為上世紀60年代生人,童年的單秀梅和內地的許多孩子一樣,跟隨家庭下放農村,在無所拘束的田野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有些與眾不同的是,單秀梅家被下放到維吾爾族聚居的村子里,幾十戶中只有他們一家是漢族。單秀梅度過了一個維吾爾族味道十足的童年。
自幼喜歡觀察的單秀梅,那時候最愛看維吾爾族婦女勞動,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美。而在與維吾爾族鄉親們朝夕相處的三年中,單秀梅不僅擁有了一個維吾爾族名字,學了一口流利的維語,更是從內心就被浸潤成一個地道的維吾爾族小姑娘……樂觀、積極、善待生活。
她穿著漂亮的布拉吉光著腳奔跑在廣袤柔軟的黃土上,學著維吾爾族姑娘用奧斯曼畫眉,看她們從井中提水時優雅的身姿。甚至若干年后單秀梅都已年過不惑,仍舊念念不忘維吾爾族大媽洗碗時的沉穩之美;仍舊能夠隨口哼唱出童年節慶時看到的十二木卡姆迷人的旋律。那是單秀梅生命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三十年后,它們被她精心縫進了片片碎步,拼湊成人們心中最原汁原味的新疆。
“十二木卡姆”中的人物造型惟妙惟肖,仿佛能聽到他們動情的歌聲;風趣、機智而又幽默的阿凡提騎著毛驢走過來正在向你問好;維吾爾族大媽抱著大西瓜樂不可支;賣馕的維吾爾族老大爺正在巴扎吆喝:大家快來買呀,便宜得很,不香不要錢……
將成功與更多的人分享
單秀梅的成功,某種意義上說是搭上了西部大開發的班車。
2000年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后,新疆旅游業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人懷著好奇踏上西域的土地,又在一片驚嘆中意猶未盡地離開。能否帶點紀念品,是很多游客的想法。可是當時,新疆連適合帶走的旅游紀念品都很難找到。單秀梅的布偶新疆娃娃正是從這里起步,走進游客的視野,也帶去了新疆的靈韻。羽西化妝品的贈品“中國娃娃”對她的啟發讓她走上手工制作新疆布偶的橋。這個發現,讓她幫助新疆民族文化產業推開了一扇窗。
單秀梅成功了!
她沒有固守自己的天地,因為所有的靈感來源于這塊滋養她的土地,她也要把這些甜美與更多的姐妹一起分享。2002年,隨著“新疆布藝人物”的問世,當年已近40歲的單秀梅決定和一家公司合作,開始人生的第二次創業。工作室吸納了一批40歲上下的下崗女工。“其中有五位心靈手巧,又有一定繪畫功底,我便毫無保留地把核心技術教給他們。五年過去了,盡管我的工作室搬了好幾次,這幾位老員工還一直跟著我。”不僅是在自己的公司里,單秀梅還把自己的創意和手藝帶給更多需要的人。從2004年開始,烏魯木齊冰天雪地的時候,她就忙著去給農村婦女搞培訓。這既是幫助烏魯木齊市婦聯開展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項目,也把民族的傳統手工藝重新帶回民間。每次去講課前,單秀梅都要選好最具代表性的圖案,按自已設計的產品要求畫樣刻版,再繪成彩圖,然后買好布和繡花線。
由于為下崗職工再就業作出了貢獻,單秀梅被評為“全國巾幗建功標兵”,“全國三八紅旗手”。
藝術或比金錢更為重要
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單秀梅用速寫本“寫”成了一篇圖文并茂的日記,正面寫字,背面用連環畫再現文中的情景。班主任老師對這個孩子的藝術天賦大感吃驚,專門把她介紹給一位新疆藝術學院的專業美術老師。四五年的時間里,單秀梅幾乎沿著專業的美術之路往下走,她以為她會一直這樣走下去,直到走向夢想。
然而命運總是一部不可排演的戲劇,高中畢業,心高氣傲的她只報了北京電影學院舞美專業,結果連考了四年最終還是以黯淡的成績結束了自己的學生生涯。為生計,她在機關工會當起了宣傳干事,又為人妻為人母。日復一日順理成章,但是每當夜深人靜時,年少時的夢想總會翻涌而出,令單秀梅惶恐得有些窒息,她越發不甘心一輩子淪陷在對夢想的背叛中。
于是她自費上研修班,照舊把生活積攢在心里。終于,她的生活在2000年開始轉身。
2001年夏天,新疆舉行首屆旅游紀念品設計大賽。她有幾分忐忑地抱著自己的布娃娃去報了名,結果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單秀梅得了唯一的金獎。
在后面接連不斷的比賽和展覽中,單秀梅的名字越來越奪目。
2002年,她的作品“龜茲情”在首屆中國旅游紀念品設計大賽中又榮獲金獎。
2005年,在杭州舉辦的西湖博覽會第六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作品展上,她的作品獲得2005百花杯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獎金獎。
2006年11月的一天,單秀梅接到一個長途電話。來自北京國家博物館。他們想收藏她的《于闐情》、《剃頭匠》和《十二姆卡姆》作品。“你的作品很獨特,我們想收藏幾件,留給后人來看,你是否同意?”聽到這樣的話,單秀梅不假思索地答應了。此前,這些作品每件都有人出高價要買,全都被單秀梅謝絕了。國家博物館收藏,她分文不取。或許,雖然成立了公司,帶了工人,骨子里單秀梅還是三十多年前那個愛用靈動的大眼睛打量世界、追求藝術之美的小姑娘;是那個在新疆春秋的風沙和冬日的寒冷中背著畫板到處畫速寫、采鳳的少女,心中懷有的只是一腔熱情和奔放的情懷,泛著大漠中俠女的豪爽奔放。
2007年,在第五屆中國工藝大師評審表彰大會上,單秀梅和新疆玉雕大師馬金貴·起,獲得“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榮譽稱號。回到新疆后,中國工藝美術界的權威,清華美院的院長常沙娜專門給她打電話,兩人足足聊了40多分鐘。這位熱愛新疆民族文化,年近占稀的藝術家交給單秀梅·項“任務”:“你是回旗人,又會說維語,對新疆民族文化情有獨鐘,同時你還年輕,你不單單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還有責任和義務女傳承和保護那些快要失傳的新疆傳統工豈品。”
一席話猶如給單秀梅吃了一顆定心丸。
狂奔在藝術追求的路上,單秀梅一直力求保持一顆安靜的心,像最初一樣靜下心來繡一頂花帽,為“龜茲情”品牌的樹曲:再添一抹動人的民族風情。雖然手工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她。“現在日生產能力雖然已從20個提高到100多個,但連國內市場都很難滿足,上萬件的單子簡贏就不敢接了。”但為了保證質量,她寧愿主動放棄。因為她心中早已有了一個新的夢想——為新疆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化,建造一個博物館。
單秀梅知道,這個夢很奢侈,但依舊可以抵達。
責任編輯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