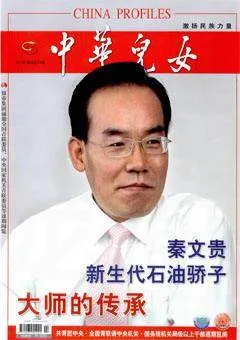當我們凝望大師遠去的背影……
大師遠行,留下讓后輩仰止的背影!大師遠行,留下讓后輩追隨的足印,
近些舒從季羨林任繼愈錢學森、土世襄到楊憲益歐陽山尊賈植芳王元化啟功等,一批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界受到國人仰慕與敬重的大師們,一個個因高齡而相繼辭世讓國家和民族平添了幾許沉重與哀傷。人們在痛感時光飛逝歲月無情的同時不約而同地將關注的目光聚焦在大師們的背影上——
這些大師是怎樣成為大師的?
大師人走了,留下的是怎樣的精神財富……
大師們的學術造詣累累成果,乃牟人品操守道德文章后繼者何人?
“第一位的是要愛國”“
“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還是作為一名學者第,第一位的是要愛國。”
這是剛剛故去的原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時常掛到嘴邊的“口頭禪”。愛國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種力量和心愿。我們盤點那些已經逝去的大師們無一例外不是常懷著一顆拳拳愛國之心都把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看得比什么都重!
當年馮友蘭先生堅決不愿把那張美國永久居留證帶回國的故事已經傳頌了幾代人,或許還將傳揚下去:兩彈Ⅱ勛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文憑的第九天就義無反顧瞀上回國的輪船,開始了他“我要為祖國的建設做些事”的壯麗人生;而錢學森為了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幾乎付出了牢獄甚至生命的代價在苦熬力撐中終得實現心愿——這是多么偉大的力量!
21歲就考進了牛津大學的楊憲益先生,畢業后已經與英國一位傳教士的女兒訂婚,卻照樣決定共同返回中國定居。1940年楊憲益與戴乃迭去申領入華護照的時候,英方官員不禁納悶:這么一個如花似玉的洋姑娘,為何非要去正在戰火紛飛的中國呢?戴乃迭小姐卻一意孤行地要伴隨她的中國未婚夫起去。就這樣,年輕的夫婦身上只揣著50英鎊從南安普敦開始了他們此世一生的雙人旅程。
季羨林先生則是于1946年自德國留學歸國從教。據些老教師回憶,當年由于季先生在東方學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學,劍橋大學曾有意聘請他到校任教,但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來,學成報國是
個極為淺顯的道理,這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操守。
即便在中國本土土生土長的話劇大師歐陽山尊,其愛國情懷照樣感人至深。2007年,已逾九旬的他為中國話劇百年題詞:雖屆耄耋壯心不已一形容自己是“生于憂患、老于安樂、留得余年報效祖國,并仿照岳飛的《滿江紅》填了一首詞:“雖耄耋,壯志丹心,余輝未減。功名利祿塵與土,藝海弄潮有年月。迄今日,癡活逾九句,不思歇……”一顆滾燙的赤子之心躍然紙上y14gHBkmtdNlleLo3711bA==。
出于這種拳拳愛國之心大師們總是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自覺與民族的發展和振興聯系在起,深入血脈的愛國熱忱與視學術為生命的治學態度高度統的結臺,才有可能建筑起座座事業的豐碑。
勤奮而嚴謹的治學之道
探尋大師們的學術歷程大多具有一些共性。
其一幼學發端基礎扎實。大師們常常發蒙于年少,專業基礎深厚,自幼練就了童子功。像啟功先生4歲入私塾學習詩文書畫;楊仁愷先生年少就以書法聞名,程十發先生幼年即接觸中國字畫;史樹青先生8歲開始逛琉璃廠,中學時即有鑒藏名家的美譽:被譽為中國話劇藝術代山尊的歐陽山尊也許從幼年過繼給伯父歐陽予那一刻起,與話劇的姻緣就已經寫定,早在中學時代,歐陽山尊就開始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話劇創作演出活動并經常為歐陽予情的戲劇擔任舞臺監督。
其二,學司專,矢志小渝,他們拋棄世俗利益的干擾,一旦確定方向便終生從事某項事業,或以某一項事業作為主干,滴水穿石矢志不渝,中學時代的鄧稼先文理基礎都好,可他接受父親的建議,覺得學理科或可為國家更有直接幫助高中畢業后一舉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從此在理論物理上徒手攀峰終其生,季羨林從求學清華到留德十年,從初歸紅樓到傳道燕園,不管是踽踽獨行一步一艱難,還是到陽關大道光風霽月之時先生從來都沒有放棄過自己的那些在別人眼里視為冷之又冷的學術追求哪怕在萬馬齊喑之時先生一邊看著門房邊還偷偷地翻譯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
其三觸類旁通修養深厚。大師之所以為大師,無一例外都是博覽群書厚積薄發,他們有的是詩書畫俱佳,有的是文史哲兼通有的是興趣愛好廣泛而高雅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并駕齊驅,相得益彰。如錢學森,成天面對浩繁枯燥的公式演算重若山崖的行政專業事務卻絲毫不影響他對歐洲古典音樂尤其對貝多芬交響樂的欣賞與陶醉:被譽為京城第一“玩家”的文化學者王世襄研究的范圍極廣,涉及書畫、雕塑、烹飪建筑等多方面他對工藝美術史及家具,尤其是對明式家具古代漆器和髹飾等研究更是開創性的獨樹幟,王世襄先生生前回憶正是在燕京大學讀書的自由的學風,讓他廣為涉獵而走上了適合自己的道路。
其四,寵辱不驚,胸懷廣闊。大師們歷經不同社會階段,有的遭遇困苦磨難但心胸寬廣樂觀向上,不論遇到何種挫折,始終向著心中的學術高峰攀登,最終領略了“險峰”的無限風光。被譽為中國硬骨頭教授的賈植芳一生經歷坎坷,曾經四進監獄,加上改造時間前后達25年之久。作為一個有著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賈植芳先生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不因歷史的震蕩,政治的榮辱而左右,他既繼承了傳統儒家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使命感,同時也堅持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啟功先生又是另一種典型。他本是地道清皇族后裔,在世俗泛濫成災的當今,有人以姓
愛新覺羅為榮耀,啟功先生對此卻冠以無聊,他認為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瑯琊王家的后人,但誰又能說他不是“書圣”呢?大師們心無旁騖一心向學的胸懷和氣度由此可見一斑。
任重而道遠的傳承
自然法則讓大師們一個個地排著隊向我們揮手告別,大師枯竭的時代正在到來。
就像壇醇香的美酒,經過了多次釀造和陳年窖藏一樣大師的造就也并非短期之功,他們的學問都是傾其一生不斷攀登學術高峰的結晶。
他們走了,雖有著作和作品傳世但其道德文章,學術秘笈仍然隨著其生命的結束而永遠塵封,不能不令人惋惜。
所幸大師們的諸多弟子在這一刻被歷史凸現出來他們原本在大師們的背影下默默做著學問,沿著老師的路徑和方向,努力接力賽跑,并且各自也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績!
然而,僅此就夠了嗎?我們每一個人又該做點什么呢?
人類創造文明的過程,就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過程。今天,對有志追慕前賢的人而言,了解已故大師們的治學特點人格魅力傳記資料乃至于軼聞趣事,都是富有意義的。毫無疑問這些精神財富不僅屬于大師本人及其弟子也是屬于我們全民族的理應繼承和發揚。
但如果為了傳承而傳承只能稱為復制和模仿,而在浩淼的歷史的長河中任何簡單的復制和模仿都會導致文化的蕭條和流失。因此,僅有傳承是不夠的又化還需要發展。這就更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同任務。
就社會而言文化的發展主要是通過社會教化的主動選擇來實現。以傳承社會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化主要通過社會教化來進行,而社會教化主要又是通過與人有直接聯系的家庭學校同輩群體大眾傳媒等來實現的。
正是基于這點,本刊適時精心策劃了“大師的傳承”這專題,以期引發廣大讀者對這問題的思考。
大師可以遠去,但大師們的高尚品德,視學術為生命的精神不能遠去,尤其在當前充滿喧囂與躁動的學術界我們更應該將大師們的精神發揚光大,以更真誠更扎實的態度,使大師們開創的事業薪火相傳,生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