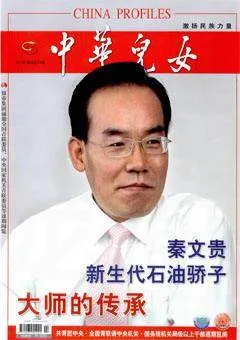陸曉光:大師王元化傳授我自由之思想
能否成為人師,往往和一個人做學問的源動力有關;對于時代,對于社會,你有沒有特別的經歷和感觸,敢不敢做出父鍵的抉擇,能不能又所堅持。
記者:您與王元化先生相處了多長時間,您怎樣理解他的學風與人格呢?
陸曉光:我從師先生可以說近25年我認為王元化先生的顯著特點在于他是一位有情感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情志概念,是從《文心雕龍》黑格爾美學別林斯基文論中綜合出來的。他認為情感滲透著思想思想應該引導情感。先生是從文學出身進入思想領域的,文學上情感本身是一種價值,所以他的思想中就包含著很多切身體驗,豐富的情感,有種動人力量,而不是光禿禿的理論或純邏輯的思辨。
比如先生讀到巴金一篇文章中‘只有女人沒有背叛句子時特別激動,常人看來這種說法有些偏頗,但先生和巴金的判斷都是以特殊的切身經歷為基礎的。文革時期,王先生的母親、姐姐和夫人張可,都給了他巨大安慰與溫暖呵護。而對巴金關于“家”的看法王先生又并不十分贊同。他認為中國的家庭是有重要意義的,他曾經把自己和顧準做過比較,認為自己要是有像顧準那樣的遭遇可能抵受不住。王先生很多思想文化觀點都是這樣包含著深切的情感體驗。
王先生本人強調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我覺得他這個特點也可以表述為有德性的思想和思想的德性。比如大家都知道學者要追求真知,但當你所認為的真知甚至你所堅持的信仰有問題的話,你是不是有勇氣對自己進行反思。比如他反思激進主義首先認為自己身上有激進主義,自己寫文章曾經喜歡把話說得刻骨鏤心才稱心意,他承認自己在胡風案件以前的文章有過這種偏頗。從自己身上的問題為思考起點敢于直面自己身上偏頗,這就是思想的德性問題了。盡管他的思想歷程未必完美+多有曲折,但他始終真誠追求真知。
記者:那王老師的“情志”和“德性”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能夠全盤接受嗎?您個人實踐的成效又如何呢?
陸曉光:“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已是熊十力提出的治學方法先生在《文心雕龍》研究中也引為指導。我體會這兩句話是說做學問要有充分的考據和論證二是說沒有什么新意就不必寫文章。從治學和做人的角度這種既尊重事實又堅持個性獨立的方法論,我也是認同的。
在這種思想方法的啟發下,我對王老師的些觀點也試圖有自己的認識。比如王先生推重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認為從先生自身的文字風格來看他的“自由”。恰恰是非常講究學術法則和嚴謹論證而顯然不是天馬行空也不是簡單化的“率性”,這與社會
一般理解的自由思想應該是有區別的。在這個意義上,王先生本人倡導的。有學術的思想,或許可以說是補正了流行所理解的“自由之思想”。
另外先生說他生有三次反思,焦點是左的教條主義極左思潮。但我認為進入新世紀以后,他有第四次反思,主要是提倡新人文精神。所謂新人文精神,一方面是區別于以前極左思潮和激進主義而言,另一方面是針對“市場至上”的偏頗。人文精神不能轉換為生產力不能以市場規則和價值為尺度。例如用市場經濟中奇貨可居待價而沽之類眼光解釋諸葛亮三出茅廬,在他看來是對大雅精神的消解,是一種市場媚俗。雖然先生本人并沒有明確說第四次“反思”,但我對這個思想遺產的認識在方法上是基于老師倡導的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已”。
記者:那么王元化先生的弟子身上有沒有什么共性的東西?大師的直接傳承者是不是都能近水樓臺先得月?
陸曉光:先生的弟子也許可分為兩類一是先生的博士生,二是被稱為私淑弟子的,如研究京劇的翁思再等。
博士生弟子都是以學術為追求。如蔣述卓教授早已是暨南大學黨委書記了,但一直堅持學術事業,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先生收到述卓郵寄來新著時的欣慰。胡曉明教授與我同在華東師范大學奉教,他主事古典文學教研室,前年當選為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學會會長。傅杰教授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擔任雙肩挑工作。還有一位吳琦幸,現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每年回上海時我們都是以文相會。我間接聽到先生對我們博士生弟子的一個評價是,“各人有所不同,都是正派人。”我想這一點至少是最基本的。
其實單從傳承角度講,嚴師未必出高徒,還有天賦、條件,機遇各方面因素。王先生對我的影響主要是他有情懷有志向,思考問題有社會關懷。此外畢竟是二十多年師生,有些影響應該留在心中,有些影響也許是不知不覺的。
記者:那么您認為王元化成為大師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在王先生的弟子一輩中能出現大師的幾率有多大,您個人又怎么想呢?
陸曉光:相對于現在分門別類的教育模式,王元化先生是一個不同尺度。先生對個人的社會作用有過一個光和鹽的比喻,光能夠照亮別人,鹽是把自己融化在社會中,兩者都對社會有貢獻。從王先生的經歷來看,他思考和提出的問題背后都有一種大的社會關懷,都是社會朝前發展要認真解答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他來說,是有歷史延續性的,而且是由自己現實生命中遭遇挫折引發的真切思考,這樣的出發點往往引起讀者感應,產生某種共鳴。從這個意義上講,能否成為大師,往往和一個人做學問的源動力有關,對于時代,對于社會,你有沒有特別的經歷和感觸,敢不敢做出關鍵的抉擇,能不能有所堅持,等等。
先生其他弟子不必由我來說我對自己要求首先是忠于大學教育,其次是追求學術上的快樂境界。先生在上海市學術貢獻獎頒獎大會上的感言中說,“學術工作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苦,走深了你也會感覺到一種快樂可以達到種忘神:你不去想它它也走到你心里面來了,你就會從各方面都迸發出種熱情。”先生認為這是學術的最高境界,這樣的快樂也是令我心向往之。
大學教師還有一種快樂如果你的課學生覺得有收獲,學生感覺很愉快,你也會感到快樂。如果學生討厭你的課,做老師也會很難受。而大學上課的快樂與潛心學術研究而又能變通地運用有關。王先生讀黑格樂,曾經覺得美不勝收,“衣帶漸寬終不悔”后而有所發現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這種喜悅我也是有所體驗的了。
記者:所謂“大的社會關懷”,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大師,為什么現在的中青年學者一方面經常被社會封為“大師”,另一方面自己又不愿承擔大師之“大”呢?
陸曉光:中國直有“勿傷大雅”的傳統,今天也應當有勿傷大師弘揚大師精神的氛圍。如果人人都想做大師那么大師可能被“大眾化”“平均化”,如果“大師”成了一種可以賣高價的標簽那么這正是“市場至”上對人文精神的種消解。而且,我們也不必把目光僅僅聚焦在大師上,應當承認小師、中師的存在和貢獻。就像《大雅》是一種比較高的尺度,但和大多數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間有所距離。《國風》《小雅》也是各有特色,各有價值的。王先生不僅說過“光和鹽”都是社會所需要的,他還說過:中國歷來就有一些知識分子與浮在表面圖具虛名的人相反,不求聞達,默默奉獻。真正使中國文化一代代傳下去并得到發揚的。正是由于有這樣一批人。
至于“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大師我想大師首先應該是有大文德的老師。人文學科與技術工作還不同,尤其需要文德。大文德首先是指關心的不僅僅是個人東西,而有一種對國家、社會乃至天下的廣闊胸襟與關懷。這可能也是《小雅》與《大雅》的區別所在。《詩經》中既有大雅的地位,也有小雅與國風的空間,我們傳統文化是提倡各得其所,而底線是敬重大雅勿傷大雅。
王元化先生關懷的是社會性時代性的大問題所以能引起比較廣泛的共鳴。王先生說他向往的是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就是先生的文德。王老師18歲時在上海加入中共,因為忍受不了當時日寇在北平的侵略,感受到了巨大屈辱。而我們現在社會中“向錢看”和以數字成果為標準,也幾乎成為種學術以外的壓迫今天想成為大師、中師小師,都要有一種對學術本身的堅持。
大師應當有學術技術以上的精神追求莊子所謂“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現在人文領域中,專家意義上的大師還是能出現,但像王先生那樣經過歷練而堅持社會關懷的人物,在學校專業體制中出現的概率會小點。那樣的人物往往打破了專業限制,而根據問題的重要意義展開研究。比如王老師對《文心雕龍》的研究,國內外一般有平行比較和影響研究兩種,而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采用的是與這兩種顯然不同的“綜合研究法”。他的研究以《文心雕龍》為基礎,以探究文藝創作規律為目標,因為之前的文藝觀輕視文藝規律,以政治法則取代文藝規律,因此文藝問題成為重大社會問題。這個研究文藝規律的目標需要通過古今中外的廣泛比較才可能達成,所以才需要“綜合研究法”。而僅僅就這種文史哲打通的方法的技術層面而言,在今天學科劃分的體制中就比較難以運用。
記者:您所接觸過的中青年學者中有沒有同樣身懷抱負又堅持學術自由的人呢,您認為他們怎樣做才能真正走上大師的成長之路呢?
陸曉光:現在的中青年學者中也有一批思考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重要問題的學者,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們之中未必不可能開辟新的道路。社會也需要創造一些承前啟后的學術環境。王元化老師生前關注過央視的《百家講壇》節目,記得他對錢文忠教授講玄奘法師是有所肯定的。他認為這樣的節目設置是有必要的可以讓更多人走近大師走近高雅學術文化。但是正如前面我說過,我關心的是大師中師小師各得其所和相輔相成相通的問題。大師標志著一種高度和廣度,所以比較可能涵蓋各專業各層次的相通問題。我本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心儀作為人文學術之典范的王元化先生的,也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而盡綿力從事推進華東師范大學“王元化研究中心”工作的。
王元化研究中心是一個約一千平米的老建筑,也是華師大最早前身大廈大學的老校址所在地,非常有歷史感。現在每天都會有人來參觀訪問,包括海內外學者進修教師、高校內外的學者文化人等。上個月我們中心掛牌成為研究生綜合素質養成活動基地。在掛牌活動發言中,我嘗試用思、通博、雅四個漢字來表達王元化學術精神對于研究生綜合素質養成的獨特意義。
“思”就是有情感有知識有思想有理想。例如他提倡用心血做學問、有學術的思想有情志有理想的文藝學:他主張知識者要有公共關懷,民主觀念應包括尊重少數人的存在,既承認人的局限也推重精神追求;他還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不是虛無,在某些方面足以和西方相抗衡等等。“通”是指打通學院圍墻內外之隔。王先生本人在文藝界出版界新聞界地下黨等社會領域都有經歷他的學問絕不限于學院,而是與社會文化需求有自覺的溝通和互動。“博”是指他廣涉古今中外文史哲的研究視閥與方法。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王老師與顧準、錢鐘書,李慎之,錢仲聯,季羨林都有靈犀相通的交往。“雅”是對高雅文化的堅守和倡導。例如他研究京劇不僅是個人興趣,更重要的是看到京劇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特殊關系,他的《清園談戲錄》據說已被國內著名大學的國學專業列為必讀書目,他對書法的愛好與推重也代表了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高雅文化。
我以為“思通博雅”不僅是王元化學術思想的重要特色所在而且理應作為大學人文教育的一種尺度。
王先生說過,學術不僅是為培育人才,更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質,影響社會風氣:“學術上的虛驕浮夸陋習,往往會形成社會上弄虛作假之風。”不管這些學生將來是否成為大師,抑或是中師小師,我認為這一點都是最基本和根本素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