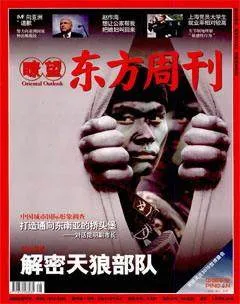IMF向亞洲“道歉”
6月28日,多倫多二十國峰會結束的翌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MF)總裁多米尼柯施特拉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 Kahn)就馬不停蹄地趕回華盛頓,召集本刊記者在內的少數記者舉行了一場小范圍的圓桌會。
圓桌會的主題,是介紹將于7月12日至13口舉行的“亞洲21世紀”高峰會。一個區域性的經濟會議,為什么讓卡恩如此看重?最大的原因,就在于IMF和亞洲國家關系敏感,恩怨是非不斷。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IMF雖向一些國家伸出了援手,但貸款條件相當苛刻——受援國必須實行嚴格的財政政策,進行更自由化的市場管理,甚至必須在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
以馬來西亞為例,IMF當時為緊急援款開出了一系列苛刻條件,其中包括開放金融市場、放松外匯管制、最大限度緊縮通脹并削減財政開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當聽到IMF的這些條件,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蒂爾曾破口大罵:“這樣還不如讓康德蘇(時任IMF總裁)來馬來西亞當總統算了。”
IMF前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穆薩(Michael Mussa)對本刊記者回憶說,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一個普遍的感覺就是,IMF的一些貸款的先決條件太具破壞性。”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家教授孫文松(sungWon Sohn)也指出,“舊的IMF太苛刻,他們過去的一些條件根本沒考慮到實際情況。”
從現在看,IMF當時奉行的就是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處處以所謂的市場規律為準,但實際上這種僵化教條的做法,反而傷害了新興經濟體,也損害了IMF的信譽。IMF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也一度使IMF和中國關系惡化。
正是由于這些不堪回首的記憶,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多年中對IMF表現出明顯的離心傾向。這次金融危機中,亞洲國家盡管也受到沖擊,但并未向IMF救助,相反,亞洲還有組建地區性貨幣組織的打算,以此取代1MF的部分職能。
現在的亞洲卻是國際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IMF要在國際金融體系扮演中心角色,就不能缺少亞洲的支持,而^’亞洲的離心傾向讓IMF產生巨大的危機感。于是,在“后危機時代”,徹底反思過去偏頗政策的副作用,修補與亞洲國家的關系,也成為IMF的一一項重要任務。
IMF在努力向亞洲國家伸出橄欖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不久前出任IMF總裁特別顧問,固然有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因素,但外界普遍認為,這也同IMF希望借助中國官員的身份來改善和亞洲關系有關。此外,IMF擬于7月初在香港發布《世界經濟展望》的更新報告,也是IMF首次將發布會放在亞洲舉行。
在這次圓桌會上,記者更不斷聽到卡恩就亞洲金融危機進行反思,他多次坦承,IMP當年在處理亞洲金融風暴對策上存有“過錯”,加劇了亞洲國家的民生痛苦。他并且表示,時代在變,IMF也必須改變;而且,在一些問題上,歐洲其實不妨學習一下亞洲的經驗。
雖然他避免直接使用“道歉”這個詞語,但其態度的誠懇、言辭的直率、反省的深刻,是以前無法想象的。
這或許正凸顯了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格局的變化。在這次危機中,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影響力大幅提升,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推動力,讓IMF已無法再忽視它們的存在。同時,美國、歐洲相繼成為危機肇源地,也讓外界開始反思西方模式的局限性。
“后危機時代”,IMF必須尋找突破,并重返亞洲。但要化解與亞洲國家的恩怨,IMP無疑還需作出更多切實的努力,包括如何化解因指責人民幣匯率問題而與中國產生的齟齬。卡恩的這次圓桌會可能是一個個開始。以下就是這次圓桌會的對話摘錄。
IMF措施“加劇了民生的痛苦,這是事實”
《瞭望東方周刊》:IMF即將在韓國舉行“亞洲21世紀”高峰會以及在香港發布更新報告,這是否是IMF在修復因亞洲金融危機而與亞洲國家惡化的關系?
卡恩:是的,IMF以前處理亞洲危機的方式,被亞洲國家認為非常糟糕。
當時IMF代表團的日的是控制危機,清除這些國家金融領域的問題。那些措施當時其實不錯,也許正是韓國、印度尼西亞、泰國金融系統沒有太大問題并能夠順利度過危機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回顧過去,IMF的措施也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付出了昂貴代價,加劇了民生的痛苦,這也是事實。
現在想起來,IMF確實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吸取教訓。(我們從中得出的經驗之一,就是)我們在處理危機時,必須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因為這些解決問題、平定事態的經濟措施,對民眾來說總是艱難的,對弱勢群體來說尤其如此。
時代在變,我認為IMF也在變,我不會說今天我們的行事方式完美無缺,但肯定這一會議(“亞洲21世紀”高峰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反思過去,看看我們所做的是否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
我們做任何事,必須將相關國家的利益放在心上。我們未來要做的,就是和亞洲國家、亞洲機構共同努力,在韓國舉行的G20峰會提出“全球金融安全網”的建議,使其在下次危機發生時產生作用。
我們無法回避、也不想回避亞洲金融危機,回避我們受到的批評。
《瞭望東方周刊》:那你是否會在目前的歐洲國家問題上,采取比10年前對付亞洲國家更加寬松的做法?
卡恩:我想說的是不會寬松,假如你和羅馬尼亞、拉脫維亞、希臘民眾交談,我敢保證,那些在街上抗議的人們絕對不會說:“哦,IMF,你對我們太好了,我們都愛你。”
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因此,這不是更加寬松,而是相關政策會更適應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
在我看來,過去的錯誤方式使IMF現在能更真誠地解決好現在的問題。我們現在會說,“OK,我們來了,來和你一起解決”。現在是解決一大批問題的好時機,有時這些問題確實存在,IMF提供的也是正確方法,但如果不考慮到危機的特殊性,將會增加這些國家的困難,使事情變得難以控制。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這是一個真實的例子,但我不想具體點出是哪個國家——當時的IMF官員建議這個國家實行土地改革。我對土地問題是一個外行,不過我也認為,土地改革確實對這個國家有好處。但這和當時該國必須要應對的金融危機沒有關系,如果在當時推進土地改革,無疑會帶來一系列的政治問題。
因此,我們最終取消了這一建議,將關注點集中在當時我們必須采取對策的那些問題上。
未來5年,會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體系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政府不久前宣布,將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每天的最高彈性是0.5個百分點、你怎什評價中國的這一舉動?中國的做法是否會有效改善全球貿易失衡問題?另外,IMF贊揚亞洲促進了全球經濟復蘇,IMF也正在推進治理結構改革,你認為你未來的接任者是否可能來自亞洲?
卡恩:我們長期以來就認為,中國采取這樣的新政策其實符合中國經濟利益,這將促使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促進。因此,當中國政府采取這一行動時,我并不感到驚訝。中國政府是基于政策連續性作出的自我決策,我也不認為相關情況會迅速發生變化。
但我們仍然認為,人民幣存在低估,當然,現在開始采取的行動,有望糾正這一點。
我們的相關研究認為,人民幣幣值重估將有助于糾正失衡問題,但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也不會解決所有失衡的問題,遠遠不夠。所以,一些人認為貿易失衡的所有問題都來自人民幣失衡,這可能是錯誤的。
換言之,人民幣重估是朝正確方向邁進,我們會鼓勵這一點,但失衡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原因,光改變匯率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舉動值得歡迎,但我也認為,人民幣回歸市場正常價值還需要一段時間。
在IMF治理結構改革問題上,我非常贊同,IMF總裁必須來自歐洲的做法已屬于過去的時代。當我離開這個機構的時候,歡迎由來自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的官員擔任我的繼任者。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此前宣布,將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IMF是否會在未來5年考慮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留權(SDR)一攬子貨幣?
卡恩:這個問題值得考慮,但我同時認為,在人民幣沒有回歸到市場價值
或者說,在人民幣沒有變成浮動匯率貨幣時,將其納入一攬子貨幣有難度。希望這個過程越快越好,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越來越多的理由需要將其他貨幣納入SDR一攬子貨幣,可以首先從人民幣開始。
但有另外一點也必須考慮到:除了人民幣幣值問題以外,人民幣如何與市場融合,也會是個問題。
在某些問題上,歐洲國家應向亞洲國家學習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認為,IMF不應該只關注匯率問題,也應該關注發達國家的金融問題。許多經濟學家都抱怨,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IMF將太多資源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匯率,但忽視了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問題,IMF應該從中吸取教訓,你對此有何評價?
卡恩:確實這次危機起源于發達國家美國。假如我們有調查美國金融問題的可能性,我們也許在危機前幾年就發出警告說:“你們在次級貸款領域將會有大問題。”
但事實是我們沒有能力這么做。直到最近,我們的金融領域評估計劃——派出龐大隊伍去相關國家評估金融領域問題的計劃,還只是一個自愿的活動。
在本次危機前,主要國家中有兩個國家決定不參加這一活動,那就是美國和中國。不過現在美國和中國都同意了。
我想我們當前的責任所在,就是盡量發現可能會爆發的各種問題,不僅在美國,也在歐洲,在日本,當然也包括中國。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對中國進行評估,我們會努力對可能的風險發出警告。
因此我們正通過這次危機修復早期預警體系中的缺陷。在事后說你應該預先看到危機來臨,這很容易,但真正在危機爆發前就發出預測的人,卻少之又少。
如果查閱危機爆發前IMF發表的相關文件,其實也可以看到,我們有幾頁關于次級貸款市場的內容,其中就警告這可能會導致問題。但顯然,我們的聲音不夠響亮,這點我們必須承認。外界說我們在預測危機和發出預警方面做得不大好,這種評價不算過分。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看來,亞洲哪些發展經驗值得發達國家借鑒?不少發達國家現在面臨加快經濟增長、減少財政赤字的挑戰,而一些亞洲國家正好在高增長和低赤字上做得不錯,你認為有沒有好的經驗供歐美國家學習?
卡恩:事情恐怕沒那么簡單。從長期來講,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在于經濟迅速增長,但短期而言,我敢肯定的是,歐洲國家必須直接在財政問題上采取行動。他們不能只坐在那里等待經濟增長直接到來。
亞洲的增長方式,與其他國家的增長方式有很大不同,特別是歐元區國家。
現在不僅亞洲經濟增長迅速,其他地區也是如此,我兩個星期訪問了南美洲,秘魯的經濟增長率是7%,哥倫比亞是7%,巴西也差不多。但亞洲國家和美洲國家能說,你們歐洲國家的增長太慢了,你參考我們的做法吧?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現在的現實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個地區發展不同,需要將這種不同納入考慮;另一方面,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一條教訓,不管怎么分析,問題的關鍵是必須去做,去落實,這才是最困難的部分。
亞洲經濟迅速增長的經驗,不能直接套用在一些老牌發達國家,比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身上。
但我也要說,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就不能從亞洲國家學習。比如促進創新,改善增長環境,在這些問題上,歐洲國家可能確實得多看看亞洲國家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