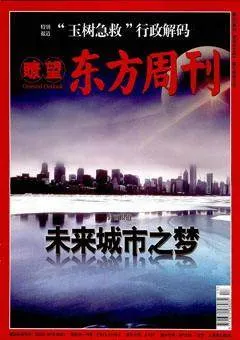流浪者的幸福和沉淪
自那部糾纏著厭世傾向和摩登主義情緒的《在路上》在美國出版以來,已經50多年過去了。凱魯亞克并不知道,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他的書在以另一種方式流浪——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心中,喚起了怎樣的內心瘋狂。比如芒克和彭剛組成的中國第一個先鋒派團體,就曾經希望以凱魯亞克為榜樣,在行走中向索然寡味的陳規陋習寫下挑戰書。
《巴黎之悟》是凱魯亞克的半自傳體小說,從中不難看出他的人生態度:在從巴黎到布列塔尼的流浪中尋找禪宗似的解脫。以正統的觀念來看,“垮掉的一代”的放蕩生活并不值得贊許,特別是吸毒、酗酒和同性戀。出于憤世嫉俗,他們穿一條破舊牛仔褲,走上了浪跡天涯的不歸路,并因自己不同凡俗的舉動而沾沾自喜。 毫無疑問,《巴黎之悟》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有著精神上的淵源。凱魯亞克在開始寫作《巴黎之晤》之前,就希望用一個名叫斯密德的敘事人來扮演堂吉訶德的跟班——傻里傻氣的桑丘潘沙的角色。堂吉訶德的冒險故事在他心中成了一種行走的范本。
那位以“頭腦有問題”而著稱的西班牙騎士一直是流浪史上的經典形象,他和忠實仆人桑丘·潘沙騎著駿馬,手持武器,周游世界,為了“將書中讀到過的游俠騎士們做過的事情也做一遍”,毫無緣由地干了一系列荒唐事。《堂吉訶德》的偉大絕不在于它是一出諷刺騎士的喜劇,堂吉訶德創立雄圖霸業的欲望使他成長為一位苦行之神——拓疆萬里,把充滿危險的旅途當成一種幸福。
《巴黎之悟》還讓人容易聯想到同樣以描寫長途跋涉而聞名的古希臘悲歌《奧德修紀》,以及它的現代版本《尤利西斯》。在這些經典中,旅途成了一種受難儀式,旅人像是迷途中的羔羊,在行走中體味著存在的價值。
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中也有一長段關于那位亂倫的繼父和他風姿綽約的繼女開車長途旅行的描寫,這是一次出逃,最終的結果是這位可憐的、因愛成恨的繼父成了一個殺人兇手。
和《洛麗塔》相仿,《巴黎之悟》也描述了一場自殺式的冒險,這種冒險雖未讓主人公在旅途中死去,但多年后他終于死于一場酗酒的狂歡。酗酒難道不是長途流浪的衍生物嗎?難道不是“垮掉的一代”基本生活方式的有機組成部分嗎?雖然他所熱愛的佛教不允許飲酒,但酒精似乎成了一個西方人幻想進入東方世界的一條捷徑——在狂飲之后任憑頭腦進行一種幻想的旅行,然后陷入短暫或者永遠的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