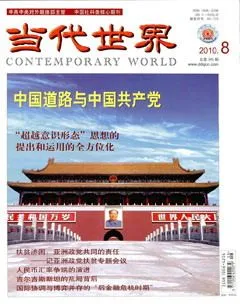“超越意識形態”思想的提出和運用的全方位化
編者按: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立足國情,縱覽天下,放眼世界,與時俱進,具有世界眼光,重視同外部世界聯系,善于同世界交往的政黨。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艱辛的開拓與創新,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逐漸成為黨和國家卓有成效的外交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地位不僅依靠其卓越地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功而獲得世界稱贊,也通過黨自身卓有成效的對外工作得到有力的提升。黨的對外工作的成就與經驗,是黨極為寶貴的財富。中國共產黨的對外關系史,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體外交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建部60周年前夕,本刊從第八期開始,開辟“黨的對外工作理論與實踐”專欄。邀請部分黨的對外工作的親歷者、參與者、見證者撥冗撰文,他們既從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戰略高度,也從黨的事業和國家總體外交關系的角度來分析黨的對外工作,既從親身經歷的黨的對外工作的重大事件,又從大量鮮為人知的重大細節,梳理了黨的對外工作的發展脈絡。總之,他們從宏觀與微觀視野,認真分析、總結了黨的對外工作的發展歷程及規律。
在新形勢下同不同意識形態政黨尋求對話和合作的一次突破
粉碎“四人幫”后,黨的對外工作糾正了“支左反修”和“支持世界革命”等錯誤作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逐步恢復和調整了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并開始同發展中國家民族民主政黨開展往來,同時也起步尋求同發達國家社會黨進行對話和聯系。而1984年5月德國社民黨主席兼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訪華則掀開了特殊的一頁。此訪不僅成為兩黨關系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而且對中國共產黨后來進一步拓展同其他社會黨類型政黨及世界各國左、中、右各類型政黨的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具有突出性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接待勃蘭特訪華過程中,首次明確提出“超越意識形態”的思想,并作為“開拓新的關系的唯一現實的抉擇”,具有劃時代的指導意義。
我有幸參加了接待勃蘭特訪華的全過程。此系他首次訪華,也成為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訪華。冷戰時期,勃蘭特主張推行“新東方政策”并把原蘇聯、東歐國家作為其政策的主要對象。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勃蘭特為何特別尋求與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接近呢?我以為,這絕非出自偶然,是有深刻原因的。
1、勃蘭特謀求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接近的時代背景
首先,國際形勢和時代主題發生了深刻變化。1969年勃蘭特出任總理后,大力推行“與西方合作、與東方和解”的“新東方政策”,他把對華政策擺在其東方政策之后,認為“聯邦德國及其盟國的命運取決于同蘇聯、東歐國家的關系”,而“中國不能代替蘇聯參與我們所肩負的歐洲與德國的任務”。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雖然世界仍處冷戰時期,但和平和發展問題日益突出出來,謀求裁軍、緩和和發展的呼聲日高。顯然,此時勃蘭特希望通過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接近,來推動在他看來中國這個“穩定和可以捉摸的因素”在世界政治中起更為積極的作用,中國既不為美蘇當牌打,又能同歐洲和第三世界國家一道形成一股新的世界輿論,以壓美蘇改變當時的對峙狀態。在訪華過程中他一再針對美蘇核競賽強調,“雙方應共同努力向美蘇施加壓力,促使他們座到談判桌旁來”,“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其次,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和對外政策調整。勃蘭特希望訪華是同他對華態度的變化相聯系的。而他對華態度發生變化的根本性因素是中國自身的變化,促使其對中國做出新的評估。勃蘭特訪華時表示,他本人和德國社民黨注意到了中國內外政策的變化,贊賞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正朝著已經確定的現實目標腳踏實地地前進”,“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穩定因素”。他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證明中國需要在世界上承擔適合中國的國情和重要性的責任,首先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作出巨大努力,再就是同第三世界一道,同時也是為了第三世界,奉行一種合理的政策”。德國社民黨一些重要人士也表示特別注意到中國領導人“重新估價”并希望了解各國社會黨類型政黨的講話,因此,他們很愿意同中國共產黨接觸,增進相互了解,加強合作。
上述背景為勃蘭特訪華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鑒于德國社民黨有上百年歷史,具有重要地位,而勃蘭特長期擔任該黨主席,并兼任社會黨國際主席和南北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把他率團訪華看作是進一步打開與社會黨類型政黨及社會黨國際交往的契機,是在不同意識形態政黨之間尋求建立適應時代變化的對話與合作的新型黨際關系的重大探索和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2、“超越意識形態”思想的首次明確提出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提出以“超越意識形態”來發展同德國社民黨的關系,無疑是雙方適應形勢、消除芥蒂、達成共識、謀求合作的結果。勃蘭特訪華,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思考和準備的。早在1978年,勃蘭特就曾表示愿以德國社民黨主席身份訪華,但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為了使此次訪華能夠實現,他特意派其主要智囊人物和被德國媒體稱為“小基辛格”的該黨聯邦理事會主席團成員巴爾于1982年8月為其訪華打前站。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邀請巴爾前來訪華。巴爾的使命就是要對中國的對外政策和改革開放情況作實地考察和了解,探詢同中國共產黨的接觸,從而為勃蘭特訪華牽線搭橋。訪華過程中,雙方開始時對提出兩黨關系彼此存在一些疑慮。巴爾說,他來的時候是帶著一個問號的,能否得到中方的響應沒有把握,經過晤談,這個問題消除了。他表示,他這次來華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兩黨之間的對話,他回國后要向黨的主席團建議繼續這種對話,相信主席團一定會贊成。中方也肯定了這次富有成果的會談,指出兩黨之間接觸向前發展了,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并闡明了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交往的“四項原則”。在巴爾訪華之后,德國社民黨主席團即決定同中國共產黨保持對話。第二年5月中國共產黨代表應邀訪德,并受到勃蘭特主席的接見,勃蘭特表示說,同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大黨保持關系是“一個很大的收獲”,并強調指出,雙方在一系列問題上有著接觸點或共同點,特別是在維護世界和平問題上,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中國共產黨代表轉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德國社民黨派團訪華的邀請,勃蘭特當即感謝邀請,并表示說,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派出德國社民黨代表團訪華。從巴爾打前站到中共代表訪德,使勃蘭特訪華的時機水到渠成。集中到一點,可以說雙方在時代的主題即和平與發展問題上存在著極大的共識。隨即,中國共產黨向勃蘭特主席發出了正式邀請,他欣然同意親自率團于1984年訪華。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勃蘭特親自率領該黨高級代表團于1984年5月28日至6月4日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予以友好熱情和高規格接待。勃蘭特主席本人也感到對他的接待是異乎尋常的,是原來沒有預料到的。他在來訪前,對中方將如何接待,多少有點摸不透。勃蘭特抵京后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實際接觸,特別是鄧小平同志出面會見和設宴招待,消除了他內心的芥蒂。他說,他早就想來中國,但真正落實花了一段時間,現在來到中國,感到很高興。胡耀邦總書記在為他舉行的歡迎晚宴上的祝酒辭更使勃蘭特在兩黨關系問題上吃了一顆定心丸。在這次講話中,時任總書記胡耀邦首先正面肯定勃蘭特多年來為維護世界和平和推動南北對話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指出當今世界上最根本的兩個問題即和平與發展問題,接著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強調恪守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同時,首次明確提出“超越意識形態”的思想。胡耀邦總書記在充分肯定雙方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強調指出,在維護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這些與世界各國人民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上,我們同勃蘭特先生為主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有不少共同點或相似點。我們愿意在共同點或相似點上同它們進行對話、交往和合作”。關于意識形態問題,他明確表示;“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歸根結底,應當由各國人民自己來選擇,分歧和差異不應當成為謀求這種合作的障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我們之間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了解和合作應當成為開拓新的關系的唯一現實的抉擇”。胡耀邦總書記闡述的中國共產黨關于“超越意識形態”的思想,得到了勃蘭特的積極反響,勃蘭特稱中國領導人的講話對他是個“很大的鼓舞”,他的收獲之多“超出預料”,這為互相充滿信任的合作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為中國黨與社會黨國際各成員黨之間的關系打開了渠道”,今后雙方可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發展作出共同努力。
“超越意識形態”思想得到全方位運用
“超越意識形態”思想是鄧小平同志關于“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思想的具體貫徹和體現。鄧小平同志在對中國對外政策進行戰略調整的過程中一再指出,觀察和處理國際關系問題不是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這方面的不同不應當成為發展國家關系的障礙,無論國家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都應當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些論述是對毛主席和周總理“和平共處”思想在新形勢下的運用和深化。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兩大陣營嚴重對峙,美國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脅之時,毛主席和周總理就強調“我們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并提出“不同的社會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合作也可以”的思想。毛主席1954年在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時說:“我們看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盡管思想和社會制度不同,兩個政黨或兩個國家,完全可以合作”。次年,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不僅精辟地闡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提出了對消除分歧產生良好效應的“求同存異”的方針。這正是作為處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關系的準則而產生的,對新中國創建和發展自己的新型外交關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當然后來在國際共運大論戰和文革期間,在中國對外關系中,曾一度出現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偏向,給國家和黨的對外工作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鄧小平同志提出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是對這一偏向的徹底糾正。
在拓展黨際關系方面,中國共產黨吸取同蘇共“老子黨”斗爭的經驗,在調整和恢復同各國共產黨關系的過程中,于1982年提出了著名的“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項原則”。到1987年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適用范圍得到延伸,提出在此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系,再到1997年,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適用范圍又作了新的表述,即“同一切愿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系”。這樣,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由當初作為處理意識形態相同的共產黨之間關系的準則發展成為也處理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之間關系的準則,即既適用于相同意識形態政黨關系,也適用于不同意識形態政黨關系。與此同時,隨著國際關系的演變和中國對外政策所作的及時調整,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適用范圍上也進行了向全方位的不斷拓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由最初作為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系的準則進而發展成為也處理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f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準則,既適用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關系,也適用于相同社會制度國家關系。歸根結底,說到一點就是“超越意識形態”(即“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思想已在處理同世界各國和各類政黨關系方面得到全方位的運用,從而使中國對外關系有了極大發展,無論是政府外交,還是政黨、議會和民間外交,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黨的對外交往也開始融入世界政黨政治,業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多層次的新型黨際交往機制。
(責任編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