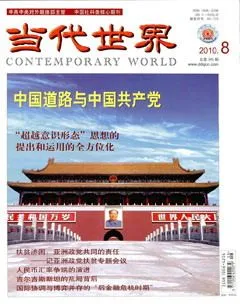論政黨政治的世界性與民族性
所謂政黨政治,可以廣義地理解為人們利用政黨這一組織形式從事的政治活動。自從世界上有了政黨,就有了政黨政治和政黨政治實踐。與此同時,政黨政治隨著自身在實踐層面的展開而具有了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特征。二者的相互交融和影響,正共同形塑著今天的世界。
政黨政治的世界性
二戰后,政黨政治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長足發展。同樣是政黨組織政治活動,所體現出來的政黨政治卻大不一樣。于是對不同國家的政黨政治進行分類、比較,就成為政黨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政治學學者們歸納出了無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區分,歸納出了極權政治、威權政治、民主政治等政黨政治類型。
在政黨政治實踐中,盡管各國政黨政治類型不盡相同、政治發展道路并有所區別,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世界性,政黨的現代化進程也得到了同步提升;隨著各國在經濟上的聯系日益加深,政治意識形態的共生和融合也漸次加深。例如,中國曾長期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特征之一,但隨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表,人們普遍接受了它并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準表述。而計劃調控與消除兩極分化這些原本是社會主義者提出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資本主義世界所批評和抵制的政策主張與社會目標,也成為當前眾多資產階級政黨的施政綱領。因此,可以說政黨政治在世界范圍內有了趨同性。
要對上述現象進行解釋并不困難。盡管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不一樣,甚至還有巨大差異,但各國民眾的利益需求卻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對生命的平等尊重、對人權的保障、對秩序的渴望、對自身處境的關切以及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民眾對政府的當然要求。因此,在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政黨屬性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無論其政黨政治模式是威權主義抑或民主主義,只要它能較好地回應民眾的上述需求,切實承擔起民眾利益代言人的政治角色,那么它一定可以獲得民眾的支持而上臺,或者維持原有的執政地位。
政黨政治與既往的皇權政治的最大區別在于,那種在皇權政治下“朕即國家”的國家與政府高度合一的關系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與政府關系的適度離散。在皇權政治下,反對政府意味著反對國家;在政黨政治下,反對政府和反對國家沒有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反對政府,最極端的情況是導致執政黨下野,新一屆政府上臺。這在一般意義上不會引發破壞性沖突,不會造成社會的巨大動蕩與國家國體、政體的存廢。可以說,世界各國性質不同的政黨及其政黨政治發展到今天,政黨被廣泛理解成是代表民眾掌握公共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的政治組織,是連結民眾與行政權力的橋梁與紐帶。而政黨政治,則相應地被廣泛理解成圍繞謀取和鞏固執政地位而進行的組織、動員、選舉、招募與施政等政治活動。并且,各國的政黨活動也大都遵循著相似的規律,維持著近似的結構,執行著幾乎沒有差別的政治與社會功能。
當政黨被理解成是民眾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政府權力為目標指向時,有學者將政黨分作代表全體的政黨和代表部分的政黨兩類。代表全體的政黨存在于一黨制國家。在這些國家,唯一政黨的存在對其他政黨有排斥性,其理論基礎乃是哲學上的一元主義世界觀。代表部分的政黨存在于兩黨、多黨制國家,其理論基礎則是哲學上的多元主義世界觀。無論在一黨制國家還是兩黨、多黨制國家,也無論這些政黨在主觀上的價值、利益取向如何,當它們作為民眾利益的代言人力爭掌握政權并引領社會發展時,它們都必須強調自己的公共性、民主性、正當性。
總而言之,無論哪一個類型的政黨,出于何種類型的政黨政治,其獲得政權的途徑也許有差異,但在其獲得政權后,其執政的基礎卻必須毫無例外地建立在民眾的同意這一現代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上。或者換句話說,政黨的所有功能,包括它所有的組織、機構、機關,其目標指向的就是民眾對自己的支持。這一點,普遍適用于世界上所有采取政黨政治的國家。這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黨政治的世界性。
政黨政治的民族性
政黨政治的民族性,是指在政黨政治的實踐過程中所形成并具有的民族特征。
如現代化國家可以分為原初的與后起的兩種一樣,政黨根據其產生的歷史背景不同,也可以大致分為適應型政黨與動員型政黨。原初的現代化國家,是指英、法等最早興起現代化的國家。當這些國家創造出了比農業生產力更高的工業生產力的時候,為了適應新的階層、階級的政治參與的需求,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政黨也應運而生。在英國,是在這些資產階級政黨的推動下,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發展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國家;在美國,是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愿構建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國家。這些國家都完成了國家構建意義上的從屈從的共同體到意愿的共同體的質的轉變,從而將人類的文明帶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被裹挾進現代化進程的那些國家,尤其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那些國家,當它們的智識階層睜眼看世界,發現了自己所處的國家與西方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結構上的巨大區別的時候,他們開始宣傳、動員本國的民眾為一個具體的政治目標如民族獨立、如民族復興、如共和國而奮斗而犧牲。于是,與適應型政黨的產生不同,在這些國家里,動員型的政黨開始出現。如中國共產黨、馬來西亞的巫統與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都是民族獨立運動的產物。
從政黨、政黨政治產生時起,它就有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就有了不同的民族性。這種不同,首先體現在政黨的目標上。在西方原初的現代國家,政黨是民眾利益的代表,是連接民眾與政府的橋梁和紐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政黨首先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工具。其次,這種差別體現在政黨的組織與意識形態上。在已經現代化了的西方國家那里,政黨的組織可以是松散的,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可以是多元共存的,民眾的政治參與是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為當然目標,以分散而有序的選舉及議會活動等體制內形式來實現的。而在殖民地半殖民的國家里,動員型政黨原本的非法身份必然要求其意識形態的立場分明,要求組織本身必須有嚴明的紀律,要求在體制外通過包括暴力手段在內的一切手段來實現政黨本身的政治目標。有學者又將這樣的政黨稱作國家構建黨。
動員型政黨的目標是執政,取得執政地位的手段是革命。正是在其動員與領導革命、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過程中,動員型政黨形成其命令一一服從的組織體系。在該體系中,黨員和每一級組織都被視作政策的執行者,其行為都受到嚴格的規范和約束,其成員的個性不被支持,也絕少受到鼓勵,其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是一種具有鮮明的集權特征的統治結構。動員型政黨的意識形態是為了取得政權服務的,因而,它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其批判的矛頭直指它所要推翻的那個政權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制度。它所使用的語言熱情并富有煽動性。緣于動員型政黨的這些特征,它很容易為富有犧牲精神的青年人所接受,為具有理想主義氣質的人所追捧。
與動員型政黨相比較,適應型政黨的目標也是執政,但其取得執政地位的手段主要是選舉。因此,此類政黨的工作是圍繞著“選舉”而展開的。或者換句話說,它所有的活動都是為了取悅選民,為了在選舉中獲勝而展開的。
為此,它需要在考慮民眾需求的基礎上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綱領,并向選民們兜售,以最大限度地獲得認同。于是,與動員型政黨取得政權主要使用的是“暴力”不同,適應型政黨主要使用的武器是“說服”;與動員型政黨所形成的那種命令——服從的組織體系不同,適應型政黨形成的是一種溝通一一說服的組織體系。在這樣的組織體系中,其每一級組織和黨員,都被因視作組織的主體和平等的成員而受到尊重。這類政黨沒有嚴格的紀律規范,甚至沒有紀律。在組織內部,組織成員不僅進退自由,并且鼓勵個性。因為越是與眾不同,才越會吸引選民們的注意。這類政黨一定程度上帶有“聯邦制”下自治主體的某些特點,有明顯的自主性、自助性。其權力運行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雙向度,是每一級組織的權力首先來源于這一級組織的所有成員的授權,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對組織成員有所規制。與動員型政黨的統治結構相比,它是一種治理結構。適應型政黨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其目標指向也是為獲得執政地位服務的。但與動員型政黨的意識形態不同,它盡管有批判,但這種批判并不指向其所在國家的政治制度。
綜上所述,政黨在形成以后,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逐漸長成了今天的這諸種模樣,并相應地形成了不同的政黨政治系統。
當一些動員型政黨取得了執政地位并執政以后,由于歷史的慣性,它們將動員型政黨的特征帶到了執政過程中,使其執政打上了命令一一服從的烙痕,具有了集權、威權的特征。其一元主義的世界觀所導致的對國家政治資源的壟斷,也被許多人認為將從根本上損害一個相對寬松、自由、多元和理性的政治生態的形成。一些國家、地區政治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也表明,在一黨體制、黨國體制下,作為表達民意、實現民主的工具的該類政黨,在其向現代化進軍的號角聲中,正不幸背離現代化的目標而使它們所在的民族重新走上它們曾經流血反對的被奴役的道路。一句話,一些動員型政黨尚沒有恰當地認識到政黨與民眾與國家公共權力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或者盡管認識到了,但在政治制度設計中還沒有理順這種關系。這種特征,可以看作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政黨政治民族性最為突出的表現。
中國在自辛亥革命至今近百年的政治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這一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同時也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各民主黨派完全平等的參政議政地位,是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建國以來,中國在內政外交國防、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證明這一制度適合中國國情。在這一制度中,既可以看到政黨政治世界性的影子,也可以發現政黨政治民族性的特征。而能否利用自身資源,著眼于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和既有的政治架構,在已取得的經濟成就的基礎上,構建出既超越傳統又與政黨政治的世界性潮流相一致、與中國現代化相適應的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的政黨政治,不僅對于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和其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是至關重要的,對于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也是具有特殊意義。
(責任編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