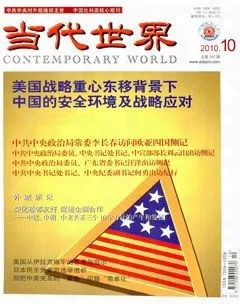外城瑣記
八、九月間,有機會出訪了鳥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和撒馬爾罕,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和阿拉木圖,土耳其的安卡拉,馬其頓的奧赫里德,阿爾巴尼亞的地拉那。
興趣和習慣使然,每到一地,總要隨手記下一些零零碎碎的見聞和思考,權作“外城瑣記”。
塔什干的表情
一座城市就是一個巨大的生命體。他有性格、有精神,當然也有表情。要了解一座城市的性格、精神,需要深入、需要時間,需要仔細體味和感覺。可一座城市的表情是外在的,就像看一個人的臉色,方便得多、容易得多。塔什干之行是短暫的,因此也只能看看他的臉色和表情。
塔什干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亞古城,去年剛剛舉行過2200年建城紀念。塔什干,烏茲別克語的意思是“石頭之城”。悠久的歷史,再加上這硬邦邦的名字,想象中的塔什干應該是一副滄桑、老態、冷漠的神情。可當你走進這座城市,看到的、感覺到的,卻與想象的完全不同。
塔什干是一座花園式的城市,寬闊的街道被云團般的樹木籠蓋,路邊開滿了五顏六色的鮮花,林間空地是青翠碧綠的草坪,淡黃、乳白的建筑掩映在郁郁蔥蔥的樹林中。本來,城市的主體應該是建筑,而塔什干的主體卻成了花草樹木。一座被花草樹木搶了風頭的城市,給人的印象是生態、自然,青春、靈動,充滿生機與活力。
我有個習慣,每到一座城市,總愿到商鋪林立的鬧市去體會市井氛圍,可作為有二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塔什干似乎沒有鬧市。即使是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也很少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很少聽到喧囂嘈雜的市聲。三三兩兩的行人,沒有匆匆的腳步,沒有焦急的面容,一個個漫不經心,那么閑散、隨意、輕松。
浮躁是當今時代的一大特點,浮躁的世界,浮躁的社會,浮躁的人,城市更成了集浮躁之大成的浮躁場。經常有最高大樓、最大廣場、最寬馬路竣工的捷報,最奇最隆最“雷人”建筑落成的消息,城市間無休止地“爭最”競賽越演越烈。到處是密密麻麻的“水泥森林”,滿眼是閃亮的“玻璃海洋”,還有泛濫成災的花花綠綠夸張的廣告牌、霓虹燈,浮躁的病毒在不斷污染城市、侵蝕城市。
本來,城市應該是人類向往的家園。希臘先哲說過,人們到城市是為了生活,居住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生活。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可浮躁,使城市失去安逸、溫馨,失去親和、魅力,甚至使人們不得不逃離城市。而在塔什干,似乎看不到浮躁,聽不到浮躁,感覺不到浮躁。這是一座沉著、淡定、理智的城市,雖然看上去多少有點冷清,但使人感到的卻是一種令人陶醉的幽靜。這可能與我們整天生活在熱鬧和浮華中有關。
當要離開塔什于的時候,思緒中突然萌生出八個字:秀美優雅、從容可親。我想,這不就是這兩天我看到的塔什干的城市表情嗎?
撒馬爾罕的尊嚴
世界上的許多名城都和名人有關,或城因人而揚名,或人因城而發跡。烏茲別克斯坦的古城撒馬爾罕就與帖木兒緊緊聯系在一起。
帖木兒是十四世紀烏茲別克的英雄。他傳承了成吉思汗的遺風,英勇善戰、金戈鐵馬、橫掃天下,在西起土耳其,東到印度、阿富汗的廣闊疆土上,建立了強大的帖木兒帝國。都城就建在他的故鄉撒馬爾罕。帖木兒把從各地掠奪來的財富聚集到撒馬爾罕,建造了富麗堂皇的宮殿。他把從各地俘虜來的精英聚匯到撒馬爾罕,文學藝術、天文歷法、科學技術一度得以繁榮。撒馬爾罕成為富甲天下、萬商云集、人才薈萃的世界名城。
因為有了帖木兒,才有了帖木兒帝國。因為有了帖木兒帝國,才有了帝國都城撒馬爾罕。帖木兒為撒馬爾罕帶來了繁榮發達,帶來了榮耀財富。帖木兒當然成了撒馬爾罕的魂魄和象征。
任何帝國都不可能亙古永恒。隨著帖木兒帝國的沒落,撒馬爾罕也衰敗了,昔日的榮光成了歷史的煙云。帖木兒死后,按照他的遺愿,葬在了他生前為其已逝家人修的家族墓里。撒馬爾罕人世代守護著他的陵墓,年年祭拜他的英魂,因為他是撒馬爾罕人的驕傲,撒馬爾罕人把他視為他們的神靈。每有游人到撒馬爾罕來,必定要謁拜帖木兒陵。帖木兒家族陵墓,自然成了撒馬爾罕的尊嚴所在。
然而這尊嚴也曾遭受傷害。烏茲別克斯坦朋友給我們介紹了發生在上世紀的一段故事。蘇聯時期的1941年,蘇聯考古學家為了考證帖木兒家族墓的真偽,要掘墓驗尸。聽到這樣的消息,撒馬爾罕人憤怒至極。挖墳掘墓對于任何一個民族,都是極大的侮辱和不敬,更何況帖木兒是他們民族的英雄,是他們引以為榮的祖宗。他們反對、抗議,但未能阻擋帖木兒墓遭掘的厄運。巧合的是,在掘墓第二天,希特勒發動了對蘇戰爭,災難降臨在蘇聯的土地上。當地的百姓也因此有了說法:這是掘墓帶來的災難。當然,這種因果報應之說是牽強的,更何況希特勒的逆行是對全人類犯下的罪行。但對撒馬爾罕來說,“報應”之說似乎挽回了些許尊嚴,盡管這尊嚴只是心理上的——使他們受到傷害和踐踏的心得到了一絲安慰。
現在的帖木兒家族墓已經修葺一新。這是一座磚石砌成的伊斯蘭風格的建筑,雄偉壯觀、富麗莊嚴,藍色穹頂高高升向天空。烏茲別克斯坦人崇尚象征權威和高尚的藍色,只要看到那陽光下閃著寶石藍光芒的穹頂,人們就自然產生了敬畏、震撼和至高無上。過去,對人們常講標志性建筑,不大理解。什么是標志性?是大,是奇,還是有什么特殊功能?看到帖木兒家族陵墓,有點明白了。一個能夠代表一座城市尊嚴的建筑,當然就是標志性建筑了。看到帖木兒家族陵墓就知道這是撒馬爾罕,看到金字塔就知道這是開羅,看到埃菲爾鐵塔就知道這是巴黎,看到天安門就知道這是北京。而且每每看到這些建筑,就會使你對他們所在的城市肅然起敬。
一座城市需要尊嚴,需要世界對他的尊重,需要外界關注他的存在。就像一個國家、一個人需要尊嚴一樣,需要堅守自己的國格、人格一樣。
阿斯塔納的精神
到阿斯塔納來,不得不用震撼和驚嘆來表達對這座世界上最年輕首都的感受。
飛機降臨阿斯塔納,已近午夜。夜幕下的阿斯塔納依然燈火通明,霓虹燈把高樓大廈裝扮得美輪美奐,激光燈五顏六色的光柱在夜空中游動,給人以如夢如幻的感覺。第二天清晨,推開旅店的窗戶,看到的是一幅現代都市的畫圖。縱橫交錯的陰蔭大道,波光蕩漾的人工湖,郁郁蔥蔥的園林,花團錦簇的廣場,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那一座座造型各異的摩天建筑,像是剛剛出土的新筍,光鮮、新穎。奇特。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青春、現代,敞亮、大氣。看到這景致,有誰能不由衷地贊譽和感嘆?
阿斯塔納,曾經是“天蒼蒼、野茫茫”的荒原,過去叫阿克莫拉,意為“白色墳墓”。蘇聯時期,赫魯曉夫曾動員過一批熱血青年來墾荒,他們滿懷改天換地的豪情壯志奔赴這里。但后來,青年們的熱情被惡劣的自然環境給消磨掉了,美麗的夢想變成泡影。
哈薩克斯坦獨立后,為了推動北部地區的發展,199’年決定把首都從阿拉木圖遷到阿斯塔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立志要把新首都建設成哈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建設成全世界矚目的一顆明珠。短短十多年時間,荒原上神話般地崛起一座令人驚奇的現代化都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有過一些國家遷都,我曾到過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巴西的巴西利亞,和阿斯塔納相類似的是,他們都在荒原上建城,在一張白紙上畫畫,但比較起來,阿斯塔納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
阿斯塔納確實創造了奇跡,創造了令人振奮的奇跡。哈薩克民族是草原民族,血液中流淌的、基因里延續的,是不畏艱苦、不甘現狀的精神和意志。哈薩克斯坦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年輕國家,一直想在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建設新首都自然成了他們實現自強和崛起的象征。他們有這樣的信念,要建就要建最好的,建讓人一看便眼睛為之一亮的。他們幾乎把罔家的意志、民族的精神,都寫在了這座新城市的規劃和發展上,這里的每一個建筑好像也都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政治使命。陪同參觀的當地官員給我們介紹,這里的每一個建筑都經過了納扎爾巴耶夫的親自審定,不少建筑本身就來自他自己的創意。哈薩克斯坦的老百姓說,納扎爾巴耶夫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現在阿斯塔納就是他的兒子,他將他的理想、志向、才情,都傾注在新首都的建設上。
阿斯塔納是倔強的、傲氣的,他似乎在向世界宣示,我年輕力壯,我能干、我能行,世界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到,世界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有人說,建筑是城市靈魂的寫照。我看,作為首都的阿斯塔納應該是哈薩克斯坦民族和國家精神的寫照。
阿拉木圖的憂傷
從阿斯塔納乘飛機一個多小時到阿拉木圖,兩座城市的反差太大了。比起阿斯塔納的新潮時尚、鮮亮現代,阿拉木圖確實有些陳舊、落伍了。依然雄偉的建筑物像褪了色的老照片有點泛黃,依然高大的古樹似乎有點萎靡困倦。太陽是燦爛的,但城市上空卻灰蒙蒙的,整座城市籠罩著一種淡淡的憂傷。
曾經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現在不是了,這對于一座城市來說當然是一種失落,地位的失落、榮耀的失落、名氣的失落。就像一個人,曾經有的政治職位、社會名分、職業頭銜突然失去了,無論是自己的感覺,還是別人的眼神,不習慣、不自在肯定會有的。不過,有機會同阿拉木圖的市長、副市長接觸后發現,他們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平和心態,有一種令人欽佩的冷靜和清醒。他們認為,首都遷走了,發展機遇來了。阿拉木圖政治中心的地位沒了,但經濟中心、科技文化中心的優勢和地位更凸顯了。他們的雄心壯志是要把阿拉木圖建成中亞地區的金融中心、科技文化中心,建成一座國際化的都市。在他們看來,首都遷走了,反而城市的定位更清晰了,發展目標更明確了,優勢特色更突出了。這就好像一個人身兼數職,貪圖的太多,很可能高不成、低不就,一座城市被賦予的責任太多,很可能是一座四不像的城市。
記得著名作家柯巖去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是誰》,從自己的經歷講起,告訴人們一個作家要有出息,一定要搞清楚“我是誰”,要有自知之明,找準自己的位置。其實,一座城市也一樣,既然不是首都了,就要坦然面對720a5d6751386c36d069c71b730a9da9,放下身段、調整心態,找準位置、輕裝前行。阿拉木圖市長們的可貴之處也正在這里。打開城市發展史,可以看到,因為資源的枯竭,因為災害的侵襲,因為交通的變遷,因為政治中心的轉移,因為戰爭的摧殘……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曾經有許多耀眼的城市,或衰落或荒蕪或湮滅。而也有一些城市,無論什么變故,都沒有阻擋他的發展、繁榮,依然熠熠發光、不老不衰。原因在于他們能順應歷史、轉身俱進。我想,阿拉木圖可能會是這樣的城市。
安卡拉的特色
有人問我,安卡拉有什么特色,我一時語塞。想了想還是做了似是而非的回答:沒有特色可能就是安卡拉的“特色”。
城市其實和人一樣。有的城市只要你看上他一眼,就會終身難忘,而有的城市只要你離開他,就再想不起他的模樣。安卡拉就屬于后一種。原因很簡單,安卡拉沒有吸引人眼球的看點,沒有讓人眼睛一亮的風景,沒有動人心魄的建筑,也沒有給人以啟迪和思考的故事,一句話,沒有鮮明的個性和特色。
安卡拉是座四面環山的山城。照理說,這樣的城市一定會更生動、更鮮活,更有層次感、更有立體感。可是,當我來到城市的制高點——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陵的平臺上,俯瞰全城,看到的景色卻有點失望。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占滿了一座又一座山頭,而建筑又多是方方正正的土黃色板樓,像是一個模子里扣出來的標準件,既不講造型,又沒有色彩,呆滯失神、灰頭土臉。
按說安卡拉既有悠久的歷史,又是國家首都,是有四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其名氣應該是很大的。可真要隨機搞一次調查,能叫出來安卡拉名字的人,我想不會很多。許多人都以為伊斯坦布爾是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爾太有特色因而名聲太響了,而安卡拉卻太一般化、“大眾化”了,其知名度自然不高。
經常可以看到媒體批評,說我們的城市建設太趨同、太沒有特色,到過的若干城市都似曾相識,千城一面成了城市的通病。其實,比較世界上的城市,雷同者、相似者居多,真正有特色、有個眭的是少數。有人拿歐洲的城市與我們的城市做對比,結論當然是人家如何如何有特色,我們如何如何平庸。說實話,依我走過的幾十座歐洲城市看,多數也大同小異。從城市的布局格調,到城市的色彩,差異無幾。市政廣場、放射狀的道路、街心公園,還有教堂、畫廊、大劇院、音樂廳、市政廳、皇宮……仔細了解,不少城市的同類建筑,就是一個設計師設計的。打開幾年前歐洲之行的攝影集,很難分清哪張照片是在哪個城市拍攝的,因為作為攝影背景的建筑似乎沒有什么大的不同。很像是前些年我們看外國人,個個都是藍眼睛、大鼻子,沒有多大區別。
歐洲大規模城市建設是在工業化的十七、十八世紀,有點像我們的現在,都想一天建一座羅馬城。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難免會出現城市間的模仿、建筑間的借鑒,甚至抄襲。一個面孔的城市,克隆式、山寨式的建筑就不足為奇了。誰要是有興趣,可以做一次調查,看看全世界有多少差不多的凱旋門、差不多的名人紀念堂(陵)。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堂、清真寺,又有幾個是自成風格?“領異標新二月花”者少之又少。
文明是多樣的,城市當然應該是多樣的。城市的價值在于有自己的特色,當然這特色不單是膚淺的表面化的建筑和景觀,更應該是他的內涵、他的歷史、他的文化。城市建筑可以突擊,可以用運動式的“大躍進”速成,而城市的文化、城市的內涵要靠時間、靠積累。
因此,人們在城市建設中,要注意城市的特色,而突出城市特色又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簡單化地在看得見的建筑和景觀上做文章,應多想一點深層的鋪墊,多有一點長遠的考慮,多做一點看不見的功夫。
奧赫里德的責任
奧赫里德市是馬其頓的旅游勝地,坐落在被譽為巴爾干明珠的奧赫里德湖畔,城因湖而建,因湖而興,也因湖而得名。每當朝陽初升或夕陽西下,透明如鏡的湖面上便會倒映出城市的身影。有人說,馬其頓有兩座奧赫里德城,一座在湖岸的山林中,一座在清澈的湖水中,山林中的奧赫里德幽靜秀美,湖水中的奧赫里德靈動嫵媚。
其實,還有一座奧赫里德城,那就是被歲月的塵土深埋于地下的奧赫里德,而馬其頓人更樂于、更熱衷向游人夸耀和介紹已經考古挖掘而再現的奧赫里德古城。因為古城是馬其頓悠久歷史的記憶,是馬其頓曾經輝煌榮光的見證。這里有記載馬其頓民族源流的“家譜”,這里有馬其頓未曾漂流走的基因,這里有馬其頓精神生命永生的、最真切最堅實的依憑。
馬其頓國家文化部的官員帶我們參觀了正在挖掘的古城遺址。一位白發飄逸的考古學家向我們介紹考古發掘的成果。公元十世紀,第一個斯拉夫馬其頓國家誕生,首都就在奧赫里德。再追溯到公元前300多年,叱咤風云的亞歷山大,也是從這里出發,橫刀立馬、遠征亞洲、跨越北非,建立了威震天下的馬其頓帝國。幽默的馬其頓專家說:“要不是喜馬拉雅山阻擋,很可能我們就是一家人了。”可不是,亞歷山大占領了印度、阿富汗,已經是我們的鄰居了。當然這是玩笑,但玩笑中也透出馬其頓人的自豪:我們的祖先也曾威風過。
作為一個獨立只有十幾年的年輕小國,現在的馬其頓格外看重自己的歷史、格外珍視自己的歷史,當然在情理之中。就像一個剛剛立足社會的小青年,常常要抬出家長或祖宗來壯膽或抬高身份一樣,作為一個年輕國家,悠久輝煌的歷史當然足可以增加立足世界的分量,因此,他們有必要從逝去的歷史中尋覓曾經有過的自豪,尋覓重新崛起的自信,尋覓支撐他們奮勇前行的力量。
這重任當然要落在考古學家們身上,也落在奧赫里德城的身上。唯有考古學家有能力、有智慧揭開馬其頓歷史的真相,而也唯有奧赫里德城有資格、有地位足以證明馬其頓歷史的真實,足以證明馬其頓從哪里走來。行走在奧赫里德古城堡的街市上,似乎感覺到滄桑的古橡樹、斑駁的老建筑,還有腳下已經磨去棱角的鋪路石,也都承載著一份沉重的責任,那是國家的責任、民族的責任。
地拉那的色彩
地拉那是亞得里亞海邊的一座小域,高樓大廈不多,名勝古跡不多,算不上繁華,也算不上冷清。但地拉那倒是一座有特色的城市,他的特色在于他的色彩。
歐洲的城市多以土黃、乳白為基調。地拉那沒有主色調,赤、橙、黃、綠、青、藍、紫,可以想到的顏色都被涂抹到城市的建筑上。有的一座建筑是一種顏色,也有的是一座建筑多種顏色,而且被涂抹成多種多樣的圖案,像是被披上了五彩衣衫。
第一次到地拉那來,是有種新鮮感、親切感。五顏六色的建筑,在巴爾于柔和陽光的照射下,鮮亮靈動、浪漫時尚,似乎走進了一座童話樂園。世界是多彩的,城市當然也應該是多彩的。有人說,城市是建筑的家園,依我說,城市更應該是色彩的家園。色彩是城市建筑最偉大的元素,色彩給了建筑以生命的神韻。如果建筑乃至整個城市失去“最偉大的元素”和“生命的神韻”,空有一個外殼,那還有價值嗎?還會有魅力嗎?還會迷人嗎?
據說地拉那的色彩與地拉那的市長有關。地拉那市長是一位有很高藝術造詣的畫家。畫家實際是色彩專家,以玩色彩為生。十年前,畫家市長一上任,便力主要給這座城市增添色彩。其實,市長是把心中的色彩,連同他的弘愿和理想一起,描繪在城市的建筑物上。他把他的城市當做一幅巨大的畫布,城市的色彩便成了他最生動的作品。
當然,也有人非議地拉那的色彩,城市被涂得大紅大綠,是否俗氣、土氣了。我見到市長拉馬,也提到這個話題,拉馬先生卻不以為然。藝術本身沒有土氣、洋氣,雅氣、俗氣之分,只有人們對待藝術的觀念、立場、標準之不同。只要可以給人帶來愉悅、帶來美感、帶來健康就好。
可也是,離開地拉那,色彩依然是最深刻、最美好的記憶,而其他包括色彩覆蓋下的建筑,似乎都沒了印象。由此我想到,是否可以多選一些藝術家來做市長,好使城市多一些藝術元素,多一些藝術氣息,多一些藝術品位,使城市更美、更宜人,也更有文化、更有魅力。如果不好做到,起碼可以提倡我們的市長們走近藝術,增加一些藝術素質、藝術修養,這對我們的城市肯定會有益的。
(責任編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