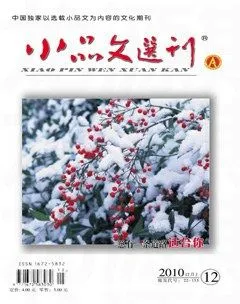大師
我遇見他總是在會議上,坐在一個角落里,很少說話,不到他發言的時候,兩條腿抖個不停,仿佛在抽風,表情激動,蓄勢待發,搞得坐在他旁邊的人也很緊張。到他發言,總是很吃力的樣子,手揮舞著,眼睛斜瞪,眼白放大,仿佛正在一口深井里面提水,而水太深,太重,提不起來的樣子。令人很擔心,覺得他的話非常重要。但他最后說出來的總是語焉不詳、雞毛蒜皮、小題大做、不得要領,會議討論南極洲是否會融化的重大問題,他卻說小區里面沒有花園也是不對的,浪費時間,被主持人中途打斷。大多數時候他保持沉默,極力控制著渴望發言而不得導致的抽風癥狀,他有很多話要說,但堅強地自我克制住了。他在會議小休或者去洗手間的時候會突然爆發,嘩拉拉地說起話來。他的口音非常奇怪,似乎躲在喉結這塊巖石下面,原始的聲音,沒有一般受過發聲訓練的人的那種磁性、自信,像是非洲人在說話,尖利而又嘶啞低沉,不愿意聲張似的,聽上去口齒不清。某個有著播音員嗓門的同事教育他,打開你的喉嚨,把聲音放出來,那人公雞般地夸張地伸縮著嘴巴,這樣,這樣!我從來沒有在會議以外的場合看見過他,我們總是一起開會,會議結束后友好地告別。
我一向對那些在會議上不說話的人報有好感,總覺得真理是在這些人的沉默里面,我們心有靈犀地相視而笑。我總是對每一個落日懷著好感,而對邁步中天、滔滔不絕的輝煌日頭沒有感覺,當太陽們發言的時候,我總是躲得遠遠的,鉆到世界的陰影堆里。只有在冬天,在寒流之后,我才喜歡那頭頂的太陽,它已經變得暖暖的,不是那么聲色俱厲了。
忽然有一天在灰色的大街上看見他,他正在金碧路的人行道上向東走去。這是我在國家會議之外第一次看到他。他走路的樣子真像一位大師。灰色的象,緩慢地移動著,似乎喧嘩的大街不過是一座安靜的森林。他身體里面裝著一塊石頭,神情茫然,看著一切而不是某一點,顯然已經靈魂出竅,神游物外了。這頭野獸聽不見汽車的鳴笛,看不出紅燈的警告,茫然地走下人行道,在眾目睽睽之下,穿過了車流,他那置身度外的神情就像盲人聾人或者已經退休但習慣性的超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