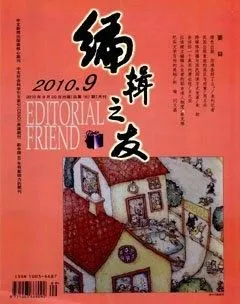紀實文學寫作的奧秘
作家應該有一種唯物的、實事求是的立場
閏文盛(以下簡稱“閆”):趙老師您好,《尋找巴金的黛莉》一口氣讀完了,許多感覺一擁而至。按照雷達先生的說法,此書屬于那種“一粒沙可見大干世界”的好例子,由7封信引出了大滄桑、大境界、大悲憫。現在我首先要談的是,您在這本書中正視了早期巴金的生活和創作,提到了那些客觀存在的、不容人回避的思想成分對于他本人以及眾多的巴金讀者所產生的作用等等。這些東西是這本書的有機構成,也正是因為有這些東西,才構成了一個真實、立體,不斷地反省自身、完善自身的完整的巴金。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這些“本應看作中華民族先進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國以來,艱難探索祖國新文學道路的一部分”的“精彩紛呈”之作,卻因為某種因素被研究界忽略、拋棄了。而在《尋找巴金的黛莉》中,您的表現也是較為節制的。可以就此展開談談嗎?
趙瑜(以下簡稱“趙”):這個問題可以這樣理解,雖然說它是從巴金的早期創作引發的,但實際上并不單單針對巴金一人,我自己也不是針對巴金研究而提出的。應該說,它是非常普遍的一種“揚棄”。我們的文學在一度時期走了一條政黨文學的道路,因此在整個百年來現代化探索的歷史當中出現的許多思想成果和文學成果,多有類似的傾向,譬如說因人廢文,以綱領性的宣傳話語切分我們的現當代文學史,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但這樣的東西無疑又是偏頗的,它不可能是整個現當代志士仁人在思想探索和文學探索方面的全貌。我在這本書里,只是通過這個現象說了說我自己的想法。
閏:《尋找巴金的黛莉》有一個關鍵部分,是關于家族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評論家陳曉明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認為,晉文化的底蘊和晉人品性的書寫,是這部作品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可見趙瑜筆法老到,恰是毫無遮掩的紀實筆法,讓讀者體驗到晉文化的特有韻味。當然,更為深層的還在于書寫晉人的歷史命運。山西在近代中國一度是經濟和金融的中心,想想當年平遙古城,多少大戶人家,如今只剩下一些殘垣斷壁。山西在近代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中的敗落,是中華民族令人驚懼的歷史變異。現在,尋找黛莉的過程正是這種歷程的艱難展開。尋找黛莉的故事攜帶出來的,是山西幾個大家族在20世紀的動蕩波折。尋找黛莉,幾經曲折,分析的卻是20世紀上半期山西的歷史,也是中國現代動蕩不安的歷史。中國的大家族卷入了生產、戰爭、政治、暴力,無一幸免,歷經事件的沖擊,或分崩離析,或顛沛流離,或茍全性命。這部作品最讓人震驚的主題隱而不現,卻時刻要爆發出來,那就是山西的也是中國的那些大家族,在20世紀無休止的戰爭動亂中的崩潰與滅亡。其實寫家族的書很多,當代小說方面,著名的有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家族》等等,您在寫這部書時,最先考慮的是什么?就是說,動筆的時候已經有了結論,還是在書寫中間才慢慢強化了這一部分主題?另外,這本書中還寫到了抗戰,寫到了閻錫山,寫到了土改,寫到了有追求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走向,這些主題非常駁雜,涉及的知識點很多,在這方面您刻意做過功課嗎?
趙:寫這本書時,我就拿著一個普通的筆記本,裝在書包里面。因為這個作品本身的資料并不需要帶多少。有一個巴金的信的復印件,不過是7張紙,還帶著一兩本巴金的傳記之類的書。這樣走到哪兒寫到哪兒。譬如,我記得去東北參加筆會,去到了一個導彈基地,看了頭一天以后,第二天我就不去了,自己在房間里寫了一天。回到北京和山西以后,也是在這個筆記本上寫。寫完以后要增刪一下,核準一下時間、人名、國共兩軍將領的名字。所以總的來說,不是刻意為之,對于家族的同情和哀怨,對于抗日的悲壯,對于土改的過激做法,都是平時積累的,當遇到了這些問題時,就很自然地把儲備的東西調度起來了。當然,也包括對于20世紀30年代文壇的一些基本認識。譬如說“兩個口號”之爭啦,魯迅怎么跟人鬧矛盾啦,以前一度時期我特別愛看這些,對基本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最后確鑿一下就行了。這里面不會有什么臨時性,惡補一下晉綏土改史,也不太需要。像閻錫山抗日,忻口作戰,我原先就曾經想過弄一個電影。當然,這里邊還提到一些東西。一開始,因為涉及家族問題,涉及寧武,涉及閻錫山抗日,也就不得不寫一寫。黛莉一家跑哪兒去了?因為什么跑了?都得說清楚。其實我自己輕易不愿意涉及這些話題。我愿意認真去處理這種題材,但是目前我還沒有寫作到山西的更深層次的許多問題。另一方面,因為這部作品不是展開來研究土改,只是為了說明黛莉這個家族在寧武活不下去了,說明這樣一個背景,也就節制了。將來要專門寫土改的書的話,可以由更多的作家來完成。我覺得,作家應該有一種唯物的、實事求是的立場。現在看來,如果說《尋找巴金的黛莉》還不錯的話,除了曲折的故事外,實事求是的歷史觀也在發揮作用。僅僅是這樣一個凄婉的故事恐怕還達不到現在這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