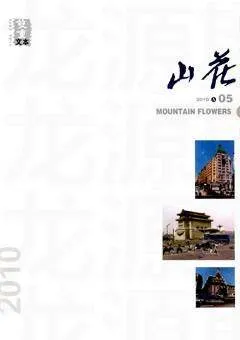仿佛快感那么快(外四首)
仿佛快感那么快
仿佛快感那么快,多少有些
痛快和愉快:一滴水落下
依舊是水,水滴石穿,沒有懸念
看見它,從潛伏的四季中現形
那些鮮花,一朵,一朵,一朵
慢慢枯干:鳥在結尾處消逝
穿著燕尾服的回憶
突然回頭,嚇了你一跳。
左耳的旅客,搭乘右耳的火車
句子里,死去的百足蟲在動
紙上雜草叢生。
鏡子魂飛魄散,被一塊石頭
深深覆蓋:它的虛幻性。
一千張臉孔隨風漂移
臉上的樓梯,咯吱吱地響
從明亮到幽暗,一天變成一條
短促的走廊,走過去
卻有一生那么長。少女輕輕
叫一聲,一個少婦
便徹夜難眠:風景畫里的
蝴蝶是輕盈的,夏天熱得無骨
冬天冷得凋謝。你站在那里
你是時間的活標本。
靜靜地發呆。兩臺發報機
向對方發送漩渦,嘀嘀,嗒嗒。
沉淪,但不曾深陷。鬧鐘里
秒針跳了一下,把你帶來的消息
轉述給分針:瞧,這個人
用乒乓球的彈性反反復復
你聽,你看,你默默無語
門關著,睡眠者醒來
嘴里長出一個下午,給衣服
穿上身體,給手套戴上手
給夢一根青藤,讓它們
走,爬,互相撫摸
讓動機動起來,一連串的響聲
在瞬間變空,你翻動書頁
上面沒有一個字
窗外:扛著鐵鍬的人
在挖一棵樹,挖一條暗道
故事這么漆黑:女房東
關掉走廊里的燈,你
在墻里埋下一張臉
你的嘆息留下一個嘆號
你如何和我一樣在夏天
你如何和我一樣,在夏天
突然想起雪:亂哄哄的,房間里
都是房客,他們玩牌,他們賭
他們賭眼睛賭手指他們賭夢
他們賭一個謎語和陷阱
他們賭星期六的命運
他們賭你身體里那場鵝毛大雪
你輸了,他們戴著你的帽子大笑
你連故鄉也輸掉了,他們不多不少
你再輸一次,他們消失了
你在回憶錄里丟了名字
你回去找,和他們一起動手
這本書太厚了,翻過一夜
又是一夜,再向后翻
旅館里的燈亮了,你站在窗前
安放好自己的眼球,你看見
臉上的季節漸漸模糊
你摸了一下,摸出幾株
互道晚安的植物,鳥在你睡眠的
形狀里叫,飛…此前一分鐘
他們給你回答,他們給你
滴著紫藥水的鄰居:
有人正在死去帶著心靈的體溫
有人卸下器官,動身去遠方
有人從斜坡上向下滾雪球
越滾越大,一直滾到:
此后一小時,雪填滿了鏡子
但你在里面挖什么?
冬天的窄下巴還是寬前額
現在,你是復數,是第二個人
讀著鏡子日志:風聲
像野貓一樣走過
歇斯底里地叫,用爪子
撓:門,咯吱咯吱響。
我跟著你到處閑逛
在想起雪的同時,我不得不想起
夏天的一副假肢。
鐘聲也是一根手指
(For Y.F)
鐘聲也是一根手指。
敲,黑夜中的白發一閃如雪。
那些嘴唇蠕動,小耳朵里植物還在生長。
鐘聲試著詞的刃,割下觸角時
你的聽慢慢往里頭移。
空:關閉。
空的那部分,空的碎紋,空的藍。
被否認的雨滴,懸浮如字。
被彈奏的岸,簡短。
翻開自己像翻開一張未完成的樂譜,
向回翻:給蝴蝶押韻,從故事里
偷走虛擲的一分鐘,
一分鐘后再轉身已是蒼茫一片。
用想象的小動物反問世界?
用一滴墨,和它潔白的口音。
鐘聲蕩漾。
大海像一塊被突然照亮的石頭。
鏡子里的一束水,它的胡須是一瞬的閃電,是閃電的根部,
點燃它,有一個呼吸的陰影就夠了。
喚回一只鳥,鳥籠,鎖著。
被打開的景色是借來的。
回憶一下,多遠了,一封航空信追上了旅行者。
現實升到了超現實之后,還在攀高。
每個人都在水上讀它。
自行車,越騎越慢。每個人都是胖子,
可靈魂又太瘦了,難以伸出手來
接住眾聲喧嘩的黑暗。
是不是增加意味著減少——
減去天空,只剩下倒敘的海水。
減去說,玫瑰的嗓音不再成形。
黑暗是一大堆靈魂
黑暗是一大堆靈魂
只在暗房里,一大堆黑社會
男蝦女蟹:全黑下來的一秒鐘
半只手摸過來,半張嘴
吃藥,吃到半截
身上的聯邦一擊即潰
剩下的器官,被各種名稱
藥水一樣浸泡:
兩顆眼珠,被玻璃球
兩只腎,被陰影
這個人可能,那個人也可能
黑暗般腎虛。把舌頭移到故事里
讓它說,說:親愛的傷口
鐘表匠擰緊的精密結構
現在一點點地轉動
半是甜蜜半是疼。不!不是
是先給這首詩一只肺
然后讓它呼吸:翻來覆去
(這只老鸚鵡)用一句話
用腹部隆起的世界
“你所孕育的只是一個死嬰
房子空空蕩蕩,沒有人”
沒有人真正懷疑比喻——
陽光照耀著老人的膝蓋
陽光照耀整條街
先是靜的,后來開始蠢蠢欲動
你睡著,聽著肉體的風聲
結果是許多條尾巴
省略號一樣游過……
手稿:偽情節
1926年,茨維塔耶娃在給里爾克的信中說過
大致如下的話——
對命運和黑暗我早已心領神會。
我唯一的使命是忠實于自己。
我一生的經歷就是證據。
我是女瓦格納。我不愛大海。我無法愛
因為不能行走。我憐憫陸地:有著兩只手
兩條腿的街道,它感到冷。“如果你
撫摸一條狗,請注意它的眼神。”
盛大的秋天。我獨自坐在這封信里
很難告訴你,同樣很難判斷
哪個城市更好,或者更糟:
柏林、布拉格和巴黎。(一個人
內在的權利就是保守心靈的秘密
說出或并不說出,取決于你是否
有突然的轉機。)一份護照里的照片
我留著短發(我從不留長發)
脖子上掛著項鏈,但像一個男孩
孤零零的,表情嚴肅(每個時代的
過時人物在他們翻開的照相薄里
都浮現著至少30種以上的微笑)
仿佛想起了什么。我寫下許多
從高音C開始的詩句(如果要讀
就請你大聲地讀,用嘴唇的運動讀
對著飛翔的耳朵讀),現在
我回頭看一眼自己的花園,就像
看一張寫滿字的紙。“每一種鐘愛中
都有重新和永恒。”但曾經有過的
時代和場景,不曾將作品與作者分開。
II
整個夜晚在舊目錄密集的標題里呼吸
像有翼的斯芬克斯,她那美女的腦袋
充盈著獨裁者的黑暗,越來越強烈的
孤獨:被強加在閑蕩的結局上
一個影子從門下溜走,絕對的空虛
“我將生活到數字允許的那么久”
而逗留在附近的最后的事態,難以置信地
被推遲(它依賴于沒有負擔的死的命名)
用新的表象,新的等待,新的講述
干擾著記憶:同一個東西里
有兩種速度:過去和未來
都來自遠方。就像從詞走向物
然后,再在詞的后面創造詞
那時我喜歡蔚藍和遼闊
喜歡花和根。現在,我熱愛人類
(人是我們注定要成為的!)
熱愛格言般孵化的時光和平等的事物
提供靈感的鏡子,秋日柔情的慢板
現在我就是活的智慧女神
寫詩,戀愛,在不同的時代
變換不同的姓名,一個個勾起
幻想的美妙音階:克莉奧佩特拉
舍赫拉扎德,薩福或艾米莉·狄金森。
“靈魂開始之處是肉體結束之地。”
我也許這樣授意過俄耳浦斯,叫他
“別回頭”,就像我很久以前
寫下的:生活就是車站,
我們很快就要上路;去哪兒,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