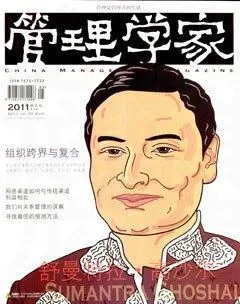組織邊界\\城市治理與系統風險
科斯在思考組織存在的理由時,基于組織管理邊界問題開創了“交易成本經濟學”,并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然而,當我們基于特定的視角和特殊的目的去考慮社會組織設計邊界的時候,雖然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暫時性的、被放大了的效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將難免會受到明確的目的和細致的邊界分類之害,其產生的潛在的系統分割風險將會導致系統的失衡甚至最終的崩潰。
長期以來,政府各個部門間由于職能劃分過細所致的銜接失靈,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及公共資源的嚴重浪費,甚而引發廣大民眾的誤解和不滿,影響社會組織結構的穩定。2009年,中國政府用于維持社會穩定負面的財政支出高達5140億元,幾乎接近國防軍費開支,可謂名副其實的“天價維穩”。一貫號稱“財政困難”的廣東省某市在“花錢買穩定”的理念指導下,花費3100萬元創建了一支包括340名成員的維穩“飛虎隊”,甚至在每一條街都安放一名像“東廠”一樣的“哨子兵”。這種滿街的全副武裝,真的能夠帶來安全感,真的能夠帶來社會系統的穩定嗎?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甚至頭疼醫腳的行政管理模式錯位,其后果必然是陷入越來越多的矛盾被激化的惡性循環,給整個系統帶來巨大的運作甚至是存續的風險。
老子曰:“無名,萬物之母,常以無欲以觀其妙;有名,萬物之始,常以有欲以觀其檄。”世間萬物自然和諧的相互關系是何等的美妙,組織設計過程中對邊界問題的考慮也是如此。杰克·韋爾奇在執政GE時,基于無邊界組織理念大力倡導打破各類組織樊籬,倡導組織各部門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于組織變革趨勢中邊界的強化或虛無,從一般組織設計常識來看,科斯的理論與杰克·韋爾奇的經驗似乎是各擲一詞而相互對立的,但從系統論的觀念來看,這一對貌似對立的理論精華與實踐經驗之間實則是和諧而高度統一的。因為系統結構的先進性和暫時性等屬性,決定了沒有永遠先進而無需變化的系統。當組織所處的環境條件發生改變的時候,系統內部的適應性邊界關系就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如果處理不當,輕則使組織發展停滯不前,重則會導致整個組織的顛覆。杰克·韋爾奇的無邊界管理理念正是在忠告我們,要直面和正視環境的變化,在系統性危機發生之前,嘗試新的組織關系和新的組織架構。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城市之一的杭州市,其社會復合主體模式對行政管理變革的嘗試,正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轉型過程中,基于這樣的新的發展思路進行設計,以進一步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生活品質,并進而推動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創新。
大城市的治理,一直是一個困擾著公共管理理論界和實踐界的世界性難題,政府在城市治理結構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發揮一旦錯位,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從根本上影響和動搖整個社會治理系統結構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任何一個系統的穩定,都不可能通過來自外界的壓制力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需要基于系統的考慮,以均衡的社會利益結構、完善的社會治理結構和成熟的法制環境為基礎。當前全國各地的社會群體沖突事件、上訪事件飆升,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官員個人或者某些打著社會公權力幌子的群體權力對公民個體利益的非法侵害所致,如果只是采取強力控制、封堵、威懾等手段,甚至有些地方通過壓縮基礎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過度的、無節制的滿足所謂的維穩支出,這無異于南轅北轍,也違背了政治的本意,從而陷入“花錢買穩定”的危險的惡性循環。另外一方面,也是當前中國城市治理結構失衡所致,決策過程不透明和決策失誤,監管缺位,法制建設不夠完善,使得社會各界在城市治理決策過程中難以有合適的渠道表達自身的意志。不同的治理結構會產生不同的治理結果,杭州市社會復合主體模式的嘗試創新了中國城市的治理結構,從政府的單一治理主體結構向黨政、知識、行業、媒體等多個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的協作治理和共同治理結構轉變。與此同時,推動了政府與其他主體之間從對立、不平等和權威關系向合作、平等和伙伴關系的轉變,培育了廣大市民在城市治理過程中的參與感,這種公民參與和協商民主也正是針對當前一系列社會群體事件和問題的治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