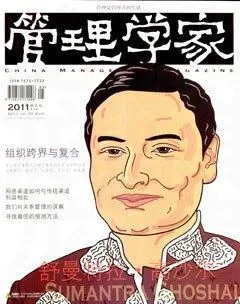張五常“纖夫合約”假說的錯誤及其擴展
“纖夫合約”的非經濟解釋
張五常觀察到:三峽上的纖夫會同意“雇一個監工來抽他們”(hiring amonitor to whip them),而且還分享他們的勞動剩余。他解釋說,因為每個纖夫的努力程度難于衡量,很難監督其他的纖夫會不會偷懶(shirking),所以一個強權的管理者是必須的,那樣才符合每個纖夫的利益。
這個例子曾經給筆者很大的啟發,它使人反思傳統的資本剝削勞動、管理者剝削勞動者的教條。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帶著文學性的同情描述工人是如何受到“拿摩溫”的欺壓。而在張五常看來,那只是一種合約形式——纖頭拿著鞭子抽人,是最殘酷的了,但其實是纖夫們自己組織勞動的需要。張五常這種解釋確實是符合邏輯的,很有說服力。在富士康跳樓事件之后,就有人引用“纖夫合約”來論證:其實工人并不存在被剝削問題,是他們自己選擇了這種被監管的合約方式。
我對“纖夫合約”假說產生懷疑,緣于2010年夏季我在北京農村的勞動經歷。幾年前,我在北京郊區買了一座宅基地。去年夏季,我請了村上的一些農民幫我蓋房子。在農村蓋房子,首先要請一個被稱作“包工頭”的人,此人需要對蓋房子有經驗、有威信、人緣好。當時的工價是“大工”一天120元,“小工”一天80元(凡是砌墻、木工之類需要一定技術的被稱為“大工”;簡單體力勞動被稱作“小工”),我被稱為“東家”。一個多月里,我都在觀察,蓋房子這樣的生產勞動是如何組織的。和張五常觀察到的纖頭以惡狠狠的姿態拿鞭子抽纖夫不一樣,我發現包工頭和蓋房子的農民之間是非常平等的關系,除了工作中經常轉來轉去指揮大家的時間較多以外,他很少呵斥干活的農民。干活的時候,大家氣氛非常融洽,還相互開玩笑;平時他經常買煙給分給大家抽,在幾個重要的日子,比如開工、上梁、封頂,他還要辦酒席請伙計們一起吃飯,給大家敬酒,感謝大家出力。
在蓋房子中會不會有人偷懶?在有些工作中偷懶是很困難的,比如砌磚,速度如何、質量如何很容易看出來。有些工作努力程度就很難衡量,比如“上大料”,一根木料至少數百斤,抬一根木頭需要至少三四個人協作。這個過程中每個人站的位置不同,誰出了多少力確實很難評估。不過也并沒有出現張五常說的要找個人拿鞭子抽大家的管理方式。我了解到,這些一起蓋房子的農民,彼此之間都有很好的關系,有些甚至是親戚,所以合作才能默契,至于偷懶的問題,則很簡單,誰要是偷懶讓大家看在眼里,下次干活就不會叫他了。
為什么張五常觀察到的長江纖夫需要專門雇一個強硬的監工來抽他們,才能有效率地干活?而我觀察到的蓋房農民卻可以自覺地甚至快樂地工作?
如果張五常觀察到的現象是真實的,那么存在一種可能情況的解釋是,拉纖時各人的努力程度,比蓋房子搬木頭更難于監督。但這個可能在實證中并不成立,是張五常浮光掠影表面觀察產生的誤解,我奶奶抗戰期間在重慶有多次雇人拉纖的經驗,在沒有經驗的人看來,幾個人在一起拉纖,很容易有人偷懶而不被發覺。其實不然,如果觀察得更細致一些,會發現每個纖夫獨自拉一根繩索,誰沒有好好使力氣,從纖繩的緊繃程度上很容易看出來。倒是蓋房子抬木頭的時候,各人付出的努力程度較難衡量。也就是說,因為拉纖的努力難于監督所以雇人來抽大家的說法是不成立了。第二種可能的假說是,在長江拉纖比蓋房子危險性更高,所以需要一個嚴厲的人來協調大家的一致行動。拿個鞭子抽大家,因而被容忍,這實際上是一種危險環境下的特殊群體文化,比如戰場的軍人,上下級之間會表現得非常粗魯甚至嚴苛,所謂“慈不帶兵”,但在共同面對嚴酷的外部危險時,這種在平常顯得極為不人道的管理手段會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這個假說邏輯上成立,但也經不起推敲。因為纖夫這個職業從抗戰后一直到現在都有,今天當纖夫依然非常艱辛,要說危險程度和過去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可已經看不見有監工拿鞭子抽纖夫的景象了。纖夫們帶頭的叫“駕長”,要指揮大家,有豐富的經驗,工資比一般纖夫略高, “總的來說對手下要狠,人要機靈”,但大家之間關系很好,“像朋友和親人一樣”, “沒有什么特殊的地位”。(陳晰,2009)張五常觀察到的拉纖需要雇個人抽大家,也不能用獨特的工作條件來解釋。
這樣接下來要問,而張五常并沒有深究的問題是:為什么當年他觀察到的纖夫,要接受請一個監工來抽自己的合約,而不能形成另一種更加人性化的合約?如給我蓋房子的農民,有一個包工頭組織勞動,但主要以相互監督和榮譽感為激勵的合約方式。纖夫之間也完全可以形成一種默契,對于有偷懶傾向的人進行排斥,“下次干活的時候不叫他了”,或者通過良好的團隊氛圍激勵大家為了榮譽感而努力工作。
之所以蓋房的農民可以形成一種相互監督、相互激勵的愉快的工作氛圍,關鍵在于蓋房的農民之間有一種長期合作帶來的信任。可以作為一種推測的原因是,在抗戰期間,大量流民進入重慶地區,當時這樣的勞動力,和筆者在北京農村遇到的蓋房農民很不一樣。第一,他們處在溫飽的邊緣,在日常卡路里不足的情況下,節約能量消耗,對生存更加重要,“偷懶”的動機更強,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這種情況下榮譽感是非常奢侈的事情;第二,他們是戰亂年代來討生活的流民,沒有熟人構成的關系網絡,彼此之間沒有信任關系來構成合作,而需要外在強力的監督;第三,在戰亂年代,有更多強制性的雇傭行為,最極端的合約形式,就是抓壯丁,用皮鞭抽較為常見,使得那個時代的勞工對于勞動尊嚴的預期比較低,更能夠忍受被鞭打的工作環境。“自由合約”的約束。
張五常把纖夫雇一個監工來抽自己視為一種合約,這本身并沒有問題,包括他對制衣廠女工計件工資制的分析,都指向合約沒有好壞之分,只有是否適宜,由此引申出他對合約自由的推崇。
在對新勞動法的討論中,張五常的觀點是:中國當前根本就不需要政府規定任何勞動法,因為勞動法是“干預合約自由”。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包括他和很多有古典自由主義傾向的經濟學者,也從其理念出發,認為中國今天不應該有工會,因為工會也會妨害合約自由。
張五常強調“經濟學不能回答ethics(倫理、道德)的問題”。這點上張五常并不完全錯誤,經濟學確實有其獨特的范式,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個經濟學家或者一個社會科學的學者不能判斷一個合約有好壞之別。
張五常曾介紹經濟學的三個范疇:①“在知道有關的約束條件(constraints)或游戲規則(這就是產權制度或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劃分)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推斷所用的競爭準則是什么”;②“有了競爭的準則,經濟學可以推斷人的行為會怎樣,資源的使用會怎樣,財富或收入的分配會怎樣”;③“要解釋游戲規則是怎樣形成的”。(張五常,2000)
由此會得出結論,游戲規則或者合約都是客觀限制條件下的結果,因此是無所謂好和壞的。張五常的核心邏輯是聽其自然是好的,一切外部干預都是壞的。
但如果順著張五常的三個范疇反推,就可以追問:從已知的游戲規則和人的行為,反向推知約束條件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樣的約束條件產生這樣的游戲規則和人的行為?
如果張五常認為資源如何使用、財富如何分配都是合約問題,而合約都是由客觀的約束條件所決定的,所以合約不存在好壞的區別,那么進一步追問,造成合約的約束條件,有沒有好壞之分?
如果張五常認為,勞動法作為外部的約束,會干預合約自由,那么勞動法之外的其他客觀存在的約束條件是不是也在干預合約自由?張五常對勞動法的約束持批評態度,這個時候他明顯有好壞的判斷,但對于其他約束條件,難道就可以都視而不見么?這樣張五常所提倡的“自由和約”更像是一個烏托邦,因為在各種復雜的約束條件下,合約本身就是不自由的。
如筆者前面分析的“纖夫合約”,張五常看到了抗戰時期長江上的纖夫會接受一個人來鞭打他們,但是他缺乏人類學意義上的細致觀察和同情,過早地概念化,認為這是一種纖夫自愿為了抑制伙伴的偷懶行為,而形成的自由合約。他草率地得出結論,是因為纖夫的努力不容易衡量,所以需要一個人拿鞭子來抽他們,卻沒有去探尋那背后更復雜約束條件。如果筆者歸納的約束條件,在抗戰時期,外患侵擾,難于有條件改善,在今天有的勞資關系中出現類似的傾向,是否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預呢?
如果把張五常的“纖夫合約”中的經濟學思想,轉化為管理實踐,是非常危險的取向。在這種分析方法下,只要不去追問各種約束條件的合理性,即使黑磚窯那樣的勞動關系,也可以說成是一種自由合約。因為那些奴工在各種約束條件下,最后放棄了逃跑和反抗,也沒有自殺,而聽從鞭子的指揮,他們的回報是粗劣的飲食和活下去的機會,也可以說這些奴工做出了自己的“合約選擇”。
像富士康這樣的大企業,雖然沒有用鞭子對付工人,但也有強大的保安系統來管理工人,包括用軍事化的手段來訓練工人的服從,瓦解他們之間萌芽的自組織和信任,使他們成為原子化的個體,而更加易于管理。對于這樣的管理模式是否因為它是“自由合約”,就不能對管理者提出質疑?
當企業的管理者的管理手段成為一種影響合約的約束條件時候,難道就應該聽之任之么?否則就是干預合約自由么?
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就指出勞動關系中缺乏有效的平衡就會導致問題,而解決手段就是:組織改革并提高管理水平;集體談判使勞資兩方平等地組織起來,平衡勞資雙方的力量;發揮法律的作用。
張五常在“纖夫合約”中另一種危險的傾向是,把理性人的假設極端化,并把用于建模的假設向真實生活作無限推演。人是理性自私的,所以人會偷懶,人又是害怕痛苦的,所以拿鞭子抽他是最有效的管理措施。這作為一種理論假說,問題并不大,但如果把它作為一種管理實踐的思想就過于簡單,對真實人性的理解也過于簡單。
這在管理學上尤其被視為一種非常過時的思想方法。管理學家麥格雷戈歸納了基于對人性的不同看法而形成的兩種理論。他認為,傳統理論是以對人性的錯誤看法為基礎的,這種理論把人看作天性厭惡工作,逃避責任,不誠實和愚蠢等。因此,為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就必須采取強制、監督、懲罰的方法。麥格雷戈把這種理論稱之為“x理論”。與之相對的是“Y理論”,其基本觀點是:人并不是被動的,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只要創造一定的條件,他們會視工作為一種得到滿足的因素,就能主動把工作干好。因此,對工作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應從管理上找原因,排除職工積極性發揮的障礙。麥格雷戈把這種理論稱之為“Y理論”。他認為“X理論”是一種過時的理論,只有“Y理論”才能保證管理的成功(Mcgregor,2006)。
而有一些有古典自由主義傾向的經濟學家在今天卻有強化“x理論”的傾向,這非常使人感到遺憾。“纖夫合約”的擴展
筆者前面對張五常“纖夫合約”假說的批評,并不意味著它不重要,而恰恰是因為它太重要了,才值得我們認真來批評它。而“纖夫合約”作為一種理論模型的認知價值,并不因為其在實證層面的錯誤而減少。
如果參照韋伯提出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概念,也就是研究可以超出具體事實而作為一種“思想試驗”(韋伯,1997), “纖夫合約”作為一種思想試驗是極為有價值的。
我甚至認為,張五常的“纖夫合約”假說的解釋力,并沒有被我們今天的學術界充分認識到。在我看來, “纖夫合約”并不適合用來解釋富士康事件中的勞資關系。因為張五常觀察的纖夫并沒有以自殺來反抗這種合約,而富士康的自殺案例比被鞭打的纖夫更加極端,顯然員工的自殺并不是員工與企業主“自由合約”的一部分。
但“纖夫合約”對于尤其是在制度經濟學的關懷下解釋人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確有極大的啟發意義。地球上的各種社會制度,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國家管理者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既有讓人民很有尊嚴,生活工作得非常愉快,也不乏有像監工鞭打纖夫這樣,在外人看來極為不人道,極為殘酷,極為抑制人的尊嚴的。但這樣的制度卻在旁觀者的鄙視和痛恨中能夠延續下去,甚至延續很長時間。如果我們把勞動者和雇傭者及管理者的關系,比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和統治者的關系,那也是一種合約關系,甚至也可以稱作“自由合約”。但這些自由合約的達成有不同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決定了,有些國家和地區,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是和諧的,是給人民以尊嚴的,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是用皮鞭來維系的。
而一些在局外人看來明顯不人道的統治,卻能夠“成功”,就在于統治者成功地創造了一些約束條件。比如將人民生存條件維持在溫飽水平,這樣可以抑止他們對于尊嚴的渴望;摧毀人民之間的信任聯系,使他們成為原子化孤立的個體。
這些約束條件,使其人民能夠忍受,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皮鞭。在這個意義上,尋常人們講的剝削和壓迫,并非否定合約的普遍性,而是合約的一方相對另一方有更強勢的人為設定約束條件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