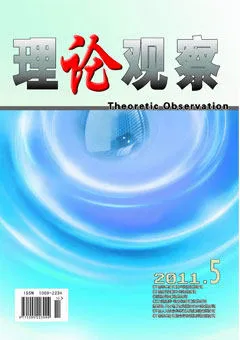當代西方政治學方法論的演進與變革
[摘要]西方政治學的進步與方法論的發展緊密相關,行為主義政治學體現了政治學研究科學化的傾向,理性選擇理論將經濟學的方法應用于政治分析,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批判地借鑒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制度研究的重要價值,凸顯了政治學的學術性與實踐性的融合。
[關鍵詞]方法論;行為主義;理性選擇;新制度主義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1)05 — 0046 — 02
方法論是起指導作用的范疇、原則、方法和手段的總和。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支撐,方法論的發展本身就是學科學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學也是如此,因而政治學方法論具有重要價值。自二戰以來,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的進展與方法論的演進和變革緊密相關。本文擬從方法論演進的角度梳理行為主義、理性選擇與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力圖展現當代西方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遷圖景,以期豐富對政治學方法論的認識,為提高我國政治學研究的學術性與科學性提供素材。
一、政治學的科學化:行為主義(behaviorism)
行為主義是二戰前后在美國崛起并迅速占據主流地位的政治學流派,其本質是政治學研究方法的革命,即以自然科學的分析工具、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政治行為和政治過程。以拉斯韋爾、伊斯頓、阿爾蒙德等人為代表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大師主張“運用實證方法研究個體或團體的政治行為,主張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1〕
行為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和現實交互作用的產物。行為主義的產生首先源自對傳統政治學的批判。傳統政治學關注政治制度的設計,即如何通過構建良好的政體來實現良好的公共生活。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以及聯邦黨人的政治思想都體現了這一點。價值性、思辨性、抽象性、定性分析是其顯著特點。然而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制度的建構也逐漸完成,“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爭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種政治制度上,而是采取什么樣的公共政策”[2],基于此,以往只注重對靜態制度、法律文本描述而忽視對現實政治行為研究的傾向遭到激烈批評。另一方面,政治學研究中的科學化情結與現代自然科學研究的新成果相結合,成為行為主義發生、發展的又一動力。20世紀以來,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快速發展,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抽樣調查、問卷訪談等社會調查方法,以及數據分析、概率論等統計學技術為行為主義提供了豐富資源。政治學有著與自然科學方法相結合的古老傳統,在古希臘,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并未分離,如柏拉圖的理念論與數學有著內在關聯,這使得柏拉圖成為“堅信可以將數學——幾何學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賓諾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驅”[3]
行為主義的方法主要包含價值中立與實證研究兩個方面。價值中立主要體現為研究客體和研究主體的價值中立。行為主義者認為事實問題可以觀察和驗證,價值問題則無法觀察驗證,政治學者不應該研究“應然”問題,而只應研究事實問題,在研究對象上與意識形態劃清界限。此外,研究者個人的情感色彩和價值取向也妨礙了政治學的科學化,為避免個人情感對研究結果的歪曲,研究者應該保持完全中立的態度。實證研究方法主要體現為研究的經驗根據。其框架模型分為觀察政治現象,確定研究主題,構建概念體系,做出理論假設,制定關系模型,收集資料,以計算機技術整理數據資料,得出結論。
行為主義綜合運用心理學、統計學、社會學以及系統論的工具極大豐富了政治學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政治心理學、政治文化學、政治人類學等研究分支極大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范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重構了現代西方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促進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提高了政治學研究的系統化水平”[4]但是行為主義方法在20世紀70年代走向衰落并向后行為主義演變,這源于其方法論本身的局限性。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做到價值中立,一些學者批評價值中立意味著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誠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政治學事業被解釋為類似科學事業的話,就有出現暴政的潛在可能性”[5]唯實證的研究方法使其對政治現實問題缺乏回應和解決能力,“政治學正在變得不關心政治學”
二、政治的經濟學分析:理性選擇理論(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選擇理論被看作是行為主義政治學向后行為主義轉變的重要標志,是將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拓展性的應用于政治研究的產物。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理性選擇作為一種研究思潮、研究方法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歐美經濟學和政治學者的關注。“在政治學中幾乎已經沒有未受過它影響的領域”[6]
理性選擇理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政治哲學傳統之中,追溯到麥迪遜和托克維爾的政治科學源流之中[7],早期的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理論將國家、政府看作人們基于利益考量,讓渡權利、訂立契約的產物;1929年經濟大危機顯現了自由市場秩序的弊端,以國家干預為核心的凱恩斯主義逐漸成為主流。隨著政府干預廣度和深度的不斷加強,人們認識到作為糾正市場失靈手段的政府干預同樣存在弊端。在此基礎上,以經濟學的理論工具和分析范式解釋民主社會中政治和選擇過程的理性選擇理論成為當代西方公共部門管理實踐特別是政府改革實踐的理論基礎。
理性選擇的方法論主要體現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經濟人假設和交易政治觀三個方面。無論是私人活動還是集體活動,無論是經濟過程還是政治過程,個人都是最終的決策者和行動者,因此分析政治活動同分析經濟活動一樣都必須從個體開始;個人無論處于何種位置都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最基本的動機,“如果把參與市場關系的個人當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個人在非市場內行事時,似乎沒有理由假定個人的動機發生了變化”[8];政治是政治參與者出于自利動機而進行的一系列交易過程,政治過程同經濟過程一樣是交易動機、交易行為和利益的交易。用交易的方法觀察政治,使人們在權力政治學之外有了理解政治過程的新視角。
理性選擇理論加強了政治學和經濟學內部的交流,為分析社會政治問題提供了統一的人性論基礎,適應了政治學科學化的要求。但是其方法論基礎仍存在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無力解釋個體行動的整體后果;經濟人假設忽略了人性的其他特征,將人的一切行為都歸結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全面的,經濟人假設在政治領域缺乏足夠的經驗依據,而僅僅是一種邏輯演繹;將市場經濟的交易原則無限制的應用于政治領域容易導致人們對政治過程的曲解。盡管如此,理性選擇理論仍然與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具有內在的關聯性“理性選擇理論假定個體是理性人,從中推導出的結論不是改造人們的經濟動機而是重視政治制度的設計對行為選擇的影響,在重視制度效能意義上成為制度理論復興的支持力量”[9]
三、批判與重構: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
方法論意義上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反對用個體主義解釋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重視制度安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張政治制度引導政治行為。1984年馬奇和奧爾森發表的《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一文標志著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產生。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是在批判吸收行為主義、理性選擇政治學基礎上產生的。首先,它對政治行為反應偏好的假定表示質疑[10]。新制度主義反對將政治行為作為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因為行為發生在制度環境中。理性選擇理論分析的邏輯一致性是以其片面深刻性為前提的,人們的逐利行為要服從于社會規范和社會制度的要求。此外,由諾斯、威廉姆森等人推動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將制度作為重要變量來解釋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的思路及其成果對政治科學中制度研究路徑的復歸與興起也具有重要影響。
方法論意義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強調制度與國家的作用。第一,以制度作為分析變量,肯定制度重要價值。政治制度不是社會成員偏好的簡單聚合,它限定政治行為的選擇范圍,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制度影響規則、行為和政治結果。新制度主義對制度的強調代表了向政治學舊制度主義的回溯與超越。與傳統舊制度主義的宏觀結構分析以及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微觀個體分析不同,新制度主義將制度分析與行為分析相結合,實現了從宏觀理論和微觀分析向中層理論建構的重大轉變。第二,肯定國家的作用。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那里,國家的作用和地位被低估甚至被忽視。行為主義以“政治系統”等術語取代國家,理性選擇理論認為“每個國家都是追求稅額和剩余最大化的利維坦,因此必須限制國家的作用范圍”[11] 。新制度主義在批判吸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上重新定位國家的性質,提出“找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國家并非是社會力量斗爭的舞臺,而是有著自身的結構性質和運行邏輯的實體。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身的偏好和行為方式來貫徹自己的意志[12]。
新制度主義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判借鑒推進了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政治學領域,批評行為主義只重過程而忽視制度的傾向,實現制度與行為的整合研究;在經濟學領域,理性選擇理論吸引了大批經濟學家研究制度問題,使分離的政治學和經濟學重新結合;在社會學領域,新制度主義者對制度概念的拓展,實現了制度概念的普遍化,為社會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13]。但是新制度主義是松散的集合體,在具體的理論構建上,新制度主義內部并未達成一致,新制度主義還不同程度地存在無法證偽的可能性。
總之,現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與研究方法的演進更新緊密相關,從行為主義、理性選擇到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與實踐性不斷增強。方法論的演進不是全盤否定而是借鑒吸收。今天我們要構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是開放的、多元的,借鑒吸收西方政治學的成果,揚長避短,總結政治生活規律,制定政治生活規則,高揚政治生活價值,實現政治生活理想。
〔參考文獻〕
〔1〕葉娟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方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2〕朱德米.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興起〔J〕.復旦學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