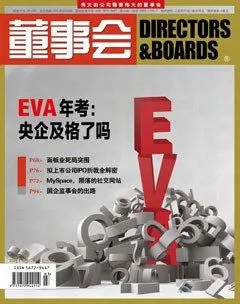為股東協議正名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都只能關注常態——即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問題,而股東的個性化需求、應急管理以及一些未雨綢繆的事宜則應當交由股東協議負責
在公司治理實踐中,股東協議大量存在,盡管其作用獨特而巨大,但并未引起立法、監管等有關主體的應有關注。
常見的也是合理的
顧名思義,股東協議即股東之間的協議,其大量存在自有合理性,是現實的市場邏輯所致。顯然,這個定義只是劃定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其界限可以說比較模糊。然而,模糊正是股東協議的一個巨大優勢。股東協議憑此能有效應對公司治理及市場交易的巨大復雜性與高度不確定性,也有效節省了日常治理實踐中的交易成本。
公司股東人數眾多、公司股權結構復雜以及公司經營范圍的廣泛等特征,都有賴于股東協議的登臺獻技。依照公司法的規定,盡管最為依賴股東協議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東人數并不算過多(50個以下股東出資設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算復雜,但由于股權結構具有高度復雜性,而這兩者之間近似于一種乘積關系(非簡單疊加關系),因此股東規模的簡潔優勢瞬間蕩然無存。以出資方式為例,按照公司法規定,股東可以貨幣、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多種方式出資,而每一位股東的出資方式并不受限制,此其一;再者,伴隨公司的存續,股權結構又會不斷發生新的變動,譬如老股東的退出、新股東的加盟,再如出資額的增減、出資方式的變更、出資資產的價值評估等,都是這種復雜性的不斷演繹。治理不斷走向復雜,但這還遠未到極致,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公司面臨的市場競爭、來自消費者的影響以及宏觀政策調控等。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影響因素的眾多,而是這些因素的影響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比如環保政策對企業能源消耗的調節(拉閘限電),再如某一品牌的產品質量事件引發全行業品類的信任危機,這些不確定性在當前社會轉型時期極易被觸動誘發。聯系到股東利益上,對這些問題僅依靠公司法、公司章程應對,毋庸置疑又力不從心。可以說,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都只能關注常態——即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問題,而股東的個性化需求、應急管理以及一些未雨綢繆的事宜則應當交由股東協議負責。
從交易成本看,股東協議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都具有節省交易成本的作用。不過,公司法與章程可以有效節省企業事前的交易成本,而對事中及事后出現的一些問題卻無法著力或者作用有限,股東協議由于具備高度的靈活機動性和股東的同心協力,不論是信息搜尋、談判決策還是監督協議的執行都能保持良好效率,這是其獨到之處。
靈活的治理工具
人們在談及股東治理問題時多將注意力聚焦于限制大股東、保護中小股東利益方面,但中小股東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其本身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是存在疑問的。中小股東們更關注短期的投資收益,相形之下,部分大股東卻更關心企業的長期價值。以利潤分配協議為例說明,中小股東與大股東間可能會達成在任何經營情況下均要求分配紅利的協議,但當公司處于虧損之時,這種協議就會損害大股東、企業的整體價值。因此,這種股東協議顯然不具有正當性,這就需要立法的介入。
當然,股東協議更多地作用于有限責任公司治理領域。眾所周知,有限責任公司更為注重人合性而非資合性,因此這里的大小股東之間的利益博弈更緊密地聯系著企業的命運。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能保持“理性冷漠”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可以“用腳投票”,而有限責任公司的退出機制在立法層面則困難得多。所以,盡管有股東派生訴訟等手段可以保證中小股東利益,但并不能解決在出現公司僵局、大股東主導控制卻不違法等情況下中小股東的利益訴求問題,譬如優先購買權及利潤分配問題等。而基于這些事項的復雜性以及可能的秘密特性,章程并不能發揮多大作用,可以依靠的便是股東協議了。以Clark v. Dodge案為例:雙方約定少數股東可持續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