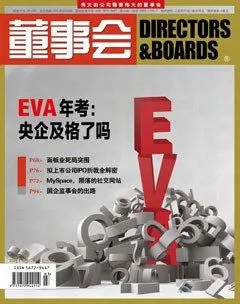中國PE監管難題
2011-01-01 00:00:00萬國華萬昊王玲
董事會 2011年3期

我國PE監管究竟采用他律好還是自律好,長期未決的重要原因是PE尤其有限合伙PE的行業性質難以定奪,是金融機構還是非金融機構?沒有現成法律依據或法理依據不足
2010年我國私募股權基金(PE)投資案例817起,其中披露金額的667起涉及投資總額53.87億美元,數量、金額均遠超前兩年。其中,有限合伙制PE案例上升速度最快,投資數量、金額年增速逾30%。不過,這一迅猛增長的投資潮背后日益顯現出諸多憂患,亟待從嚴監管。
市場準入——徘徊于審批與注冊之間
市場準入是有限合伙PE監管須面對的首要問題,其自PE問世以來一直為各國監管者重視。PE的設立包括審批制和注冊制兩種模式。英國實行審批制,由金融服務局負責;美國實行注冊制,但依據2010年的《金融改革法案》,金融危機后對沖基金和PE的投資顧問必須強制性注冊。
由于法律缺位和行業發展不成熟,目前我國整體PE準入實行的是審批制還是注冊制,法理或立法仍未有定論,或模糊不清。國家層面部門規章如《創投辦法》(2005年)對PE采取的是獎勵性“備案”制,法理上似乎比西方發達國家的注冊制還寬松,但現實中所有產業投資基金(類似PE)卻又都是發改委審批的結果。目前正在討論的《私募股權辦法》(草案)中,發改委規定對5億元人民幣以上PE擬實行強制備案。另外,對PE的性質、特點、企業形態和治理結構等方面沒有進行科學界定與分類,如國外并不存在產業投資基金的提法,我國卻把它與有限合伙PE一起規范,也是導致市場準入規則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
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并結合我國PE市場發展實際,宜建立以強制注冊制為原則、選擇性審批制為例外的市場準入模式。其前提是,應對現有PE進行科學分類與界定。普通型PE包括但不限于有限合伙PE宜采用強制性注冊制,即任何PE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并提出申請,主管部門進行形式審查合格后即可設立;而對那些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產業投資基金應適用有選擇的審批制,這是我國資本市場有序運行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保障。
權利義務——GP與LP角色游離
與PE市場準入監管密切相關的是基金管理人(GP)的準入與執業監管。美國《金融改革法案》對私募基金投資顧問的注冊監管趨強勢。我國由于有限合伙PE發展較晚,目前對GP還沒有真正法律意義上的監管,完全由投資契約或基金募集契約自律監管,所以實踐中出了不少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有二:一是基金GP與投資人(LP)角色缺乏正確定位,要么越位要么缺位;二是監督機制不健全。如溫州東海創投LP從交錢不交心到有限參與直至最終架空GP,結果成為中國首家解體的有限合伙PE,這是中國目前法律、誠信約束體系缺失及GP也不夠成熟的情況下,LP的自我保護之舉。
該案例的要害就是監督機制不到位導致的基金GP與LP角色錯位。但LP介入有限合伙企業決策和管理,模糊了LP與GP的角色,也加大了LP自身的風險,因為LP深度介入決策的話,法理上可能被視為放棄了“有限責任”的保護。一旦造成重大損失,有限合伙PE的第三方債權人可以揭開有限責任“面紗”,要求LP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目前為止,盡管《創投辦法》對創業投資基金高管有一定的準入標準要求,但該條款適用既不具有普遍約束力,也缺乏可操作性。筆者建議《私募股權條例》在借鑒美國經驗對PE科學分類的基礎上,應對GP和LP的資質、組織形式、資產狀況和權利義務等內容作出強制性或半強制H7lL03xSZzr42ATRrVohwgzp317or8LsWmVA08O38AY=性注冊規定,以便厘清雙方角色定位與權力邊界。
信披規則——透明度與私密度難平衡
GP與LP角色游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換言之,由于PE項目篩選及投資決策的程序和內容透明度不高或信息披露不足,導致了LP的越位乃至“篡位”。從投資人保護角度看,信息披露事關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是政府監管的重要內容,所以透明度越高越好。從有限合伙PE性質講,由于具有很強的契約型,其私密性和靈活性歷來被視為競爭優勢或生命所在,并成為慣例廣為世人所接受,故私密度或保密性越高越好。這樣理論上天生的矛盾,就必然導致實踐的混亂與無序。溫州東海創投的GP與LP反目也與此有關。
然而有限合伙PE的募集和運行均屬非公開,誤導或虛假陳述等欺詐現象在所難免,于是PE監管開始關注透明度規則的設計。如英國《PE信息披露與透明度指引》(2007年),重點關注信息披露原則和內容,而內容又重點放在有限合伙人的報告等方面。
我國PE應否有透明度、透明程度如何和誰來監管等,是監管部門長期未決的瓶頸問題。由于PE披露的對象一般只限于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等特定受眾,披露方式可靈活多樣。披露內容一般包括真實資本、資產質量和負債規模等。另外,如果有基金份額轉讓、合并、分立、減資、解散等特殊情況發生時,GP應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以便適時有效監管。但是,有限合伙PE運行透明度應該到何程度,相關信息內容披露的廣度與深度該如何等問題,還有待于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
監管模式——他律與自律未理順
PE尤其有限合伙PE監管事關資本市場體系的效率與安全,監管模式的選擇歷來為各國所重視。英國PE 監管模式以行業自律為主、政府監管為輔。美國證監會( SEC)、小企業管理局和全美風險投資協會(NVCA)是監管PE的三駕馬車。金融危機前,對PE 市場更多依靠NVCA的自律監管。《金融改革法案》通過后,加強了他律監管的力度。這表明美國對PE監管的理念和模式有了巨大轉折。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我國PE市場或行業監管模式定位似乎還不清晰。依國情宜采用他律監管模式,以國際慣例則應借鑒自律監管模式。況且即使采用政府監管模式,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以及發改委多頭監管似乎也不太合適宜,監管權的競爭與協調已迫在眉睫。2010年11月證監會和發改委就平衡慣例與國情、宜粗不宜細、牌照管理和信息披露等四項監管基本原則達成共識,這是巨大進步。
我國PE監管究竟采用他律好還是自律好,長期未決的重要原因是PE尤其有限合伙PE的行業性質難以定奪,是金融機構還是非金融機構?沒有現成法律依據或法理依據不足。如果真以自律監管為主,必須做到: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權法律淵源明確;PE市場比較發達和全國行業自律組織的設立。目前,天津、上海等城市成立的地方或區域性的PE協會還不足以擔此重任。所以,無論從我國金融監管傳統還是國際PE發展趨勢來看,有限合伙PE采取自律或監管為主模式可能都不太合適。相反,將行業自律作為政府監管的有益補充,可能是現階段有限合伙PE監管最明智的選擇。
(萬國華為南開大學法學與公司治理教授、天津商法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