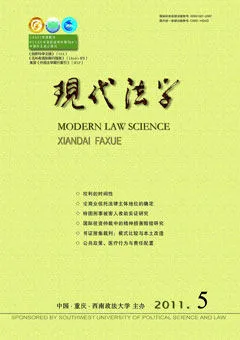為自己作證的權利及其真實義務
摘要:被告人作證權制度是英美法特有的一項制度,是在十九世紀中期邊沁功利主義思想影響下確立的。在英美法國家,被告人如果要在法庭上陳述事實就要像其他證人一樣,走上證人席,宣誓作證。被告人作證時不受不得強迫自證己罪原則的保護,對控辯雙方的提問必須如實回答,故意虛假陳述將構成偽證罪。二戰之后,部分大陸法國家或地區在改造職權主義庭審方式時,都不約而同地借鑒了被告人作證權制度,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調查被告人程序。我國也不例外。但我國的調查被告人程序不符合無罪推定原則、控辯平等對抗原則和證明責任分配原則的精神,有待進一步的完善。
關鍵詞:被告人;作證權;功利主義;真實義務;新型混合式訴訟
中圖分類號:DF0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i.issn.1001—2397.2011.05.13
2011年6月10日,“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再次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早在前一個五年規劃中,《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就已經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對立法規劃,學者們積極響應,很快就形成了一系列關于《刑事訴訟法》修改的研究成果和修改方案。在學者們的建議稿中,庭審方式仍然屬于修改的重點;其中,對調查被告人程序的修改成為重中之重。比如,陳光中教授課題組就提出,根據被告人的認罪情況,調查程序可以分為:在認罪的情況下,對被告人的調查首先由公訴人實施;在不認罪的情況下,公訴人就不能訊問被告人,應將對被告人的調查移至公訴人舉證之后。徐靜村教授課題組、陳衛東教授課題組也提出了類似的修改方案。為什么要進行這樣的修改?學者們給出了三個原因:第一,“這體現了法庭調查的中心從查證被告人口供的真偽轉移到對證人證言、物證、書證等證據的調查,此種方案對于相對弱化口供的作用、防止司法實踐中對口供的過分重視,有積極的作用”;第二,“公訴人舉證之后,審判長應當詢問被告人是否進行陳述或者發表意見,是尊重被告人自行行使辯護權的體現”;第三,“辯護人在公訴人之前向被告人發問,這是交叉詢問的要求和體現。在此,被告人的地位相當于辯方的證人,按照交叉詢問規則,應當由提出證人的本方進行主詢問,然后由對方進行反詢問”。
可見,學者們對調查被告人程序修改與否已基本上形成共識;但是,對如何修改,特別是為什么要進行修改的問題,他們并沒有進行充分的、有根有據的論證。對此,本文將考察英美法被告人作證權制度的形成原因,探討該制度對大陸法被告人調查程序影響,研究我國調查被告人程序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的路徑,為即將進行的《刑事訴訟法》修改提供一點理論上的支持。
一、英美法被告人作證權制度的形成史
在英美法的歷史上,被追訴者始終都沒有獲得“被告人”這種獨立的證據身份,最終在證據法上取得的身份仍然是證人即當事人型的證人(party—witnesses)。在13世紀之前,英國的神示裁判程序有三種證人:宣誓輔助證人、交易型證人(transaction—witnesses)和契約型證人(deed—witnesses)。古老的證明制度對這三類證人的適格性并沒有做出禁止性規定,他們可以是原、被告的同族人、家屬及其他具有親密關系的人。到了15世紀,當陪審團漸漸成為最主要的糾紛解決方式時,交易型證人和契約型證人被吸收到陪審團中作裁決者。當時的法律也沒有規定因為裁決者與當事人有親密關系就可以申請其回避。可見,在15世紀之前,英國人并沒有證人適格性的觀念。15世紀中期至16世紀初,在陪審團由知情向不知情轉變之后,英美法現代意義上的證人才開始形成。了解案件事實的人不能再成為陪審員,必須以第三人即證人的身份向法庭提供證詞。這一時期也沒有因為證人和當事人有親密關系就禁止其成為證人。恰恰相反,與當事人沒有任何關系的證人卻很少出庭作證;因為出庭為當事人作證會受到助訴罪(maintenance)的懲罰,根據法官或陪審團命令作證的除外。到了17世紀,證人不適格問題開始出現,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不具有證人適格性的觀念被普遍接受。17世紀中期以后,這種觀念被牢固地確立下來。它的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不知情陪審團為了獲得真實的案件信息,做出客觀公正的裁決,渴望那些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的、也沒有偏見的證人向法庭提供證言;二是受羅馬法的影響,證人不適格規則早已在教會法訴訟中被普遍使用,這影響了英國。英國普通法中的證人不適格規則就是直接從教會法引進的。當事人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是顯而易見的,英國就效仿教會法,禁止當事人成為自己案件的證人。這一規則一直保留至19世紀中期。
19世紀初期,邊沁對證人不適格問題進行了批判。他的批判在英美法掀起了一場證據革命。英美法國家開始反思和改革與案件、案件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不適格作證的問題。1843年,英國通過了丹瑪勛爵法(Lord Denman’s Act)即《1843年證據法》,該法規定:任何人都不應該因涉嫌犯罪或與案件當事人有利害關系而被剝奪作證的資格;但是該人只有在宣誓后才能提供證詞。該法取消了與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無作證資格的規定。這是對證人不適格問題的第一次變革。1851年,英國又通過了《1851年證據法》,取消了民事當事人不具有證人適格性的規定。該法規定:民事當事人有資格也有義務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向法庭提供證言。1853年,英國再次通過法令取消了當事人的配偶不具有證人適格性的規定。該法規定:除非本法有特別規定,當事人的丈夫或妻子有資格和義務通過口頭或書面的形式向法庭提供證言。在英國法的影響下,美國也開始著手改革證人不適格的規定。1846年,密歇根州在民事案件中取消了與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不具有適格性的規定;1849年,康涅狄格州取消了民事當事人不具有證人適格性的規定;1864年,聯邦司法系統認可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具有作證資格;直到1885年,除了阿拉巴馬州、阿拉斯加州、特拉華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馬州、田納西州、德克薩斯州和維吉尼亞州之外,美國其他各州的司法管轄區均取消了證人不適格的禁止性規定。
在刑事方面,美國的改革步伐要比英國快一些。緬因州是英美法系第一個賦予被告人作證權的司法管轄區。早在1950年代,緬因州就賦予某些犯罪案件被告人的作證資格;1864年,又將作證資格賦予所有的被告人。在隨后的20年,除了喬治亞州之外,美國其他各州都確立了被告人的作證資格。聯邦司法管轄區也在1878年采納了這一規則。美國的變革對其他英美法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英國在《1898年刑事證據法》、加拿大在《1893年證據法》,新西蘭在《1893年刑事法典法》和《1908年證據法》,北愛爾蘭在《1923年證據法》,愛爾蘭共和國在《1924年刑事司法(證據)法》,印度在《1955年刑事證據(修正)法》中將作證資格賦予被告人。至此,被告人作證權制度在英美法國家全面確立。
二、英美法被告人作證權制度的理論根據一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
英美法廢除禁止民事案件當事人、刑事案件被告人及與他們有親密關系的證人作證的法律,是由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火花點燃的一場證據法革命。
英國普通法一直禁止被告人作證,主要是認為被告人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會導致被告人作偽證。邊沁批判了這種觀點。他認為與案件有利害關系并不必然導致利害關系人提供虛假的證言:法律人要在可信與不可信、可聽與不可聽、有利害關系與無利害關系等問題上做出評價,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更不要說作出選擇了。如果必須要做出選擇,那么持“受利害關系影響的那些人不會說真話”的說法要比持“受利害關系影響的那些人不會說假話”的說法更荒謬。你可以總是確信某人或任何人會受各種抑制說謊型動機(mendacity—restrainingmotives)影響的支配,但你不可能總是確信某人或任何人會受各種激勵說謊型動機(mendacity—pro—moting motives)影響的支配。如果你確信某人或任何人會受各種激勵說謊型動機影響的支配,那么,是否就可以推斷出那就是他說謊的理由?倘若是這種隋況,那么確實存在的說謊危險是否必將威脅到確定性?如果確實如此,不只是應該把某些證人關在作證的大門外,對任何人都不應該敞開大門。某種利害關系確實會影響某人違背他的職責行事,但是,你能認為他們就是在服從于他們的動機嗎?可見,人們行事的方向取決于影響行為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誰占上風。實際上,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有某種感性的力量在影響行為的方向。邊沁否認動機對行為的決定作用,因利害關系產生的說謊動機,并不必然導致證人說謊。因此,不能因為有利害關系就認為某人不具有作證資格。邊沁的上述批判實際上體現了這樣一個觀點,即證人撒謊的動機只涉及證言價值,與它的可采信無關。與案件結局有利害關系只可能導致證言證明力的削弱,而不會造成證據方法的不適格。
因利害關系導致證人(包括被告人)的不適格是當時證據排除規則中的一種。邊沁一直都對整個證據排除規則持否定態度。他認為證據排除規則是一種極其糟糕的救濟措施,因為證據排除可能會導致錯誤的判決。發現真實的惟一模式就是看見能夠看見的;盡可能地從那些了解案件的人那里去聽見能夠聽見的;特別是或者首先是從那些對案件最知情的當事人那里去聽取事實;這種發現真實的模式,不論是在現在還是在將來,不論是在村舍還是在宮殿,不論是在家庭還是在法庭,都是完全相同的。邊沁從發現真實模式的惟一性視角批駁了不切實際的排除規則。針對排除規則,邊沁還認為,雖然證據是虛假的,但證據的虛假性可能會被法官發現;拒絕這類證據進入法庭,會導致錯誤的裁判。被允許進入法庭提供證言的證人,不管他是否被人們相信,我們要看結果。陪審團可以看見證人,也可以聽到證人證言的全部內容;他們可以聽到控辯雙方對證人的交叉詢問,可以親自對證人進行詢問;如果有其他證人,陪審團還可以聽到他們的證言;另外,陪審團也可以看到被告人和指控者到底長什么樣,到底說了些什么。總之,陪審團可以看見整個案件的全貌。由于某些原因就排除證人的作證資格,那么,陪審團就會對被告人和指控者想說的內容一無所知,對案件也就一無所知。防止說謊證人進入法庭可能導致錯誤判決的救濟措施有很多。陪審團鑒別真偽的睿智,法官鑒別真偽的睿智,辯方律師和控方律師有更超強的鑒別真偽的能力,這些都是正確裁判的有效保障。邊沁從人的洞察力視角,駁斥了古老的證據排除規則。邊沁還認為,排除被告人作證還會導致其他證明力低或者品質不好的證據進入法庭,以替代被告人這種證據方法。比如,被告人的庭前自白。這種證據是傳聞證據,通常都是在沒有給被告人解釋和修正機會的情況下被采信的。并且,在采信這種證據時,法官通常會尋找其他補強證據來增強自白的證明力。這必然導致訴訟延遲或者訴訟負擔。
對被告人作證資格的論述,充分體現出邊沁關于證據法的功利主義思想。他認為:“從應然的角度來看,法律的目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為最大多數的人提供幸福。無論是好法律還是壞法律,它們只能通過創造權利和義務來運作”。在這里,邊沁所指的法律是實體法。為了保障實體法的有效執行,立法者在證據立法時有兩點必須注意:其一,法律應該能夠確保有充足的證據去支持訴訟中爭議的權利或義務;亦即不能因為缺乏或者沒有證據而導致不能做出判決。其二,法律應當保障法官不受虛假證據的欺騙。如何做到這些?邊沁認為,法律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保障證據本身有最大的證明力。因此,立法者不應當隨意地排除證據,以免錯誤的裁判。
三、英美法被告人作證權制度的基本內容
(一)被告人應當在庭審的什么時段作證
在英美法的法庭上,被告人只能作為辯方證人,并在辯方舉證階段作證。這是被告人作證的一項基本規則。為什么被告人不能作為控方證人?因為被告人不具有控方證人的資格始終是普通法的一項規則。普通法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規定?因為,在19世紀中后期被告人取得作證權時,不得強迫自證己罪的觀念就已經深入人心。如果讓被告人成為控方證人,必然會違背該原則。19世紀英國的判例法也明確表明了被告人在訴訟中只能作為辯方證人。
被告人應當在庭審程序的什么階段作證?根據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辯方始終只能在控方舉證結束或者控方案件結束之后舉證,所以,被告人也只能在辯方舉證階段作證。如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第1條第1款規定,“任何被指控的人……,在刑事訴訟的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成為適格的辯方證人,不論單獨被指控還是與其他被告一起被指控”;“除非依其申請,任何被指控的人都不可以被傳喚作為證人”。在辯方舉證階段,被告人又應該在什么時段作證呢?根據該法第2條的規定,“辯方傳喚的目擊證人如果是被指控者,他應當在控方舉證完畢之后立即被傳喚作證”。可見,被告人只能以辯方第一證人的身份作證。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9條也規定:“在刑事審判中,如果辯方打算傳喚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證人作證,其中包括被告人的,除非法院有其他指示,被告人應當在其他證人之前作證”。英國的判例法也明確表明了這種立場。
為什么被告人必須以辯方第一證人的身份作證?英國法官認為,“這樣做的理由十分明顯:如果允許被告人在作證之前旁聽其他證人的證言,那會誘使被告人修飾、裁剪他的證言”。美國法官也認為,“因為被告人在審判中始終有在場權,而不會像其他證人一樣在作證前被隔離。所以判例和法令要求被告人必須在其他辯方證人作證之前作證,這是一種減少對被告人不利影響的替代措施”。可見,被告人以辯方第一證人的身份作證是被告人在場權與證人隔離規則之間平衡的結果。1972年,美國改變了這一傳統做法,賦予被告人有在辯方舉證的任何時段作證的選擇權。
(二)對被告人的交叉詢問及對其前科的調查
交叉詢問是英美法對證人證言進行調查的一種重要手段。當被告人自愿走上證人席,適用于一般證人的交叉詢問規則也適用于被告人。但是也有例外。第一個例外是,被告人在作證時不受不得強迫自證己罪特權的保護,控辯雙方對其提出的問題有回答的義務。如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第1條第(5)規定:“被指控的人如果作證,在反詢問中必須要回答任何問題,即使該問題可能證明其犯有本案被指控的犯罪”。美國最高法院在判例中也做出了相同的規定。
第二個例外是,在交叉詢問的過程中可以對被告人的品格進行調查,但調查受到嚴格限制。根據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608條、第609條的規定,只有在證人的可信性受到攻擊之后,才可以對證人的品格、特定行為和先前定罪的情況進行調查。可見,對證人品格等的調查,在啟動程序上并沒有太嚴格的限制,通常表現在:控辯雙方可以在反詢問中提出不良品格證據對證人可信性予以彈劾,在第二輪主詢問中提出良好品格證據對證人的可信性予以恢復。但是,對被告人品格證據的調查卻有嚴格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限制對被告人的品格(包括犯罪前科)進行調查。比如,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第1條第(6)規定:“被指控的人如果作證,不應該被問及,如果被問及也不得被要求回答任何傾向于表明其已經實施了本案以外的犯罪,或者曾經因本案以外的犯罪定過罪,或者已經被指控本案以外犯罪的問題;也不應該被問及,如果被問及也不得被要求回答任何傾向于表明其不良品格的問題”。
第二,在例外情況下,可以對被告人的品格證據進行調查,但啟動程序受到嚴格限制。比如,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第1條第(6)規定,只有在三種情況下可以提出調查被告人的品格:(1)被告人的前科對本案的犯罪有證明力,即證明被指控者已經實施了本案以外的犯罪或者證明曾經因本案以外的犯罪定過罪的可采性證據,可以證明本案的犯罪;(2)被指控者自己或者其辯護律師為了證明其具有良好品格,對控方證人進行詢問,或者向法庭提供其良好品格的證據;或者辯護行為的性質和辯護行為本身對指控者的品格或者控方證人的品格構成責難;(3)被指控者向法庭提供對其他同案犯不利證言時。可見,控方一般不得首先或主動提出對被告人的品格證據進行調查。
(三)對被告人沉默的不利評價或推論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強迫自證己罪”條款規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為不利于自己的證人”。這是美國關于沉默權原則的規定。除了沉默權的宣示性條款之外,美國還禁止控方和法官對被告人的沉默做出不利評論或推論。在格里芬訴加利福尼亞州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認為,不得因被告人行使憲法保障的沉默權而作出有罪推論,檢察官不得因為被告人沉默而向陪審團發表評論,也不得要求陪審團推斷被告人不作證的惟一原因就是因為他有罪;如果被告人向法官提出了請求,法官必須指示陪審團不得作出這樣的結論,否則就違反了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第1條第1款也規定,被告人不僅可以在刑事審判中成為辯方證人,而且除非根據被告人的申請,任何人不得傳喚其成為證人。這是英國關于沉默權的規定。與美國法不同,英國法只禁止控方對被告人不作證的行為做出不利評論,卻允許法官對被告人的沉默做出不利評論。根據《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第35條、36條、37條的規定,法官或者陪審團還可以對被告人庭審中的沉默行為做出不利推論。
(四)被告人作證時的真實義務
被告人在庭審中的沉默權只適用于是否選擇作證;如果被告人選擇了作證,他在作證過程中拒絕回答問題,將受到藐視法庭罪的處罰;如果在宣誓后做虛假陳述將受到偽證罪的處罰。在哈里斯訴紐約州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每一個被告人都有權為自己作證,或者拒絕為自己作證。但是被告人的這種特權并不能被視為他有作偽證的權利。如果他自愿作0iv+O/Hhg9fQZ9u00+d4b6xj9lswrnOhsR8+3lUSilI=證,他有義務講真話;控方有權對其進行反詢問以便發現真實。可見,英美法的被告人在選擇作證之后有如實陳述的義務,亦即被告人在作證時有真實義務。
四、英美法對大陸法的影響——新型混合式訴訟中被告人調查程序的結構性變化
在訴訟制度的發展過程中,英美法的庭審結構對大陸法的影響主要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在變革糾問式訴訟的過程中,借鑒和引進了英國的陪審團審判程序,形成了職權主義訴訟。職權主義訴訟的特點就是在審前階段保留了糾問式,在審判階段引進了當事人主義的一些庭審方式,比如公開審判、法庭辯論、辯護制度等。第二次重大影響發生在二戰之后的日本,以及近三十年來在意大利、俄羅斯、我國臺灣地區發生的改造職權主義訴訟的運動。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進行的庭審方式改革,都以引進和借鑒英美當事人主義庭審結構為主要內容,形成了新型混合式庭審結構。在英美法第一次影響大陸法時,被告人的作證權制度尚未形成,職權主義庭審調查被告人的模式仍然保留了糾問式的風格,通常稱為“職權調查”模式。在英美法第二次影響大陸法時,對被告人庭審調查模式的改革是新型混合式庭審結構變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英美法的影響下,新型混合式庭審結構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被告人調查程序,主要表現在:
第一,被告人在法庭調查程序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改變。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新型混合式庭審中,日本、意大利和俄羅斯一改職權主義時期的做法,將法官首先訊問被告人的權力交給了辯護人。如日本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對被告人“先由法官來訊問,但通常的順序與詢問證人一樣,辯護人先對被告人發問,然后檢察官提出反問,再由法官補充發問”。意大利刑事訴訟法也規定,辯護人可以首先詢問被告人。俄羅斯刑事訴訟法規定,首先詢問被告人的是辯護人和辯方的法庭審理參加人,然后是國家公訴人和控方的刑事訴訟參加人;法庭在控辯雙方詢問被告人之后提問。這種變化說明被告人不再是法庭的證據方法而是辯方的證據方法。與當事人主義一樣,新型混合式庭審中的被告人也具有了黨派性。這表明證據調查程序的對抗性較之以前有所增強,新程序加強了對被告人的保護,無罪推定原則得到了較徹底的貫徹。
另一方面,新型混合式訴訟國家或地區在將庭審方式轉向當事人主義的過程中,把對被告人的調查移至證據調查階段,改變了法庭在調查其他證據之前首先調查被告人的職權主義做法。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在控辯雙方證據調查完畢之后,如果被告人表示愿意陳述的,法官、檢察官、共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質問被告人”。意大利刑事訴訟法也規定,在對證人、鑒定人、技術顧問調查之后對當事人進行詢問;如果被告人和其他當事人愿意接受調查的,被告人應當最后接受詢問。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將對被告人的詢問作為證據調查的一個部分。我國臺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將對被告人的調查放在了證據調查的最后。這種做法雖然使調查被告人程序失去了原先的獨立程序地位,但由于對被告人的調查被安排在控方證據調查結束之后,或者被安排在其他所有證據被調查之后進行,因此被告人的訴訟地位較之以前卻有了較大的提高。
第二,對被告人庭審調查實行“交叉詢問+職權訊問”模式。這種模式既有當事人主義的特征,也有職權主義的特征。交叉詢問是典型的當事人主義調查模式,而職權訊問是典型的職權主義調查模式。但是,在日本、俄羅斯和意大利新型混合式被告人調查程序中,這兩種調查方式并存。首先是控辯雙方對被告人的交叉詢問,最后才是法官的職權訊問。新型混合式訴訟雖然在對被告人的調查時引進了交叉訊問,但是并沒全面引進相應的證據規則,而且在審判程序中仍然實行職業法官審理,因此,對被告人實行交叉詢問,象征意義要大于實質意義。另外,引進了當事人主義的交叉詢問,也不意味著新型混合式庭審中對被告人的詢問程序就完全成為對抗制模式了。因為一方面,法官會在控辯雙方交叉訊問之后行使職權訊問權,以彌補交叉詢問的不足,澄清尚未澄清的地方;有時甚至會直接打斷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插入職權訊問;另一方面,新型混合式庭審并沒有建立起庭審中的公訴審查制度,使控方案件始終成為庭審的焦點。這說明當事人主義所奉行的嚴格的證明責任分配機制在新型混合式庭審中并沒確立起來。這也是新型混合式訴訟庭審控辯對抗不如當事人主義的重要原因。
第三,對被告人犯罪前科的調查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型混合式庭審中,由于被告人辯方證據方法的角色較之職權主義時期得到了強化,通常對被告人犯罪前科的調查也是通過對控方證據的調查來實施的。但是新型混合式訴訟與職權主義訴訟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沒有像當事人主義,在實行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完全分離的情況下,仍然保留了職權主義時期定罪活動和量刑活動在一個程序中進行的做法,只是在證據調查階段和法庭辯論階段將量刑證據(或情節)放在定罪證據調查(或辯論)之后調查(或辯論),實行了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的適當分離。如日本就規定,在開庭程序中,核實被告人身份“一般要核實起訴書記載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職業、住所、原籍等內容”,不再包括對被告人前科的調查。對量刑所需前科的調查,除無爭議案件外,應當在證據調查的最后,即訊問被告人之后進行調查。我國臺灣地區新刑事訴訟法,也將對被告人的事物訊問移至證據調查的最后,在訊問被告人之后再行科刑資料的調查。
五、對我國庭審方式改革的借鑒意義
(一)我國“控辯式”庭審中被告人調查程序存在的問題
1996年,我國為了改變庭審程序“走過場”的情況,強化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舉證責任,借鑒了英美當事人主義庭審結構,在庭審程序中引進了一些對抗制的要素,形成了獨特的“控辯式”庭審方式。這種新型的混合式庭審結構雖然增強了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對抗性,但在調查被告人的程序中卻存在著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第一,我國法庭調查被告人程序,嚴重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有“有罪推定”之嫌。在英美法國家,被告人只能做辯方證人,不能成為控方證人,所以他始終都是辯方的證據方法,在作證時由辯護律師進行主詢問。這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要求。但是,在我國,法庭上首先對被告人進行直接訊問的不是法官而是公訴人。這表明被告人不再是法庭的“被告人”,而是控方的“被告人”。被告人接受公訴人訊問是為了證明控方的指控,實際上,這是讓被告人自證己罪,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
第二,我國法庭調查被告人程序,違反了控辯平衡的原則,直接使被告人淪為控方的證據方法。現代刑事訴訟無論是大陸法還是英美法都強調控辯之間的平衡。控辯平衡強調平等武裝,權利義務對等。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控辯之間的積極對抗才能夠形成。現在,公訴人可以強制性地直接訊問被告人,并將被告人作為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犯罪成立的首要證據方法,這毫無疑問是將被告人作為證明控方案件成立的最重要的手段。這嚴重背離了控辯平等對抗的原則。
第三,我國法庭調查被告人程序,違反了刑事案件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使被告人承擔主要的證明責任。在刑事訴訟中,實體問題的證明責任由控方承擔,被告人既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也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即使在大陸法和英美法都存在著被告人在某些案件中因提出積極抗辯(如犯罪時精神不正常、不在犯罪現場、正當防衛等)而承擔證明責任的情形,但是這些都屬于例外;而且,在這些案件中,被告人承擔的證明責任都屬于證明自己無罪或罪輕的責任,不會被要求承擔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然而,現行法卻直接將被告人置于控方強制訊問之下,而且是首先接受調查的對象,這實際上是讓被告人承擔證明自己有罪的主要責任,違反了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二)英美法被告人作證權制度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我國控辯式庭審中被告人調查程序的設置,已經違反了各國進行刑事訴訟都應當遵循的一些普適性原則。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國家實行的是典型的對抗制庭審。這種庭審方式經過若干世紀的實踐才最終形成,在程序結構上完全貫徹了無罪推定原則、證明責任分配原則和平等對抗原則的要旨,成為大陸法改革庭審方式的范本。就目前而言,我國控辯式庭審方式的改革方向與日本、意大利、俄羅斯等國一樣仍然是趨當事人主義的。因此,英美法庭審程序中的一些基本結構,在我國完善庭審方式時仍然值得借鑒。參照當事人主義和新型混合式訴訟的模式,筆者認為,在庭審調查被告人程序的改革中,程序結構的改革重心應當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改變調查被告人在證據調查程序中的時段。現行法規定被告人是法庭調查的首要證據方法,這一地位應當被改變,將對被告人的調查移至證據調查階段,并將其作為辯方的證據方法。這一思路與新型混合式庭審程序的設置相符。現在的問題是,被告人應當在證據調查的哪個時段接受調查比較合適?從英、美兩國的差異來看,英國將被告人作為辯方第一證據方法,目的是為了避免被告人受其他辯方證人影響,追求的是被告人證言的真實性。美國法把被告人作證的時段交給辯方直接選擇,強調的是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就目前我國現狀而言,筆者認為,英國的做法比較符合我國國情。1996年以來,隨著我國控辯式庭審方式的推進,人權保障的觀念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程序公正雖然被司法人員普遍認可,但到目前為止它并沒有成為社會觀念中的主導性價值。在這種狀況下,刻意地去追求對被告人權利保障的完美性,不僅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甚至會引起實踐部門的抵制。新《律師法》的運行狀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第二,在證據調查程序中,應當實行“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適當分離。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分離是典型的當事主義的庭審結構。這種“二步式”庭審結構的形成與英美法對抗制訴訟的司法傳統密切相關。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分離對被告人調查程序的改革有重大影響。如果能夠實現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徹底分離,對被告人犯罪前科的調查,就應當在量刑程序中進行。這樣就不會制約被告人在定罪程序中有效地行使辯護權和沉默權。
但是,我們應該像英美法那樣實行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完全分離,還是應該像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那樣實行“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適當分離?筆者認為,后者比較適合我國的國情。因為在“一元審判主體”的結構模式下,“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完全分離,就意味著同一審判主體要進行兩次庭審,這種做法很不經濟。而且,英美法實行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嚴格分離,主要是為了防止陪審團在定罪時受到量刑證據的不當影響。我國并沒有陪審團審判,大多數刑事案件都由職業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進行審理,在這種狀況下,實行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完全分離,意義不大。
第三,被告人作為證據方法時應當科以真實義務。在對被告人進行調查時,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新型混合式訴訟最大的區別,就是被告人在作證時有真實義務。主要表現在:被告人在選擇作證后要宣誓,不受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特權的保護,在反詢問中對控方的提問必須如實回答,如果被告人拒絕回答問題將受到藐視法庭罪的處罰,如果故意作虛假陳述將受到偽證罪的懲罰。而在職權主義和新型混合式訴訟中,被告人在放棄沉默權接受調查時,沒有法律上的真實義務:法律不要求被告人在陳述前宣誓,對被告人作虛假陳述的行為法律上也沒有任何處罰措施。雖然實踐中,被告人的偽證行為會影響法官的信任,在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被法官視為沒有悔罪表現,成為從重處罰的根據,然而這僅僅是“潛規則”,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通常,我們講證據有三性:客觀性、相關性和合法性。其中,“證據的客觀性,是指證據事實必須是伴隨著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而遺留下來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存在的事實。”在證據客觀性的概念中包涵了真實性價值的判斷。“沒有任何客觀存在為依據的任何一種陳述,是理所當然的謊言,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從這種意義上講,客觀性就是審查判斷證據的一條基本標準。”由于人證的特殊性,證據信息在人的大腦進行輸入和輸出的過程中,比物證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響。為了保證證據信息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法律通常會對作為證據信息載體的人提出要求,比如要求證人要如實陳述案件事實,否則將承當偽證罪的責任。英美法要求所有的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狹義的)證人和鑒定人,只要向法庭提供證據信息,必須要對證言的真實性進行宣誓,并以偽證罪作為威懾,這種做法完全符合證據客觀性或者真實性的要求。
在我國,被告人在陳述時應當科以真實義務,這樣做有利于沉默權制度的確立。沉默權是國際人權公約倡導的一項基本人權。我國也早已成為世界上的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沉默權制度在我國刑事司法制度中至今尚未確立。為什么會如此?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害怕沉默權會阻礙司法機關發現案件真實。筆者認為,國際社會公認的被告人在刑事司法中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權利應當得到保障;同時,我們也不應當不顧國情,賦予被告人過度的防御權而阻礙了案件真實的發現。基于這樣的思路,筆者認為,我國在賦予被告人沉默權時,必須要強調被告人放棄沉默權后的真實義務,即被告人在放棄沉默權后應當如實陳述,否則要承擔一定法律后果。這樣做既貫徹了無罪推定原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也兼顧了司法機關發現案件真實的能力,更容易被目前的社會所接受。
參考文獻:
[1]陳光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304.
[2]L J.Wigmore.A TreMise 0n the Anglo-AmericaanSystem of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M].2nd ed.Boston:Little Brown Company,1924:375,986—1002.
[3]5 Jeremy Bentham.RmionMe of JudiciM Evidence[M].London:Published by Hunt and Clark,1827:36-40.
[4]理查德·梅.刑事證據法[M].王麗,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27.
[5]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M].張凌,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37.
[6]樊崇義.證據法學[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