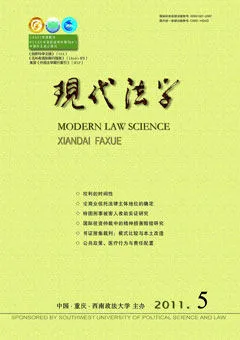書(shū)證搜集裁判:模式比較與本土改造
摘要:引入兩大法系共通的書(shū)證搜集裁判,有利于解決我國(guó)當(dāng)事人提交書(shū)證能力不足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在裁判模式上,大陸法系和美國(guó)在基本問(wèn)題上達(dá)成共識(shí),其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適用范圍大致相似,并且裁判本身都在解決糾紛過(guò)程中發(fā)揮決定作用。在裁判效果上,妨礙書(shū)證搜集的一方應(yīng)當(dāng)在不同情況下分別于證據(jù)、事實(shí)、請(qǐng)求和程序?qū)用娉袚?dān)不利后果。從現(xiàn)有制度出發(fā),法院依申請(qǐng)取證制度應(yīng)當(dāng)引入比較法上書(shū)證類(lèi)型的共識(shí)并且區(qū)分法官的裁判義務(wù)事項(xiàng)和自由裁量事項(xiàng),同時(shí)從條件和過(guò)程兩方面控制法官的裁量權(quán),強(qiáng)調(diào)以裁判的形式加以保障。我國(guó)《證據(jù)規(guī)定》第75條正是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現(xiàn)行法基礎(chǔ),有必要重塑和細(xì)化其規(guī)范要件,并且建構(gòu)層次清晰的裁判效果體系。
關(guān)鍵詞:書(shū)證搜集裁判;文書(shū)提出命令;證據(jù)開(kāi)示;申請(qǐng)取證;證明妨礙;《民事訴訟法》修改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F71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5.15
一、引言
證據(jù)制度一直是司法改革的熱點(diǎn),也是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點(diǎn)領(lǐng)域。特別是在當(dāng)事人承擔(dān)舉證的法定負(fù)擔(dān)、不得不積極主動(dòng)收集散落各處的證據(jù)材料以滿足法官對(duì)要件事實(shí)證明的要求時(shí),證據(jù)持有與主觀證明責(zé)任的承擔(dān)相分離(“證據(jù)偏在”)的矛盾更加凸顯:如果掌握關(guān)鍵證據(jù)的當(dāng)事人拒絕分享證據(jù)信息,應(yīng)當(dāng)證明要件事實(shí)存在的對(duì)方當(dāng)事人必將無(wú)法舉證并因此承擔(dān)敗訴后果;同時(shí),囿于辯論主義的約束,法庭也將無(wú)法獲得充分的裁判依據(jù),這將對(duì)司法發(fā)現(xiàn)真相和解決糾紛的功能直接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這一矛盾重點(diǎn)體現(xiàn)在一般情況下證明作用直接、證明載體相對(duì)穩(wěn)定、同時(shí)爭(zhēng)議頻發(fā)的書(shū)證上。目前,我國(guó)現(xiàn)行法主要通過(guò)法院依職權(quán)或依申請(qǐng)取證制度加以應(yīng)對(duì)。但是,這項(xiàng)制度的具體標(biāo)準(zhǔn)相對(duì)抽象,在賦予法官過(guò)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以致減損當(dāng)事人取證權(quán)的同時(shí),也使當(dāng)事人主義下的自己責(zé)任機(jī)制喪失司法正當(dāng)性。
事實(shí)上,由于證據(jù)在當(dāng)事人間的物理分布不可能與請(qǐng)求權(quán)構(gòu)成要件完全對(duì)應(yīng),搜集書(shū)證時(shí)的信息不對(duì)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wèn)題是非常普遍的。為了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兩大法系國(guó)家和地區(qū)在制度和實(shí)踐中都試圖以民事裁判為載體,引入了某種針對(duì)書(shū)證的證據(jù)收集手段(大陸法系的文書(shū)提出命令和美國(guó)法證據(jù)開(kāi)示程序中的裁定)。在不違背居中裁判底線的前提下,各國(guó)法官均會(huì)在一定條件和程序下發(fā)出書(shū)證搜集裁判,為一方的證據(jù)攻堅(jiān)戰(zhàn)提供助力。近年來(lái),學(xué)界對(duì)相關(guān)制度問(wèn)題已有較多討論,對(duì)于比較法的相關(guān)知識(shí)已經(jīng)有了較為豐富的論述,但是在訴訟理論的角度上仍有所不足。本文試圖在概要厘清各典型模式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從功能意義上提取各種制度間的公因式,對(duì)深化裁判理論和解決取證難等實(shí)踐問(wèn)題提供有益指引。
值得補(bǔ)充說(shuō)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場(chǎng)域。本文主要將書(shū)證搜集裁判置于較為正式的普通訴訟的語(yǔ)境下,并以商事訴訟為代表。從司法統(tǒng)計(jì)上看,商事訴訟在目前法院審判負(fù)擔(dān)中占有相當(dāng)大的比重,而且能夠代表一類(lèi)當(dāng)事人訴訟能力大致相當(dāng)、更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責(zé)任、一般爭(zhēng)議數(shù)額較大、糾紛對(duì)專業(yè)化處置的需求比較強(qiáng)烈的訴訟,因此也更接近比較法制度本來(lái)處理的對(duì)象。特別是,在整體司法改革方向微調(diào)、但前期成果已經(jīng)得到廣泛認(rèn)同和保留的當(dāng)下,處于繁簡(jiǎn)分流光譜中正式性一端的這類(lèi)案件仍構(gòu)成了司法改革的主要對(duì)象。同理,本文在程序分類(lèi)視角上所做的嘗試性研究,也服務(wù)于民事司法權(quán)優(yōu)化配置新模式的建構(gòu)。
二、提取公因: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模式選擇
總體而言,各國(guó)書(shū)證搜集裁判在制度、理念以及功能上相同遠(yuǎn)多于相異。無(wú)論是大陸法系還是美國(guó)制度,都大致體現(xiàn)了在權(quán)力/權(quán)利的配置與行使以及書(shū)證類(lèi)型上的基本共識(shí),摒除表面的差異,兩大法系對(duì)于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應(yīng)用大致相似。
(一)大陸模式
書(shū)證搜集裁判在大陸法系體現(xiàn)為文書(shū)提出命令,即法官依一方當(dāng)事人(主張方)的申請(qǐng),發(fā)布要求持有書(shū)證的另一方當(dāng)事人(相對(duì)方)提出該書(shū)證的命令。就德國(guó)、日本和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來(lái)看,大陸法系普遍賦予當(dāng)事人此項(xiàng)申請(qǐng)權(quán),并以相似的條件控制和過(guò)程控制維持權(quán)利的合理邊界。以德國(guó)為例,在條件上,一旦雙方對(duì)于一方是否應(yīng)當(dāng)提交書(shū)證產(chǎn)生爭(zhēng)議,主張方應(yīng)當(dāng)陳述所申請(qǐng)的書(shū)證及其內(nèi)容、文書(shū)的證明對(duì)象(要證事實(shí))、文書(shū)的證據(jù)能力和證明力(證明必要)、書(shū)證持有人以及相對(duì)人負(fù)有提出義務(wù)的理由。在過(guò)程上,法官需要在綜合判斷后就相對(duì)方義務(wù)是否存在的爭(zhēng)議做出判定,如果法官支持主張方,應(yīng)當(dāng)以裁判的形式發(fā)布文書(shū)提出命令。此時(shí),相對(duì)方提出書(shū)證的義務(wù)與主張方的權(quán)利就此產(chǎn)生,并且隨后經(jīng)由一般的訴訟進(jìn)程得以實(shí)現(xiàn)。因此,大陸法系整體呈現(xiàn)“裁判解紛-具體賦權(quán)-搜集書(shū)證”的進(jìn)路。
在整體共識(shí)之下,該模式內(nèi)部的書(shū)證搜集權(quán)利配置方式并不盡相同。作為《民事訴訟法》母本的德國(guó)法,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同時(shí)適用了程序和實(shí)體兩種規(guī)范:基于程序法規(guī)范,相對(duì)人應(yīng)提出其為舉證而引用的書(shū)證;實(shí)體規(guī)范則指向出賣(mài)人、受托人、合伙人、無(wú)限公司和兩合公司的有限責(zé)任股東等,而且后續(xù)判例也大大擴(kuò)展了《德國(guó)民法典》第810條較為概括的范圍限定。善于揚(yáng)棄的日本法則放棄了假手實(shí)體法的“曲線救國(guó)”,而走上了純粹程序法建構(gòu)的道路。程序法上書(shū)證類(lèi)型中的引用文書(shū)、權(quán)利文書(shū)、利益文書(shū)、和記載雙方法律關(guān)系的文書(shū),大致覆蓋了德國(guó)模式的內(nèi)容。此外,日本還創(chuàng)設(shè)了舉證的一般性義務(wù),規(guī)定除了具有免證特權(quán)或者為了保持文書(shū)商業(yè)價(jià)值、專供持有人使用的書(shū)證外,都屬于可被搜集的范圍。而在繼受前兩者的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相對(duì)人的提出范圍由引用文書(shū)、權(quán)利文書(shū)、利益文書(shū)、商業(yè)帳簿以及就與本件訴訟關(guān)系有關(guān)的事項(xiàng)所作的文書(shū)組成。其中第5項(xiàng)兜底條款為2000年的修法成果,修法理由認(rèn)為現(xiàn)代型訴訟中有必要擴(kuò)大文書(shū)提出義務(wù)范圍,故而擴(kuò)大了原條文本與德國(guó)實(shí)體規(guī)范相同的輻射范圍。近年來(lái),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法官主要通過(guò)對(duì)立法上商業(yè)秘密保護(hù)和訴訟中獲得信息的權(quán)利(證明權(quán))兩種價(jià)值的衡量,解釋兜底條款以維持書(shū)證范圍的合理邊界。
(二)美國(guó)模式
在平等武裝(equality of arms)和當(dāng)事人對(duì)抗(adversary system)的理念下,如果主張方無(wú)法占有必要的訴訟材料,民事訴訟將無(wú)法正常實(shí)現(xiàn)其糾紛解決功能。因此,更崇尚通過(guò)對(duì)抗實(shí)現(xiàn)正義的美國(guó)通過(guò)在程序法上發(fā)展證據(jù)開(kāi)示制度(Discovery),要求雙方容忍并配合對(duì)方搜集書(shū)證的需求,一開(kāi)始并不需要司法介入。只有雙方發(fā)生爭(zhēng)議時(shí),法官才得以出場(chǎng),并作出書(shū)證搜集裁判以確定是否需要開(kāi)示以及開(kāi)示范圍的大小。從整體上看,這套機(jī)制呈現(xiàn)出“抽象賦權(quán)一搜集書(shū)證一裁判解紛”的進(jìn)路。具體而言,《民事訴訟規(guī)則》規(guī)定了主張方必須特定地描述請(qǐng)求開(kāi)示的證據(jù),為持有方確定合理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和方式出示(比如復(fù)印文書(shū)),證據(jù)不一定具有可采性而只需有助于可采證據(jù)的開(kāi)示。
美國(guó)證據(jù)開(kāi)示規(guī)則分為兩個(gè)階段,規(guī)則也相對(duì)復(fù)雜。概括而言,在強(qiáng)制披露(disclosure)階段,除了在一些明文排除的訴訟類(lèi)型外,雙方當(dāng)事人都有義務(wù)預(yù)先提出能夠支持其主張或抗辯的全部書(shū)證(documents);在開(kāi)示階段,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要求對(duì)方提供未受到免證特權(quán)保護(hù)的、與其主張或抗辯相關(guān)的事項(xiàng),法院也有權(quán)要求當(dāng)事人開(kāi)示與訴訟標(biāo)的相關(guān)的事項(xiàng)(any matter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mat-ter)。美國(guó)證據(jù)開(kāi)示的范圍雖然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但是大致也能覆蓋大陸法系文書(shū)提出命令的內(nèi)容。
(三)小結(jié):殊途同歸
雖然各法域控制書(shū)證搜集權(quán)的立法進(jìn)路不同,但是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適用范圍大致相同。德國(guó)在法官適用過(guò)程中解釋實(shí)體法請(qǐng)求權(quán)以擴(kuò)張其適用范圍,并以類(lèi)型限定的方式試圖明確其邊界;日本和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在程序立法中引致實(shí)體法規(guī)范作為程序法上請(qǐng)求權(quán)的要件,并分別以一般性義務(wù)配合除外情形的方式和限縮解釋兜底條款的方式,緩和德國(guó)樣本在實(shí)踐中顯露出的不足;美國(guó)立足程序保障的方式,直接在程序法中委諸法官判斷,較少通過(guò)程序性制定法而側(cè)重強(qiáng)調(diào)正當(dāng)程序、精英法官以及晚近的“管理型審判”保證書(shū)證搜集權(quán)的正當(dāng)使用。無(wú)論如何,各個(gè)法域允許當(dāng)事人向?qū)Ψ剿鸭臅?shū)證范圍都大致相似。從結(jié)果上看,立足于各國(guó)較高層次的法官法教義學(xué)知識(shí)和成熟的裁判方法,無(wú)論具體的立法方式和法教義推演過(guò)程有何區(qū)別,各國(guó)當(dāng)事人均有權(quán)要求相對(duì)方提出書(shū)證,身處法律人共同體的法官在實(shí)際操作中也“冷暖自知”,在依職權(quán)裁量中極少逾越書(shū)證提出的合理邊界。有道是多歧路猶在,卻無(wú)一例外地通往燈火闌珊處尋的那個(gè)他。
特別重要的是,雖然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進(jìn)路不同,但書(shū)證搜集的裁判都在解決糾紛過(guò)程中發(fā)揮決定作用。在大陸法系,針對(duì)個(gè)案做出的裁判是申請(qǐng)方可以搜集證據(jù)的權(quán)利淵源,其書(shū)證搜集權(quán)在訴訟過(guò)程中才產(chǎn)生;在美國(guó),證據(jù)開(kāi)示中的書(shū)證搜集權(quán)則是雙方當(dāng)事人基于抽象成文規(guī)定自訴訟開(kāi)始時(shí)自動(dòng)擁有。但是,在這看似不同的制度表象背后是書(shū)證搜集裁判地位的共通性,即無(wú)論當(dāng)事人如何以及何時(shí)有權(quán)搜集他方持有的書(shū)證,司法行為的作用都是裁斷權(quán)利行使中產(chǎn)生的爭(zhēng)議。易言之,一旦證據(jù)持有方不愿提出書(shū)證(這恰恰正是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常態(tài)選擇),如果沒(méi)有解決糾紛的裁判行為,當(dāng)事人無(wú)論在哪種模式下都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其搜集書(shū)證的請(qǐng)求。
因此總體而言,各國(guó)制度在細(xì)節(jié)上雖具特色,但在基本問(wèn)題上實(shí)屬殊途同歸。
三、分層互動(dòng):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效果體系
如果拒絕履行書(shū)證搜集裁判所規(guī)定的內(nèi)容,即不提出裁判所涉及的書(shū)證,自當(dāng)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后果。在理論上,各國(guó)學(xué)界一般有證明責(zé)任倒置、證據(jù)評(píng)價(jià)、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等多種學(xué)說(shuō),同時(shí)也有學(xué)者關(guān)注了妨礙行為的可歸責(zé)性、證據(jù)價(jià)值等因素,并主張對(duì)案件進(jìn)行類(lèi)型化處理。在此基礎(chǔ)上,下文將根據(jù)當(dāng)事人主義在實(shí)體法、證據(jù)法和程序法上三個(gè)層次的劃分并進(jìn)一步將辯論主義展開(kāi)為事實(shí)和證據(jù)方面,結(jié)合其不同功能分析展開(kāi)拒絕提出證據(jù)的效果分層體系。
(一)四層構(gòu)造體系
裁判效果的第一個(gè)層次限于證據(jù)層面,即將書(shū)證內(nèi)容視為真實(shí)。德國(guó)法就停留在這一層面,根據(jù)德國(guó)《民事訴訟法》第426條和第427條規(guī)定,相對(duì)人如果拒不提出文書(shū)或者經(jīng)詢問(wèn)被法官認(rèn)定確實(shí)占有所涉文書(shū),將可能產(chǎn)生兩種效果:要么文書(shū)復(fù)本被視為正本(證據(jù)能力),要么主張方關(guān)于文書(shū)性質(zhì)及內(nèi)容的主張被認(rèn)為獲得心證(自由心證)。通說(shuō)認(rèn)為該項(xiàng)規(guī)定為自由心證的內(nèi)容,一般在結(jié)果認(rèn)定上對(duì)主張方較為有利。另外,在日本、美國(guó)和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這種類(lèi)型也都是效果體系中的基礎(chǔ)類(lèi)型。
其次是事實(shí)層面,即視待證事實(shí)為真實(shí)。這又可以細(xì)分為三個(gè)子類(lèi)。其一是日本模式。經(jīng)過(guò)1996年的修正后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24條第3款規(guī)定,法官在主張方表明文書(shū)內(nèi)容和以其他證據(jù)證明待證事實(shí)“顯著困難”兩個(gè)要件被滿足的情況下,有權(quán)將待證事實(shí)本身擬制為真。易言之,只有法官認(rèn)為在事實(shí)認(rèn)定上“無(wú)藥可抓”且實(shí)體保護(hù)主張方“天經(jīng)地義”時(shí)本條才能適用,使法官的裁量權(quán)在立法上受到了相當(dāng)嚴(yán)格的限制。其二是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模式。根據(jù)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款規(guī)定,法官擬制事實(shí)為真的裁量權(quán)并沒(méi)有額外限制(“審酌情形”即可)。但是,在解釋論上,學(xué)者們還是傾向于嚴(yán)格解釋并考慮更多的因素,如申請(qǐng)的對(duì)象和內(nèi)容,待證事實(shí)的證明難度,持有人的特殊情況,期待提出的可能性以及文書(shū)對(duì)訴訟的重要性等。其三是美國(guó)模式。美國(guó)也有指示陪審團(tuán)作不利事實(shí)推定(directing as estab-lished)的制度設(shè)計(jì),在獨(dú)立裁判事實(shí)問(wèn)題的陪審團(tuán)審判中,也可以達(dá)到將事實(shí)至少推定為真的效果。
再次是請(qǐng)求層面,此時(shí)將最為嚴(yán)厲地直接觸發(fā)訴訟程序終結(jié)的后果。在美國(guó),法官在綜合考慮相對(duì)方的主觀歸責(zé)要件和對(duì)主張方的損害程度之后,有權(quán)發(fā)布進(jìn)一步命令,采取包括駁回起訴(striking pleading)、即決判決(summary judgment)、不應(yīng)訴判決(default judgment)等手段懲罰當(dāng)事人不遵守證據(jù)開(kāi)示命令的行為。比如,在ComputerAssociate International v.American Fundware案中,被告在被送達(dá)起訴狀后仍然不斷更新涉及侵權(quán)軟件的源代碼,導(dǎo)致原告無(wú)法證明被告侵犯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官認(rèn)為被告的惡意行為是原告嚴(yán)重受害的原因,由于沒(méi)有其他手段足以懲罰和預(yù)防(punishand deter)類(lèi)似行為,應(yīng)當(dāng)直接通過(guò)不應(yīng)訴判決認(rèn)定被告侵權(quán)成立。
最后在程序?qū)用嫔希鲊?guó)立法參照例中還有其他程序性裁判也試圖達(dá)到類(lèi)似效果。除了立法上針對(duì)第三人但邏輯上也可以針對(duì)相對(duì)人的強(qiáng)制執(zhí)行標(biāo)的物和課以罰款措施外,還包括排除相對(duì)方提供的證據(jù)(exclusion of evidence)(對(duì)滿足了證明責(zé)任的本證方而言,如果拒絕提出被認(rèn)為足以將事實(shí)認(rèn)定推回到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的文書(shū),法官可以裁定排除其原本提出的有證明力的證據(jù);對(duì)反證方而言,如果拒絕提出被認(rèn)為足以使法官獲得事實(shí)存在心證的文書(shū),法官裁定排除其提出的反證)、訴訟中止(staying further proceedings)(以便等待相對(duì)方提出文書(shū)再進(jìn)行訴訟,避免對(duì)主張方造成進(jìn)一步損害)、作為藐視法庭罪追究責(zé)任(目前專屬于普通法系)、以及責(zé)令相對(duì)方負(fù)擔(dān)費(fèi)用(以便補(bǔ)償主張方和遏制相對(duì)人違法行為)。
(二)體系內(nèi)部互動(dòng)
如前所述,當(dāng)一方當(dāng)事人拒絕提出涉案證據(jù)時(shí),法官有權(quán)考量其(不)作為行為的主觀惡性、所涉法益大小以及對(duì)程序的影響,相應(yīng)做出發(fā)揮證據(jù)、事實(shí)、請(qǐng)求或其他程序?qū)用嫘Ч臅?shū)證搜集裁判。其中,效果體系的前三個(gè)層面分別對(duì)應(yīng)訴訟的證明手段、事實(shí)依據(jù)和權(quán)利主張/抗辯,隨著后者對(duì)于程序進(jìn)程意義的愈發(fā)重大,前者對(duì)訴訟活動(dòng)的干預(yù)程度也就逐漸增強(qiáng)。當(dāng)然必須承認(rèn),如果關(guān)注實(shí)務(wù)上的差別,各層面的做法可能并沒(méi)有司法技術(shù)上對(duì)效果強(qiáng)弱的區(qū)分那樣涇渭分明。比如至少在效果上,解決事實(shí)真?zhèn)蔚氖聦?shí)層面與早期終結(jié)訴訟的請(qǐng)求層面的差別并不明顯:由于待證事實(shí)情況復(fù)雜,一旦法官認(rèn)定了相對(duì)方的過(guò)錯(cuò)和因果關(guān)系,侵權(quán)行為基本上已經(jīng)得到證明,此時(shí)在判決實(shí)際結(jié)果上與直接判其敗訴并無(wú)兩樣。
同時(shí),各層面之間也是相輔相成的。一定類(lèi)型設(shè)置對(duì)應(yīng)著一定功能考量,而一種功能的滿足卻可能導(dǎo)致其他消極影響,實(shí)際上單一層面的舉措都無(wú)法解決全部的問(wèn)題。證據(jù)層面的主要目的是“回復(fù)”,即補(bǔ)償主張方因相對(duì)方不法行為造成的不利益,但同時(shí)也會(huì)導(dǎo)致文書(shū)內(nèi)容空洞、證明力的降低甚至鼓勵(lì)當(dāng)事人拒絕提出證據(jù);事實(shí)層面的主要功能是“預(yù)防”或“懲罰”,雖然能使讓心存僥幸的相對(duì)方承擔(dān)比實(shí)際提出文書(shū)更大的風(fēng)險(xiǎn),但也可能導(dǎo)致主張方因他方違法行為獲利、有違真實(shí)發(fā)現(xiàn)以及傾斜實(shí)質(zhì)正義天平,并進(jìn)而由證據(jù)搜集領(lǐng)域僭越至對(duì)自由心證主義的動(dòng)搖;請(qǐng)求層面的功能兼具兩者,一方面補(bǔ)償主張方程序上的損害,另一方面預(yù)防并懲罰相對(duì)方的嚴(yán)重違法行為,但是否過(guò)于嚴(yán)厲并適合多數(shù)案件,更是不無(wú)疑問(wèn);至于其他程序性裁判,多基于具體個(gè)案情況靈活發(fā)揮,在制度框架中雖不占核心地位,但也有其在特殊情況下的功效。
四、本土路徑:關(guān)注裁判技術(shù)的修法方向
相較考察不同模式確立的背景和原因,筆者更關(guān)心在我國(guó)語(yǔ)境下的具體司法技術(shù)問(wèn)題,特別是在當(dāng)下《民事訴訟法》修改如火如荼之際,后者的意義更為重大深遠(yuǎn)。考慮到我國(guó)一貫的法律傳統(tǒng)、與現(xiàn)行法律體系的銜接與過(guò)渡、當(dāng)事人對(duì)于訴訟整體成本的容忍力以及社會(huì)對(duì)法官的信賴程度,保持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無(wú)疑是最好的選擇。
(一)模式:以法官依申請(qǐng)取證制度為基礎(chǔ)
在作為超職權(quán)主義“罪證”之一、幾乎沒(méi)有制約的法官依職權(quán)調(diào)取證據(jù)制度逐步退出歷史舞臺(tái)之后,證據(jù)偏在結(jié)構(gòu)下的書(shū)證搜集主要依靠當(dāng)事人訴權(quán)和自我決定基礎(chǔ)上的法官依申請(qǐng)調(diào)取證據(jù)制度。目前,我國(guó)現(xiàn)行法逐步完善了對(duì)其中“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的解釋,學(xué)者專門(mén)探討了證據(jù)收集或調(diào)查制度的框架和具體問(wèn)題,《民事訴訟法典專家修改稿》第144條也明確建議法院有依申請(qǐng)要求書(shū)證持有人提交書(shū)證的職權(quán)。顯然,法律共同體早已意識(shí)到這些問(wèn)題的重要性,并試圖在立法和司法解釋上予以解決。
但是,現(xiàn)有制度面臨的困境與不足也是顯而易見(jiàn)的。雖然相關(guān)規(guī)定希望克服超職權(quán)主義的不當(dāng)影響,但是其規(guī)則設(shè)計(jì)并未對(duì)所謂“客觀原因”做出進(jìn)一步的細(xì)化解釋,因而難以抑制實(shí)踐中可能出現(xiàn)的兩種情形:一種是法官在案外因素介入時(shí)隨意通過(guò)擴(kuò)大解釋,向一方當(dāng)事人不當(dāng)傾斜并擴(kuò)大調(diào)查范圍;另一種是法官在案件過(guò)載壓力或其他因素影響下,恣意拒絕確有協(xié)助搜集必要的案件(比如日益復(fù)雜的商事交易)中當(dāng)事人的舉證申請(qǐng)。因此,為了發(fā)現(xiàn)真相并維護(hù)實(shí)體正義,類(lèi)型化書(shū)證搜集制度并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實(shí)屬證據(jù)制度改革的重點(diǎn)之一。
那么,我國(guó)應(yīng)采取何種進(jìn)路加強(qiáng)當(dāng)事人搜集書(shū)證能力呢?從功能視角出發(fā),單純引入外國(guó)法上的文書(shū)提出命令或證據(jù)開(kāi)示制度并非本文的研究目的,關(guān)鍵在于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有制度框架盡可能少的變動(dòng)來(lái)實(shí)現(xiàn)類(lèi)似功能。于是,考慮到前述比較法共識(shí)和我國(guó)的制度基礎(chǔ),筆者認(rèn)為問(wèn)題可以轉(zhuǎn)化為:如何將現(xiàn)行法缺失的書(shū)證類(lèi)型共識(shí)嵌入既有的依申請(qǐng)調(diào)取證據(jù)制度,進(jìn)一步明確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的控制方式,特別以裁判形式加以程序保障。
因此,解決問(wèn)題的第一步即引入上述書(shū)證類(lèi)型共識(shí),并區(qū)分法官的裁判義務(wù)事項(xiàng)和自由裁量事項(xiàng)。在書(shū)證類(lèi)型共識(shí)中,“相對(duì)方在訴訟程序中曾經(jīng)引用的”體現(xiàn)了平等武裝的理念,“主張方有交付或閱覽的實(shí)體請(qǐng)求權(quán)的”保障了私法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為主張方的利益而作的”兼顧了前兩種價(jià)值,“商業(yè)帳簿”對(duì)于商事訴訟中證明雙方的商事交易也具有重要的意義,都有必要作為立法上的固定類(lèi)型,為法官審查當(dāng)事人的取證申請(qǐng)?zhí)峁└唧w的指引。同時(shí)觀察比較法可見(jiàn),上述四種類(lèi)型都屬于“無(wú)特別理由就應(yīng)當(dāng)提出”(裁判義務(wù)事項(xiàng)),而我國(guó)目前的實(shí)踐則是法官“基于特別理由(客觀原因)才批準(zhǔn)”(自由裁量事項(xiàng))。只有扭轉(zhuǎn)這種對(duì)依申請(qǐng)調(diào)取證據(jù)的限縮理解,取消上述四種類(lèi)型證據(jù)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才有可能使以上類(lèi)型真正發(fā)揮功效。
進(jìn)而,為了避免自由裁量權(quán)的濫用,引入相應(yīng)的制約機(jī)制是下一步的任務(wù)。借鑒前述比較法經(jīng)驗(yàn)首先可以發(fā)現(xiàn),考慮到我國(guó)近期將主要通過(guò)民事程序法解決書(shū)證搜集的問(wèn)題,德國(guó)通過(guò)案例解釋實(shí)體法的進(jìn)路并不適合我們。筆者認(rèn)為,從民事程序法的一般理論出發(fā),限制自由裁量權(quán)也應(yīng)當(dāng)并重條件控制和過(guò)程控制兩種手段。在條件控制中,結(jié)合除外條款(日本模式)和價(jià)值考量具體化(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模式)的綜合方法更具有生命力。日本模式通過(guò)除外條款規(guī)定了不適于提出的文書(shū)類(lèi)型,分為保密特權(quán)、公務(wù)特權(quán)、專用文書(shū)以及有關(guān)刑事訴訟的文書(shū),在商事訴訟中更細(xì)分出公司內(nèi)部報(bào)告、人事安排或財(cái)務(wù)狀況記錄、特定的會(huì)議記錄等子類(lèi),這種相對(duì)嚴(yán)格的列舉主義正是解決我們?cè)谌狈Ψㄖ尉竦臒o(wú)奈中控制裁量權(quán)的良方。同時(shí),對(duì)那些處于條文表述的語(yǔ)義邊緣的情形,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提供的范本提示我們明示解釋論上的價(jià)值衡量更有利于制度預(yù)設(shè)功能對(duì)法律解釋的指引作用。特別考慮到我國(guó)民事程序法不大重視理由書(shū)的撰寫(xiě)和發(fā)布(這在各法治相對(duì)昌明的法域恰恰廣為重視),這樣的價(jià)值開(kāi)示無(wú)異將引導(dǎo)法官的說(shuō)理,更有可能緩和當(dāng)事人對(duì)司法的質(zhì)疑。在過(guò)程控制中,要求法官對(duì)準(zhǔn)許或者拒絕書(shū)證提出的裁判說(shuō)理,在指導(dǎo)性案例的發(fā)布中關(guān)注類(lèi)似程序規(guī)范的形成,更可能促進(jìn)漏洞填補(bǔ)、司法統(tǒng)一甚至法律發(fā)展的法律自治。
上述設(shè)想的實(shí)現(xiàn),需要通過(guò)裁判的形式來(lái)保障。隱藏在兩大法系都以裁判為載體的現(xiàn)象背后,是裁判在司法運(yùn)作中的預(yù)設(shè)功能與作用。多數(shù)司法行為可能影響當(dāng)事人之間的訴訟結(jié)果,為了獲致利害相關(guān)人的信任,裁判者必須表明其行為遵守程序性規(guī)范,滿足立法預(yù)設(shè)的條件,一般理性的法官在類(lèi)似情況下也會(huì)采取相同的司法行為。為了將這些信息以書(shū)面的方式表達(dá),形式上符合常例、實(shí)質(zhì)上說(shuō)理精當(dāng)?shù)牟门袩o(wú)疑是最好的選擇(信息獲取)。而且,面對(duì)雙方的爭(zhēng)議,通過(guò)剝離具體生活事實(shí)和價(jià)值判斷的司法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定分止?fàn)幍墓δ艿穆氊?zé)也必然落在裁判肩上(糾紛解決)。進(jìn)而,在民事程序上的各種書(shū)面材料中,只有依法形成的裁判才有可能獲得復(fù)審機(jī)會(huì),也有可能進(jìn)入不限于《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5項(xiàng)的審判監(jiān)督的視野(程序救濟(jì))。最后,只有裁判才能借由指導(dǎo)性案例的快車(chē)道,迅速穩(wěn)健地促進(jìn)更完善規(guī)則的形成(法律發(fā)展)。可惜在我國(guó)實(shí)踐中絕非個(gè)案的是,雖然卷宗中有當(dāng)事人申請(qǐng)調(diào)取證據(jù)的文狀,但是在任何裁判中(無(wú)論是中間的還是終局的)都覓不得只言片語(yǔ)的回應(yīng)。沒(méi)有強(qiáng)制要求的裁判,上述功能根本無(wú)從實(shí)現(xiàn),辯論主義下當(dāng)事人對(duì)于事實(shí)發(fā)現(xiàn)的自我責(zé)任也成為無(wú)本之木。
事實(shí)上,相較滯后的立法,司法實(shí)踐早就走在了前頭。針對(duì)當(dāng)事人取證難的諸多問(wèn)題,各地已經(jīng)嘗試了很多有創(chuàng)造力的方案,其中就以上海地區(qū)出現(xiàn)的證據(jù)搜集調(diào)查令制度為代表。相比大陸模式中的文書(shū)提出命令制度,調(diào)查令主要就是缺少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形式要件,在沒(méi)有立法授權(quán)的現(xiàn)狀下只能以司法命令的面目示人。而且,調(diào)查令的實(shí)踐從一個(gè)側(cè)面印證了書(shū)證搜集裁判發(fā)揮功效的可能性。最初由于立法上的限制,調(diào)查令的運(yùn)行效果并不容樂(lè)觀,但是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熟悉、習(xí)慣和認(rèn)可,這種狀況現(xiàn)在已經(jīng)大大改善了。實(shí)踐先行,立法也應(yīng)當(dāng)相機(jī)而動(dòng)。
(二)效果:以《證據(jù)規(guī)定》第75條為中心
《證據(jù)規(guī)定》第75條規(guī)定,有證據(jù)證明一方當(dāng)事人持有證據(jù)無(wú)正當(dāng)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duì)方當(dāng)事人主張?jiān)撟C據(jù)的內(nèi)容不利于證據(jù)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學(xué)界有力說(shuō)認(rèn)為,這即是我國(guó)法上的證明妨礙規(guī)則。筆者認(rèn)為,本條規(guī)定的其實(shí)恰恰是不履行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后果,從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比較經(jīng)驗(yàn)及司法實(shí)務(wù)來(lái)看也有必要加以完善。
最先需要明確的是本條針對(duì)的對(duì)象。筆者認(rèn)為,本條規(guī)定的主要是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效果,而不是一般性的證明妨礙規(guī)則。其一,就民事訴訟法學(xué)理而言,證明妨礙可分為兩種情形,即消極的不提供證據(jù)和表現(xiàn)為故意毀滅、隱匿或妨礙使用證據(jù)的積極的一般妨礙。本條只與當(dāng)事人消極的不協(xié)助調(diào)查行為有關(guān),正屬于前者;而后者中證明妨礙的范圍很廣,妨礙書(shū)證提出的效果是其中的一部分,還包括證人、勘驗(yàn)、鑒定等內(nèi)容,對(duì)應(yīng)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1款第1項(xiàng)規(guī)定的“妨害民事訴訟的強(qiáng)制措施”的范圍。從概念的準(zhǔn)確性來(lái)看,將之視為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效果更為恰當(dāng)。其二,就立法示例而言,本條不同于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282條的一般性證明妨礙規(guī)定,而類(lèi)似于該法第345條第1款的關(guān)于文書(shū)提出證明妨礙的特別規(guī)定,或者德國(guó)《民事訴訟法》第427條和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24條關(guān)于文書(shū)提出命令效果的表述。其三,就具體規(guī)則而言,與證明妨礙相比,本條也更接近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效果。比如,大陸法系文書(shū)提出命令/書(shū)證搜集裁判的法律后果只發(fā)生在訴訟中。由于當(dāng)事人只有在訴訟進(jìn)行中才有權(quán)申請(qǐng)法院裁判,在訴訟系屬成就之前,當(dāng)事人不可能因?yàn)槲臅?shū)提出命令而遭受不利后果。再比如,文書(shū)提出命令以違反法官裁判且沒(méi)有合理理由為限,而證明妨礙要求可歸責(zé)性(過(guò)錯(cuò)要件甚至故意要件)。因此衡量本條構(gòu)成要件,結(jié)論也是唯一的。
同時(shí),條文本身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過(guò)于寬松,其規(guī)范要件有待重塑和細(xì)化。首先,“正當(dāng)理由”的除外要件言之不確。由于這與前述模式論中的“客觀原因”所面臨的是同類(lèi)問(wèn)題,因此筆者也主張采取結(jié)合除外條款和價(jià)值考量具體化的綜合條件控制:在前者,主要考慮免證特權(quán)、當(dāng)事人未占有證據(jù)等;在后者則有必要考慮公正、效率以及必要的利益權(quán)衡。而且,相關(guān)價(jià)值在不同類(lèi)型訴訟中的位階并不相同:在商事訴訟中,要特別關(guān)注商人的形式平等性及其較強(qiáng)的訴訟對(duì)抗能力,總體上采取對(duì)“正當(dāng)理由”進(jìn)行限縮解釋的態(tài)度;而在普通民事案件中,由于不能期待一般當(dāng)事人會(huì)聘請(qǐng)專業(yè)律師或者自身即掌握足夠的訴訟技能,對(duì)“正當(dāng)理由”的解釋?xiě)?yīng)當(dāng)較為寬泛。其次,“證據(jù)不提出”的行為要件語(yǔ)之不詳。法條并未明言該條針對(duì)的證據(jù)不提出要件應(yīng)當(dāng)發(fā)生在法官命令后還是當(dāng)事人要求后,更沒(méi)有規(guī)定相應(yīng)的程序保障,完全是一片空白。再次,“無(wú)法證明或者證明困難”的后果要件付之闕如。如前所述,涉爭(zhēng)證據(jù)本身應(yīng)當(dāng)具有證明利益(證明必要),但是由于相對(duì)方的行為無(wú)法發(fā)揮原有的證明價(jià)值,因而有得到救濟(jì)的正當(dāng)性。如果不規(guī)定如上的后果要件,很可能不當(dāng)?shù)財(cái)U(kuò)大證據(jù)提出的范圍并使訴訟過(guò)程偏離正義的軌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裁判的效果要件更有必要做明確規(guī)定。條文所指的“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當(dāng)中的“主張”的具體含義為何?由于前述“主張”的含義是“關(guān)于證據(jù)的內(nèi)容是不利于證據(jù)持有人的主張成立”因而無(wú)法被“推定成立”,理論上自恰的解釋就出現(xiàn)了兩種:一解為文書(shū)所記載的內(nèi)容主張,另一解可為文書(shū)的待證事實(shí)主張。易言之,對(duì)本條中“主張”的解釋可能包含了前文區(qū)分的證據(jù)層面和事實(shí)層面兩種情形。在實(shí)務(wù)中,判例傾向于“認(rèn)定書(shū)證內(nèi)容為真實(shí)”的證據(jù)層面:侵權(quán)糾紛中,由于相對(duì)方各當(dāng)事人要么提供的財(cái)務(wù)資料不完整要么根本拒絕提供材料,法官認(rèn)定了主張方提出的損害賠償數(shù)額,或者法官在認(rèn)定相對(duì)方持有經(jīng)案外人簽字的《撤銷(xiāo)指定交易申請(qǐng)表》“客戶聯(lián)”后,推定該書(shū)證上載有主張方所主張的“617”字樣;合同糾紛中,法官基于相對(duì)方房產(chǎn)公司單方持有《業(yè)主入住驗(yàn)收單》而拒不提出,推定主張方關(guān)于收房時(shí)已對(duì)窗外有鋼梁一事提出書(shū)面異議的主張成立。但是如前所述,單純證據(jù)層面的解釋思路無(wú)法對(duì)妨礙證明者施以大于其潛在獲利的懲罰,更不可能達(dá)到威懾警示的目的。特別是,在本證方無(wú)旁證可舉、又不能詳細(xì)描述文書(shū)內(nèi)容的情況下,出于對(duì)實(shí)體正義和客觀真相的孜孜追求,我國(guó)法官應(yīng)當(dāng)在對(duì)待定事實(shí)形成自由心證時(shí)握有“視待證事實(shí)為真實(shí)”的殺手锏。因此,應(yīng)當(dāng)通過(guò)立法明確這種可以納入裁判技術(shù)的但書(shū)規(guī)范,為法官的價(jià)值判斷留下法教義學(xué)上的合理空間。
從前述比較法評(píng)述出發(fā),不同強(qiáng)度的裁判效果體系也是我們應(yīng)當(dāng)追求的。如前所述,理論上無(wú)論是試圖“回復(fù)”的證據(jù)層面,“預(yù)防”或“懲罰”的事實(shí)層面還是在效果上與直接判決敗訴無(wú)異的請(qǐng)求層面制裁,任何單一的選擇都面臨一定的功能缺陷。我國(guó)當(dāng)前的立法規(guī)定相對(duì)簡(jiǎn)單,對(duì)不提出證據(jù)行為的規(guī)制主要包括妨害民事訴訟的強(qiáng)制措施和證據(jù)法上的推定效果兩種,其中前者的要件為“偽造、毀滅重要證據(jù),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后者如前所述限于“認(rèn)定書(shū)證內(nèi)容為真實(shí)”效果。可見(jiàn),我國(guó)目前的制度略顯簡(jiǎn)單,更無(wú)法達(dá)到規(guī)制當(dāng)事人舉證行為的預(yù)期效果。筆者認(rèn)為,除了在解釋論上明確證據(jù)層面效果并輔以高度限定的事實(shí)層面效果之外,強(qiáng)制執(zhí)行書(shū)證的物理載體、證據(jù)排除、訴訟費(fèi)用轉(zhuǎn)移(cost shifting)等配套程序舉措也值得考慮。至于是否在我國(guó)引入極端情況下直接終結(jié)訴訟程序的進(jìn)路,由于懷疑其實(shí)效并考慮到一系列訴訟體制和模式困難,筆者暫持否定態(tài)度。
五、結(jié)語(yǔ)
總而言之,加強(qiáng)書(shū)證搜集制度并解決大量訴訟中證據(jù)分布與證明責(zé)任分配不對(duì)稱的情形,在理論上是維持辯論主義所必需的制度保障,在立法上也呼喚對(duì)可能持有證據(jù)的一方課以提出書(shū)證的義務(wù),并對(duì)其拒絕提出的行為施加消極效果。各國(guó)的立法舉措和司法實(shí)踐給我們大量可資參考的信息,但是我們必須盡可能站在既有制度的基礎(chǔ)上,讓域外經(jīng)驗(yàn)融合到本土司法傳統(tǒng)之中,而不是相反。
這種相對(duì)類(lèi)型化的書(shū)證搜集裁判設(shè)想,在增加了法官批準(zhǔn)依申請(qǐng)調(diào)取證據(jù)的幾率之外,也可能帶來(lái)對(duì)效率受損的擔(dān)憂。比如,證據(jù)開(kāi)示程序最經(jīng)常被提及的一個(gè)重大缺陷就是過(guò)于耗時(shí)費(fèi)力,大量文書(shū)的相互傳遞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huì)資源浪費(fèi)。但筆者認(rèn)為,書(shū)證搜集裁判制度并不會(huì)帶來(lái)上述問(wèn)題。在大陸法系證明理論下,具有證明必要且需要搜集書(shū)證的范圍十分有限,而且我國(guó)實(shí)務(wù)中法官很難容忍或放任所謂摸索證明(Ausforschungsbeweis)或釣魚(yú)取證(fishing expedition)的行為,這種對(duì)效率影響的擔(dān)憂很難成為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
從系統(tǒng)角度出發(fā),書(shū)證搜集裁判制度的有效運(yùn)轉(zhuǎn)也有賴于法官的闡明義務(wù)、判決后說(shuō)理等制度的配合,更與裁判文書(shū)體系的重構(gòu)關(guān)系重大。沒(méi)有一審普通程序的全局聯(lián)動(dòng),書(shū)證搜集裁判制度即使在民事程序?qū)嵺`和新的《民事訴訟法》中倉(cāng)促上陣,效果也會(huì)大打折扣。囿于撰文時(shí)機(jī),本文的討論無(wú)法參考新《民事訴訟法》立法草案中的其他創(chuàng)新機(jī)制,因而仍有很大后續(xù)探討空間。
參考文獻(xiàn):
[1]張衛(wèi)平.證明妨害及對(duì)策探討[G]//何家弘.證據(jù)學(xué)論壇:第7卷.北京:中國(guó)檢察出版社,2004:160.
[2]李軍.民事訴訟的書(shū)證問(wèn)題研究——以合同訴訟為例[M].成都:西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6:1—6.
[3]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M].臺(tái)北:學(xué)林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14.
[4]羅森貝克,施瓦布,戈特瓦爾德.德國(guó)民事訴訟法[M].李大雪,譯.北京: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7:888.
[5]奚瑋,余茂玉.論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妨礙[J].河北法學(xué),2007,25,(3):152—153.
[6]黃國(guó)昌.民事訴訟理論之新開(kāi)展[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221.
[7]沈冠伶,等.摸索證明與事證搜集開(kāi)示之協(xié)力[G]//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四).臺(tái)北:三民書(shū)局,2007:202.
[8]張永泉.書(shū)證制度的內(nèi)在機(jī)理及外化規(guī)則研究[J].中國(guó)法學(xué),2008,(5):120.
[9]邱聯(lián)恭.程序制度機(jī)能論[M].臺(tái)北:三民書(shū)局,1996:186.
[10]高橋宏志.重點(diǎn)講義民事訴訟法[M].張衛(wèi)平,許可,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61.
[11]李浩.論民事訴訟當(dāng)事人的申請(qǐng)調(diào)查取證權(quán)[J].法學(xué)家,2010,(3):118-119.
[12]江偉.民事訴訟法典專家修改建議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78.
[13]李浩.民事訴訟程序權(quán)利的保障:?jiǎn)栴}與對(duì)策[J].法商研究,2007,(3):88.
[14]胡宜奎.論民事訴訟中的調(diào)查取證權(quán)——兼論調(diào)查取證模式與調(diào)查取證權(quán)的關(guān)系[J].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06,(7):56.
[15]占善剛.論民事訴訟中的當(dāng)事人之文書(shū)提出義務(wù)[J].求索,2008,(3):155.
[16]王亞新.對(duì)抗與判定——日本民事訴訟的基本結(jié)構(gòu)[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0:139—140.
[17]韋揚(yáng),曾俊怡,劉亞玲.當(dāng)事人調(diào)查取證權(quán)之程序保障的路徑嘗試——以調(diào)查令制度的檢討及其實(shí)證量化分析為研究視點(diǎn)[J].法律適用,2008,(3):20.
[18]羅筱琦,陳界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jù)規(guī)則”若干問(wèn)題評(píng)析[J].國(guó)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11,(1):30.
[19]陳計(jì)男.民事訴訟法論[M].臺(tái)北:三民書(shū)局,2007:485-486.
[20]趙信會(huì).民事訴訟中的證據(jù)調(diào)查制度[J].現(xiàn)代法學(xué),2004,26,(6):91.
[21]黃國(guó)昌.證明妨礙法理之再檢討——以美國(guó)法之發(fā)展為借鏡[G]//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三).臺(tái)北:三民書(shū)局,2006:294.
[22]占善剛.證明妨害論——以德國(guó)法為中心的考察[J].中國(guó)法學(xué),2010,(3):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