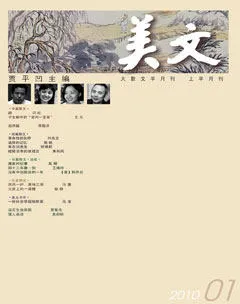革命性的灰燼
葉兆言
1957年出生,1982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xué)中文系,1986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xué)中文系碩士班。歷任金陵職業(yè)大學(xué)教師,江蘇文藝出版社編輯,江蘇作家協(xié)會(huì)專業(yè)創(chuàng)作員。1980年開始發(fā)表作品。現(xiàn)為江蘇省作家協(xié)協(xié)專業(yè)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
一
記憶總是靠不住,小說家契訶夫逝世,過了沒幾年,大家為他眼睛的顏色爭論不休,有人說藍(lán),有人說棕,更有人說是灰色。同樣道理,歷史也是靠不住的玩意,有人進(jìn)行了認(rèn)真研究,考證出胡適先生并沒說過那句著名的話,他并沒有說“歷史是個(gè)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我們更愿意相信,胡適確實(shí)是說過這句格言,有些話并不需要注冊商標(biāo),誰說過不重要,大家心里其實(shí)都明白,歷史這個(gè)小姑娘不僅任人打扮,而且早已成為一個(gè)久經(jīng)風(fēng)塵的老婦人。
一九七四年初夏,我高中畢業(yè)了,接下來差不多有一年時(shí)間,都在北京的祖父身邊度過。這時(shí)候,我讀完了能見到的所有雨果作品,讀了幾本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讀海明威、讀紀(jì)德、讀薩特,讀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格醫(yī)生》,讀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我胡亂地看著書,逮到什么看什么。事實(shí)上,北京的藏書還沒有南京家中的多,因此我小小年紀(jì),看過的世界文學(xué)名著,已足以跟堂哥吹牛了。
這是一個(gè)非常荒唐的年代,就在前一天,在網(wǎng)上看到一篇文章,分析我們這一代人,中間有首打油詩,開頭的幾句很有意思:
五十年代生,今生是苦命。
生下吃不飽,餓得臉發(fā)青。
本應(yīng)學(xué)知識(shí),當(dāng)了紅衛(wèi)兵……
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吃狼奶長大,公認(rèn)最沒有文化。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人情練達(dá)既文章,就像做生意算賬要仔細(xì)一樣,爬雪山過草地,打日本鬼子打右派,這些都可以算作資歷和本錢,經(jīng)歷了最殘酷的文化大革命,為什么卻不能算。江山代有人才出,各有各的造化,輕易地就為一代人蓋棺定論,硬說人家沒文化,多少有些不太妥當(dāng)。記得有一次和女作家方方閑談,說起我們的讀書生涯,很有些憤憤不平,她說憑什么認(rèn)為這一代人讀的書不多,憑什么就覺得我們沒學(xué)問。本來書讀得多或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跟有無學(xué)問一樣,有,不值得吹噓,沒有,也沒什么太丟人,可是這也不等于說你說有就有,你說沒有就沒有。
事實(shí)上,相對(duì)于周圍的人,無論父輩還是同輩晚輩,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都屬于那種讀書讀得多的人。說賣弄也好,說不謙虛也好,在我年輕氣盛的時(shí)候,跟別人談到讀書,談古論今,我總是夸夸其談口若懸河。有一次在一個(gè)什么會(huì)議上,聽報(bào)告很無聊,坐我身邊的格非忽然考我,能不能把白居易《長恨歌》中“漁陽鼙鼓動(dòng)地來,踏破霓裳羽衣曲”的后兩句寫出來,我覺得這很容易,不僅寫出了下面兩句,而且還順帶寫出了一長串,把一張白紙都寫滿了。
女兒考大學(xué),我希望她能背些古詩,起碼把課本上的都背下來。對(duì)于一個(gè)文科學(xué)生,已經(jīng)是最低要求,女兒覺得當(dāng)?shù)暮苡馗尚ΑN艺f愿意跟她一起背,她背一首,我背兩首,或者背三首四首。結(jié)果當(dāng)然廢話,女兒的搶白讓人哭笑不得,她說不就是能背幾首古詩嗎,你厲害,行了吧。現(xiàn)如今,女兒已是文科的在讀博士,而我實(shí)實(shí)在在又老了許多,記憶力明顯不行了,不過起碼到目前為止,雖然忘掉太多的唐詩宋詞和明清小品文,然而那些文明的碎片,仍然還有一些保存在腦子里,我仍然還能背誦屈原的《離騷》,仍然還能將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默寫出來。
絲毫沒有沾沾自喜的意思,我知道的一位老先生,能夠?qū)⑽迨蝗f字的《史記》背出來,這個(gè)才叫厲害。真要是死記硬背,一個(gè)十歲的毛孩子就能背誦《唐詩三百首》。我所以要說這些,要回憶歷史,無非想說明我們這一代人未必就像別人想得那么不堪,同時(shí),也想強(qiáng)調(diào)我們這一代人曾經(jīng)非常的無聊,無聊到了沒有任何好玩的事可做。沒有網(wǎng)絡(luò),沒有移動(dòng)電話,沒有NBA,沒電視新聞,今天很多常見的玩意都根本不存在。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現(xiàn)在回想起來,索性廢除了高考,沒有大學(xué)可上,有時(shí)候也并非完全無益。譬如我,整個(gè)中學(xué)期間,有大量的時(shí)間讀小說,有心無心地亂背唐詩宋詞和古文。壞事往往也可以變?yōu)楹檬拢抑烙腥司褪且驗(yàn)閷懘笞謭?bào)練毛筆字,成為了書法家,因?yàn)榕峙籽芯抗艥h語,最后成了古文學(xué)者。
二
在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看到了厚厚的一堆小說手稿,這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因?yàn)槊飨先思业奶貏e關(guān)照,別的小說家差不多都打倒了,都成了黑幫,獨(dú)獨(dú)他獲得了將小說寫完的機(jī)會(huì)。我還見過浩然的《金光大道》手稿,出于同樣原因,這些不可一世的手稿,出現(xiàn)在了我祖父的案頭,指望祖父能在語文方面把把關(guān)。后一本書沒什么好看的,是一本非常糟糕的書,根本就讓人看不下去,我一口氣讀完了《李自成》,祖父問感覺怎么樣,我當(dāng)時(shí)也說不出好壞,回答說反正是看完了,已經(jīng)知道故事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說,在那個(gè)文化像沙漠一樣的年頭,閱讀畢竟是一件相對(duì)愜意的事情,畢竟姚雪垠還是個(gè)會(huì)寫小說的人,還有點(diǎn)故事能看看。
在此之前,能見到的小說,都是印刷品,都已加工成了書的模樣。手寫的東西,除了書信,就是大字報(bào)。雖然隱隱約約也知道,我第一次完全明白,小說還是先要用手寫,然后才能夠印刷成文字。第一次接觸手稿的感覺很有些異樣,既神秘,又神奇,仿佛破解了一道數(shù)學(xué)難題,一時(shí)間豁然開朗,原來這就是寫作的真相。有時(shí)候,故事的好壞并不重要,關(guān)鍵是你得把它寫出來。李自成是不是高大全也無所謂,它消磨了我的時(shí)間,滿足了一個(gè)文學(xué)少年的閱讀虛榮心,你終于比別人更早一步知道了這個(gè)故事。很多事情無法預(yù)料,八年后,《李自成》第二部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我跟別人說起曾在“文革”中看過這部手稿,聽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說老實(shí)話,我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
有時(shí)候,閱讀只是代表自己能夠與眾不同,我們?nèi)ヅ鏊皇且驗(yàn)樗餍校∏∈且驗(yàn)閯e人見不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學(xué)愛好者對(duì)世界名著的迷戀,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不能夠很順利地看到。同樣的道理,人們更容易迷戀那些被稱之為“內(nèi)部讀物”的黃皮書,我們?nèi)琊囁瓶实亻喿x,是因?yàn)樗鼈兎磩?dòng),是毒草,因?yàn)榻詿幔驗(yàn)椴蛔尶矗砸欢ㄒ础S袝r(shí)候,閱讀也是一種享受特權(quán),甚至也可以成為一種腐敗,當(dāng)然,在特定時(shí)期特定環(huán)境下,寫作也會(huì)是這樣。《李自成》這樣的小說,從來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學(xué)理想,它也許可以代表“文革”文學(xué)的最高水準(zhǔn),但它壓根不是我所想要的那種文學(xué),既不是我想讀的,也不是我想寫的。我曾不止一次說過,從小就沒有想到過自己將來要當(dāng)作家,因?yàn)榧彝リP(guān)系,作家這一職業(yè)對(duì)我并不陌生,然而我非常不喜歡這個(gè)行當(dāng),而且有點(diǎn)鄙視它,因?yàn)榘凑談e人的意志去寫小說,勉為其難地去表達(dá)別人的思想,這起碼是一點(diǎn)都不好玩,不僅不好玩,而且很受罪。
一九七四年,民間正悄悄地在流傳一個(gè)故事,說江青同志最喜歡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記得有一陣,我整天纏著堂哥三午,讓他給我講述大仲馬的這本書。三午很會(huì)講故事,他總是講到差不多的時(shí)候,突然不往下講了,然后讓我為他買香煙,因?yàn)闆]有香煙提精神,就無法把嘴邊的故事說下去。這種賣關(guān)子的說故事方法顯然影響了我,它告訴我應(yīng)該如何去尋找故事,如何描述這些故事,如何引誘人,如何克制,如何讓人上當(dāng)。我為基督山伯爵花了不少零用錢,三午是個(gè)地道的紈绔子弟,有著極高的文學(xué)修養(yǎng),常會(huì)寫一些很頹廢的詩歌。同時(shí)又幻想著要寫小說,他的理想是當(dāng)作家,可惜永遠(yuǎn)是個(gè)光說不練的主,光是喜歡在嘴上說說故事。
我不止一次說過,談起文學(xué)的啟蒙,三午對(duì)我影響要遠(yuǎn)大于我父親,更大于我祖父。歷史地看,三午是位很不錯(cuò)的詩人,劉禾主編的《持燈的使者》收集了《今天》的資料,其中有一篇阿城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很誠摯地回憶了兩位詩人,一位是郭路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食指,還有一位便是三午。這兩位詩人相對(duì)北島多多芒克,差不多可以算作是前輩,我記得在一九七四年,三午常用很輕浮的語氣對(duì)我說,誰誰誰寫的詩還不壞,這一句馬馬虎虎,這一句很不錯(cuò),一首詩能有這么一句,就很好了。
關(guān)于三午,阿城的文章里有這么一段,很傳神:
三午有自己的一部當(dāng)代詩人關(guān)系史。我談到我最景仰的詩人朋友,三午很高興,溫柔地說,振開當(dāng)年來的時(shí)候,我教他寫詩,現(xiàn)在名氣好大,芒克、毛頭,都是這樣,毛頭脾氣大……
振開就是北島,毛頭是多多,而芒克當(dāng)時(shí)卻都叫他“猴子”,為什么叫猴子,我至今不太明白。是因?yàn)樗粋€(gè)綽號(hào)叫猴子,然后用英文諧音給自己起了一個(gè)筆名,還是因?yàn)檫@個(gè)筆名,獲得了一個(gè)頑皮的綽號(hào)。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就知道并且熟悉這些后來名震一時(shí)的年輕詩人,就讀過和抄過他們的詩稿,就潛移默化地受了他們的影響。“希望,請不要走得太遠(yuǎn),你在我身邊,就足以把我欺騙”。除了這幾位,還有許多稀奇古怪的人,有畫畫的,練唱歌的,玩音樂的,玩攝影的,玩哲學(xué)的,嘰里呱啦說日語的,這些特定時(shí)期的特別人物,后來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有一個(gè)叫彭剛的小伙子給我留下很深刻印象,他的畫充滿了邪氣,非常傲慢而且歇斯底里,與“文革”的大氣氛完全不對(duì)路子。在一九七四年,他就是凡高,就是高更,就是摩迪里阿尼,像這幾位大畫家一樣潦倒,不被社會(huì)承認(rèn),像他們一樣趾高氣揚(yáng),絕對(duì)自以為是。新舊世紀(jì)交匯的那一年,也就是2000年12月,在大連一個(gè)詩歌研討會(huì)的現(xiàn)場,我正坐那等待開會(huì),突然一頭白發(fā)的芒克走了進(jìn)來,有些茫然地找著自己的座位。一時(shí)間,我無法相信,這就是二十多年前見過的那位青年,那位青春洋溢又有些稚嫩的年輕詩人。會(huì)議期間,我們有機(jī)會(huì)聊天,我問起了早已失蹤的彭剛,很想知道這個(gè)人的近況。芒克告訴我彭剛?cè)チ嗣绹闪说氐赖拿绹耍芯渴裁椿瘜W(xué),是一家大公司的總工程師,闊氣得很。
一時(shí)間,我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就好像有一天你猛地聽說踢足球的馬拉多納,成了一個(gè)彈鋼琴的人,一個(gè)優(yōu)雅地跳著芭蕾的先生,除了震驚之外,你實(shí)在無話可說。
三
在一九七四年,“毛頭的詩”和“彭剛的畫”代表著年輕人心目中的美好時(shí)尚,這種時(shí)尚是民間的,是地下的,是反動(dòng)的,然而生氣勃勃,像火焰一樣猛烈燃燒。如果說在一九七四年,我有過什么短暫的文學(xué)理想的話,那就是能夠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為一名像毛頭那樣的詩人。三午的詩人朋友中,來往最多的就是這個(gè)毛頭,對(duì)我影響最大最刻骨銘心的,也正是這個(gè)毛頭。毛頭成了我的偶像,成了我忘卻不了的夢想。我忘不了三午如何解讀毛頭的詩,大聲地朗讀著,然后十分贊嘆地大喊一聲:
“好,這一句,真他媽的不俗!”
從三午那里,常常會(huì)聽到的兩句評(píng)論藝術(shù)的大白話,一句是這個(gè)真他媽太俗,另一句是這個(gè)真他媽的不俗。俗與不俗成為最重要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說白了,所謂俗,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所謂不俗,就是和別人不一樣,就是非常非常的獨(dú)特,老子獨(dú)步天下。藝術(shù)觀常常是搖擺不定的,為了反對(duì)時(shí)文,就像當(dāng)年推崇唐宋八大家一樣,我們故意大談古典,一旦古典泛濫,名著大行其道的時(shí)候,我們又只認(rèn)現(xiàn)代派。說白了,文學(xué)總是要反對(duì)些什么,說這個(gè)好,說那個(gè)好,那是中央臺(tái)《新聞聯(lián)播》,那不是文學(xué)。
有沒有機(jī)會(huì)永遠(yuǎn)是相對(duì)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在一九七四年,因?yàn)闆]有文化,稍稍有點(diǎn)文化,就顯得很有文化。因?yàn)闆]有自由,思想過分禁錮,稍稍追求一點(diǎn)自由,稍稍流露一點(diǎn)思想,便顯得很有思想。有一天,三午對(duì)毛頭宣布,他要寫一部小說,然后滔滔不絕地說自己準(zhǔn)備怎么寫。那一陣,毛頭是三午的鐵哥們,三天兩頭會(huì)來,來了就賴在了長沙發(fā)上不起來,說不完的詩,談不完的音樂。也許詩談得太多了,音樂也聊得差不多,三午突然想到要玩玩小說。他是個(gè)非常會(huì)吹牛的人,這個(gè)故事他已經(jīng)跟我說過一遍,然后又在我的眼皮底下,興致勃勃地說給毛頭聽。在一開始,毛頭似乎還有些勉強(qiáng),懶洋洋坐在那,無精打采,漸漸地坐直了,開始聚精會(huì)神。終于三午說完了故事梗概,毛頭怔了一會(huì),不甘心地問,完了。三午很得意,說完了,于是毛頭突然從沙發(fā)上跳起來,說我要向你致敬,說你太他媽有救了,這絕對(duì)太他媽的棒了,你一定得寫出來。
和許多心目中的美好詩篇一樣,三午的這部小說當(dāng)然沒有寫出來。人們心目中的好小說,永遠(yuǎn)比實(shí)際完成的要少得多。時(shí)至今日,我仍然還能清晰地記得那個(gè)故事梗概,一名老干部被打倒了,落難了,回到了當(dāng)年打游擊的地方,從廟堂回落到江湖,老干部非常驚奇地發(fā)現(xiàn),有一位年輕人對(duì)他尤其不好,處處要為難他,隨時(shí)隨地會(huì)與他作對(duì)。老干部想不明白這是為什么,他忍讓著,討好著,斗爭著,反抗著,有一天終于逼著年輕人說了實(shí)話。年輕人很憤怒地說,你身上某部位是不是有個(gè)印記,說你還記不記得當(dāng)年的戰(zhàn)爭年代,還能不能記得有那么一位村姑,在你落難的時(shí)候,她照顧過你,她愛過你,可你對(duì)她干了什么。這位老干部終于明白了,原來這位年輕人是自己的兒子,是他當(dāng)年一度風(fēng)流時(shí)留下的孽債。年輕人咬牙切齒地說,你把衣服脫下來,你脫下來。老干部心潮起伏,他猶豫再三,終于在年輕人面前脫光了自己,赤條條地,瘦骨嶙峋地站在兒子面前,很羞愧地露出了隱秘部位的印記。
如果三午將這個(gè)故事寫出來,如果時(shí)機(jī)恰當(dāng),在此后不久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這樣的小說獲得全國獎(jiǎng)也未必就是意外。說老實(shí)話,就憑現(xiàn)在這個(gè)故事梗概,它也比許多紅極一時(shí)的得獎(jiǎng)小說強(qiáng)得多。不妨想一想一九七四年的文學(xué)現(xiàn)場,不妨想一想當(dāng)時(shí)文學(xué)觀念上的差異。文化大革命已是強(qiáng)弩之末,四人幫正炙手可熱,那年頭,最火暴的文學(xué)期刊是《朝霞》,那年頭能發(fā)表的作品不是說基本上,而是完全就不是文學(xué)。當(dāng)然,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如果當(dāng)時(shí)文學(xué)期刊上的文字是文學(xué),我以上提到的那些活躍在民間的東西,那些充滿了先鋒意義的詩歌,三午要寫的那個(gè)小說,就絕對(duì)不是文學(xué)。
極端的文學(xué)的都是排他的,極端的文學(xué)都是不共戴天。事隔三十多年,以一個(gè)小說家的眼光來看,三午當(dāng)年準(zhǔn)備要寫的那部小說,就算是寫出來,也未必會(huì)有多精彩。同樣,白云蒼狗時(shí)過境遷,當(dāng)年那些讓我入迷的先鋒詩歌,那種奇特的句式,那種驚世駭俗的字眼,用今天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也真沒什么了不起。無可否認(rèn)的卻是,好也罷,不好也罷,它們就是我的文學(xué)底牌,是我最原始的文學(xué)準(zhǔn)備,是未來的我能夠得以萌芽和成長的養(yǎng)料。它們一個(gè)個(gè)仍然鮮活,繼續(xù)特立獨(dú)行,既和當(dāng)時(shí)的世界絕對(duì)不兼容,又始終與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保持著最大距離。有時(shí)候,文學(xué)藝術(shù)就只是一個(gè)姿態(tài),只是一種面對(duì)文壇的觀點(diǎn),姿態(tài)和觀點(diǎn)決定了一切。從最初的接觸文學(xué)開始,我的文學(xué)觀就是反動(dòng)的,就是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對(duì)著干,就是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樣,要“不俗”。我們天生就是狼崽,是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的產(chǎn)物,是真正意義的文學(xué)左派。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來到這個(gè)世界上,如果要從事文學(xué),就一定要革文學(xué)的命,搗文學(xué)的亂。
四
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末,我開始偷偷摸摸地學(xué)寫小說,所以說偷偷摸摸,并不是說有什么人不讓寫,而是我不相信自己能寫,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我從來就是個(gè)猶豫不決的人,一會(huì)信心十足,一會(huì)垂頭喪氣。記得曾寫過一篇《白馬湖靜靜地流》的短篇,寄給了北島,想試試有沒有可能在《今天》上發(fā)表,北島給我回了信,說小說寫得不好,不過他覺得我很有詩才,有些感覺很不錯(cuò),可以嘗試多寫一些詩歌。
到了一九八六年秋天,經(jīng)過八年的努力,我斷斷續(xù)續(xù)地寫了一些小說,短篇,中篇,長篇,都嘗試過,也發(fā)表和出版了一部分,基本上沒有任何影響,還有很多小說壓在抽屜。這時(shí)候,我是一家出版社的小編輯,去廈門參加長篇小說的組稿會(huì),見到了一些正當(dāng)紅的作家。當(dāng)時(shí)廈門有個(gè)會(huì)算命的“黃半仙”,據(jù)說非常準(zhǔn)確,很多作家都請他卜算未來。我未能免俗,也跟在別人后面請他預(yù)言。他看了看我的手心,又摸了摸我的鎖骨,然后很誠懇地說你是個(gè)詩人,你可以寫點(diǎn)詩。周圍的人都笑了,笑得很厲害,笑出了聲音。不知道他為什么會(huì)這么說,也許是我當(dāng)時(shí)不修邊幅,留著很長的胡子。反正讓人感到很沮喪,因?yàn)槲抑雷约鹤钊钡木褪窃姴牛揪筒豢赡艹蔀橐幻錾脑娙恕N覠o法掩飾巨大失望,問他日后還能不能寫小說,他又看了看我,斬釘截鐵地說:
“不行,你不能寫小說,你應(yīng)該寫詩,你應(yīng)該成為一個(gè)詩人。”
這位“黃半仙”也是文藝圈子里的人,他只是隨口一說,根本沒想到會(huì)有什么后果,根本就不在乎我會(huì)怎么想。當(dāng)時(shí)在場的還有很多位已成名的小說家,小說家太多了,多一個(gè)不多,少一個(gè)不少,我只是一名極普通的小編輯,實(shí)在沒必要再去湊那份熱鬧。一時(shí)間,我想起了北島當(dāng)年的勸說,說老實(shí)話,那時(shí)候真的有些絕望。雖然已經(jīng)開始愛上了寫小說,雖然正努力地在寫小說,但是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也讓我開始懷疑自己真沒有寫小說的命。
這時(shí)候,我已經(jīng)寫完了《棗樹的故事》,《夜泊秦淮》也寫了一部分,《五月的黃昏》在一家編輯部壓了整整一年,因?yàn)闆]有退稿,一直以為有一天它可能會(huì)發(fā)表出來,可是不久,被蓋了一個(gè)紅紅的公章,又無情地退了回來。《棗樹的故事》最初寫于一九八一年,因?yàn)楸徊粩嗟赝烁澹冶悴煌5匦薷模煌5馗淖償⑹鼋嵌龋Y(jié)果就成了最后那個(gè)模樣。我已經(jīng)被退了無數(shù)次稿,僅《青春》雜志這一家就不會(huì)少于十次。我有兩個(gè)很好的朋友在這編輯部當(dāng)編輯,可就算有鐵哥們,仍然還是不走運(yùn)。
一個(gè)人不管怎么牛,怎么高傲,退稿總是很煞風(fēng)景。還是在七十年代末,南京的一幫朋友聚在一起,像北京的《今天》那樣,搞了一個(gè)民間的文學(xué)期刊《人間》。我的文學(xué)起步與這本期刊有很大關(guān)系,與這幫朋友根本沒辦法分開。事實(shí)上,我第一部被刊用的小說,就發(fā)表在《人間》上。沒有《人間》我就不會(huì)寫小說,那時(shí)候我們碰在一起,最常見的話題就是什么小說不好,就是某某作家寫得很臭。我們目空一切,是標(biāo)準(zhǔn)的文壇持不同政見者。這本刊物很快夭折了,有很多原因,政治壓力固然應(yīng)該放在首位,然而自身動(dòng)力不足,克服困境的勇氣不夠以及一定程度的懶惰,顯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我們中間的某些人在當(dāng)時(shí)已十分走紅,他們寫出來的文字不僅可以公開發(fā)表,而且是放在頭條的位置上,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不管今天把當(dāng)時(shí)民間文學(xué)刊物的作為拔得多高,希望能夠公開發(fā)表文章,希望能夠獲得廣大讀者的認(rèn)同,還是一個(gè)最基本的原始動(dòng)機(jī)。官方的反對(duì)和禁令會(huì)阻礙發(fā)展,文壇的認(rèn)同同樣可以造成流產(chǎn)。毫無疑問,民間刊物是對(duì)官辦刊物的反抗,同時(shí)也是一種補(bǔ)充。我們的文學(xué)理想是朦朧的,不清晰的,既厭惡當(dāng)時(shí)的文壇風(fēng)氣,又不無功利地想殺進(jìn)文壇,想獲得文壇的承認(rèn)。很顯然,在公開的文學(xué)刊物上發(fā)表自己文字是很難抵擋的誘惑,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家中,有一次北島來,我跟他說起顧城發(fā)表在《今天》上的一首詩不錯(cuò),北島說這詩是他從一大堆詩中間挑出來的,言下之意,顧城的詩太多了,這首還算說得過去。安徽老詩人公劉是我父親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因?yàn)楹皖櫝歉赣H顧工熟悉,讓顧城給他寄點(diǎn)詩,打算發(fā)表在自己編的刊物上,結(jié)果顧城一下子寄了許多,仿佛小商品批發(fā)一樣,只要能夠發(fā)表,隨便公劉選什么都行。
寫作是寫給自己看的,當(dāng)然更是寫給別人看的。公開發(fā)表永遠(yuǎn)是寫作者的夢想,有一段時(shí)間,主流文學(xué)之外的小說狼狽不堪,馬原的小說,北島的小說,這些后來都獲得很大名聲的標(biāo)志性作家,很艱難地通過了一審,很艱難地通過二審,終于在三審時(shí)給槍斃了。我是他們遭遇不斷退稿的見證者,都是在還不曾成名時(shí),就知道和認(rèn)識(shí)他們。我認(rèn)識(shí)馬原的時(shí)候,還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時(shí)候的馬原非常年輕,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標(biāo)準(zhǔn)的帥哥,他還在大學(xué)讀書,小說寫出來了無處可發(fā),正在與同學(xué)們一起編一本非常好賣的“文學(xué)描寫辭典”。而北島的《旋律》和《波動(dòng)》,也周轉(zhuǎn)在各個(gè)編輯部之間,在老一輩作家心里,它們也算不上什么大逆不道,尤其是《旋律》,我父親和高曉聲都認(rèn)為這篇小說完全可以發(fā)表,然而最終也還是沒有發(fā)出來。
五
上世紀(jì)的八十年代中期,現(xiàn)代派一詞開始甚囂塵上,后來又出現(xiàn)了新潮小說和先鋒小說。這些時(shí)髦的詞匯背后,一個(gè)巨大的真相被掩蓋了,這就是文壇上的持不同政見者,已消失或者正在消失,有的不再寫作,徹底離開了文學(xué),有的被招安和收編,開始名成功就,徹底告別了狼狽不堪。先鋒小說這個(gè)字眼開始出現(xiàn)的那一天,所謂先鋒已不復(fù)存在。馬原被承認(rèn)之日,就是馬原消亡之時(shí)。北島的《波動(dòng)》和《旋律》終于發(fā)表,發(fā)表也就發(fā)表了,并沒有引起什么波瀾。詩人毛頭改名多多,也寫過一些小說,說有點(diǎn)影響也可以,說沒多大影響也可以。
多少年來,我一直忍不住地要問自己,如果小說始終發(fā)表不了,如果持續(xù)被退稿,持續(xù)被不同的刊物打回票,會(huì)怎么樣。如果始終被文壇拒絕,始終游離于文壇之外,我還有沒有那個(gè)耐心,還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寫下去。也許真的很難說,如果沒有稿費(fèi),沒有叫好之聲,我仍然會(huì)毫不遲疑地繼續(xù)寫下去,然而如果一直沒有地方發(fā)表文字,真沒有一個(gè)人愿意閱讀,長此以往,會(huì)怎么樣就說不清楚了。時(shí)至今日,寫還是不寫根本不是一個(gè)問題,再說仍然被拒絕,再說沒什么影響,再說讀者太少,多少有些矯情。我早已深陷在寫作的泥淖之中,生命不息戰(zhàn)斗不止。寫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為什么寫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什么和怎么寫,無法想象自己不寫會(huì)怎么樣,不寫作對(duì)于我來說,已完全是個(gè)偽問題。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開始寫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顯然是因?yàn)橛行┵€氣,不斷地退稿,讓人產(chǎn)生了一種不可遏制的沖動(dòng),退一短篇也是退,退一長篇也是退,為了減少退稿次數(shù),還不如干脆寫長篇算了,起碼在一個(gè)相對(duì)漫長的寫作期間,不會(huì)再有退稿來羞辱和干擾。從安心到省心,又從省心回到安心,心安則理得,名正便言順。事實(shí)上,我總是習(xí)慣夸大退稿的影響,就像總是有人故意夸大政治的影響一樣,我顯然是渲染了挫折,情況遠(yuǎn)沒有那么嚴(yán)重。被拒絕可以是個(gè)打擊,同時(shí)也更可能會(huì)是刺激和惹怒,憤怒出詩人,或許我們更應(yīng)該感謝拒絕,感謝刺激和惹怒。
思想的絢麗火花,只有用最堅(jiān)實(shí)的文字固定下來才有意義。我知道對(duì)于一個(gè)作家來說,除了寫,說什么都是廢話,嘴上的吹噓永遠(yuǎn)都是扯淡。往事不堪回首,我希望自己的寫作青春常在,像當(dāng)年那些活躍在民間的地下詩人一樣,我手寫我心,我筆寫我想,睥睨文壇目空一切,始終站在時(shí)代前沿,永遠(yuǎn)寫作在文學(xué)圈之外。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最耳熟能詳?shù)囊痪淇谔?hào),就是要繼續(xù)革命。要繼續(xù),要不間斷地寫,要不停地改變,這其實(shí)更應(yīng)該是個(gè)永恒的話題。文化大革命是標(biāo)準(zhǔn)的掛羊頭賣狗肉,它只是很殘酷地要了文化的命,并沒有什么真正意義的文學(xué)革命。文學(xué)要革命,文學(xué)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為文學(xué),真正的好作家永遠(yuǎn)都應(yīng)該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