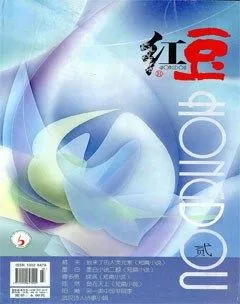我的行為藝術(創作談)
《狼來了的人類元素》是我正在寫的一組跨文本小說的首篇,還沒有寫完。
這組小說,篇與篇之間,既獨立成章,相互間又有所關聯。之所以稱其為“非常文本實證小說”,有兩層意思,一是這組小說使用的寫作手法是非傳統的,它呈現出游離和跨越傳統文體的特點,卻又雜糅了現存文本具有的所有可能的意指。二是它的真實性與荒誕性的融合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屬于非虛構的生活原材料所本真具有的荒誕,這種荒誕比真實更加真實,文中援引的例證以及所述皆有確鑿事實和出處為依據,這便是它被我稱之為“實證小說”的原因。它試圖借助所有現存的種種文體和文本樣式,努力把自己武裝到牙齒,打扮得光怪陸離,幾近四不象。究竟意欲何為?究竟想要以此來實證一些什么東西呢?
這里,先不做回答,姑且容我從頭說起。
小時候讀伊索寓言,便知道有—個放羊孩子五次三番喊“狼來了”,騙來周遭許多聞聲趕來打狼的人。以為是孩子氣的頑皮,無非是輕松一笑的事情,孰料后果卻很嚴重。謊言欺世的最終是失去了人們的信任。當狼真的走來時,卻沒有人相信他發出的告警和呼救,以至被狼自由自在地咬出了一片血腥。是否連帶孩子也被狼吃掉或是咬傷,似乎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誡孩子們的世界以至成人們的社會,許多事情是不可以撒謊的,否則便會悔恨莫及。
在我的眼里,不論是西方的上帝還是東方的神祗,都是造化和自然。
地球曾是一片地肥水美物產豐富鳥語花香生態平衡的草場,人類則如同顏色不同、種類不同、區域分布不同的羊只。那么誰是牧羊人呢?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他還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舍命。”他又說,“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信他的人也承認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辨別好壞牧人的方法也很是直白:“雇工只為金錢而看守羊群,耶穌則為著愛,專心照料自己的羊;耶穌不單是履行責任,他更愛我們,甚至為我們舍命。偽冒的教師和假先知就不會有這種奉獻了。”
我以為,上帝只是人類的一種精神寄托,眾生皆羊只是因為內心的惴惴不安所使然。圣經中所說的“雇工”便是被時代造就或是被從羊群中公選(當然也可能有賄選)出來或是任命的,如同伊索寓言中那個被村民選出來放羊的還動輒愛撒謊的孩子吧?
也未可知。人類原本是自然之子,在連篇的謊言中玷污了牧羊人的清白,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慎淪為一個毒孩子,擁抱自然的同時侮辱和損害了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懷欲,勿施于自然。要想潔凈這個世界,先得潔凈人類自己。如果真能這樣,那個草場上的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樹那些草那些花鳥蟲魚那些飛禽走獸那些萬物和生靈就有福了。
人類也因此有福了。
蜥蜴爬來爬去,是該殺死它的肉體,還是殺死它的行為?人類與生俱有的自私和貪婪的習性,限制和妨礙了人類科學與自然偉力的六神合體。妄自尊大以為地球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結局是捉襟見肘。20世紀80年代我的劇本《山林的女兒》要拍電視劇,去大興安嶺找外景,發現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毀得很厲害。當地人說,以前推開家門就是樹,現在得坐汽車跑上一天才能找到樹。這對我觸動很大。我把這事寫成了—個中篇《森林的性格》,發表在1984年的《啄木鳥》上。獵天者必被天獵。由此伊始,便與人類的極端欲求做了對頭,黑色生態系列長篇《黑雪》、《毒吻》、《天獵》、《地獵》、《天欲》、《地欲》、《人欲》、《極樂》等書應運而生。銷得很火。可是發現許多人不求甚解只是看熱鬧。竊思再高妙的琴聲,也不如—聲吆喝,一記鞭撻,來得有效。行動是美麗的。真正的“行為藝術”可以直接干預那些“雇工”的急功近利和為富不仁,哪怕呵護一棵小草,維護一只小動物,植一株樹,制止一起對自然的殺戮,呼喊一聲綠色的口號,也強似坐而論道,勝過坐以待斃。
言論不如行為,而追求美好理想的行為本身,就是藝術。
“行為”的結果從1997年我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哲夫文集》十卷本之后,便棄小說而開始寫報告文學,只因為報告文學可以直接干預社會,明白說話,人人都看得懂。“藝術”的結果是先寫下了第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檔案》上下冊,寫中國環保的歷史和淮河的治污過程。這本書得到了時任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的曲格平先生的關注和好評。他邀我參加中華環保世紀行,從此便跟隨中華環保世紀行記者團走遍大江南北直接干預社會。先走黃河八省區,寫了《黃河追蹤》上下冊,在人民大會堂開新聞發布會,曲格平主任親自主持會議,北京廣播電臺長篇連播,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然后走長江十三省區,從上海走到沱沱河,走了一百零八天,記者們人多可以輪換,作家就我—個人。過后我寫了《長江生態報告》,先在國外出版,后在國內出版,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兩年后又補充資料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江河三部曲《淮河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長江生態報告》,也引起不小的反響。再后來我又走了西部九省區,寫了一部60萬字的大書《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要說有什么信念在支撐我,那就是,你我他,大家都是環境中人,環保不只是公益的事業,更是人類自我的反省與救贖,貌似公益,實乃自救。就這么簡單。
十四個年頭的“行為藝術”,近三百萬字的生態環境報告文學作品,使我淪肌浹髓地深切感到:我們給予自然的愛總是太少,而自然給予我們的愛總是太多。過去、現在,甚或將來,人類總是以自己的低能蔑視萬物,以自己的無恥濫用資源,還自以為得計。當它們不再愛我們,悄悄地隱匿身影,消失蹤跡,并遠離我們時,真正恐慌的不是它們,而是我們。
我們有什么理由居高臨下地看待它們?不是我們在呵護它們的生存權利,而是它們在呵護我們人類的生存根本。別以為人類可以主宰萬物,別以為自然生態可以任我們損害,自然界的每株樹每根草每滴水每個生物的手里都攥著我們人類的呼吸,它們纖細美麗的手指時刻都扼在我們人類的喉嚨上,它們溫潤馴良的牙齒無處不在隨時隨地都咬在我們人類的命脈上。
這些年我幾乎嘗試并使盡了所有的文學手段,小說、紀實、散文、詩歌、雜談、評書、影視、廣播劇,還多次舉辦過環保講座,辦了環保博客,成立了環保的圈子,幾乎是冷兵器熱武器長槍短匕都用盡,如今又轉回頭寫小說。前不久為不拘一格糾聚更多力量與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的冰凌先生合伙打出了國際生存文學研究會的旗幟,只因環保已經重要到來不得半點矜持和拘泥,需要全世界全社會全人類全方位總動員。也就是全能總動員。
我們唯有放下人類那一款淺陋的功架,走向自然那一份深邃的本真,擺脫與生俱有的自私屬性,淡化和克服自身的貪婪,使自己成熟起來、偉岸起來,才有可能繼續生存下去。文學即人學,生存之學最接近人類的本質,也最接近文學的本質。生存環境一旦潰滅,一切學科都將蕩然無存。文無定法,所以我也來了個跨文本全能總動員,來實證人類生存的困窘。
這就是我創作這一組“非常文本實證小說”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