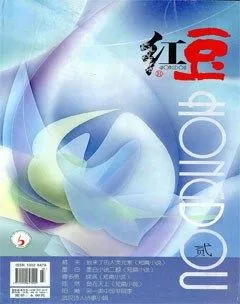漂泊三章
粟子珍,南寧市作協(xié)會(huì)員。作品在《散文》、《湖南文學(xué)》、《紅豆》等刊物發(fā)表,曾獲得首屆“芙蓉杯”文藝創(chuàng)作大賽優(yōu)秀獎(jiǎng)、“千禧杯”詩(shī)文大賽優(yōu)秀獎(jiǎng)。并于近期獲得“龍盛寨柳城市花園”杯“首善之區(qū)”散文大賽二等獎(jiǎng),作品專輯《風(fēng)塵的顏色》正在出版。
漂泊路上的雪
不知道從什么時(shí)候,外面渺渺茫茫,下起了大雪,天地間一片迷蒙。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tái)。”
這叫我有些猝不及防!在這一條漂泊的路上,雪花,在這一個(gè)夜晚,這一趟由南向北奔馳的列車(chē)上,不期然地,鋪天蓋地,來(lái)到了我的身旁,鋪滿了我此去的行程。
我不過(guò)是從一段睡眠中醒來(lái),也許是想看看天色吧。偶爾習(xí)慣性地撩起窗簾,向外打望時(shí),才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片雪花,這一片車(chē)窗外的紛紛擾擾,漫天的喧鬧與迷離。
這一種猝然的相逢,略微地叫我有些訝異,也激起了我心里的驚喜,讓我生起了一種他鄉(xiāng)遇故知般的興奮號(hào)情瀾。
我頓時(shí)睡意全消,干脆披衣而起,坐在我處于下鋪的位子上,向玻璃窗的外面張望。雪光,映亮了幽暗中的原野,雖然有些微弱,但大地與雪花的影子,仍然清晰可辨。我就在那微亮的雪光里,細(xì)細(xì)地觀賞著,這一片玉牒瓊花,自廣寒的碧落間,紛紛地灑落。然后,我又站起身來(lái),躡手躡腳地,走到對(duì)面的窗口下,坐在那可以自行翻轉(zhuǎn)的短椅板上,撲在窗玻璃上,凝足了目力,向夜空里,觀看著她們飛揚(yáng)的飄蕩與舞蹈。
列車(chē),穿過(guò)夜色,在廣袤的、丘巒起伏的大地上奔馳著;而雪花,在原野上,在北風(fēng)呼嘯的天空中,在幽微的雪光里,縱情地飛撲,打著回旋,歡舞成一片。雖然有些影影綽綽,但我仍然能感知她們形跡的變化:她們一陣疾了,又一陣變徐;有時(shí)疏了,而有時(shí)又驟然地趨密。當(dāng)雪花疾時(shí),如蝶醉蜂狂,一陣一陣卷動(dòng)著,密密撲來(lái),窗外一片繚繞迷亂;而徐時(shí),雪片大團(tuán)大團(tuán)地,悄無(wú)聲息紛紛揚(yáng)揚(yáng),在夜深里,在空闊而沉默的土地上,無(wú)邊地飛灑,飄飄搖搖,如一片一片旋舞的鵝毛。
臥鋪的車(chē)廂里熄掉了燈光,只有車(chē)輪震蕩著碾過(guò)鋼軌的聲音,不停地傳來(lái),以及人家酣睡時(shí)的呼吸或夢(mèng)囈,清晰可聞。此外,四周一片岑寂。或者,此時(shí)的天地間,已只有我一人,在這車(chē)窗邊,在這冷而沁著芳香一樣的夜空里,在這泛著夜光的雪地前,守望與陪伴著這一天的雪花吧。
我盡情地享受著這一刻的放任與陶醉。長(zhǎng)年的漂泊,我只是在風(fēng)塵中不住地往返,身系著一家數(shù)口的生計(jì),如一只在曠野天空里,在風(fēng)霜雪雨、寒暑塵土中飛越往還,尋覓食物的鳥(niǎo),身上積滿了塵土與疲憊,猶自常常憂懼,擔(dān)心不能尋找到足夠的食物,以果腹自己,也養(yǎng)活家人。歲月,在這樣的穿梭中,已逐漸地磨礪變老,蝕刻滄桑,好似陳舊不堪,令人生出冷漠與麻木。可是,漂泊途中突然邂逅的這一片雪花的相伴,人生的歲月中偶然擁有的這一片刻的旖旎,卻叫我久久地迷狂、沉醉著,不忍放棄,不能自已。
雖然隔著車(chē)窗,我并夠不著那些雪花,與她們相親,那些雪花,也只是一些迷亂的影子,在窗外飛撲著,而且總是一閃而過(guò),可是,我卻感覺(jué)到與她們廝處在一起,濡沫無(wú)間。
夜已經(jīng)很深了,或者已是臨近天明的時(shí)分了吧。我在黑暗中,時(shí)而伏在車(chē)窗上,望著外面的雪花,時(shí)而又從那自行翻轉(zhuǎn)的短椅板上站起來(lái),在過(guò)道里,一段極短的距離間,也就是那一個(gè)窗口旁,悄悄地徘徊,久久地延留著,不肯離去。人生的遭際,生命的歷程,已讓我從內(nèi)心的極深處,更加鐘情與喜愛(ài)著這一群飛逐的花朵,我感覺(jué)到自己,與她們生命相接,神與魂授,而融為一體。
此一刻,我所感受到的,她們所給予我的,不是那種“千里冰封,萬(wàn)里雪飄”、“數(shù)風(fēng)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為江山大地折腰的氣吞山河、豪放胸襟、慷慨激昂。
不是“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fēng)大散關(guān)”、“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那樣的報(bào)效家國(guó)的鐵血壯歌。
不是“輪臺(tái)東門(mén)送君去,去時(shí)雪滿天山路”那樣的繾綣惆悵,纏綿不絕,別離情深。
不是“飛揚(yáng),飛揚(yáng),飛揚(yáng)——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的輕揚(yáng)熱烈,愛(ài)情與浪漫。
也不是“梅雪爭(zhēng)春未肯降”那樣的公允平正,閑情逸致。
我首先會(huì)心與默契地感知與喜悅著的,是她們身上的一種無(wú)畏。
這些小小的精靈,來(lái)自遙遠(yuǎn)的窮荒極地,她們是朔風(fēng)與冰川之子,是大自然的苦冽與嚴(yán)寒的結(jié)晶。她們坦蕩從容、一任自然地,存身在北風(fēng)里,隨風(fēng)奔驟、回轉(zhuǎn)、飄蕩著,從來(lái)沒(méi)有憂傷與畏懼過(guò),高天寒流的洶涌、大地暴風(fēng)的激烈與嚴(yán)寒的凍裂,反而由衷地歡喜著這一切。她們把那些寒冷的凍裂,結(jié)成了自己的潔白;寒冷愈是凜冽,她們的潔白,愈是晶瑩與透徹。
其次,我感知與喜悅著的,是她們身上的一種歡樂(lè),一種華貴、雍容、曼妙與美麗。她們從來(lái)沒(méi)有拒絕,而是縱身地投入到北風(fēng)的肆狂和撕裂中。她們把這種北風(fēng)的肆虐與撕裂,變成了自己的輕盈與舞姿,漫天蹁躚,飄飄飛舞,怡然高蹈著,倏爾忘情。北風(fēng)愈是狂野,她們的舞姿,愈是流光溢彩,愈加回蕩與熱烈。
接著,我喜歡的是她們的自由。她們把自己小小的身軀,縱入天地間飛揚(yáng)著,天高地遠(yuǎn),六極八荒,長(zhǎng)空浩蕩,天地愈是廣闊,她們的自由,就愈是奔放與灑脫。
最后,我喜歡著的,是她們的一往情深、從不自棄。她們從來(lái)就沒(méi)有哀怨,也不妄自菲薄,自己是多么地微弱與渺小,從不卑微自己顏色的單一。她們從不放棄,而是以自己的屑末身軀,始終不懈地奔赴著,擁抱在一起,用自己的些微的潔白,鋪滿了這個(gè)世界,直至讓這個(gè)世界,變成了瓊雕玉琢一樣的美麗。
寂寞沙洲冷
棲入那一家旅館的時(shí)候,已是薄暮時(shí)分。暮靄正在升上來(lái)。
這是一座有著濃重暮霏的城市,那些向晚的云氣,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lái),一陣一陣,成團(tuán)成片,在近地的空中,在城市的建筑問(wèn)卷動(dòng)、蔓延,由淺入深,漸漸地籠蓋了整個(gè)的城市與寬闊的水濱。一輪黃色的半圓的月亮,在那些云濤的上空緩緩地穿行,更叫人增添著這種旅途的蒼茫之感。
這是一個(gè)叫做“龍門(mén)”的旅館。并不是很高的建筑樓頂上,高高地矗立著“龍門(mén)賓館”幾個(gè)字樣,而“龍門(mén)”二字,尤其凸顯得巨大。援步而上,登上那些高高的臺(tái)階時(shí),我的腳下沉重而緩慢,我差不多已邁不動(dòng)自己的雙腿了。走進(jìn)那半開(kāi)的大門(mén),總是有一種很深、很濃重的江湖的意味。
進(jìn)門(mén)的地面上鋪著紅地毯,看起來(lái)厚重、其實(shí)并不寬敞的大廳,裝修得有些低矮。服務(wù)臺(tái)后面的墻壁上,照例嵌著幾面大鐘,標(biāo)示著世界幾個(gè)主要大城市不同的時(shí)點(diǎn)。一男一女,兩個(gè)扎著領(lǐng)結(jié)、穿著白襯衣藍(lán)馬褂的年輕人接待了我。他們告訴我,剛好有一個(gè)單問(wèn),標(biāo)準(zhǔn)房的價(jià)格是150元,但可以打八折,是120元。我可以先看一看房間。
沒(méi)有電梯,拖著已不大聽(tīng)使喚的雙腿,爬上了三樓,一個(gè)同樣裝束的年輕女孩,已等候在樓梯口:“先生,是您要看房嗎?”她伸著手,一直把我引到樓道盡頭的一個(gè)房門(mén)前,她的服務(wù)臺(tái)正設(shè)在那里。她用手里的—個(gè)卡片插了插,打開(kāi)了房門(mén)。
房間雖然不大,但還整潔,一應(yīng)俱全。單獨(dú)的房間,讓我感到自主與安全;120元的價(jià)格,不是很貴;而且旅館正處在一個(gè)十字路口,兩邊都有公共車(chē)站,那利于我趕早,一出門(mén)便可直撲我要去的市場(chǎng)。
就是這里了罷!我掏出錢(qián)與身份證,交給那位女孩,讓她去代為辦理入住手續(xù)。我實(shí)在已不想動(dòng)彈了。
隨著市場(chǎng)的發(fā)達(dá),它也越來(lái)越詭譎。哪里越是喧騰、熱氣炙人,哪里就越是迷惑,暗藏著驚悚與變幻。我必須如履薄冰,不辭勞形,各處反復(fù)甄別,仔細(xì)辨明,找到源頭,認(rèn)清真?zhèn)危忻髑熬埃M(jìn)到有利可圖的貨物,這樣才致不被獵牢、力避傾覆。而這樣一天奔走下來(lái),待尋找到一家合適的旅館時(shí),我已差不多累成一攤軟泥了。
那個(gè)女孩進(jìn)來(lái),為我換過(guò)了床上的被套與褥單,我總算可以停下來(lái),略一歇息了。
我竟然感到一些莫名的踴躍。我就好像一只飛行中的遠(yuǎn)騖,偶然遇到了一片暫可棲身的沙洲,可以在那里剔一剔自己翎羽上的風(fēng)寒、塵土與勞乏了。
我先痛快地洗一個(gè)澡出來(lái)。平時(shí)的一年四季里,我都洗浴著冷水;而這時(shí),我打開(kāi)蓮蓬,把水調(diào)到微溫。我全身拍打、用力按摩一遍,這樣,可以盡快恢復(fù)我的體力。然后,我圍著寬大的浴巾出來(lái),略開(kāi)一些空調(diào),躺到床上,拉開(kāi)被子臥著,閉上眼睛,讓自己的頭腦處于一種易醒而清澈的狀態(tài)。這樣略靜一靜神,我便可一躍而起。
我可以打開(kāi)電視,細(xì)細(xì)地搜索那些我喜愛(ài)的節(jié)目。這時(shí),沒(méi)有人與我爭(zhēng)奪遙控,我像一個(gè)自由王國(guó)的君主。我喜歡那些充滿智慧、張揚(yáng)個(gè)性、恣肆著才情而又沉淀著底蘊(yùn)的談話或語(yǔ)言節(jié)目,譬如鳳凰衛(wèi)視中文的《李敖有話說(shuō)》,央視的《百家講壇》、《子午書(shū)簡(jiǎn)》等。我很輕易地就可明白并欣賞到那些嘉賓或主講人的才華、氣質(zhì)與特征之所在,那像一道奢華的大餐一樣,大快著我的朵頤。
我可以熄滅了燈光,靠窗而立,欣賞著城市的夜色。那些異地的風(fēng)光與氣息,總是吸引著我。隨著我們生活的繁華,城市越來(lái)越流光溢彩,她追求著個(gè)性與特色的燈光與亮化工程,越來(lái)越炫目與燦爛。
我也可以在黑暗里獨(dú)坐,什么也不想,只是閉上眼睛,靜靜地聆聽(tīng)夜籟,聆聽(tīng)城市的聲音、天空的細(xì)語(yǔ),聆聽(tīng)這旅途上,隱約而來(lái)、時(shí)遠(yuǎn)時(shí)近,而又似有似無(wú)的風(fēng)塵的濤響……
但今夜,電視里我所喜愛(ài)的那些節(jié)目,一個(gè)也沒(méi)有;而明天,自己的行程繁重而緊張。我只有盡早睡下,以養(yǎng)足自己的精神與體力。
我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見(jiàn)自己駕著一葉小舟,陷入一片藕花里,不能掙脫,卻又有一種清遠(yuǎn)的馨香,一片喜悅的鷗鷺的聲音……
睜開(kāi)眼來(lái),窗外是一片蒙蒙的亮了。連忙一跳起床,洗漱出門(mén)。女孩的服務(wù)臺(tái)那里,赫然是一群年輕的女孩。她們服色各異,形容不一,或倚墻而坐,或伏案而臥,或在幫著那位女孩迎送賓客。見(jiàn)我一臉詫異,那位服務(wù)員連忙迎上來(lái)照應(yīng),一面向我解釋,這些都是她的女友,是來(lái)陪伴她值班守夜的。
我與那位女孩告別,一路離去,卻一路抹不去我心里深深的狐疑……
父親的天空與母親的土地
我的身體,其實(shí)禁不得勞頓。
許多年的漂泊,我不過(guò)是不間斷地,也從來(lái)不敢懈怠地,跑到那些生產(chǎn)的城市,從那些廠商手里,采集了貨物,運(yùn)到別的城市去販賣(mài)罷了,以此來(lái)維持自己的生計(jì)。
憑借著我對(duì)美的一點(diǎn)感覺(jué),我販賣(mài)著時(shí)裝。
二哥說(shuō),我平時(shí)是一個(gè)行動(dòng)遲疑的人,即使是買(mǎi)一棵小菜,也常常優(yōu)柔寡斷。可是不知道為什么,一到了進(jìn)貨的服裝市場(chǎng),我便換了一個(gè)人。我的目光犀利,動(dòng)作敏捷,在浩如煙海的市場(chǎng)里,在縱橫交錯(cuò)的穿行間,在幾近奔跑的匆忙中,我一眼便能捕捉出自己所要的貨物,而且毫不猶豫地訂下單來(lái)。二哥感嘆,他就怎么也沒(méi)有那兩下子!他常年做著那些大路貨,獲利甚微,生意總是險(xiǎn)象環(huán)生。而我卻感謝著老天,因?yàn)樗o我的這一點(diǎn)點(diǎn)感覺(jué),讓我在這日益艱難險(xiǎn)惡的服裝市場(chǎng)中,得以突圍。雖然不曾暴發(fā),卻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的確,一到打貨的時(shí)節(jié)——我們稱進(jìn)貨為打貨,那猶如“打魚(yú)”與“打獵”一樣,確實(shí)并無(wú)二致一我的生命里,便會(huì)充滿一種才思與激情,我會(huì)感覺(jué)到自己的神思,如一柄利器,在市場(chǎng)里直立著,“嗡嗡”地震動(dòng),閃著寒光。
或者正因?yàn)槿绱肆T,因?yàn)檫^(guò)度的緊張,因?yàn)殚L(zhǎng)途車(chē)馬的顛簸,因?yàn)槟切R不停蹄的穿梭與奔走,以及伴隨其間的飲食失時(shí)、憩眠無(wú)據(jù),還有大自然的暴寒暴暑、市場(chǎng)里空調(diào)的冷熱失常、身上的汗流汗息,一場(chǎng)奔波下來(lái),我常常頭腦昏沉沉地生疼,周身不適,神疲力乏,興趣低怠,甚至常常食不知味。
可是,我知道為了生計(jì),自己別無(wú)選擇,從來(lái)不能放棄,只有在抖擻精神中,砥礪向前。我唯有在病苦般的沉默中,祈愿自己的貨物采集成功,得到市場(chǎng)的青睞,賺來(lái)足夠的帑資,以告慰藉。
但很多很多的時(shí)候,盡管我們嘔心瀝血,付出了艱辛與努力,市場(chǎng)卻并不認(rèn)同,也不憐憫我們。它會(huì)讓我們一無(wú)所獲,甚至血本無(wú)歸。我們只有一身創(chuàng)痕、黯然神傷地離開(kāi)那里。市場(chǎng)里每年中,總是走馬燈似的輪換著新的面孔,時(shí)刻上演著悲歡離合的情節(jié)。
為了遵循市場(chǎng)的法則,節(jié)省時(shí)間,減少開(kāi)支,我們這些奔波的行程,多在夜間。這樣可以不誤白天,日夜并用,又可免去許多住宿的麻煩與費(fèi)用。而交通市場(chǎng),他們也競(jìng)爭(zhēng)激烈,為我們提供著日趨優(yōu)化的便利。在市場(chǎng)社會(huì)里,商戰(zhàn),始終更趨白熱化地在進(jìn)行著,廝殺,在速度與費(fèi)用這兩個(gè)領(lǐng)域里殘酷地展開(kāi)著,從未間斷,而那些極限,總是在一天一天地被壓縮與打破。
而夜空下的奔行,總是更叫人心潮難平、思緒紛沓。正是倦鳥(niǎo)知返、萬(wàn)物歸巢的時(shí)候,我們卻在匆匆地出發(fā);正是人家燈下團(tuán)聚、圍桌而坐、喁喁細(xì)語(yǔ)、款款分食的時(shí)候,我們卻在向著夜色深處,顛簸向前。
夕煙生起的村落,暮色籠罩中的田園,荷鋤歸去的農(nóng)人,偕牛暮歸的牧童,樹(shù)影下的燈光,夜幕里隱隱的人聲,城市初上的華燈,這一切,都常常叫我心里涌動(dòng)著,生起蒙蒙的淚花。
而那些夜色中幽暗的山影,月光下朦朧的曠野,那廣厚的土地及其生長(zhǎng)的一草一木,總是叫我感到如此熟悉與親切,我仿佛能聞到童年的氣息。其實(shí),我生命的深處,一個(gè)隱秘的角落里,一直有一個(gè)潛在的渴望,那就是回歸到一個(gè)有青山與流水的地方,置身于草木與土地問(wèn),過(guò)一種與大自然的露珠與寧?kù)o為伴的日子。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這種漂泊,何日可到盡頭,我是否有一天,能夠得到我心中的愿望!
在那些風(fēng)雨如織、孤影飄蕩、旅途迷茫的時(shí)刻,我的心里會(huì)泛起愁悶,充滿了憂郁與悲傷。
然而,這種漂泊,也時(shí)刻給予著我歡悅與狂喜。
每當(dāng)天色微明,車(chē)子抵達(dá)一個(gè)新的地方時(shí),我會(huì)滿懷欣喜地,看著東方的天空上,露出第一抹魚(yú)肚的白色;看著那一團(tuán)藍(lán)色的光影,在天空里漸漸地浸透、擴(kuò)散;看著那些鉛色的層云,漸漸地變換顏色,幻化出奇詭的圖景;驚詫著那些流霞,在空中翔動(dòng),在異鄉(xiāng)的土地上,如飛布的火焰。
那時(shí),我的心里,會(huì)充滿了歡欣與振動(dòng)。
一個(gè)冬天的日子,天剛放明的時(shí)候,天空中突然飄起了雪花。鵝毛般的雪花,大朵大朵的,在空中飛舞著,在北風(fēng)的吹刮里打起旋渦,隨著車(chē)子的行進(jìn)迎面撲來(lái)。車(chē)子在一種不可思議的繚亂迷離中,穿越向前,仿佛跌入一個(gè)奇異的時(shí)間的隧道;空氣冷而清新,仿佛開(kāi)滿了花朵。
那種美景,會(huì)永遠(yuǎn)銘刻在我的記憶里。
盡管這種逐利而奔的日子,并非完全是我所愿,盡管它已逐日地平常、暗淡、陳舊不新,可是,它給我的激情卻從未減退,我好像在其中淬礪,歷久而彌新。
這是一個(gè)血色的黃昏,晚霞的緋紅,奇異地浸染了天空與大地,久久久久地,也并不退去。我背起行囊,匆匆地趕往車(chē)站時(shí),碧藍(lán)碧藍(lán)的天穹,如洗過(guò)一樣,像天鵝絨一般美麗;西邊的天上,是一彎如鉤的新月,還有它旁邊,一顆閃爍的孤星。
我突然在路邊停留下來(lái),不知是為這一片澄澈的天空,為這一彎如鉤的新月與孤星,還是為了這種漂泊。我的眼睛里涌滿了迷蒙的淚水,在路邊輕輕地哭泣——
我依然乍驚乍喜地,蹈著生活給我的這些火焰,它在這一條漂泊的路上,一步一步地穿繞、焚燒著,誕生著我新的生命。
那一節(jié)一節(jié),浴火而生的生命,無(wú)論她是痛苦的、歡樂(lè)的、寂寞的,還是憂傷的,她都是我的所愛(ài),是我的幸福與期盼。
在那—個(gè)時(shí)刻,我會(huì)脫盡塵垢,在一片澄澈中,風(fēng)華絕代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