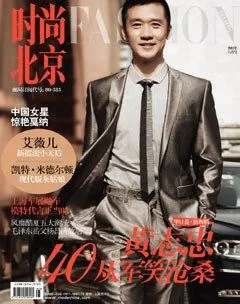他們在北京
“臥游”作為北京國際設計周代表團在米蘭設計周的外圍展區(qū)托爾托納(Via Tortona)的重頭戲,將北京通過一種全新的形式展示在了世人面前。在此次參展的原創(chuàng)設計師中Marcella Campa、Stefano Avesani和Bo Young Jung、Emmanuel Wolfs分別是兩對來自異國的設計師,前者是搭檔,后者既是搭檔更是伴侶;前者生活在胡同,后者教學在中國藝術類的頂尖高校中央美術學院。在看資料的時候,心中已暗自覺得這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如今卻都生活在北京,那北京于他們到底是什么,我真的很想知道。這一次,他們不僅僅是設計師,更是生活在北京的“北京人”。
他們生活在胡同里
Marcella Campa和Stefano Avesani
Marcella Campa和Stefano Avesani來自意大利,定居北京已有六年多的時間,一直在創(chuàng)作Instant Hutong項目,探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深層關系。他們對中國城市的變化和發(fā)展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致力于研究當代中國城市和鄉(xiāng)村在時代大背景下的變化和轉型,從都市研究到視覺藝術表達,努力探討空間與社會的互動關系。
Marcella和Stefano來自文藝復興的發(fā)源地——意大利。我們之間的對話帶有濃濃的意大利腔調(diào),時不時的兩個人還會蹦出一兩句中文,于是整個過程英文、意大利文和中文夾雜,總是讓人感覺有些一知半解。可即便如此,你還是可以從他們真誠的目光中找到你要的答案,甚至可以看到更多。
電話、郵件溝通了許久,這次采訪終于在某個午后被落實了下來,地點就在帽兒胡同他們的工作室。帽兒胡同是一個誕生過不少王公貴族的地方,胡同兩邊一邊通往后海,一邊通往南鑼鼓巷,都是北京著名的旅游勝地。而他們就在某個不起眼的小院子里面,安靜地做著他們的創(chuàng)作。在這樣一個地方,即使它們已經(jīng)輝煌不再,居住在這里的人也還是能感受到那些歷史的痕跡,而這種感覺對于他們這樣兩個來自異鄉(xiāng)的人尤甚。
他們已經(jīng)住在北京6年,他們對胡同以及四合院這種具有濃厚的北京特色的組合總是有無盡的好奇。你看到他們在“臥游”的作品似乎就是一張地圖,可即使就是這樣一幅看起來不起眼的地圖,其實背后也蘊育了許多故事。他們是設計師,或者你可以說他們是藝術家,但是他們一定不是地圖描繪師。他們筆下每一處胡同密集地都是經(jīng)過他們的巧心思量,光是地點的選擇便已經(jīng)沒那么簡單。談話間Stefano也向我展示了一些他們既往的作品,雖然同樣關于“胡同”,但是他們卻把北京的胡同組合成了變形金剛,甚至讓我這樣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都驚嘆不已,想不到我的家鄉(xiāng)還有這樣一番風貌。而不僅僅是在北京的胡同,他們也做了許多其他的關于人、社會以及居住環(huán)境的作品,最新的作品叫做“120公里”,涉及了山東省與河北省之間的近60個村莊,從其中可以看出時代的變遷,歲月的更迭,甚至也可以讓這些居住在這里的人們?nèi)フ嬲牧私馑麄兊降咨钤谠鯓右环N環(huán)境之中。
誠如我所說,他們的英語帶有濃濃的意大利腔調(diào),連我都會時而遲疑,不知道他們到底要說些什么,如今這胡同里生活著的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那他們是不是也有所交流,生活在這么北京的地方,他們是不是也會遇到許多問題,其實我也真的好奇。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也笑了起來,然后說:“是有一些不方便,不過這不阻礙我們和他們一起生活。”也許,我說這樣的話是帶有些自我炫耀的架勢,可是你還能找到哪個城市里有這樣一群可愛的人,他們或許沒有過高的文化水平,可是他們的熱情無人能敵,即使他們和外國人的對話僅僅能局限于“你好”、“謝謝”、“對不起”、“再見”的層面之上,可他們還是能有辦法知道對方到底需要什么,這就是北京人。而更具體的就是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人,尤其是那些最最北京的大爺大媽。他們總有最豐富的肢體語言來幫助他們彌補言語上的不足,而那些最原始的、最樸實的北京人的特質(zhì),在新一代的北京人,在我們的身上已經(jīng)慢慢消逝。CBD是北京,那是一種都市與忙碌,胡同也是北京,那是一種閑適以及安逸。我問他們最愛北京哪里,他們說是胡同,除了那些古代的雕廊畫棟以及隱藏在這小院之中的歷史讓他們著迷之外,更是這種真實讓他們感覺溫暖。
從大學至今,他們已經(jīng)合作了14年,一起研究人、社會、環(huán)境三者的關系也已經(jīng)過去了10年,Marcella說他們也還會繼續(xù)這樣合作下去。相識如此之久并可以一直與其并肩同行必定是因為對方身上有與眾不同的閃光之處,而這也并不僅僅是“異性相吸”這種太過淺顯的道理就可以一概而過的。Stefano說,他最欣賞的是Marcella那種專注于目標以及永不放棄的精神。Marcella說,她最欣賞Stefano的是他的想法,他們總能想到一起,那種默契是別人無可替代的。話說到這里,他們相視一笑,其實也就是默契的最佳體現(xiàn)。
我無法向你說明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每當他們認真地聽著我說的話,而我卻又似乎只明白了80%她所說的話的時候,我心里也會有些小小的內(nèi)疚,可即便如此,很多事情你甚至都可以透過他們的眼睛看到,真誠且美好,我也希望你可以看看他們更多的作品,感受一下這個不一樣的北京,不一樣的中國。
www.instanthutong.com
他們生活在校園里
Bo Young Jung和Emmanuel Wolfs
Bo Young Jung和Emmanuel Wolfs畢業(yè)于英國皇家美院,目前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工作和生活在北京。他們自2005年起便通過概念設計來探索情感與思維的可能性。他們的設計實踐通常包含并挑戰(zhàn)當代社會的種種問題,例如全球關于自然、科技、心理學和多元化趨勢的辯論。這種設計實踐把設計當作一種媒介而不是專業(yè),并希望借此拓寬對關乎我們生活環(huán)境的公共事件的批判方法。
Bo Young Jung來自韓國,母語是韓語,是一位標準的美女,我們交談的時候,恰好起了風,風吹過她的發(fā)絲,讓我都有些心動,總忍不住想要把這些美好的畫面記錄下來。Emmanuel Wolfs來自比利時,母語是法語,是一位標準的帥哥,綠色的眼睛泛棕的頭發(fā),看起來格外賞心悅目,甚至讓人對比利時這個國度也多了更多好奇。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說著兩種截然不同語言的人,卻在命運的驅(qū)使下在英國相識,并相知相伴,如今一同在中央美術學院教書。盡管說命運這件事太有些電影的感覺,聽起來有些夸張,可我還是覺得這真的太過奇妙,以至于讓我也有些心生艷羨。
他們第一次來到北京是在2008年,僅僅四天的旅程便讓他們對這個城市有太多期待,這讓他們在得知中央美院招聘外國教師的時候欣然應允。直至今日他們也依舊喜愛北京這座城市,喜愛那些生活在北京的人們,更喜愛這片校園以及他們的學生們。
說起決定前來北京的這段經(jīng)歷的時候,Jung的臉上依舊有掩飾不住的興奮,此時他們甚至已經(jīng)把北京當作了他們的家,他們真正的家鄉(xiāng)如今卻反而成了他們短期旅行的駐地。
Emmanuel說,很多年他的家鄉(xiāng)都是一成不變的,即便過了幾年再回去依舊是同樣的街道同樣的建筑沒有太大的變化,可每次他回到北京,即使只是過了半個月,這里也會有巨大的變化,他甚至不知道這些變化是何時發(fā)生的。他們相識于英國,英國于他們,也總是有很深的含義,Jung在那里遇到很多來自不同國度的人,也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Emmanuel在那里總能找到推動他的力量,他說那里對設計師來說是好的,因為你永不會止步。故鄉(xiāng)是一個起源,而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感受那些不同的文化,或許才可以讓我們更好的了解我們自己。
我想你會好奇,兩個異國的人要怎樣在中央美院教學?他們又可以教些什么?他們在美院教授藝術,不是教學生歷史、理論和那些枯燥無味的知識,他們更愿意告訴他們的學生該如何思考,如何設計,如何利用媒介的力量,如何找到自信。這世界我們每天能看到的東西太多,該如何將這些元素打散使其成為自己的,將它們更好的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的確相當重要,尤其對學習設計、藝術的學生來說。他們也不照搬西方的經(jīng)典理論,因為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西方有西方的文化,即使它們在設計領域已經(jīng)很成熟,但那也不適用于中國。我說中央美院總是帶有一些藝術家的感覺,而他們也覺得如此,學院派、實用派、藝術派的院校各有千秋,但藝術派在思維上的確最是活躍,而這也就是他們喜歡他們的學生的原因。
他們說過去總是有許多人說,中國的文化只有過去,可是他們來到這里,看到許多富有創(chuàng)意的新一代年輕人,他們也相信中國設計的未來,也許再過幾年,便會有更多的人看到中國的新興文化的誕生,我們不能輕言那些年少輕狂者一定不好,因為誰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借由這些“自由散漫”去打開另一扇設計的窗戶,或許也是推動著我們前進的良方。
和Marcella、Stefano比起來,Jung和Emmanuel之間多了另一層聯(lián)系,那就是“伴侶”。在講述他們彼此之間的故事之前,我可以告訴你一件小事,那就是采訪過后,在為他們拍攝的時候,每拍攝完畢一張,Jung都會看一下并找出其中的不足,然后告訴Emmanuel,甚至也會上前擺弄一下他,告訴他應該怎樣擺出一個好看的姿勢。這時,Emmanuel就會無奈地沖我笑笑,然后說:“你看,她工作的時候也會這樣,意見多多。”聽見這話的時候,心里洋溢出了一絲暖意,這感覺不是甜膩,而是沁人心脾的一種舒暢,溫暖且毫無負擔。他們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可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這些當然與他們不同的文化背景有關,因此他們也常常意見不合,甚至也會爭論,但再多工作上的不統(tǒng)一也不影響彼此對對方的欣賞。她說:“我在很多方面都很信任他,并欣賞他的許多獨到之處,和他在一起我永遠不會感覺無聊。”他說:“她是一個總是可以看得到未來的人,而我甚至連五分鐘以后是什么樣都不知道。每當我們有矛盾的時候,她就會說起韓語,而我則會說起法語,這種感覺確實也會很奇妙。”每次我說完一個問題的時候,Jung都會首先回答,語畢之后再望向Emmanuel,或者說一句:“你怎么想?”或者又只是看著他。這時他又會仔細地說些他的想法,銜接的總是恰當好處。于我的感覺是,Jung是個有些感性的人,Emmanuel則似乎有些理性,因為相比較Jung的情緒的表達,他可以把每個問題都陳述地有條不紊,句句真諦。這種感覺真的很奇妙,甚至更多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他們和身在同一國度的人有什么區(qū)別,情感總是相同的,而樂趣或許恰恰就在那些不同之中。
采訪過后,他們又帶著我在中央美院里簡單游歷了一番,并且我們又說了些對設計和時裝設計的不同的想法。更有意思的是,上學時學的那幾句法語也終于有了用處,我終于可以和真正的French Speaking表達我對法語這個語言語法之復雜的深惡痛絕。我們從設計談到語言又談到現(xiàn)在和未來,確實也有些意思,而更多時候我愿意和他們交流,甚至覺得這種交流會比同樣的語言更加順暢,那順暢超越了國別,超越了語言,是一種真心的交流,沒有距離。
結語:
“中國”這兩個字有時是沉甸甸地壓在中國的設計師的身上,他們試圖找到屬于中國的東西去表達,但是卻一直不得其所,甚至會變得不倫不類。其實,也許我們不一定要背負這么大的一個責任,而當有一天你真的對你的祖國有了更深的理解的時候,那個東西即便沒有雕飾,沒有龍,不是黃色,不是紅色,它也可以叫做“中國制造”,因為你就代表了中國。而恰恰是這些來自異國的設計師,反而時常比我們更了解我們的祖國,因為他們不存在這樣一個所謂的責任與抱負,于是也更自由地去看待這座城市。
芮成鋼曾說:“現(xiàn)在的中國就像一個暴發(fā)戶,而我們希望今后能告訴世界,經(jīng)濟的增長只是我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是我們的文化,也希望透過文化告訴世界到底什么才是中國。”感謝北京國際設計周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讓中國的設計師們與外國的設計師們有了更多的交流,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們來到這里,我們走出去,這種感覺真的很好,因為在這里你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