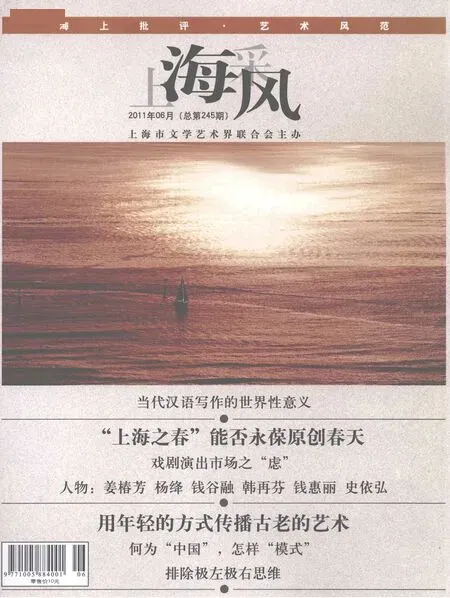說他好,還是說他壞?
文/黃佟佟
說他好,還是說他壞?
文/黃佟佟
人人都說好的《巨流河》放在案頭擺了很久,一直鼓不起勇氣讀,前天終于讀了,一讀就不能放手。這是臺灣政治老人齊世英的女公子齊邦媛的人生回憶錄,文字樸素而美,深情而節制,國家大事都不去說了,我喜歡的是她與飛虎隊空軍張大飛的一段情——
四月的一天黃昏,我們正在準備晚餐,有個女孩跑來說,有人在操場上等我。我出去,就看到張大飛走過來,穿著一件很大的軍雨衣。他已經是中尉了,制服領上是飛鷹,走路真有精神,是戰爭年代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種英雄。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說:“邦媛,你怎么長這么大,這么好看了呢。”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贊美我。以前我骨瘦如柴,弱不禁風。張大飛說,部隊調防在重慶換機,七點半要趕回機場,他只想來看我一眼。這時驟雨落下,他拉著我跑到屋檐下,把我攏進他的大雨衣里。隔著軍裝,我聽見他心跳如鼓。只是片刻,他松開我,說:“我必須走了。”我看著他在雨中跑步到門口,上車疾馳而去。一九四三春風遠,今生我未能再見張大飛。
少男少女的情感,純潔如斯,點到為止,此次分手之后齊邦媛開始讀大學。大一的周一她必能接到他的信,其中不乏熱烈的表白“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來看你,但是,我多么愛你,多么想你!”轉折在他受傷之后,“信中不再說感情的話。只說你二十歲了,所有學習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斷。”
當齊邦媛表示要轉學到云南時,他表示堅決不贊成,原因是沒有能力照顧她,大家惟一的生路是戰爭勝利。1944年她接到他的遺書,遺書上他花了許多筆墨解釋為什么他不能愛她,因為他是“必死之人,活著是害她,死了也是害她。”而叫人悚然一驚的是他在信后的淡淡幾句:“秋天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學老師,她到云南來找我,圣誕節和我在駐地結婚。”這不到一百字的內容把還在柔情蜜意中的讀者震了個目瞪口呆,完全可以想象當時還是小女孩的女主角受到的巨大打擊,“種種交糾復雜的情緒在我心中激蕩”,慟哭。
作為從不憚以惡意揣測人的民族的后裔,如用電臺情感DJ穿云透霧的解析能力來解述的話,即是:帥空軍看上了老師的女兒,在生死火海中把純潔的少女當成了他的精神避難所。“對于他,這些信大約像煙酒跳舞一樣,有幫助忘卻猙獰現實的用處吧!”然后他終于發現這種純柏拉圖感情落不到實處,正好撞到了女中學老師,覺得適合做老婆,她來找他索性就結了婚。也就是說,他在信里慢慢不說感情事的原因是因為他已經另有所愛,當小女孩認真了要跑去云南時他就害怕了,急急阻止她,“你對我的實際生活,知道得愈少愈好。”還有什么更明顯的欺騙么?一邊和少女情真意切談著紙上戀愛,一邊找了個宜家宜室的女子做老婆,知已的歸知已,老婆的歸老婆,幾乎就是少女不幸遇到感情騙子的翻版。
雖然齊邦媛在書里實在寫得非常克制,但你仍然可以看到她所受到的巨大打擊,不久之后她即受洗成為基督徒。她終身都在懷戀他,他給她信直到她八十歲仍歷歷在目,把他送的皮面燙金的《圣經》隨身攜帶,甚至七十五歲的時候回大陸陵園去尋他的名字,她對他惟一的責怪是:“要退回去扮演保護者兄長角色雖遲了一些”。只是遲了一些,但她仍然覺得他在保護她,她要終身紀念他。
很多女人,都會美化她們往昔的愛情,順便也會美化那個可能并不完美的戀人,但我想一想,挺對的挺好的。個個如張愛玲,把男人皮袍子下的小都榨出來,幾十年以后寫《小團圓》,寫出胡蘭成與桑弧在愛里的那種種不堪,“他不愛我”和“他們都不愛我”或者“他們都不夠愛我”,到底哪一種傷害更大?我不知道哪種更大,但那種慘淡的心情卻真真是對自己的二度傷害——講真,就連我這種鐵粉級的粉絲都替偶像心酸。
和他分開了,是說他好還是說他壞,其實是偽命題,說他壞是否就能讓你好過一點,能把自己內心的難過減輕一點,其實恐怕是更苦吧。所以,當感情逝去,何妨把他想好一點,就連心硬如張愛玲此生做過的最快樂的夢仍然是那個傷她最深的男人:“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映著碧藍的天,陽光下滿地樹影搖晃著,有好幾個小孩在松林中出沒,都是她的。之雍出現了,微笑著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澀起來,兩人的手臂拉成一條直線,就在這時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

黃佟佟 廣東作家,在多家媒體開設專欄,著有《感情這東西》《最好的女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