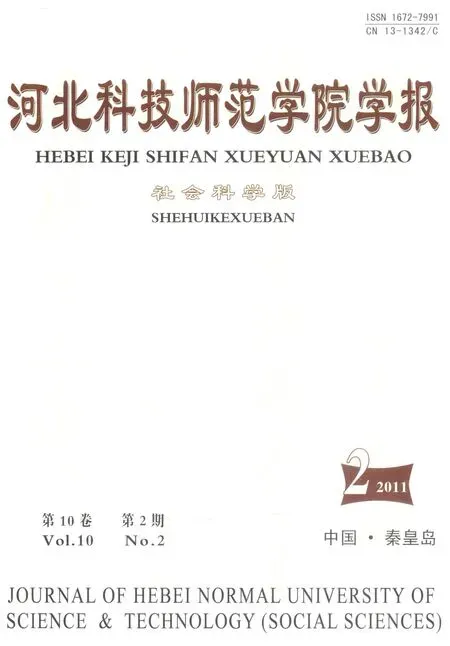量刑實踐中的被害人過錯考察
陳海平,張澤惠
(燕山大學 文法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量刑實踐中的被害人過錯考察
陳海平,張澤惠
(燕山大學 文法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被害人過錯作為量刑情節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越來越多,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分析其都成為量刑辯護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為量刑的關鍵情節。但是,立法上并沒有對被害人進行專門規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為酌定情節被加以適用,因此,賦予法官較大自由裁量權使得被害人過錯在量刑實踐中適用失衡,加之被害人過錯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缺乏相應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維護被告人的利益。
被害人過錯;量刑;自由裁量
刑事司法活動中,當事人及社會公正不僅期待定罪的準確,更關注量刑的公正。被害人過錯對于評判被告人行為(即定罪)、裁量被告人刑事責任(即量刑)均有重大影響,“被害人的過錯大小直接影響到加害人的刑事責任程度”[1]46,研究被害人過錯有利于定罪的準確與量刑的公正,刑事司法理應認真對待被害人過錯。
一、被害人過錯是量刑辯護的重要理由
犯罪不是單向的過程,不是一方積極加害而另一方消極被害的過程,是一種互動的存在[2]。犯罪人和被害人對犯罪行為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呈現出博弈狀態,犯罪評判中忽視任何一方都難免失之于片面。在犯罪人與被害人互動過程中,尤其是當被害人過錯成為誘發、促使或者強化沖突的關鍵因素時,就絕不應該將罪責全部歸結于被告人[3]。
事實上,考察審判實踐即可知,在涉及具體被害人的犯罪中,被害人過錯往往是辯護方慣常主張的重要辯護理由。對此可作如下說明:第一,理論上來說,被害人過錯成為量刑辯護的重要理由,正是通過司法裁決沖突進行社會治理的必然要求。被告人以被害人過錯為理由主張辯護,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司法機關對被告人的犯罪判處相應刑罰,并對被害人行為進行否定評價,通過公正裁決被告人——被害人之間的微觀社會沖突,真正落實法律對社會公眾行為的指引、規范作用。被害人過錯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出被告人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在存在被害人過錯的案件中,理應考慮到被害人在引起案件發生或者擴大損害結果中所存在的責任,充分考慮被害的前因后果,明確被害人在案件中的責任。法律在給被告人設置辯護理由時,應保持雙方利益的平衡,考慮到被告人給被害人造成傷害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到被害人對引起這一犯罪行為發生所應負的責任。面對各類犯罪,不能僅對被告人口誅筆伐、不依不饒,而對被害人予以無限的同情,對于有責任的被害人,應該在量刑時作為被告人的辯護理由予以考慮。第二,考察司法實踐可知,例如,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過錯情節是被告人挽救生命的關鍵。被害人過錯的認定攸關被告人生死,被害人有無過錯情節對于量刑是有重大影響的。對于辯護方來說,被害人過錯情節是辯護的基本根據。司法實踐的現狀表明,對于犯罪事實清楚的死刑案件,被害人過錯情節已成為辯護人進行成功辯護的重要理由。法院也越來越重視被害人過錯情節對刑罰裁量的影響,并在死刑適用中予以關注[1]47。例如,一位資深法官所列的87個故意殺人案例中,有24個案例都是因為“被害人過錯”而適用死緩或死緩以下刑罰的[4]。筆者調查的75件故意殺人案件中,也有31個案件是因為“被害人過錯”而適用死緩或死緩以下刑罰的。這些案件中被告人均依據被害人存在過錯這一辯護理由而免于死刑的處罰,使得生命得以延續。
二、被害人過錯是量刑裁量的關鍵情節
從量刑實踐來看,被害人過錯在量刑裁量中的適用越來越多,作用越來越關鍵。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被害人過錯影響量刑的實證資料難以獲取的情況下,筆者意圖分析刑事裁判文書,提煉其中被害人過錯影響量刑的信息,以及被害人過錯主要集中在哪些案件中,通過檢索“北大法寶”數據庫,最終整理了存在被害人過錯的案件288件。其中,故意傷害的案件208例、故意殺人和過失致人死亡的案件43例、尋釁滋事9例(包含涉及故意傷害的2例)、交通肇事15例、詐騙類4例、放火罪1例、非法拘禁罪2例、非法行醫1例、盜竊3例、爆炸1例、搶劫1例、綁架和敲詐勒索2例。可見,被害人過錯情節在多種不同的案件中都有體現,并主要集中在人身權利案件中,尤其在故意傷害案件、故意殺人(包括過失致人死亡)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中適用比例較大。筆者通過搜索北京、上海、重慶、深圳、西安、鄭州五大城市的法院官方網站(部分故意殺人案件還取自陜西省高院的官方網站),主要收集了2009年至2010年的307件有關被害人過錯的案例(包括一審、二審)。其中故意傷害案件117件、故意殺人75件、交通肇事114件,意圖分析被害人過錯對量刑裁量的影響,并列表如下:

?
通過數據分析,可以得出:第一,在故意殺人和過失致人死亡案件中存在被害人過錯的案件比例達34.67%,而因為被害人過錯的情節法官從輕處罰被告人的比例為17.33%。該類案件中,在沒有法定從輕情節的情況下,被害人過錯作為酌定從輕情節則發揮著愈益重要的的作用,已成為關鍵情節,因被害人過錯而減輕犯罪人刑罰并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案件日趨增多。例如,在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年辦理的125件故意殺人案件中(含一、二審),有48件因被害人有過錯而對被告人判處了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有17件因被害人有嚴重過錯,對被告人判處了10年以上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如被害人有嚴重違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有加害行為在先、被告人有防衛因素等;有3件定性為防衛過當,減輕處罰;有2件義憤殺人,情節輕微,并有自首法定情節的,均被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5]。第二,在故意傷害案件中,存在被害人過錯的案件比例相對更高,而且法官對被害人過錯的支持率也相對更高。這說明,法官也認同被害人過錯的關鍵作用,而在故意傷害案件中越來越重視被害人過錯這一情節,并據此在量刑中給與被告人從輕處罰。第三,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存在被害人過錯的比例較少,但是也有將近20%的案件已經涉及被害人過錯,在這些案件中法官支持這一情節并從輕處罰的案件比例較小,這一數據比前面的故意傷害和故意殺人案件有所降低,但是相對其他類型的案件,這些案件的數量也不可忽視。因為立法上對交通肇事責任區分為全部責任、主要責任、次要責任,這本身就體現了對被害人過錯的考慮,有相當比例的案件中被告人負主要責任,而筆者未把它們納入明確主張被害人過錯的案件中。從立法上對交通肇事責任的區分就已經體現出被害人過錯對適用罪行法定原則的關鍵作用。對于被告人而言,最大限度地減少可能獲得的司法懲罰,早日獲得自由是其迫切希望的,法院基于被害人過錯在量刑時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對減輕被告人的罪責起到很大作用,成為被告人為自己辯護的關鍵情節。
三、被害人過錯在量刑實踐中適用失衡
量刑均衡,就是指同罪同案同判,異罪異案異判,司法裁判在時空上保持高度的一貫性和一致性[6]。按照量刑均衡,同罪同案同判的要求,量刑失衡主要表現為判決偏輕、過輕或者偏重、過重,即同等的罪行沒有得到同等的量刑。有學者做了更詳細的歸納,主要表現為:對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在法律規定的刑罰幅度之內,有的做出了刑事處罰的決定,有的做出了免于刑事處罰的決定;在法定刑幅度內,有的做出了接近最高刑的處罰,有的做出了接近法定最低刑的處罰;在法律規定可以并處數種刑罰種類的,有的做出了并處決定,有的只單處了應當判處的刑罰;在刑罰執行的基礎上,有點被判決宣告緩期執行,有的被宣告立即執行[7]。
(一)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過錯在量刑中的適用并不均衡
“被害人過錯的認定及其對刑罰裁量的影響力、特別是對死刑適用的影響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1]47“被害人的過錯,在我國刑法中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本來酌定情節也是從輕情節,在對被告人量刑時也是應當考慮的,但在司法實踐中往往不予考慮。”[8]的確,被害人過錯在立法中未明確為法定量刑情節,如前面所述在審判中屬于酌定的量刑情節,在具體的裁量過程中是否考慮,完全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如何具體適用,立法沒有明確的規定,法官是否采納,完全取決于法官自身的素質和經驗。有些案件中,法官考慮被害人過錯這一情節,有些案件中法官則不予考慮該情節,所以,被害人過錯在量刑中適用不均衡的現象時有發生。如下例:
2001年3月2日晚,何鵬持在某銀行辦理的儲蓄卡到校外ATM機上查詢余額時,奇怪地發現,原本只有10多元余額的銀行卡,卡面余額竟有百萬元之多。2002年7月12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法院認為其行為具有秘密竊取的性質,已構成盜竊罪,且數額特別巨大,判處無期徒刑。宣判后,何鵬不服,提出上訴。2002年10月17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而2006年4月21日,許霆與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許霆取出17.5萬元。2008年3月31日,再次開庭,許霆被以盜竊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追繳所有贓款17.3826萬元,并處2萬元罰金。
兩個案例驚人的相似,但是被告人的命運卻大不相同。不管經歷了怎樣的一波三折,許霆最終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而何鵬在5年前就被判了無期徒刑。這說明,許霆案中法院對量刑情節做了考慮,法官對被害人過錯情節的適用相互不一致,云南的法官在審理何鵬案件時就沒有考慮銀行管理不善,給被告人賬戶誤存大量金額的過失,而廣東法院的法官則考慮到被害人有過錯這一情節,即銀行ATM存在漏洞,銀行沒有一個報警預設系統,其存在過錯。可見在相似的案例中,被害人過錯在量刑中適用并不均衡。另外,在許霆案件發生后,何鵬成為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在已經服刑了7年后,2009年11月18日,何鵬家人終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再審決定書。短短一周之后,獄中的何鵬收到了省高院的再審判決書。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和罪名與之前的判決并無二致,但刑期由無期驟減為8年零6個月。令人欣慰的是,最終兩個案件的量刑結果達到了均衡。但是,如果何鵬在獄中得知許霆案,沒有給中央臺的主持人寫信,沒有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那么結果,可能就是忽略了被害人過錯,導致量刑失衡。
(二)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過錯在量刑適用時的從輕幅度失衡
作為酌定情節的被害人過錯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定量分析,其過錯的程度以及應該對應的量刑幅度并不清晰。雖然其在審判實踐中有所體現,但是還無法發揮有效的規范作用,保證量刑的均衡。因為被害人過錯是酌定情節,適用的幅度和范圍都存在模糊性,從輕的幅度過大或者過小完全出于法官的自主判斷,而且在法律上我們也找不出有力的反駁證據,從輕幅度過大或者不從輕不違法。實踐中雖然被害人過錯作為酌定的情節在量刑中有所適用,但是從輕幅度存在失衡的現象,筆者以下面的兩個案件為例,進行說明。
2009年的鄧玉嬌案中,巴東縣地區檢察院將鄧玉嬌起訴至巴東縣法院,罪名是故意傷害罪。檢方同時也認為鄧玉嬌具有防衛過當、自首、死傷者有過錯在先等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6月16日,湖北省巴東縣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鄧玉嬌案”,并作出對鄧玉嬌免予刑事處罰的判決。
但是,在2009年還發生了一例相似的案件,甚至被害人的過錯程度要大于上例案件中被害人的過錯,案件發生的情況更加危險緊急,但是量刑的結果卻大不相同。
2009年2月的一天,洛龍區關林鎮一女青年宋麗加完夜班后,單身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被剛吃過宵夜喝過酒的公務員江某盯上,江某按住宋麗的嘴將她拖到樹林深處實施強奸,宋麗在被強奸的過程中沒有配合江某,導致江某生殖器官折斷,在明知江某喝酒有醉意的情況下,也不及時打120求救,導致江某失血過多而死亡。2010年3月26日,洛陽市洛龍區檢察院向洛龍區法院提起公訴,指控宋麗犯有故意傷害罪。法院認為,被告人宋麗應當預見強奸者江某可能造成傷害,可宋麗在被奸時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導致江某死亡,宋麗的行為應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另外,鑒于被告人宋麗在案發后認罪態度比較好,同時,被告人積極進行民事賠償,已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有悔罪表現,且被害人江某有一定責任,故從輕處罰。結果,宋麗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執行。
在此案中,法院也考慮到了被害人江某負有一定責任,也對被告人宋麗做出了從輕處罰的決定,但是量刑的幅度明顯要小于“鄧玉嬌”案。何況,從輕處罰的決定還綜合考慮了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的情節。
兩個案件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判決結果的不同,特別是量刑的不同。兩個相似的案件,在法律規定的刑罰幅度之內,“宋麗案”做出了刑事處罰的決定,“鄧玉嬌案”做出了免于刑事處罰的決定。筆者認為,在“宋麗案”中,被害人江某的過錯要更為嚴重一些。其預謀實施強奸的行為對被告人宋麗造成的人身危險更加緊迫。但是,量刑時從輕的幅度卻小于“鄧玉嬌案”。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被害人過錯作為酌定情節,法官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同地區的法官量刑時標準不統一,造成量刑幅度的不一致。
四、被害人過錯在量刑中缺乏程序保障
法官隨意量刑,忽視被害人過錯情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缺少對量刑的程序性保障。特別是偵查環節,被害人過錯證據似乎都處于被遺忘和忽視的角落。
筆者調查的49例提出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傷害案件中,除去26例法官在量刑時考慮了被害人過錯從輕處罰、2例認為被害人未達到過錯程度不予采納、13例不考慮被害人過錯外,8例案件法官都不予采納被害人過錯的辯護理由,其理由不約而同地都寫到“被害人過錯缺乏證據,法院不予支持。”這說明在偵查環節,被害人過錯的問題就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偵查機關往往注重有罪證據的收集,對減輕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險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的證據卻被忽略,這使得被害人過錯在以后的量刑程序中沒有證據支持而不能得到法院支持,使司法人員對整個案件的事實缺乏足夠的認識,導致量刑失衡。而在我國目前的偵查構造下,被告人和辯護律師在審判前獲取被害人過錯的證據非常困難,往往在審判前被告人都已經被羈押,處在偵查機關的控制之下,根本無法為自己取證,聘請律師的權利也受到很大限制。立法雖然明確要求偵查機關履行告知義務,但是,實踐中依然是不如實告知,甚至是不告知的現象大量存在。偵查階段律師幫助制度的現有規范在落實上嚴重走樣變形[9]。有調查表明,近80%的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認為應該告知犯罪嫌疑人法定訴訟權利,72.6%的警察和89.6%的律師表示,立法應明確偵查階段應告知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的權利,且85.9%警察、92.3%的檢察官表示辦案中實際告知了犯罪嫌疑人應該享有該項權利,但是,在1159名服刑人員中只有35%表示直接從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那里知道訴訟過程中可以得到律師幫助,18%的服刑人員甚至不知道律師可以幫助他,62.4%的服刑人員表示不知道經濟困難可以免費獲得律師幫助。而即便被告知了聘請律師的權利,會見律師又受到很大限制,不安排會見的情況屢見不鮮[10]。從偵查需要的角度,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初,刑事拘留期間,為了獲得犯罪嫌疑人認罪口供或者核實相關證據,以及獲得相關證據線索,偵查人員會限制律師權利的行使。所以,被告人要獲得被害人過錯的證據舉步維艱,第一,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要獲得律師的幫助尚不樂觀;第二,犯罪嫌疑人會見律師也困難重重。可以說,偵查機關不重視被害人過錯證據的調查,被告人自身調查被害人過錯的證據是不太現實和可能的,要求其律師去調查又不安排會見,總之,偵查環節獲得被害人過錯的證據十分有限。
[1]任志中,汪 敏.被害人過錯與死刑適用[J].法律適用,2009(1):46-50.
[2]白建軍.罪行均衡實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4-75.
[3]初紅漫.論構建以被害人過錯為基礎的刑事抗辯原則[J].法學論壇,2010(5):154-160.
[4]張正新.中國死緩制度的理論與實踐[J].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159-216.
[5]畢長海.論被害人過錯對量刑的影響[D].吉林:吉林大學法學院,2005.
[6]白建軍.罪行均衡實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70.
[7]曹利民,鄭馨智.對量刑均衡的一些思考[J].法學雜志,2009(11):116-118.
[8]陳興良.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從被害與加害的關系切入[J].當代法學,2004(02):118-126.
[9]陳海平.偵查階段律師幫助:法律梳理與司法實踐考察[J].中南大學學報,2010(1):65-72.
[10]黃 立.訴訟權利告知實證研究[J].法學雜志,2007(5):95-98.
Observation of Victims’Fault in Sentencing Practice
Chen Haiping,Zhang Ze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Hebei 066004,China)
As a circumstance of sentencing,victims’fault is applied more and more in judicial practice.Analyzing it in terms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can both make it an important reason in sentencing defense,and become a key circumstance of sentencing in some cases.However,the legislation does not make special provisions for victims,which has always been applied as a discretionary circumstance,therefore,endowing judges greater discretion right lead to unbalanced application of victims’fault in sentencing practice,in addition,the use of victims’fault in the actual process lacks the appropriate procedural safeguards,so the interest of the defendant can not be maintained well.
victims’fault;sentencing;discretion
D920.5
A
1672-7991(2011)02-0027-05
2011-05-10;
2011-06-02
陳海平(1979-),男,甘肅省渭源縣人,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刑事訴訟法和司法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