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在暗影里
文/王天寧
一
海捧著一盆灰頭土臉的含羞草,怯生生地躲在母親身后。母親溫暖修長的手掌探到身后,緊緊攥住海的手腕。
他從母親有些胖有些軟的腰間朝前瞧去,面前立著一個干瘦的老太太。老太太低下頭,不言語,用藍(lán)底兒白點的圍裙擦手,忽而抬起頭,耷拉的眼皮底下放出精明的光。
“好吧,你們忙,把他留在這兒就成。”老太太對母親說,目光低下來,落到躲在母親身后的海的臉上。母親明白過來什么似的,身子一頓,把他從身后拉到跟前,力氣太大,含羞草整株搖晃得厲害,如尖尖細(xì)指般的小葉子,呼啦一下全合上了。
“小海,小海,來叫奶奶。”母親在海耳邊說。海嘴里嘟囔了一下,算給老太太打招呼。“你這孩子!”母親在他屁股蛋子上狠狠擰了一把,海“嗷”的一聲慘叫,疼得身子猛顫,雙手忙下力使勁摟住含羞草,怕它掉在地上,把花盆摔碎了。
“算了算了,孩子怕生,以后就好了。”老太太的聲調(diào)軟軟的,含著與她年齡不相稱的——甜蜜。海想。她的手摸過海的頭,放在他臉上,替他揩去淚水。干枯蒼老的手,像是用一張砂紙摩擦臉頰,不好受。
她瞧著海的眼,她眼底精明的光并未就此暗淡下來。這是……這是我的奶奶。男孩心想,低下頭,好像忘記了什么。含羞草的葉子慢慢展開,海一吹氣,它一搖三晃地又合上了。
“我要……我以后要跟你住嗎?”海問。眼睛盯著含羞草,誰也不瞧。他猜她倆是明白的。“嗯,跟我住。”老太太開口。起了風(fēng),房檐下的燕子出出進(jìn)進(jìn),院子用板磚鋪成,黃乎乎的紅色,間或夾雜成片的土壤,用來種長勢不怎么喜人的蔬菜。海仔仔細(xì)細(xì)打量著,有些泄氣。不出所料,這里果然什么想要的都沒有。
“可是……”海想說些叫母親泄氣的話,簡而言之就是他不想在這兒住。可這倆字剛一蹦出口,母親的眼睛就鼓起來了:“這不是你能決定的,小海。因為,因為你的病……”
“我沒有病!”海高聲打斷母親,“你們干嗎不相信!說一萬遍也是這樣,我沒有病!”
這當(dāng)兒,它不知從哪兒鉆出來了。海發(fā)現(xiàn)原來自己并沒有忘記它,或者說,就算海忘記了,甭管他走去哪兒,只要想它,它就會出現(xiàn)。它粗壯的身子搖來擺去,小爪子用力抓緊地面,發(fā)出噠噠的聲音,滿身白毛像被順過,服服帖帖地貼在兩側(cè)。它緊貼著海的腿繞來繞去,仰起胖胖的臉,盯著他手里的含羞草。海知道它想吃。
男孩對它搖手指:“小歐,乖,小狗是吃肉的,不可以吃草。”而后海指著它對母親和老太太說:“你們看,它就在這兒呢,你們看啊,我沒有病。我哪兒有病啊?誰說我有病誰才有病呢。”
兩個人的目光探過來。母親睜圓眼睛,無奈地頓住,轉(zhuǎn)身瞧老太太。老人皺起眉頭,海對上她的眼神,那眼底精明的光一道一道射出來,簡直要把海的臉照亮了。涼的,他想,合上眼似乎能在空氣中抓來一把雪。
它格外聽話,沒撒嬌也沒吵,縮著脖子在海腳邊繞了兩圈,就搖晃著胖胖的身子離開了。它鉆進(jìn)有些打蔫的菜叢中,轉(zhuǎn)瞬沒了蹤影。
母親住了嘴,格外憐惜地瞧著海。她慢悠悠地把他往老太太身邊擁,老太太就勢奪來海手里的花盆:“在這兒住吧,小海,奶奶會侍弄花,幫你把含羞草養(yǎng)大啊。”
海的心被一些黏稠的悲涼之感填滿,晃晃悠悠地仿若要溢出來了。海知道她們不相信他,無論怎么解釋都不相信。海有一只小狗,不知它從哪兒來,不知什么時候來到他身邊的。海叫它小歐。海走到哪兒它就會跟到哪兒,只要海想它,它就會出現(xiàn)。
可每個人都說,小歐是海想出來的,它是假的,不存在。
海不信,他偏不信。它明明在這兒,它搖晃尾巴要吃海手里的含羞草,海不給,它就聽話地離開了。
鼻子很酸,委屈和悲涼越積越滿,最終溢出來了。是淚,一道道從眼瞼中鉆出來,勢頭比挨打時還洶涌。他在淚眼中什么都瞧不清,迷迷糊糊不知抓住誰的手,嘴里頭嗚咽,像小獸。那段時間仿若很長,海掰著手指頭怎么也數(shù)不清。母親的鞋跟敲擊路面的聲音在身旁穿梭,越來越急促。海支棱起耳朵,那聲音居然越來越小。他心里一涼,忙擦凈眼淚,那個有些胖有些矮的身影就這么在他跟前消失了。干瘦的老太太立在近旁,表情悲愴,海的含羞草上掛滿水珠,被壓得直不起身,小葉子齊刷刷閉得死死的——原來她也哭了。
海頭一次知道,老人家的淚水竟然這樣重。
海說:“你們要我住在這兒就住在這兒吧,反正你們大人什么都是對的,無論你們說什么做什么都是為我好。”
老太太努力睜開哭得紅紅的眼睛,一根根血絲清晰地橫亙在眼球里。她盯著海,精明的光一點點會聚起來。她的眼對著他的眼,仿佛要看穿海的內(nèi)心。
海被瞧得心虛,忙把頭低下去。抬起頭時,老太太身邊多了一個黑瘦的老頭。他張開長長的手臂,一把把海抱在懷里。“哎喲,乖孫子,多少年沒見了,可想死我了。”他用仙人球刺一般的胡子扎海的臉,海感覺臉頰仿佛要被挑開一個個往外冒血的洞。
無疑,這老頭是海的爺爺。
“兒媳婦呢?”他問,這一次是對老太太說。
“走啦,又不是回娘家,人家憑啥在你家待好久啊。兒媳婦工作調(diào)整,今年特別忙。還有,你看這孩子,這病,這不是還得找醫(yī)生治嘛。她給我說她要去找小海的……”她帶著鼻音回答,大概是看到了海的表情,她把話說了一半就忙掐斷了。
老頭不言語,搖了搖海的身子:“想養(yǎng)狗不?”
“我有狗啊,”海說,“它叫小歐。”
“那……爺爺準(zhǔn)許你再養(yǎng)一只。你看,這是爺爺家,爺爺家有院子,不和你一樣住樓房。以后啊,這也是你的家。養(yǎng)一只小狗,你看著它長大,它能陪你玩,多好。”未等海應(yīng)答,他站在院子當(dāng)間兒,扯開嗓子沖隔壁喊:“小瀚,小瀚,來來來,把你家豆子抱過來。”
那邊應(yīng)了一聲,接著平房間隔的長巷里傳來磕磕絆絆的跑步聲。一會兒一個小男孩抱著稍顯大的狗站在海面前,他有些怕生,不言語。狗被卡住脖子抱著,長長的身子懸空晃悠,平平的臉被擠得更扁。
被稱作“小瀚”的男孩在老太太的示意下把小狗擱在地上。他抬起頭,羞澀的表情減去了大半。圓圓的臉,皮膚黝黑,眼睛不大。海打量他,他也不避諱,蹲下身順小狗的毛。老人站在近旁,勸他們要“交流交流”。
他看著海笑:“小瀚。”他告訴海他的名字。
老太太忽然一拍腦門,嘴里念叨:“哎喲,該做飯了,孫子來了得做點兒好的。”走了幾步回身沖盯著他們的老頭喊,“你傻啦你,叫孩子們玩,你過來幫我燒火。”老頭應(yīng)著,忙不迭地跑過去。四周趨于安靜,午時的陽光順著樹梢落下來,帶著春末暖得嗆鼻的香氣。即使站在樹底下,也能感覺到燥熱。
“真熱啊。”海摸摸微出汗的額頭。
“夏天快到了。”小瀚點點頭,指著趴在地上的狗說,“豆子是小女狗,你爺爺說等它降了小狗,留一只給你呢。”豆子吐出粉紅色的舌頭,瞇著眼睛瞧了海一眼,又懶洋洋地合上了。
海忽然聽見響動,菜叢中發(fā)出窸窸窣窣的聲音。它扁平的臉從里面探出來,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瞧著海,海猜它吃醋了。“小瀚,其實我有一只小狗。”海用手指著菜叢給他看,“你看,白色的小狗,叫小歐。”
男孩皺緊淡淡的眉,圓乎乎的臉縮成一團(tuán),許久才慢慢舒展開。“嗯,我看到了,很漂亮。”他這樣回答海,聲音像凝在弦上,一搖三晃的。
二
“刺啦——”
長長的一聲,像某根筋某根血管在心底繃斷了,讓人身體猛然一顫。海和老頭老太太方散步回來,眼前的小巷空空,黃昏里宛若罩了霧氣,一層一層被最后的陽光攏著。這聲音就穿透又薄又輕的霧氣沖進(jìn)他們的耳膜里。它不停變換調(diào)式,讓人的心被提起來,提得又高又陡。
老頭牽著海的手,他偷偷掙過兩次,想甩開,可老人抓得又牢又緊。回身看,偌大的夕陽掛在天邊,光芒漸漸隱去,夜晚快來了。老太太邁著小步跟在后面,斜眼瞧著咧嘴笑的老頭,眉頭攢得很緊。
“刺啦——”
又是一聲,這一聲更長更幽怨,明顯是從小瀚家傳來的,嚇得海一個激靈立在原地。“這什么動靜啊?”他問,盯著小瀚家的門縫看。
聲音再次響起的時候,連豆子都聽不慣,隨著嚷嚷起來。老頭緊兩步跑到小瀚家門口,海剛聽老太太急迫地說了一個“別”字,老頭已經(jīng)扒著門縫往里頭喊:“有孩子的趕緊抱好了,小提琴大師小瀚要開始演奏啦。”
這一聲過后,小巷便歸于沉默,徹徹底底的,沉默。海用腳劃拉著長滿青苔、綠得冒油的磚塊,清清楚楚聽到老太太嘟囔:“死老頭子,竟瞎找事。”海這才知道那動靜是小瀚拉琴發(fā)出的。只是它未再響起,仿佛在和巷子較勁兒,比誰的沉默更長久一些。
綠色的鐵門“咣”的一聲被扯開,一個燙著大波浪的女人頭探出來。海看著她,綠衣黑褲,像極了老頭子種得那些打蔫的菜。“大爺,”她沖老頭說,“您老人家怎么說也是長輩,對小孩子發(fā)展愛好、培養(yǎng)藝術(shù)細(xì)胞該挺支持的。這小瀚年紀(jì)小啊,手臂又不夠長,拉著難免吃力,老師都說他樂感好了,您就算不喜歡,怎么著也別說風(fēng)涼話不是?”
老頭不言語,瞇起眼睛朝院子里瞧,表情訕訕的。老太太忙揮手打圓場:“唉唉,閨女,說著玩的、說著玩的,你大爺愛開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瀚啊,拉得挺好,你叫我們小海,肯定拉不出來。”她把海往前推。海離女人那么近,能看到她臉上一個一個粗大的毛孔和黑褐色的斑。她可能抽煙,牙齒黃黃的,沾了其他顏色的牙垢。離那么近,女人身上濃烈的香水味兒不停往他鼻孔里頭鉆。
“這是您孫子吧,”她看著海,表情平靜,眼睛毫無神色,“挺好的。”她簡潔地說了兩句,卻不知指向海的哪里。女人向老人點了下頭,縮回門后。仿佛頓了那么一會兒,連空氣都凝固了,藏在草叢中的昆蟲的鳴叫在夜色里清晰起來。琴聲忽然在意料之中響起,“刺啦刺啦”的,較之前并沒有任何改觀。
“那是小瀚的媽媽。”老頭點點門縫告訴海。“得了吧你,”老太太忽然說,“挺大歲數(shù)的人了,沒事找什么事啊你。”老頭不吭氣,走到海身旁抓住他的手,托起來翻來覆去地看:“我們小海要是練琴,絕對比小瀚強,對不?”
“嗯。”海應(yīng)著,老頭便笑,露出粉紅色的牙花和鑲金補銀的牙齒。老太太也笑,嘴角斂著,眼睛直視前方,仿佛真看到她手腳一點兒不麻利的孫子成了知名小提琴大師。一格一格石板路在腳下飛速后退,積滿水的路面反射光,能在里面照見自己的影兒。
琴聲是在這時候停止的。海和兩個老人仿佛約定好一般,站住腳等,只有那仿佛鋸東西一樣的琴音按時響起,他們才能安心回家。
巷子竟然一直安靜著。相反,小瀚家的談話聲忽然越來越大,像是爭吵。砸摔東西的聲音,在巷子里清清楚楚地回蕩。豆子跟著叫起來。潮綠色的鐵門“咣”的一聲被拽開,小瀚和他媽前腳后腳往外沖,女人高舉雞毛撣子,邊跑邊用力揮,狠狠地抽在小瀚圓滾滾的屁股上,他的慘叫伴隨豆子哼哼唧唧的叫聲,一直沒停過。小狗緊緊跟在兩個人的后面。
“別打別打,教育孩子哪兒有打的?”老太太揮舞著手臂,扯著脖子沖兩人喊。
“我叫你不聽話,給你買個琴花多少錢啊,你以為你娘的錢那么好賺啊,你憑什么不學(xué)?沒出息的東西!”女人吼道,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露出來。
“我……我學(xué)不會,都說我拉得不好聽,連爺爺都……媽你別打了,哎喲!”小瀚圓滾滾的臉邊跑邊顫,眼淚一顆一顆往下掉。
女人俯下身去,雙手撐著膝蓋,喘粗氣,眼角使勁盯著老頭。小瀚嘴里頭嗚咽,頓了兩下,許是碰到臀部的痛處,又嗚嗚地哭起來。
聽傻了的老頭張著嘴,半天擠出不成句的幾個字:“我……我沒,孩子,你……”海趁這空隙,把手偷偷抽出來,熱乎乎的,全是汗。老太太掐著腰:“你該啊你,我說什么來著。”老頭百口莫辯,用手拼命撓頭發(fā)。海忽然意識到,這老頭是他的親人啊,他是自己的爺爺。他覺得,必須說點兒什么。
“其實小瀚老早就不愿學(xué)琴了,就算爺爺不說,他也會告訴你他不喜歡這玩意兒的。這事兒,不該算到爺爺頭上。”海說。這話一針見血。所有人一齊盯著小瀚,尤其是女人,目不轉(zhuǎn)睛的,要把小胖子看進(jìn)眼里頭。
“是嗎?”她不相信一般又問。
小瀚不言語,連眼珠子都不轉(zhuǎn)。過了一會兒才慢慢點頭,很輕很緩,卻瞬間打破了平衡。
“走,跟我回家,不爭氣的東西。”女人罵道,涂滿紅色指甲油的手抓住小瀚的衣領(lǐng)就往回拖。男孩似是極不舍地瞧了他們一眼,眼睛與海對視的那刻,海看到里面干干凈凈的光,不摻一點兒雜色。
海忽然咬牙切齒地恨起那個女人來。
“走吧。”回過神來的爺爺又牽住海的手,這次任海怎么掙也脫不開了。
回身望去,老太太小步跟在后面,神情帶著消不去的埋怨。豆子的白尾巴一閃,鉆進(jìn)大門里。可是,小歐這家伙怎么跟在豆子后面?海想,它從哪兒冒出來的?它們,認(rèn)識嗎?難不成它們第一次見面,就已經(jīng)把對方當(dāng)朋友了?
就像,他和小瀚一樣?
三
在這兒住得時間一久,海開始想家。
其實那個家并沒有什么好的,好多年,一直少了些什么。海想起母親的一句話:“少了一個像樣的男人。”
父親多年前離開了他們,如今他對海來說就是一個名字,還有,他多年前拍的相片深深印在海的腦海里。現(xiàn)在,他是胖了還是瘦了?他什么時候回來?他還要自己和母親嗎?還有,他離開前的承諾還能兌現(xiàn)嗎?
罷罷罷,不去想他了。海告訴自己,拼命強迫自己不去想那張臉。
夏天利落干脆地到來了。世界仿佛只剩下不斷蒸發(fā)的汗水、緋紅的臉頰和永遠(yuǎn)過不完的白天。含羞草的葉子無精打采地往下垂,收攏的速度仿佛變慢很多。腳邊的一攤水,不消幾分鐘就不見蹤影,消失得這樣迅速徹底,連做蒸汽都做不痛快。
海躲到屋檐底下,屁股下塞著凳子。凳子的一條腿短,不穩(wěn),搖搖晃晃間,身上又密密匝匝出了一層汗。困。他用手托著腮,幾欲睡過去,眼縫間塞進(jìn)來的光影重重疊疊。
打哈欠的空當(dāng),海聽見一聲脆響,接著頭頂又麻又痛。他用手緊緊捂住吃痛的地兒,努力睜開眼睛,老頭正坐在面前,把書本緊緊卷起來,高舉過頭,要再給海來一下。
男孩猛地一震,徹底清醒了。
“打起精神來,你這是在學(xué)習(xí)呢。學(xué)習(xí)地理知識,以后都用得著,你要是出國啊什么的,迷不了路,明白不?”老頭沖海說。
海看到書脊上的“初中一年級使用”,心里一陣陣發(fā)涼。無論再怎么掰著手指算,他也沒完成小學(xué)六年的課程,學(xué)這玩意兒,究竟有什么用啊。他于是又把眼合上了,托腮的手把臉上的肉擠到一起,整張臉都變了形:“我就在這兒,我哪兒也不去。我跟這兒過了這么多年,怎么還能不認(rèn)識路啊。”
“那你去咱這兒的學(xué)校上學(xué)吧,跟在你家一樣,啥都不耽誤,”老頭把臉沉下來,“你和小瀚一樣大,正好去和他一個班。你不是不想跟我學(xué)嗎,大熱天教你學(xué)習(xí),提早把初中的學(xué)了,以后你也省力一些,不是嗎?”
海坐直身子:“那我學(xué)成以后出國,像我爸爸一樣不回來了,你不會想我嗎?”
老人立馬泄了氣。他盯著世界地圖上的某一點好久,眼睛似乎沒了聚光點。那一聲悠長的嘆息持續(xù)了很長時間,不知從胸腔的哪個位置傾瀉出來,把光滑的地圖吹得全是皺褶。整個人的元氣似乎隨那一聲嘆氣漏出,眼瞧著開始變得蒼老。
海這才知道自己說了一句錯話。
海想起幾天前母親那一通電話。
他拿起話筒,母親的聲音斷斷續(xù)續(xù),像從很遠(yuǎn)的地方傳來。他很興奮,興奮地想喊,激動和歡呼卡在喉嚨間,混成“嘰里咕嚕”的雜音。那聲音,像……像小瀚拉的琴。他在心里頭想,右手把話筒越握越緊。
“還能看到那只狗嗎,小海?”母親開口卻是這句話。
海的心猛然一沉:“能、能、能看到。”——竟然開始變得結(jié)巴。
那邊一聲嘆氣,許久沒有動靜。海的心懸在半空,卻一刻不停地往下降,似乎永遠(yuǎn)觸不到底兒。母親終于又說話了:“你的病有著落了。我想過一段時間帶你去上海看看,你的病……”
海想也沒想就把電話掛斷了。
電話一直響,仿佛海不接就永遠(yuǎn)不停下來,偏偏聲兒又大,那一把金屬碰撞的聲音像在胸腔里頭響起一樣,叫人不安寧。
“誰的電話,怎么不接啊?”老太太從外屋走進(jìn)來,指著顫動得幾欲跳起來的電話筒問。
“我沒病,奶奶,我沒病!”海猛然抬起頭來,直視老太太的眼。那精明的、即使不犯錯誤也會叫人心虛的眼光,他毫不躲閃地一概承接著。老太太近視,瞇起眼睛往海的眼底瞧。那里面似乎閃著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讓人感覺男孩和從前不一樣。這算勇敢、執(zhí)著還是什么,老太太也道不清楚。她依稀記得自己的兒子,也就是海的爸爸,背著一個帆布的藍(lán)色大登山包離開家門時,眼里也有這樣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他曾面對眼睛發(fā)亮、不諳世事的海說:“我走了,小海,等爸爸給你帶一只最好看最好玩的小狗回來。”他應(yīng)允著回來。全家老老少少堅定地相信,只要他擁有了自己的事業(yè)一定會立馬回來。一開始和他還有電話、書信來往,后來聯(lián)系變少,再后來聯(lián)系徹底斷了。逢年過節(jié)往家中打電話的人很多,可就是聽不見他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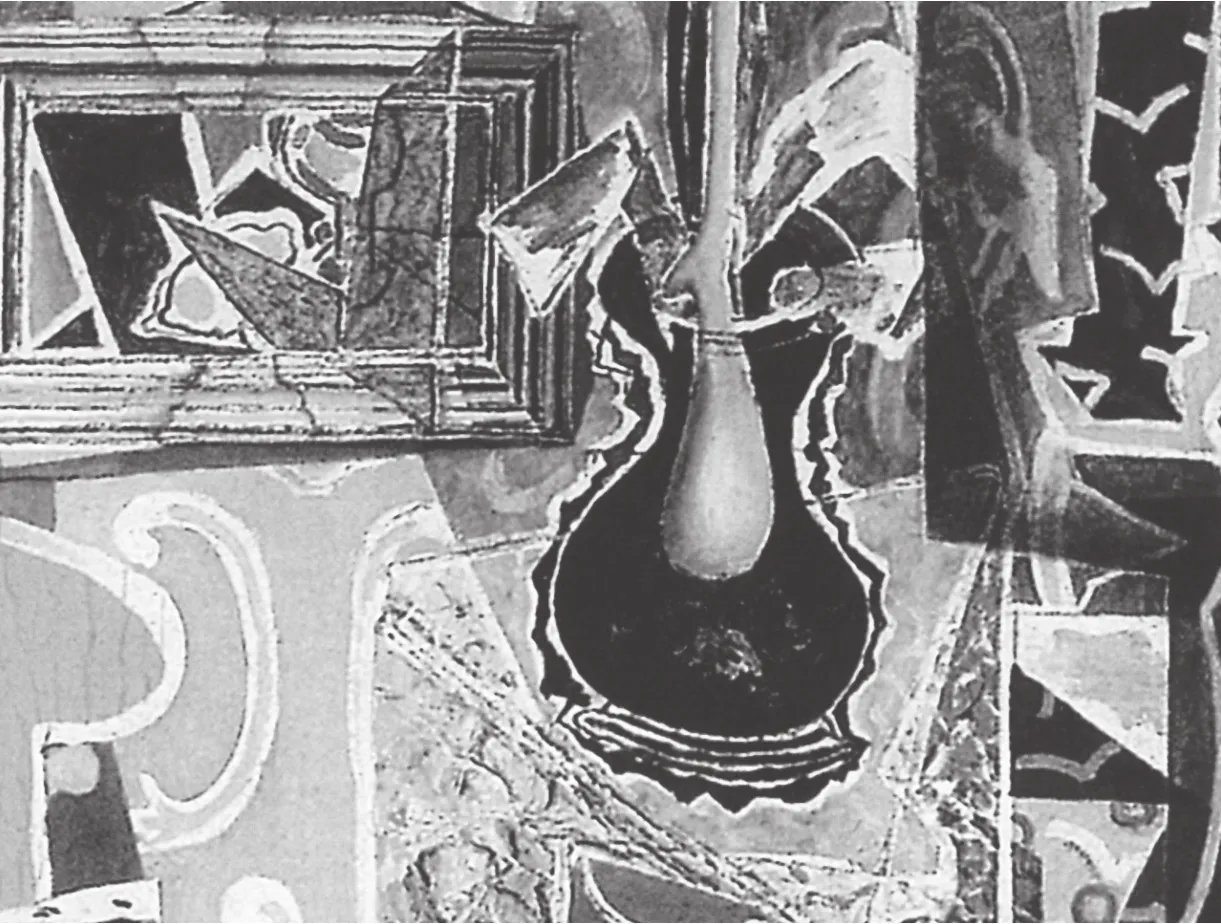
■美術(shù)作品:勃拉克
只有一次,老太太記得清楚,可僅僅是那么一次,老太太接到一個電話。那是大年初一,她朝話筒里“喂喂”了兩聲,那邊卻一直沒回應(yīng),老太太只能聽見“嗚嗚”的風(fēng)聲。等了一會兒,那邊竟把電話掛了。老人這才反應(yīng)過來是他,懊惱自己沒多說兩句,沒抓緊時間問問他過得好不好。偏著頭想了一會兒,方分辨出那風(fēng)聲是兒子的呼吸。
原來一個人從肺深處呼出的氣息竟然可以這么大。
外面的傳言很雜,有人說他在美國,有人說他在上海。老太太猜他過得不好,不然他干嗎不和家里聯(lián)系?不然他為什么不回家呢?想到這兒,老太太禁不住打哆嗦。她害怕了,她不得不承認(rèn),她害怕了。她已經(jīng)夠老了,已經(jīng)受不住離散和失去了。她彎下身把海摟在懷里,拍拍委屈的海的背:“奶奶信你,你沒病。”
“小海不想學(xué)地理?那我們寫詩好不好?”老頭說著,把書本合上,放在腳邊。
“你會寫詩?”海挑起眉毛,他想起語文課本上的那些什么“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什么“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但憑他怎樣努力,也無法把那些奇形怪狀的句子和眼前黑瘦的老頭聯(lián)系在一起。
“會寫一點兒吧,我年輕時候教過語文呢。”老頭揚起臉兒顧自說,“聽沒聽說過一首叫《生活》的詩啊,全詩就一個字:網(wǎng)。精辟吧?太精辟了。我當(dāng)時一讀就被震住了。雖說這思想你可能理解不了,”他看了看海的臉,“但是我們可以借鑒那寫法。你看,寫‘天空’就是‘無盡’,寫‘爸爸媽媽’呢,就是‘回家’。你看就這樣,多好。”他說完,露出金銀參差的牙齒,笑。
“得了吧你,別耽誤孩子了。”老太太抓著一把菜走過來,塞進(jìn)老頭手里,“洗洗,把菜擇了,時候不早該做飯了。”
老頭應(yīng)著,隨老太太離開了。臨了老太太忽然把臉轉(zhuǎn)向海:“你爺爺年輕的時候是教人寫字兒的,他教的字兒,人家都識。其實就一書法老師,他連讀都讀不好,還教你寫詩呢。”
“還有,你媽叫我告訴你一聲,你要不想去上海就待在這兒養(yǎng)病。你該明白她為什么把你送來這兒——醫(yī)生說清靜的環(huán)境對你有好處。噢,還有,”老太太頓了頓,“你好了她就帶你回家。”
海的手指環(huán)著小歐的耳朵繞了兩圈,在他腳邊趴了整整一上午的小狗睜開眼睛,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粉紅的舌頭吐出來,“哈嗤哈嗤”地喘氣。男孩清楚瞧見它小小的嗓子眼,一顫一顫的,像活的洞。
“聽到爺爺說的沒有?寫‘爸爸媽媽’就是‘回家’。我現(xiàn)在,想回家了。”
“小歐,你以后能不能,別來找我了……”
四
“這是臆想癥。”醫(yī)生用口罩嚴(yán)嚴(yán)實實捂住臉,只露出眼睛。圓圓的眼睛,往外凸,再搭配一張一合的櫻桃小口,就是魚。海想到此要笑,只得拼命忍住,可仍有些許氣兒從嘴角的縫隙間嗤嗤漏出。
醫(yī)生坐在海面前,卻不朝他看,眼睛直直地朝向男孩身后——海的母親在那兒。或者說,搖錢樹在那兒。他盯著女人的臉,觀察她的表情,因為注意力太過集中,壓根兒沒聽到海笑,嗤嗤的漏氣聲,他以為是在初春早早蘇醒過來的蒼蠅在哼。他往四周揮了揮手,把手反過來,大拇指戳著自己的胸口:“病因在這兒。”
女人攢起眉頭,似乎動了急,五指用力,把肩膀上的女士坤包越捏越緊。“那……怎么辦?我的意思是,怎么治療?”
醫(yī)生忙不迭地用筆在藥單上刷刷寫下幾字,遞給女人:“找個清靜的地方住一段時間,主要是心理治療。另外,配以藥物輔助治療。這是藥單,沒問題的話,去樓下開藥吧。”
母親接過單子,不知是藥名太晦澀,還是大夫的字太草,她橫看豎看愣是沒看懂這藥究竟叫什么。她倒是看懂價格了,羅列在漢字后面一連串的零,叫人頭暈?zāi)垦!!皼]問題。”她把藥單疊起來,緊緊攥在手里,“我這就去開。”眼里頭一閃一閃的,叫醫(yī)生看得愣神。
海看到它從白色的病床下鉆出來了,逗弄躺在地上的線頭,跳起時身上“噗噗”地往下掉灰,不知它剛從哪兒爬過。
“小歐,小歐,到這兒來!”海喚著,朝小狗張開手臂。
母親的手里出了汗,望著兒子,眼睛瞪得溜圓。
“這孩子,病得不輕啊。”醫(yī)生凝神,喃喃自語道。
“你有臆想癥。”小瀚媽媽搖晃著滿頭打卷兒的紅頭發(fā),用篤定的語氣對海說。海覺得這話有些熟悉,兩三年前便有人這樣對自己和母親說過。他們?yōu)檫@句話花去一大筆錢買了一堆毫無效果的藥,害得海幾個星期渾然不知肉味。他閉上眼睛拼命回憶,只想起一雙外凸的眼睛,掛在稍顯大的口罩上面。現(xiàn)在這話和從前一樣,連語氣都與那時的無異。
“這得治,我告訴你,你回去給你奶奶說,叫你在我這兒治吧。”女人把海送來的清蒸草魚連同里面的湯湯水水一齊倒進(jìn)自家碗里,把碟子遞還給海,“小海,姨開診所這么多年了,真的,什么奇病怪病都治過,叫你奶奶考慮考慮吧,我可是為你好,半點兒私心也沒有啊。”說完偏頭瞧著停下手里的琴給海做“不是我說的”表情的小瀚,皺起眉喊:“拉你的琴啊,別干什么都不專心,跟你那死爹似的。掙錢供你學(xué)這玩意兒容易啊?”
小瀚忙把視線擱在琴譜上,拖腔拿調(diào)的“刺啦——”聲立馬響起來。
“不是小瀚說的,是我那次看到的,就是你對著墻角叫‘小歐’的那次。”女人笑,滿臉褶子堆在一起。
這會兒,海掀開診所印著紅十字的門簾,準(zhǔn)備離開。先前他聽過老太太談小瀚的父親,說是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而今聽到女人談自己的丈夫用那樣不屑、鄙夷的語氣,他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悲哀。他催促自己趕緊離開,這里的一切,白色的病床,人體脈絡(luò)圖、光屁股的身上標(biāo)著穴位的塑料小人,這一切都因為女人的存在,叫他感到難以言表的、頭昏目眩的惡心。
他想,要不是老太太非要他來給小瀚送草魚,他才不理會這女人。他回去就告訴老太太,以后別差遣他干這營生了,他受夠女人的尖酸和門診里的西藥味兒中摻的劣質(zhì)香水味兒,他聞了就想吐。可那味道偏偏不受控制地往他鼻孔里頭鉆,擋也擋不住。
海把腳邁出去時,手臂又被女人抓住了,他回過頭去,看到女人在角落的冰柜里翻了半天,掏出一根涼嗖嗖的冰棍放進(jìn)他手里。“拿著,”她說,“在我這兒瞧一次病送一根冰棍,叫你提前享受一下。跟你奶奶說,謝謝她的魚,下次她來瞧病我給她優(yōu)惠。”
海不答理女人,往里屋瞧,小瀚正抬起頭向他看,陽光不知從哪里照進(jìn)來,一股腦兒投在他臉上,圓圓的臉,像太陽。
在陽光的照耀下,小歐蜷在小瀚的腳邊。
“小海,小海。”他聽到小瀚叫他的名字,轉(zhuǎn)過身去,小胖子在太陽底下大汗淋漓地朝他跑過來,停住腳,怎么也喘不勻氣兒。
海拍拍他的背,他咳嗽了兩聲,才重又站直身子,在額頭上胡亂摸一把,滿頭滿臉的汗。
“啥事?”海問他。
“那個……我媽說,下星期診所搬到新房去,要你和你爺爺奶奶一塊兒去,會放鞭炮啊什么的,你要能去就好了,我媽還說會做好吃的款待客人呢。”小瀚的眼睛閃閃發(fā)亮。
海猶豫,他想起女人的臉還有滿頭打卷的頭發(fā),心里就一陣陣發(fā)緊。
“你一定要去,小海,因為……那天是我生日。”小瀚搖著海的手,潮乎乎的,把海的手整個包裹起來。海和他對視,又瞧見那些光,那些不摻一點兒雜色的光,從他不大的眼睛深處迸射出來,像是從云層深處濺出來的陽光。這目光讓海的心軟得將融化掉,即使他再不愿見卷發(fā)女人,可小瀚的要求他無論如何拒絕不了。
海偏著頭想了一會兒,嘴里沖小瀚嘟囔:“等我一會兒。”然后,他小心地捧著盤子撒丫子跑進(jìn)自個兒家門,一會兒又風(fēng)風(fēng)火火跑出來,把一把焦糊的爛豆子倒在小瀚的胖手里。“這是含羞草的種子。”海解釋說。幾天前他剛從緊閉的葉間摘下這些種子,“你現(xiàn)在把它們種下去,到你生日那天,約摸能長出芽。”
“狗喜歡這東西。”海指著一直跟在身旁的小歐,說。小瀚的目光順著海的手指看過去,一愣神兒,接著抬起頭,露出排列整齊的牙齒,沖海笑。
五
老太太喜歡梳頭。
隔三差五的清晨,她在太陽剛露臉的時候,坐在一張小馬扎上,從灶臺上扯下一張油脂麻花的報紙,板板正正地鋪在腳邊,埋下頭,用木梳子順著頭皮,梳。
她自來卷兒,即使站得遠(yuǎn),海也能清楚聽到木梳拉扯頭發(fā)的聲音,那些灰的白的、卷得有些過分的毛發(fā)稀稀拉拉往下掉,飄在傾瀉下來的陽光里,發(fā)出難以言狀的光芒。一層一層疊加,是雨后垂在天邊的彩虹才有的光彩。
老太太盯著粘在報紙上的頭發(fā)好久,那些純粹的白色刺得她眼睛睜不開,嘴里喃喃言語,大約是“老了”“不中用了”一類的感慨。她低著頭,看見海的影子映在報紙上。老太太抬起頭,沖海羞怯一笑。這笑容讓海著迷,此時老人再沒有精明得難以接近的氣勢,相反,她周身的一切都透著一股慈祥勁兒,或者說,蒼老勁兒。海覺得老人之所以在那一刻變得平順,全是那一把花色頭發(fā)的功勞。蒼老的老太太叫海打心底喜歡。
老頭不同。他眼見著蒼老,心卻一天比一天年輕。他不和老太太一起侍弄花草——特別是把海的含羞草作為重點保護(hù)對象。他種菜,閑來無事就把庭院里的板磚撬開,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堆土,滿滿堆在里面。而菜的長勢卻始終不喜人,無論怎樣施肥,它們總是耷拉著臉,黃黃的,一副半死不死的樣子。
老太太對老頭把好好的庭院挖得跟搞地雷戰(zhàn)一樣極其不滿,瞪大眼睛訓(xùn)他教育他不是一次兩次了。在海看來,老太太掐著腰站在庭院當(dāng)間兒,一會兒指點坑坑洼洼的路面,一會兒指點低眉順眼的老頭,這時的老太太,是頗具教師或者長者范兒的。
老頭像孩子,是調(diào)皮得讓老師家長無計可施的那種。他嘴里頭應(yīng)承著:“好,我馬上把窟窿填起來。”過后卻能使各種花招叫老太太忘記這事兒,或掏腰包拿來些糖衣炮彈叫海的小嘴活絡(luò)些,多在老太太眼巴前兒說好話。大概是海的那幾句“我喜歡在院里種菜,綠綠的,多青蔥啊”真起了些作用,好久后老太太就不嘮叨了,即便鋪在院子里的板磚日益減少也不再上心。她只關(guān)心她的那些花。她賭氣一般把花草侍弄得愈來愈旺盛,那些花也給足她面子努力開放,一朵朵飽滿得仿佛將要爆開,紅的綠的各種鮮艷得發(fā)膩的顏色似乎要從花骨朵里淌出來。
這邊花團(tuán)錦簇,招惹得蜜蜂蝴蝶從庭院上方飛進(jìn)飛出;那邊是半死不活的蔬菜,進(jìn)入夏季后因為溫度過高,老頭光著膀子天天給它們澆水,肩膀被太陽曬得發(fā)紅,它們?nèi)圆灰姸↑c兒復(fù)蘇的樣子,仍舊打蔫,蔫得更厲害。
老頭還偏愛書法,這應(yīng)該是他除了種菜之外唯一的愛好,而且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明顯比種菜要高。他早些年當(dāng)過書法老師,在小學(xué)校握著孩子們的手,一遍遍臨摹“上、下、天、方”等。而今換他努力握住海拼命掙脫的手,教海寫。海若不寫,老頭就給他講詩,信口謅來,把句子說得顛三倒四,直煩到海丟盔棄甲般投降、不得不提起筆來練書法為止。
海在衣櫥里翻出過老頭老太太年輕時的黑白結(jié)婚照,用墨色相框嚴(yán)嚴(yán)實實地裝起來。兩個年輕人肩并肩站著,細(xì)看能在他們的眉眼中尋到兩個老人現(xiàn)在的神態(tài)。女方手里捧著鮮花,紅的還有粉的,和新人咧開嘴露出的白牙齒交相輝映。海盯著發(fā)黃的老照片看了半天,從光彩異常的邊邊角角中看出兩個字兒來:幸福。
海領(lǐng)悟到真諦后連忙把相框塞到衣櫥的最深處,他猜母親若看見這照片,肯定打心底不舒服。她常說父親的肩太軟,依靠不得;脊椎又太硬,死也不會低頭。海覺得這是母親在抱怨父親瘦呢。
海又想起哪次在附近的路上撞見小瀚,小胖子走路一瘸一拐的,嘴角有瘀青,還有腫起來的痕跡。他拉住小瀚濕乎乎的胖手:“你怎么了,誰打你了?”
小瀚抬起手做了個安靜的手勢,嘴里頭“噓”了一聲,他神神秘秘地從背包里掏出瓶瓶罐罐,塞給海。“快,快給我涂上。我媽看見可了不得,會和他們拼命的。”
“他們是誰?”海邊開罐子邊問,濃烈的酒味鉆進(jìn)鼻孔,是碘酒。
“我們班的幾個毛孩子,壞學(xué)生。”小瀚答,忽然嘴里頭“嘶嘶”倒吸涼氣,海用手指蘸著碘酒戳到他的痛處了。海告訴自己小心再小心,還是有幾滴流進(jìn)小胖子彎彎的嘴角里。小瀚往地上“呸呸”地吐了兩口,嘴里又輕聲叫疼。
“他們?yōu)槭裁创蚰惆。俊焙H滩蛔枴?/p>
“看我沒爸爸唄,沒人護(hù)著我啊。”小瀚滿不在乎。
沉默著走了一段路,小瀚盯著酡紅的夕陽看,兩個小光點出現(xiàn)在他眼睛里。這光點讓海沖動,他突然有股強烈的傾訴欲望。“小瀚……”他欲言又止,瞧著映在小胖子眼睛里的太陽。
“其實啊,我挺羨慕你的,你心里跟明鏡一樣,知道自己爸爸出事故了,不可能再見到他了。可我呢?我壓根兒不知道我爸是死是活,有人說他在上海,有人說他在美國,可他忘了嗎?我在這里啊。他為什么不回家呢?
“他臨走前答應(yīng)回來送我一只小狗的,我不要了。他走后沒幾年小歐就來了,我猜小歐是他派來陪我的,它任性地只讓我看見……
“我常想,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他回家。前些天我半夜起床尿尿,聽見奶奶在臥室里對爺爺說,媽媽找到他了,他就在上海,母親求他給我尋個好醫(yī)生瞧病……
“我犯毛病了,我不想去上海。我想讓他回來,回這里,他是在這兒出生的。即使我去了,他不要我和我媽,我們還得回來。爸爸回這里就不會再走了……”
“別哭。”小瀚輕聲說。
“我沒哭!”海的回答有些斬釘截鐵,他用手背用力擦去眼角的潮濕,嘴里頭“呼呼”地喘粗氣。過了一會兒,他猛然破涕為笑,指著前面的路對小瀚說:“你看,小歐!它又來了。”
小狗扭著身子跟在兩個男孩的身后,海忽然想起什么,若有所思地說:“你有你的豆子,我有我的小歐,這樣,其實挺好的。”
小瀚笑,嘴角牽動的傷口依然痛,不過不比剛才了。他瞇起眼睛望著眼前的路,石板鋪成,筆直而又漫長,上面布滿綠油油的青苔,露出藏在綠色苔蘚下的青泥,有些滑,每一步都必須很小心。
原來回家的路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樣簡單。
六
海告訴老太太小瀚他媽邀請他們參加門診的搬遷儀式時,老人正在縫衣。她用舌頭舔了一下線頭,小心擱進(jìn)針眼里。“這女人!是不是又沒錢了,想著法兒要人隨錢呢。”她頭也不抬地說,但隨即又一愣,意識到對孩子說話不該這么直白。于是她撂下針線,盯著海認(rèn)真地說:“這是大事兒,咱得去。”又沖屋里頭喊:“老頭子,寫副字兒,給小瀚他媽帶著,人家喬遷新居,要過好日子了呢。”
老頭子應(yīng)著,馬上在桌上鋪開筆墨紙硯開始動手寫。他退休后自比陶淵明,不愛官場愛清凈,哪天心血來潮題了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裱起來,端端正正地掛在客廳的正墻上,跟沙發(fā)對著。客人一來,抬眼就能瞧見那幾個字,不想看也得看,不懂欣賞也得看。當(dāng)然客人都給他面子,什么好聽揀什么說。那幾個字,明明版權(quán)都不是老頭子的,卻被夸贊得簡直能與王羲之的《蘭亭序》媲美。
老頭子自此養(yǎng)成一個習(xí)慣,說毛病也可以:逢紅白喜事就給別人題字,甭管別人能不能欣賞,喜不喜歡。在他看來,這手堪比王羲之的字,人家有什么理由不稀罕呢?他寫完后,把毛筆撂在硯上,讓海和老太太過來瞧:大紅色的紙張,幾個字排列得很齊整:“妙手回春”“恭喜發(fā)財”。
老太太攢著眉頭,指著“恭喜發(fā)財”中的“財”字,指頭尖點了兩下桌面:“這不行,你得改。”
“怎么不行?”老頭說著,抓頭發(fā)。海也摸不著頭腦,他覺得這幾個字中,“財”字尤其好,那一撇很長,極有氣勢。
“俗話說:‘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這個字可不能往紙上放。”老太太一本正經(jīng)地解釋。
“噢!”老頭子明白了,忙低下身去,重寫。
海隱約聽懂了。這字和他們的黑白結(jié)婚照一樣,藏龍臥虎地潛著力量,一不留神就會把人刺傷。
一連幾日,雨也沒有止住的意思。
海眼睜睜看著老太太大而茂盛的鮮花和老頭瘦弱的蔬菜被雨水打得彎下身子,它們腳下的泥土被雨水層層剝離,植株的根系清晰地暴露在空氣中。
他一直看不見小歐,目之所及一片狼藉。地上的積水散不去,夜晚時海聽到昆蟲壓抑的鳴叫聲,推開窗,一股發(fā)霉發(fā)臭的味道撲鼻而來。
外界壓力如此沉重,小翰他媽還是堅持把門診里的全部家當(dāng)搬去新房,儀式仍定期舉行。那幾日雖停了雨,天卻總是陰的,顯得很低很沉。沒想到那一天竟然放晴了,光線從云里瀉下來。海從遠(yuǎn)處看到小瀚家門診的煙囪里冒出煙,被風(fēng)吹得散了形體,仿若飄到高高的天上,就能變成云。純白的,不摻任何雜色。
照慣例,要放鞭炮。小瀚媽堅持要海舉著掛鞭炮的竹竿,卻把小瀚胖胖的身體護(hù)在身后。她皺起撲著厚厚粉底的臉,沖海擠眉弄眼地笑:“小海,這開業(yè)第一炮啊,必須由小孩子舉,而且必須是膽大的小孩舉,你看我們家小瀚,還沒豆子的膽兒大呢……”說到半截兒想起什么,住了嘴。
海左顧右盼,沒見豆子出來湊熱鬧,倒見躲在女人身后的小胖子,沖他憨厚地笑。
四鄰越聚越多,海恍然發(fā)現(xiàn)自己一條后路都沒有,心里叫苦,暗暗罵道:這女人可真有招啊。一咬牙一閉眼——舉!
鞭炮點著的時候,周圍人都退得遠(yuǎn)遠(yuǎn)的。人自動圍成一個圈,海站在最中間。海其實頂怕這帶響的東西,動靜又這樣大。竹竿一直在劇烈地發(fā)顫,震得他手麻。他想尖叫,想撂下竹竿撒腿跑,每一個爆竹都仿佛要崩到他身上。他瞇著眼睛看四周,青色的濃煙中只瞧見老太太的眼,精明的目光,攢著眉朝他看。臉上的神色,不知是憐惜還是贊許。
直熬到鞭炮燃盡了,他的耳朵還“嗡嗡”直響,每個爆竹都好像在耳廓里炸開一樣。老頭子和老太太分別給他說了句什么,他沒聽清楚。女人張羅著剪彩,一批鄰居各執(zhí)著從自家拿來的小剪刀,整齊有序的“咔嚓”一聲,那彩帶不知斷成了多少截。直到小瀚跑來沖著他的耳朵說:“你給我的含羞草長出芽來啦。”海才恢復(fù)聽覺。他清清楚楚地聽見這句話。
要把禮錢和禮品送進(jìn)女人手里,才能上桌吃飯。
女人打開老頭子的字瞧了一眼,立馬扔進(jìn)了禮物堆里。她倒把禮錢清清楚楚地數(shù)出來,記上名單,臉笑成一朵雛菊。海注意到老頭子蹙緊眉毛,滿臉不高興——對他這手承了王羲之遺風(fēng)的字如此不在意,這女人還是頭一個。但這畢竟是大喜的日子,他不好說什么。老太太沖他使了半天眼色,老頭終于恢復(fù)了常色,鼓起腮幫往外一吐氣,露出金銀參差的牙齒笑起來。
最終坐上餐桌的人寥寥。女人站起來,聲音嘹亮地開始講話,從“歡迎大家來出席我們門診重新開張的儀式”開頭,到“希望大家經(jīng)常來,我給大家打折”收尾,海一直把笑憋在嘴里,這個女人平時動輒就罵死去的丈夫,罵小瀚沒出息,從未見她如此一本正經(jīng)。直到身旁的年輕人嘟囔一聲“還經(jīng)常來,誰看病看著玩啊”,海的笑終于沒忍住,“噗哧”一聲漏了出來。女人忙著敬酒,沒聽到。老太太不樂意,怕小瀚媽聽到,用手拍他的背。海抬起頭,迎上老頭和小瀚的目光,兩個人也笑。
菜是好菜,出乎海的意料,居然還有肉,是海從沒吃過的肉。小瀚見了肉沒命,一邊往嘴里塞一邊從嗓子眼里嘟囔“好吃”,末了高聲向女人喊:“媽,這什么肉啊,真好吃。”
女人正忙,不耐煩:“狗肉,今兒不是你生日嘛,改善伙食,吃你的吧,哪兒那么多話。”老頭咂巴嘴,灌下一口酒:“是狗肉,剛殺的,很鮮。”
小瀚埋頭吃著,還忘不了豆子,留了幾根骨頭,打著飽嗝兒朝門外喚小狗的名字。豆子始終未蹦跳著跑進(jìn)來。又叫了幾聲,還是沒反應(yīng)。
狗肉?海忽然覺得不安。哪兒來的狗肉呢?
“媽!”小瀚又叫,“豆子呢,豆子呢?”這次聲音里帶了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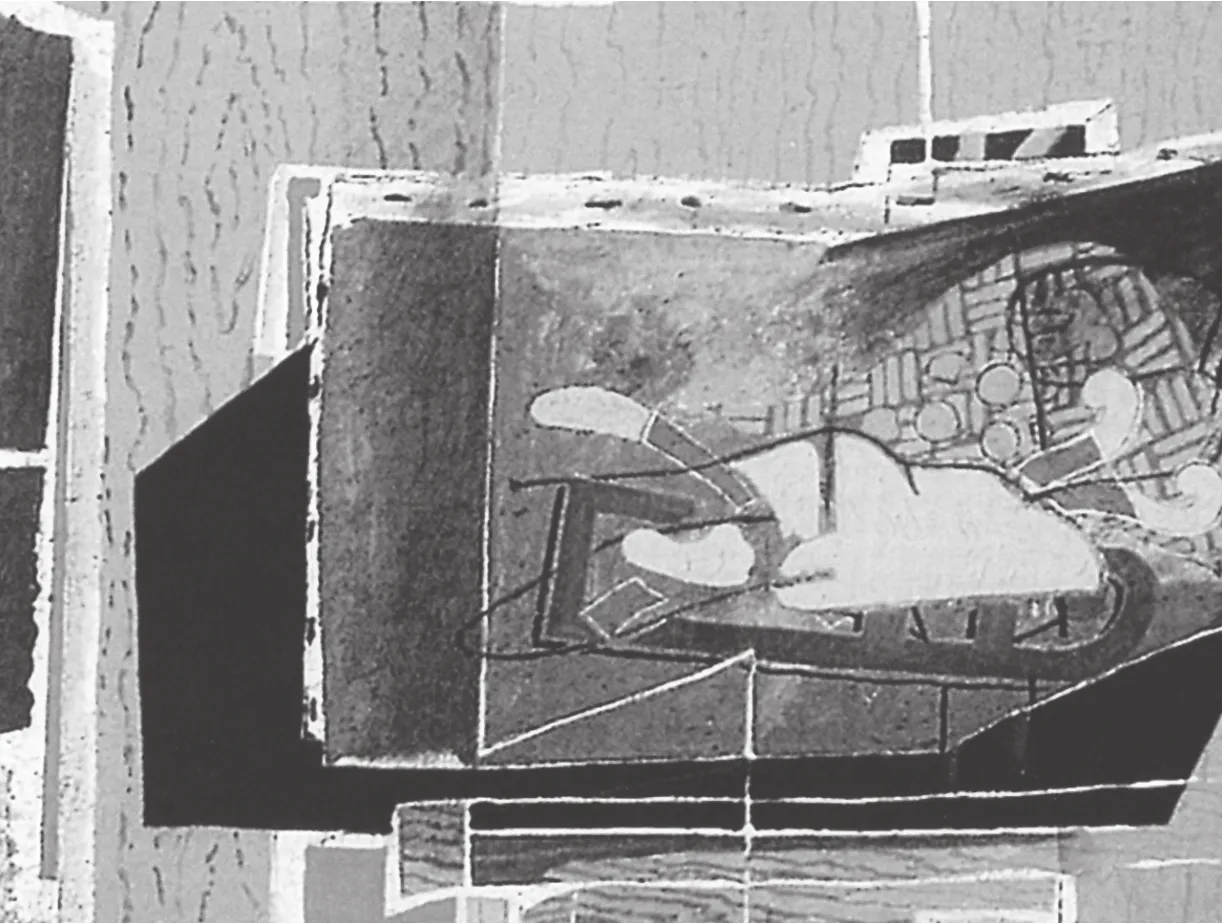
■美術(shù)作品:勃拉克
女人抬抬眼皮:“你不是剛吃了嗎?”她用手指了指桌上的骨頭。
滿座忽然安靜下來。海一愣,盯著小瀚的臉。小胖子的臉忽然變紅,飽漲得鼓起來,眼睛合上,“嗷”的一聲吼叫著哭出來。
人們不再談笑,大喜的日子見了淚,怎么想怎么尷尬。空氣都要凝固了,小瀚的哭聲越發(fā)突兀。小胖子里屋外屋走了個遍,一邊哭一邊叫“豆子”。
女人拉下臉嘟囔道:“哭啥呀哭,天天想著你那狗,還要買狗食,你出錢啊?你以為掙錢這么容易啊,這孩子怎么這么不懂事。”
老太太沖女人擺手:“行了行了,別說了,別說了。”
海跟在哭喊的小瀚身后里里外外轉(zhuǎn)悠,每經(jīng)過桌邊就用眼睛狠狠剜女人擦脂抹粉的臉。他覺得惡心,胃里翻江倒海的。特別是看到女人,這種感受更強烈。他隨小瀚轉(zhuǎn)到院子里,目光瞥到剛發(fā)芽的含羞草和旁邊的一堆東西,他立馬擋在那堆東西前,不要小瀚看見。
可惜已經(jīng)晚了,小胖子俯下身,“哇哇”吐起來。
那是一堆剛被剝下來、帶血的皮毛。
旁邊,嬌小的含羞草許是受了風(fēng)吹,尖尖細(xì)指般的小葉子閉得死死的。
海醒來時覺得頭痛。四周昏昏暗暗的,天畢竟沒放開,似乎又開始下雨了。
他回憶起剛才的事情,狗皮、含羞草,還有小瀚的哭喊和眼淚。
客人已走凈,桌上杯盤狼藉。小瀚媽,還有老頭老太太坐在床邊。“醒了?”老頭問他,低下身看他的臉,“小瀚吐得太多,缺水,給他掛了點滴倒頭就睡。你喊困,在他身邊躺著,也睡著了。”頓了頓,又說,“是受刺激了吧,這種事,小孩子受不了。”
海偏過臉去看小瀚,他醒了,也不再哭。兩眼只是盯著天花板,無神,沒有聚光點。可這讓海格外放松。過了一會兒,小胖子忽然開始唱歌,把每個字咬得清清楚楚,面無表情地唱。女人驚慌失措地摸他額頭。“我沒病,”小瀚停下歌聲,“我只是想唱歌了,你叫我拉了好幾年沒調(diào)的小提琴,不讓我唱歌。媽,我想唱了。我以后也要唱,我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也明白自己該怎么做,你以后別瞎指揮我了,你不配!”他說,“還有,你不許罵我爸爸,我也是他的兒子。”小瀚說完就繼續(xù)唱。女人一愣,想發(fā)作,卻不知該擺出什么表情。她悻悻地起身,去收拾桌上的殘局。
“這就對了,”老太太在女人離開后說,“小瀚長大了。”她笑,眼角的皺紋攢在一塊兒。
女人忽然在廚房里哭起來,嚇得海一愣。“老頭子啊,你怎么這么早就走了呢,你叫我一女人帶著孩子怎么過啊。孩子又不孝,殺他一只狗跟我記仇呢。我怎么辦啊。”她的哭音極其清晰,卻半點兒不影響小瀚繼續(xù)唱下去。
海在心里冷笑:早干嗎去了,你?他從床上穿鞋下地,門診室的一串串珠子穿起來、眼瞧著珠光寶氣的門簾忽然“嘩啦”一聲被撞開,小歐踮著小腳跑進(jìn)來。它用涼鼻子尖拱海的手,海蹲下身,看著它一路踩出的梅花樣的水漬,果然下雨了。
海仔仔細(xì)細(xì)盯著小歐的臉盤看,這小子除了沒眉毛,怎么眼神、嘴巴,哪里都和自己那么像!他想笑,便真的露出牙齒笑,直笑到鼻子發(fā)酸、眼睛發(fā)漲。“還好還好,你一直都陪著我呢。”他不知自己怎么忽然冒出這么一句,不笑了。老頭子老太太轉(zhuǎn)臉來看他。“它來了,”他指著眼前對他們說,“小歐。”
小瀚的歌聲一刻也沒停過。
新房子果然比先前干凈,窗子能毫無阻礙地一眼望到外。
先是幾道閃電撕裂天空,光芒如陽光一樣透亮。而后不知哪兒來的風(fēng),使勁敲打窗子,只一會兒,風(fēng)雨大作。
海想起那首叫《生活》的詩,他忽然明白了,生活啊,果然是一張網(wǎng)。
海起勁兒地往窗外望去,那是一個暗淡的、水淋淋的世界。閉上眼,層層疊疊的光影接踵而來。
滿天滿地都是灰色的雨,萬籟俱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