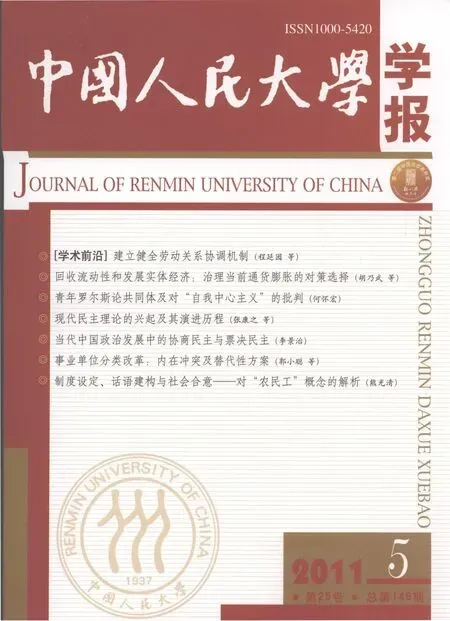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內在沖突及替代性方案*
郭小聰 聶勇浩
事業單位是我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載體,也是公共服務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本質上就是改革公共服務體制,調整國家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公共服務體制變遷是理解事業單位改革的基本視角。對于任何國家的公共服務體制,政府所發揮的作用都取決于對以下兩個基本問題的回答:第一,政府應當提供哪些公共服務?第二,政府應當使用什么方式來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第一個問題涉及的是公共服務應不應當由政府付費,第二個問題則是公共服務應不應當由政府直接生產。值得注意的是,某項服務應當由政府付費,并不意味著這項服務就必須由政府自己生產,政府完全可以借助市場機制從外部購買服務,而后提供給有需要的公民。例如,推行公開招標、委托運營和政府采購等多元化公共服務供給形式,使政府從公共服務的“直接提供者”、“生產者”轉為“合作者”和“發包人”,通過這種角色的轉換保證“服務被提供”。對應上述兩個基本問題,公共服務體制也必須包括兩種基本機制,一是付費機制,二是生產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改革事業單位體制,就是針對政府在這兩個機制中的角色定位設計新的制度方案。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事業單位綜合性改革的基礎,是事業單位其他體制創新的前提。事業單位在人事制度、收入分配、財政管理、養老保險等領域的改革,都必須以分類改革作為前提。然而,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現有方案所運用的公益性標準只能夠解決某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付費的問題。至于事業單位在組織形態上應該轉型為行政類、公益類抑或經營服務類,本質上屬于公共服務生產機制的問題,是無法運用公益性標準來進行回應的。現有方案的這種錯位導致了分類改革的內在沖突,可能引發制度設計上功能失調的風險。基于此,本文立足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借助公共產品理論闡明現有政策方案的內在沖突之處,并且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公共服務生產機制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而試圖為我國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提出一個新的替代性政策方案。
一、理解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公共服務的視角
(一)作為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必須放在公共服務體制轉型的宏觀框架下才能夠理解其本質特征。事業單位產生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屬于我國單位組織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類型。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下,中國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高度合一的“總體性社會”,整個社會的組織體系屬于行政色彩和依附性極強的單位制度。事業單位作為隸屬于政府部門的“子機構”,很大程度上依賴財政撥款來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并且接受主管部門在業務、人事上的指導提供公共服務。作為一種準政府機構,事業單位誕生之初的最主要使命就是協助政府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務。由此,事業單位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行業和領域,承擔著向社會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協助政府管理社會的責任。“國家辦事業、國家養事業、國家管事業”,形象地概括了事業單位在組織與管理體制上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征。
市場化改革以后,事業單位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部門或者說準政府機構,仍然是社會中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結構從原先比較簡單的狀態開始向復雜化的方向發展,治理社會的難度和技術要求越來越高,而不同利益群體日益分化和沖突的訴求也加深了社會的不穩定程度。這些都對政府有效治理社會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由于行政機關自身規模的擴張受到組織法和機構編制管理的嚴格限制,事業單位作為政府的輔助機構,所承擔的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協助政府進行社會治理的功能反而得以強化。各級中國共產黨有關組織機關,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民主黨派機關、人民團體機關利用國家資源舉辦了名目繁多、體系龐雜的各類事業單位。目前,教育、衛生、文化、農林牧水等領域都擁有數量眾多的事業單位,對于我國的公共服務提供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社會轉型對事業單位體制的挑戰
盡管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公共服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事業單位,但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體制色彩的既有事業單位體制和市場經濟的要求并不協調。在政府已經逐步淡出對國有企業的直接管理的情況下,事業單位體制依舊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特征。這至少在管理上帶來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就傳統而言,事業單位是政府的附屬和實現自身職能的載體。因此,事業單位不可避免地成為主管部門的“小金庫”或者人員精簡時的“緩沖地帶”,成為行政機關獲取部門利益的工具。(2)盡管建立事業單位的初衷是提供特定類型的公共服務,但是某些事業單位卻利用其準政府的地位以及與主管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和特殊身份,通過參與市場活動來謀求各種經濟利益。這不僅偏離了提供公共服務的宗旨,而且扭曲了市場機制。(3)隨著事業單位規模日益擴大,活動日益復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起來的政府監管體制很難適應新環境下的監管要求,事業單位監管機制不健全。目前,對事業單位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既沒有明確的前期計劃審核,也缺乏有效的事后業績評估,對事業單位的服務數量、服務質量、資源占用使用情況缺乏明確、合理的要求,缺少定期評估并依據評估進行獎懲,以至于許多事業單位的業務活動內容和方式偏離了國家和公眾的需要,偏離了社會事業發展的基本要求和規范。
正是因為事業單位在社會治理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以及存在的問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事業單位體制成為我國建設和諧社會,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提高事業單位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基礎性的工作就是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公共服務體制。因此,中共十七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明確要求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應該說,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現有思路正是對這一訴求的回應。然而,現有方案對公共服務的全球改革趨勢缺乏足夠認識,沒有意識到一項公共服務需要由政府提供,并不意味著必須由政府生產,從而導致了現有方案在制度設計上的內在沖突。
二、現有改革方案的內在沖突
(一)現有改革方案的基本思路
從2006年起,我國開始在廣東、浙江、山西、上海、重慶5個省(市)推進以分類改革為內容的新一輪事業單位改革試點。改革依據承擔的職能和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單位分為行政類、公益類和經營服務類三大類型。對于依據法律和行政法規授權履行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劃為行政類;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經濟社會秩序和公民基本權利的事業單位,劃為公益一類;面向全社會提供涉及人民群眾普遍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劃為公益二類;從事的業務活動具有一定公益屬性,但社會化程度較高,與市場接軌能力較強的事業單位劃為公益三類;從事經營性活動的事業單位,則劃入經營服務類。
其中,行政類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是職能歸位、逐步歸入行政機關。經營服務類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則是企業,部分承擔公益服務職能的單位將有關職能整合到相關事業單位中去。公益類事業單位將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等情況,再具體劃分成公益一類、公益二類、公益三類三小類,分別實施不同的改革方式和措施,采取不同的投入政策,執行不同的財務管理辦法,進一步實施分類改革。
可見,現有分類改革方案的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在于,根據事業單位所提供的服務,也就是社會功能的公益性來確定事業單位的轉型方向。如果某個事業單位提供的服務屬于政府的法定職能,那么,這個事業單位就逐步轉型為政府機構;如果不屬于政府的法定職能,那么,所提供服務屬于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屬性的事業單位轉型為公益性機構,屬于私人產品屬性的則轉型為企業。
(二)現有改革方案的內在沖突
我國目前正在推行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其最終的目的是要完善公共服務體制。但是,站在公共服務提供和生產環節可以分離的立場上,除了哪些服務應當由政府提供這個問題,改革還必須解決政府應當采用什么方式來提供這些服務的問題。但令人遺憾的是,現有政策方案沒有意識到改革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需要使用不同的分類標準進行回應,錯誤地將只能應用于提供機制的分類標準應用于生產機制,因此導致了制度設計上的內在沖突。現有改革方案的內在沖突,正是在于將僅適用于判斷一項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付費的公益性標準,錯誤地適用于去判斷一項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自己來生產。
對于公共服務“提供”和“生產”環節的區分,公共產品理論有過非常豐富的討論。亞當·斯密和密爾都曾經提出過公共產品的私人生產問題。[1]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等人指出,由公共支出承擔的產品以及服務,其提供(Provision)和生產(Production)完全可以分離。[2]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對于公共服務“提供”和“生產”的區分做了更加明確的闡述。[3]在她看來,提供是指在受益者之間分擔服務成本,安排生產、管制使用者、確定服務的具體用途和配置。生產是指把投入轉換成產出。提供一項公共服務的政治單位的組織不必一定生產該項服務。對于地方性公共產品的生產,提供單位至少有六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用,包括建立和經營“自己的”生產單位、與私人企業簽約、與其他政府單位簽約、內外部混合提供、特許經營以及憑單制度。薩瓦斯在公共服務的基本參與者中區分了生產者和提供者(或者說安排者)[4],公共服務的生產者直接組織或者直接向消費者提供服務,而服務提供者則指派生產者給消費者、指派消費者給生產者或選擇服務的生產者。在他看來,服務提供與服務生產之間的區分是政府角色界定的基礎,對很多公共產品來說,政府本質上是一個提供者,或者說是安排者。
不可否認,現有改革方案提出的公益性標準對于一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付費是能夠進行回應的。公益性這個概念和公共產品的理論具有內在契合之處,并且這一分類標準具有多年的地方改革實踐基礎。張朝太等就總結了“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幾種地方實踐[5],李春林等探討了鄂爾多斯市和包頭市的經驗[6],深圳市也結合中央的改革要求以及自身實踐進行了一定的探索[7]。這些改革實踐都是以公益性程度作為分類基礎的。地方的改革實踐,加上中央有關政策文件的規范,就使得公益性標準盡管在實踐中還存在種種缺陷,卻依然具備對某項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付費的區分能力。
但是,分類改革所提出的作為事業單位機構轉型方向的政府、企業以及公益機構這三種組織類型,從本質上說卻是屬于公共服務生產機制的范疇。如果事業單位轉制為行政機關,就意味著此類事業單位提供的公共服務今后將通過政府內部生產方式提供。如果轉制為企業,就意味著政府認為此類服務可以交由市場來提供。相應的,如果轉制為公益類機構,則是通過公私混合的方式來提供相應服務。因此,在改革方向的選擇上,行政類遵循的是內部生產邏輯,經營服務類遵循的是外部生產邏輯,公益類則是公私混合生產邏輯。由于事業單位究竟轉制為政府機關、企業或者公益類機構,在現有改革方案下取決于它所提供服務的公益性程度,因此,現有改革方案的基本邏輯就在于:產品或者服務的公益性越強,其生產方式越應當使用內部生產或者說科層制的方式,相反,產品或者服務的公益性越弱,則可以采用外部生產或者說市場機制的方式來提供。
然而,確定提供某項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到底應當采用內部生產、外部生產或者混合生產方式,社會功能的公益性高低并不是一個適用的標準。因為即便是將要轉型為企業的經營服務類事業單位,同樣可以生產需要由政府付費的、公益性很高的公共服務。可見,公益性的高低,只和某項服務是否需要由政府付費存在聯系,和這項公共服務是否需要由政府自己生產并沒有必然聯系。事實上,現有政策自身也凸現出這種邏輯上的混亂。現有改革方案提出,經營服務類事業單位即便改制為企業后,也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獲得財政支持。也就是說,現有政策承認經營服務類完全可以提供公益性服務,這對分類改革的基本邏輯其實是一種自我背離。如果說經營服務類也可以提供公益服務,那么,它們和公益類事業單位相比,其公益性的差異又體現在哪里呢?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混淆,關鍵在于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政策框架對于公共服務生產方式多元化這一全球改革趨勢認識不足,沒有意識到公共服務的制度建構需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片面認為只要解決了某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提供這一個問題,理順政府在公共服務中角色和作用的改革目標就可以自動實現。事實上,公共服務的多元化生產在我國的實踐中早已是一個普遍現象。自2003年以來,上海、北京、無錫、浙江、廣東等省(市)地方政府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探索不斷增多。購買的領域涉及教育、公共衛生和艾滋病防治、扶貧、養老、殘疾人服務、社區發展、社區矯正、文化、城市規劃、公民教育、環保、政策咨詢等諸多方面。[8]
三、公共服務的生產機制選擇: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現有方案制度設計的內在沖突之處,在于混淆了提供機制和生產機制兩個問題。公益性標準只能解決某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付費的問題,如果運用這一標準去解決一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生產,很可能將導致公共服務體制的功能失調。那么,到底應當依據什么標準來判斷一項公共服務應該選擇哪種生產機制呢?
對于這個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契約理論是最為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并且為設計替代性政策方案提供了基礎。契約理論討論了來自于不完全信息和不確定性的交易費用或者風險如何影響一項交易(或者說契約)。威廉姆森認為,契約所具備的不同交易特征,會使追求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人尋求不同的治理結構。[9]其中,科層(內部生產)或者市場(外部購買)都是屬于治理結構的具體類型。政府獲取公共服務的過程,在性質上可以被看做是一項交易,即政府投入財政資金,選擇需要的服務水平和類型,政府內部或外部的生產單位則負責生產并且配送公共服務。
站在契約理論的視角,在公共服務的多元生產方式之間進行選擇,其實就是為政府獲取公共服務這一交易選擇差別化的治理結構。將事業單位分為行政類、經營服務類或者公益一類、二類、三類,就治理結構而言構成了一個連續漸變的光譜,可以按照科層化程度進行排序。利用行政類機構生產公共服務屬于內部生產,在治理結構上是完全的科層制,利用經營服務類機構意味著完全的外部生產,在治理結構上屬于完全的市場機制,它們構成了兩個極端。公益類機構介于兩者之間,在治理結構上屬于威廉姆森所說的混合制。由于公益類可以再細分成三類,所以混合制的治理結構需要再劃分為準科層制、科層和市場混合制、準市場機制三種類型。那么,哪種類型的契約應當匹配科層制這一治理結構,哪些應當匹配市場機制或者混合制呢?
遵循威廉姆森的思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適用哪種方式進行生產,取決于能否降低公共服務的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因此,在依據公益性標準明確了某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付費的前提下,這項服務應當選擇什么樣的生產方式,或者說,政府獲取這項公共服務的契約應當采用什么樣的治理結構,就取決于治理結構能否降低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生產費用由投入資源的機會成本決定,由于規模經濟和技術效率的存在,市場機制通常能夠削減這一成本。但是,比起內部生產,市場機制下交易費用通常會上升。[10]因此,一項公共服務究竟適合由內部機構生產還是由市場機制生產,關鍵在于運用市場機制是否伴隨著很高的交易費用。如果由市場機制提供會帶來很高的交易費用,這種服務通過內部生產來獲取,對于政府而言就是有效率的。
政府獲取公共服務的交易費用高低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呢?格洛伯曼和瓦伊寧指出,決定交易費用的主要因素包括任務的復雜性、資產專用性以及可競爭性。[11]布朗和波托斯基也指出,此類交易費用主要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服務自身特征和市場條件。[12]對于服務自身特征而言,資產專用性和服務的可測量性是最常被引用和界定的相關因素。當資產專用性上升而服務的可測量性降低時,內部生產更加受到青睞。相應的,競爭性市場的存在,即如果存在很多潛在賣主可供選擇,也能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合同效率。由于任務的復雜性與服務的可測量性是直接相關的,因此,選擇治理結構時需要考慮的交易費用,其決定因素可以具體化為以下三種:提供服務的復雜性、資產專用性以及服務市場的競爭程度。其中,對于在公共部門中應用交易費用理論時最有爭議的資產專用性,鄧穗欣和盧永鴻進一步將它們轉化成是否行使公共權力,以及是否提供關鍵性服務。[13]這樣,政府獲取公共服務的交易費用就包括四項影響因素:是否行使公共權力、是否提供關鍵性服務、提供服務的復雜性程度以及服務市場的競爭性程度。
此外,對于制度變遷的過程而言,還必須考慮外部制度環境的因素,因為制度環境限制了改革選擇的范圍和界限。在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行政組織法以及行政編制管理體制這些法律和制度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事業單位轉型時可以選擇的范圍。根據現有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方案的精神,一方面,沒有法律法規授權的事業單位,不論是否承擔行政職能,都不能定為行政類事業單位。部分受地方行政機構數額限制列入事業單位的機構(如林業局、體育局等)及綜合執法類機構不能定為行政類。這類機構應結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為行政機構,或將行政職能尤其是無法律和行政法規授權的行政許可職能劃歸行政機構。另一方面,允許各地對符合條件的行政類事業單位進行“轉行政”改革,但又要求機構限額、行政編制總額“兩個不突破”。現有方案的這些折中規定,對于制度環境如何約束制度方案選擇提供了極佳的證據。
綜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公益性并不適用于公共服務生產機制的選擇,在討論事業單位在組織形態上應當轉型為行政類抑或經營服務類的過程中,新制度經濟學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可能更加適用。對于某項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而言,如果需要行使公共權力,服務對于政府部門非常關鍵、任務本身非常復雜難于測量,同時市場的競爭性很弱,那么,這樣的服務就應該傾向于內部生產方式。也就是說,提供這種類型服務的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是行政類或公益一類。反之,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則是經營服務類或者公益三類。同時,分類改革還必須考慮外部制度環境的約束,特別是行政組織法以及編制體制這些法律和制度的約束。圖1對公共服務生產機制的可選方案以及影響方案選擇的各種因素進行了概括。

圖1 公共服務生產機制的影響因素和可選方案
四、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替代性方案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現有政策方案的關鍵缺陷,在于沒有正確區分公共服務體制的兩個環節,導致了現有方案的內在沖突。要解決這一內在沖突,新的替代性分類改革方案必須有能力對公共服務的提供和生產兩方面機制進行回應,這就要求以二維的分類標準體系替代一維的公益性標準。圖2所描述的新的替代性方案,根本性的變化正是在于引入了針對事業單位組織形態轉型的新的分類標準。

圖2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替代性分類方案
在替代性方案中,分類的對象依然是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但是對服務要從兩個維度進行分析。由于公益性標準在很大程度上總結了各地改革的經驗,契合公共產品概念的基本特征,具備對一項公共服務是否應當由政府提供作出區分的能力,所以,在決定一項服務是屬于政府付費、私人付費還是政府和私人付費的時候,服務的公益性標準是有能力做出區分的。不過,決定事業單位在組織形態上應當轉型為行政類、公益類還是經營服務類,也就是在選擇公共服務生產機制的時候,應用公益性標準就存在嚴重弊端。生產機制的選擇,即事業單位的組織形態轉型應當綜合考慮四方面的因素,即是否行使行政權力、是否提供關鍵性服務、服務的復雜性程度以及市場的競爭性程度。此外,分類還必須考慮既有制度環境對選擇范圍的約束。可見,替代性方案的核心在于兩個階段的分類,首先根據公益性明確某項公共服務是否屬于政府付費的范圍,接著再根據事業單位所提供服務四個方面的特征決定它在組織形態上的轉換方向。
這一替代性方案之所以區別于現有方案,關鍵在于將服務的公益性和事業單位的組織形態轉型要求分離開來,從而能夠對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提供更加明確的政策指南,而且可以化解現有分類方案當中的很多問題。比如,在事業單位相當集中的衛生領域,就公立醫院來說,它既有經營性活動,又肩負著向社會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職能,在公共衛生和防疫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活動的公益性盡管存在很大差異,但是往往由一個部門提供,甚至技術上可能就是同一種服務。如果適用公益性標準,強行在機構層面把這些活動分開,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按照“就低不就高”的現有原則,那就可能使很多公益性活動失去必要的政府投入。然而,在新的分類框架下,醫院所提供服務的公益性并不和它的組織形態有關聯。醫院即使在組織形態上被劃入公益三類甚至經營服務類,也并不妨礙它的公益性活動獲得政府的足夠支持。再如,兼具技術支撐和監督管理職能的行政類事業單位(如質量監督、安全監督事業單位)是否需轉為行政機構值得商榷。如果所需人員的專業技術素質要求較高,保留在現行事業單位體制內更有利于按照專業技術序列對人員進行管理。
再比如,我國的大眾媒體,如果只是從社會層面探討它的公益性,完全應該被劃入經營服務類,況且大多數國家的新聞媒體也確實都是營利性企業。但是,大眾媒體在我國還具有意識形態宣傳教育以及監督公權力運作的功能,這對于政府而言就屬于關鍵性服務,而且這種服務和它的經營性活動屬于同一個過程,根本就無法分離。正是因為現有方案的公益性標準無法涵蓋事業單位職能的復雜性,在具體操作時不得不作出很多修正,進而模糊甚至扭曲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如果運用新的分類標準,鑒于新聞媒體提供著關鍵性服務、服務的復雜性很高、市場競爭性也不強,完全可以將新聞媒體劃分為公益一類或者公益二類,但是在財政支持上則實施政府和私人付費,甚至完全的私人付費。
還有,在事業單位最為集中的教育領域內,基礎教育一般被劃入公益一類。確實,公立小學所提供的服務公益性很強,教育經費由財政支持的程度也很高,然而,劃入公益一類意味著公立小學今后組織形態的轉型方向應當是準政府機構,這點就很值得商榷。因為就教育本身的技術特征而言,公立小學和民辦學校提供的服務并沒有差別,差別只在于服務對象的不同。前者針對社會所有階層,后者只提供服務給特定人群。所以,公立小學和民辦小學在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上完全可以采用相同的形態。但是,為了遷就前者的教育經費主要由政府提供這一現實,就將公立小學和民營小學在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上截然區分開來,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不過,最后還是需要指出,盡管這一替代性的政策方案指出了現有方案的內在沖突,并且運用具體案例分析了新方案的適用情況,但是,這些政策建議主要來自理論的推導,其有效性還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檢驗。同時,這一方案最重要的貢獻在于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實際應用時的具體分類規則依然有賴于進一步的實證調研以及政策實踐。
[1]許蕓:《從政府包辦到政府購買——中國社會福利服務供給的新路徑》,載《南京社會科學》,2009(7)。
[2]Vincent Ostrom,Charles M.Tiebout,RobertWarren.“The O 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Metropolitan A reas:A Theoretical Inquir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1,55(4):831-842.
[3]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公共服務的制度建構——都市警察服務的制度結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4]E.S.薩瓦斯:《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5]張朝太、田從科:《事業單位分類管理與改革》,載《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9)。
[6]李春林、張國強、趙首軍:《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及其啟示——來自鄂爾多斯市和包頭市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調研報告》,載《中國行政管理》,2008(8)。
[7]深圳市人民政府:《全面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創新社會事業管理體制和機制》,載《中國經貿導刊》,2007(8)。
[8]蘇明、賈西津、孫潔、韓俊魁:《中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研究》,載《財政研究》,2010,(1)。
[9]奧利弗·E·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0][11]Steven Globerman,Aidan R.Vining.“A Framewo rk fo r Evaluating the Government Contracting-Out Decision w ith an App lication to Info rmation Technology”.Public A dm inistration Review,1996,56(6):577-586.
[12]Brow n,Trevor L.,Matthew Potoski.“Transaction Costs and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fo r Government Service Production Decisions”.Journal of Public A dm 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3,13(4):441-468.
[13]Tang Shui-Yan,Carlos Wing-Hung L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rvice Organization Reform in China:An Institutional Choice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A dm 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9,19(4):731-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