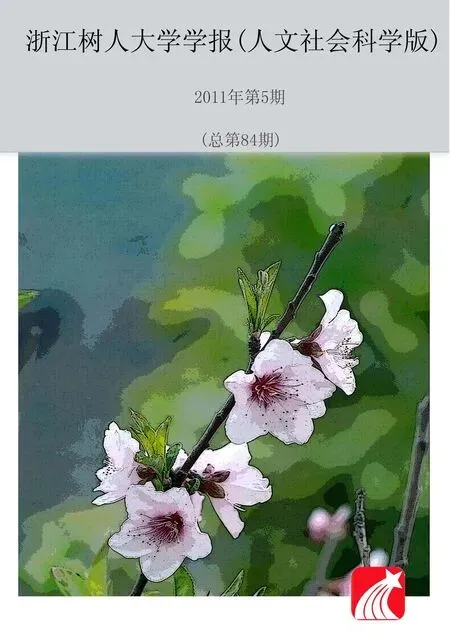試論新感覺派小說的敘事模式
程娟娟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300071)
“現代城市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國家的政治組織方式,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的經濟分布結構,同時,也是更重要的,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態……它是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1]新感覺派作家作為都市生活的一員,受到都市文化的熏陶,盡情地揮灑著才情之筆,抒發著對都市難言的熱愛。都市中人的心態和視角、市場機制和世俗趣味的影響以及對于現代藝術手法的自覺追求,決定了新感覺派小說所具有的獨特性質。在情節模式上吸收和借鑒早期海派、同期左翼小說、日本新感覺派及西方現代小說,形成了豐富蕪雜的創作特色。
一、現代主義思潮推動下產生的先鋒實驗
先鋒實驗派小說是新感覺派小說中最具有創作特色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滿足了市民追求新潮的獵奇心理和時髦愛情故事的新鮮感覺。
這一類型的小說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作品多采用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屬于人物敘事情境,這與傳統的全知全能視角的故事講述方式迥然不同。敘事者由一個反映者所取代,敘事的焦點集中在一個人物上,以人物內部聚焦的方式展開情節。作者不再將曲折的故事表達放在首位,著重表現自我的感覺和情緒,表達自我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和觀點,描寫的重心由外部世界轉向人物的視角,不是客觀理性地分析社會,而是要寫出人物眼中的世界,他所真正感覺到的外部世界以及他內心的小宇宙。他們不屑于用社會解剖分析的X光來透視這個光怪陸離的都市,也自覺地割斷了對于鄉土世界的留戀,無所依傍,無所憑借,只求真實形象地傳達出自己細微敏銳的感覺,包括對于城市的沉溺、迷亂與痛苦掙扎的靈魂。
第二,女主人公往往美麗妖艷,大膽地放逐自己的欲望,男性迷戀上女性的美色,最后男性被嘲弄,成為感情的消遣品,從而改寫了傳統小說中女性被動等待男性追求的模式。這一典型的敘事模式是新感覺派小說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女性在戀愛游戲中的大膽主動并不意味著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相反,在個性解放的幌子下,掩藏的是金錢的巨大支配力量以及人在外界異己力量的壓迫下被異化的現象。它打破了人們心中堅守的社會道德,使一切都處在變化無常之中。從社會發展來看,這一模式反映了時代的變遷,都市生活物質的極大豐富,交通的方便舒適,人口的流動性,社會思想的解放,這些都為女性走出家門創造了條件。當時的上海充斥著追求享樂與消費的風氣,即周作人所批評的“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社會風氣的開放對女性來說是極大的刺激,她們不再懼于舊傳統的威嚴,輕松地走上了摩登瀟灑的生活之路。
第三,從敘事順序來看,大部分作品按照敘事功能的順序展開,這是為了符合人們注重首尾呼應與關照的特性,形成情節的翻轉。例如,《熱情之骨》和《流》描述的是遭到嘲弄,處于被動的地位,顛覆了傳統的以男性為主體的情節模式。《夜》《五月的支那》和《PIERROT》都包含著“尋找”主題,主人公要擺脫空洞的靈魂,就要想辦法來填補這個空白,故事情節由此展開。
新感覺派作家進行的先鋒性的藝術實驗是其最具流派特征的部分,改變了情節功能按照時間線性發展的順序,敘述事件的過程不再完整嚴密、符合邏輯,不同事件發生了交叉、平行、并置,從而出現了在小說形式上極富開拓與創新意義的作品。《夜總會里的五個人》將時間的線性發展線索巧妙地變幻為在空間中的平面化展開,從而打破了傳統時間敘事對寫作的束縛。
第四,小說的結尾往往是主人公陷入憂郁苦悶中難以解脫,孤獨地“一步一步地在人生的路上彳亍著”。這是“卷在生活的激流”中的人們所患的都市憂郁病,它不是西方現代派作品中真正的徘徊在“城堡”外的荒誕感,也沒有實際的對于現存社會價值、人的生命意義的虔誠而痛苦的心靈拷問,一切只是淺嘗輒止,一再出現的“在路上”的意象,表明主人公并未徹底地失去所有的希望,陷入黑暗的無底深淵,雖然找不到解除痛苦的濟世良方,但他們仍然懷著對世俗生活的留戀,選擇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可以說,表面上是對于人生消極頹廢的感嘆,深藏的是對于命運、生活的強烈留戀和欲求。正是由于對都市的深深迷戀,使他們不能遠距離地、理性地審視,缺乏冷靜的思考,更缺乏懷疑和反叛的精神,是一種有待于升華和提高的情感體驗。
內部聚焦的敘述方式、美麗妖艷的女主角、引人入勝的洋場愛情故事、多種形式的敘述實驗、傷感悲哀的結尾以及華麗感性的語言,構成了風靡一時的洋場故事的基本要素,也顯示了其流派的重要特征。
二、滿足市民審美需要的通俗愛情故事
新感覺派的作家們在玩弄著先鋒的文字游戲時,也以市民文化本位的心態制造了新鮮的大眾愛情故事,顯示出新感覺派小說對于本土文學傳統資源的繼承與創新。
這一類型的小說主要特點是:
第一,主人公追求的是感情的契合而非身體的結合,推崇的是浪漫唯美的“柏拉圖式的戀愛”,純真美好、憂郁感傷是作品的風格。小說《公墓》描述了“帶有早春的蜜味的一段羅曼史”,他們注重心靈的溝通,任何有關身體接觸的想法都是不潔的,在心理上受到超我的嚴厲譴責。
“圣女”是這一類型小說女主人公的形象特點,與前面的洋場女郎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為何新感覺派作家會塑造完全不同的兩類女性形象呢?事實上,“海派小說并非泯滅了對性愛理想化的追求。性的沉溺,兩性情感的極度浪費,反彈出都市男女對根本無愛和愛的稀釋的性關系感到厭足,并且開始了他們在惡中尋求善、美,在性糜費中捕捉真情的艱難旅程。”[2]
開放性的都市女郎使得崇高的愛情蒙上了銅臭氣,欲望的快餐式滿足并未給人們帶來幸福的滿足感,而是更深更廣的空虛感。再加上處于新舊過渡的時代,對于現實的失望與厭倦很快轉向對于傳統美德的贊同,因此,在同一時期,同一作家的筆下,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時代女性的身上寄予了都市生活的現代性,“圣女”形象則顯示了作家對于傳統道德、美好人性的執著尋求,與“妖婦”形象一樣是男性中心的菲勒斯文化的解讀。
第二,從情節設置來看,主人公的追求存在著障礙,但已不是早期鴛蝴派小說中存在的封建禮教的壓制,而是某種外在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朦朧縹緲的愛情無法真正地在現實中立足,這就注定了小說結局是悲劇性的,女主人公非死即走,男主人公沉浸在愛情失落的感傷的回憶中。在新感覺派小說的純情文本中,作者無意于作個性解放的吶喊者,著意展現的是純潔美好的愛情無法實現造成的心靈痛苦,從而引起讀者的共鳴。與鴛蝴派相似的一點就是重情輕欲,原因正是傳統倫理道德觀的影響,無論作者是在倡導思想解放的五四時代中猶豫觀望,還是在歐化時尚的十里洋場里見慣了聚散離合,都逃不脫傳統文化的影響,隱含著對傳統的溫柔嫻靜、婉約含蓄的東方古典美的尋求。
第三,從敘事手法來看,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事方式,這樣更有利于傳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哀艷纏綿的情思、低回婉轉的悲傷打動讀者。敘事者兼主人公的角色在講述一個自己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真實親切的敘事方式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在體裁形式上,選擇的是復雜敘述的手法,在《第二戀》和《朱古律的回憶》中,將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兩種自我,“經驗”自我和“敘述”自我對立地交叉在一起,也就說在溫馨的回憶過程中,穿插事隔多年后的感受,這樣,不諳世事時的純潔感受與成熟穩重時的悔恨惆悵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獨特而富有韻味的張力。事后回憶的“我”充滿了悔恨和對逝去青春的遺憾,這種感情滲透在當時美好初戀的甜蜜回憶中,增添了幾分難以化解的苦澀。
這一類型的市民通俗愛情故事既有一定程度的迎合讀者的媚俗性,又有文體形式的花樣翻新,其散文化的筆法,新舊雜糅的手法,疏散靈活的結構,感傷詩意氛圍的營造,愛情的圣潔化,第一人稱的故事文體,敘事時間上的交叉對比,文筆的精致優美等,都展示出新感覺派作家除了張揚迷狂的都市先鋒的一面,還有溫情脈脈的回歸傳統的另一面。
三、犀利地解剖人性的心理分析性作品
早在20世紀初,精神分析學說就開始被引入中國,早期使用這種理論還有些生疏機械,不夠圓熟自然,而真正得到弗氏理論精髓的則是新感覺派的作家。他們繼承了前輩的開拓,充分利用這一犀利的解剖刀深入剖析人物的靈魂,展現出人性的復雜變化。
這一類型小說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小說主要描寫了主人公在外在對象的刺激下引發的一種欲望與理性的強烈沖突,而正是這一貫穿全文的沖突推動了故事的情節發展。作者用心理分析的解剖刀深入人物心靈的深處,展示了人性的復雜和深邃,對微妙細致的心理沖突的捕捉再現構成了小說的情節主線:在情欲的驅使下展開行動,行動過程中的心理矛盾與掙扎,以及小說的結尾——本我滿足抑或超我勝利。人物無一例外地糾纏在心靈的痛苦中,被巨大的毒蛇所纏繞,無論是古時的高僧勇將、武林好漢,還是處于邊緣生活中的寡婦、都市中的男性,都陷入情義兩難的尷尬境地之中。在情節發展中,主人公追求過程的障礙往往不是外在客觀的,而是自己內心難以把持的“心猿”,異性的出現是一種具有誘惑性的刺激物,使人的心靈躁動不安。
第二,強大的本能沖動對人的驅動作用,顛覆和解構了以往神圣社會的宗教、倫理、禮教等道德傳統。社會文明的進步象征人類的不斷前進,同時也對人性造成了極大的束縛。借用弗氏學說對人的內在心理的發掘和對人性的犀利透視,必然要褪去圣人君子的神圣光環,排除外在的浮華表象,展示人性的普遍存在。在小說中我們找不到道德完美的人,主人公都處于無休止的心理波動之中,五蘊皆空的圣僧不過是個愚弄善男信女的凡人而已,急公好義的江湖好漢石秀在垂涎義嫂的美色,馳騁疆場的猛將原來也兒女情長,現代人亦如此,苦守貞節牌坊的寡婦也有動情的一刻。作者采用了“崇欲抑理”的手法,即強大的本我的存在顛覆了外在的倫理道德傳統,消解了崇高的意義,褻瀆了英雄的形象,在放逐欲望的文本書寫中揭示了人的精神危機。“這已經超出了對破除傳統禮教的五四批判精神的繼承,而帶上了后現代的先鋒意識和顛覆性色彩”。[3]
第三,從敘事人稱上看,這一類型的小說多是用第三人稱展開敘述,這樣拉遠了敘事者與故事的距離,可以全面地展開故事的講述。作為揭示人物情感沖突的心理分析小說,這種手法并不妨礙敘事效果的真實可感性,作者巧妙地運用了內、外聚焦結合的方式來講述故事,使用內部聚焦可以直接切入,很好地展示人物內部的本能與文明的矛盾斗爭,而外部聚焦的使用可以講述與人物相關的其他事件,彌補單一視角的不足,在內、外部聚集的自由切換中,使故事得以完整統一的敘述,人物的心理也得以細致入微的展示。《石秀》和《將軍低頭》都使用了從內部聚焦向外部聚焦自然轉換的手法,不落痕跡地展示了人物的心理與外在的環境,既避免了西方小說大段內心獨白造成情節的淡化,也規避了只重動作無視心理的傳統模式帶來的弊端。
這樣,心理分析性作品以精神分析理論為依托,著意展示心靈的矛盾與沖突,挖掘人性深處的潛意識,從而由現實的真實進入到人物的靈魂的真實,以日常生活的世俗描寫消解了傳統意義上的崇高和神圣,以其具有的創新性與顛覆性的文本、多變靈活的敘述方式在新感覺派小說中獨樹一幟,為后來的小說敘事創造了一個廣闊深邃的心理想象世界。
四、表現底層民眾艱難生存的“左”傾作品
上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采用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從政治審美的角度推進文學與政治的有機結合,積極地參與到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對于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處于“近水樓臺”的新感覺派作家自然也受到它的影響,創作了一些反映社會底層小人物生存悲哀的作品。可以說,他們的作品并非純粹的革命小說,借用評價穆時英早期小說《咱們的世界》來說,“Ideologie上固然欠正確,但是在藝術方面是很成功的”。[3]即他們不在乎思想要多么正確先進,注重的是形式技巧的鍛煉。
這一類型小說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從情節的發展過程來看,主人公為生活所迫,需要做出違背自己做人原則或道德的事情,心靈承受著生存的艱難與道德的譴責雙重壓力,而做壞事的行動過程往往被人發覺、受到指責,《偷面包的面包師》中的主人公違背自己的做人原則偷蛋糕。主人公的結局一定會比初始情景更加糟糕。作者沒有安排人物走上決絕的反抗之路,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人物似乎仍然生活在混沌麻木的狀態中,沒有啟蒙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他們的夢仍會繼續做下去。
從文本分析來看,造成主人公悲劇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具體的個人,作者沒有刻意凸顯老板、廠長之流的兇惡殘忍,不是左翼小說中萬惡的社會需要勞苦大眾將它推翻,而是一個混沌曖昧無形的具有強大神秘力量的存在,或者說是人人擺脫不了的命運——懸在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墜落下來。失敗早已命中注定,無論怎樣掙扎反抗,悲劇的命運也無法改變。因此,這一類型的小說沒有像同時期的左翼小說設置一個光明的未來,給人以強烈的壓抑感、窒息感,充滿了灰暗的色調,人物找不到任何出路,在能量的損耗與外在的折磨中,生命就這樣慢慢過去了。
第二,從主人公的身份來看,他們的職業身份非常明確,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都屬于革命的主要力量或團結對象。那么如此明確地強調職業出身,顯然是要凸顯人物強烈的求生動機和生存的惡劣環境,給讀者以善良被無辜毀滅的震撼。當然,身份的強調并不意味著作者以階級性遮蔽了普遍的人性。面包師在商鋪里是個老實巴交、不善言辭的人,回到家里就將心里的委屈無端向兒子發泄,孩子成了可憐的受氣包。作為底層民眾,他無法將怨氣轉嫁到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身上,只能在家庭中向弱者施威,來維護自己的心理平衡和家長的尊嚴,這是國民劣根性的一種表現。也許他并不是不疼愛孩子,只是艱難的生存已經麻木了他的神經,無法從容地感情表達,就以這種極端的形式展現出來。
第三,這一類型的小說都是采用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有助于客觀平實地展示人物的生存境遇。不過,小說的敘事手法和小說技巧卻是多種多樣的。在塑造人物時,并不是簡單地平鋪直敘人物的命運如何悲慘,控訴社會的黑暗不公,而是以內部聚焦的方法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幻覺、夢境、意象及意識流等手法使人物的形象更加豐滿生動,擺脫了左翼小說人物平面化、語言口號化的缺點。特別是下層人物的語言通俗曉暢、親切活潑,語言個性化、口語化,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斷了條胳膊的人》中在出事前描寫了人物的噩夢,既顯示了人物強大的心理壓力,又為下面的情節做好了鋪墊。還有人物醉酒后的幻覺,恍惚中妻子回來了,分不清是真是假,這也符合醉鬼睡意朦朧的情景。
以社會底層民眾生活為表現對象,以多樣的藝術手法表現人物,試圖展示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通過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揭露了“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社會,這個喧囂浮華世界的黑暗一面。題材的相近與同時期的左翼小說具有一定的親和力。需要指出的是,題材不能決定作品的成就,由于對社會底層人們生活的隔膜,只是流于表面的善意而缺乏歷史洞察力的溫情關照,描寫浮泛不無失真之處。其價值不在生活嚴酷性的直面書寫,更多的是文學技巧的嫻熟炫耀。
[1]李書磊.都市的遷徙—現代小說與城市文化[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3.
[2]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86.
[3]白杰.穆時英研究述評[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9(9):4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