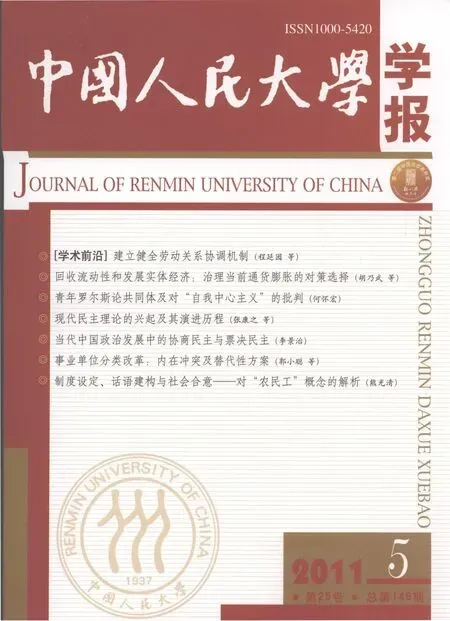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現狀與問題
李麗林 袁青川
所謂三方協商,是指國家(通常以政府作為代表)、雇主和工人之間,就制定或實施社會政策而進行的所有交往,也稱為“三方合作”、“三方關系”或者“三方性”。[1]而三方協商機制則是一種協調勞動關系主體不同利益的基本制度。這一制度早在1848年就開始在法國出現,經過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 r O rganization,以下簡稱ILO)的大力提倡,目前已經成為一種國際勞工標準,逐漸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采用。
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逐漸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也開始嘗試采用三方協商機制來解決勞動關系問題。但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我國主要由政府主導的三方協商機制能否有效發揮作用尚處于爭論之中,需要根據社會需要適當擴大其職能,協調好勞動關系。
一
三方協調機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后期,一些國家為了有效處理勞資糾紛開始創建三方協商機構。法國早在1848年成立了一個勞動咨詢委員會,使工人有機會參與政府有關政策的制定過程。因為開會的地點為盧森堡,因而也被稱為盧森堡委員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于通貨膨脹的困擾,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開始尋求雇主和工會的合作,設置了一些三方協商機構。20世紀的20年代,在一些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為了解決勞動爭議,政府開始與工會或(和)雇主達成某些兩方或三方協議。隨后,引進三方協商機制的國家越來越多。[2]
三方協商機制的發展得益于ILO多年來的努力。1944年,ILO發表了《費城宣言》,重新定義了ILO的目標和宗旨,宣稱ILO有“莊嚴的義務……推進……各種計劃,以達到……工人和雇主在制定與實施社會經濟措施方面的合作”。現在,“加強三方機制和社會對話”仍然是ILO的四大戰略目標之一。
ILO推行三方協商機制的主要方式是通過有關的國際勞工公約和建議書,使其形成一種國際勞工標準在世界各個國家實行。1960年,ILO通過了《產業和國家一級公共權力機構與雇主和工人組織協商與合作建議書》(第113號),建議各國在國家及產業層面建立三方協商機制。此后,ILO又在1976年通過了《三方協商促進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公約》(第144號)和(國際勞工組織活動)三方協商建議書(第152號)。
ILO多年來一直在持續關注三方協商的問題。在1996年的國際勞工大會上,“國家一級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的三方協商”問題被列入大會的議事日程,各方就經濟和社會決策中加強三方合作達成一致意見。在2000年的國際勞工大會上,三方協商問題再次被列入議事日程。2002年,ILO就三方協商和社會對話提出了解決方案。2008年,第97次勞工大會通過了《關于爭取公平全球化的社會正義宣言》。在宣言中,ILO明確指出,社會對話和三方性(安排)是促進良好的勞動關系、加大勞動法的實施效果等工作的最適宜的方法。ILO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在談到三方協商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作用時曾經這樣說過:“在所有的地區,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了社會對話與三方協商的價值。當政府和社會伙伴們一起設計政策應對這場危機時,這些制度具有更加特別的價值。”
此外,ILO還通過其他一些手段促進三方協商在各國的發展。這些手段有調查研究、信息傳播、技術性會議、技術性咨詢服務或技術合作。近年來,ILO在以下問題上都開展了類似的活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就業問題、社會保護以及向市場經濟過渡問題等。
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批準144號國際勞工公約的國家有131個,約占ILO成員國的72%。這些國家遍布全世界,既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包括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加蓬等欠發達國家。在亞洲,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越南等國家都批準了該公約。雖然在180多部國際勞工公約中,我國只批準了25部,但144號公約正在其中。我國在1990年就批準了144號有關三方協商的國際勞工公約。
按照144號公約的規定,凡批準該公約的國家,都“承諾運用各種程序保證就……有關事宜,在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代表之間進行有效協商”。毫無疑問,有些國家雖然沒有批準144號公約,但也設置了某些機構和程序,進行了有效的三方協商。例如,新加坡在1972年已經設立了“全國工資理事會”(NWC)這樣的三方機構,但直到2010年4月才批準了144號公約。因此,可以說,三方協商機制是一種在世界各國被普遍采用的制度。
各國采用三方協商機制的形式可以分為兩大類:最主要的一類是正式的機制,有常設的機構,通過正式的協商會議協調勞動關系;另外一類是非正式的機制,為了處理某個問題或者某個事件而成立臨時機構,進行三方協商。
在那些采取正式的三方協商機制的國家,協商機構的設置存在較大的差別。在一些轉型國家,以及一些在ILO推動下建立三方協商機制時間較短的國家,通常以某個正式的機構為主進行三方協商。[3]而在那些擁有三方協商傳統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則可能存在多個三方協商機構。例如法國,既有討論和協商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經濟和社會委員會”、“計劃委員會”,也有一些針對具體問題而成立的專門的三方協商機構:國家集體談判委員會,中央就業委員會,個體爭議產業法庭中央委員會,職業教育、社會進步和就業中央委員會等等。日本在1946年成立了勞動委員會,由中央勞動委員會、地方勞動委員會(共47個)組成;在1970年還成立了“產業和勞動圓桌會議”,討論工資、價格、就業和勞動權利等問題。由于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日本于1979年開始召開“就業問題政策會議”,三方針對就業政策、技術變革等方面問題交換意見。另外,日本在勞動部、國際貿易和產業部等部委及機構還成立了一些委員會,處理特定問題,例如職業培訓、殘疾人、家庭務工人員等問題。[4]
在有些國家,正式的三方機構還設置了分支機構或者專門的委員會。例如,奧地利的價格和工資聯合委員會,在價格、工資及其他國際問題方面成立了分支委員會。匈牙利的利益協調委員會設有下面一些專門委員會:經濟協商、收入政策、工資和勞工、勞動力市場、社會政策、信息委員會等。[5]
非正式的三方協商機制在各個國家都可能存在。在西班牙,從1977年至1987年的后佛朗哥時期,三方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簽訂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契約。20世紀80年代初期,澳大利亞首次召開全國性的經濟首腦會議,使澳大利亞開始使用協調發展的經濟政策。澳大利亞勞動黨和澳大利亞總工會在1983年勞動黨選舉前簽署了協議,該協議倡議在澳大利亞的大多數地區建立三方協商機制。
美國雖然沒有正式的三方協商機構,但一直有一些非正式的組織在活動。美國著名的勞動關系專家約翰·鄧洛普在1974—1975年擔任勞工部長時成立了峰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他離任數年后依然在私人贊助下運行著,鄧洛普出任了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主要討論的是集體談判之外的各種勞工政策問題。1985年,前任勞工部副部長馬爾克姆·洛弗爾(M alcolm Lovell)建立了由工會領袖和企業界領袖組成的集體談判論壇,這個組織一直存在,經常討論改善集體談判的長遠戰略。1993年,克林頓首次執政的時候有意打破在勞工政策上為時甚久的僵局,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委員會,名為“勞資關系的未來委員會”,也稱為鄧洛普委員會,因為約翰·鄧洛普擔任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創設的目的就是要探討更新美國的勞工政策,設法提高美國的競爭力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6]
一般而言,三方機構通常包括來自三方的成員,即工人組織的代表、雇主組織的代表和政府部門的代表。日本在經濟泡沫破裂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就業問題,為此在1998年成立了“就業政策三方委員會”,參與協商的有來自雇主方的日經聯、工會方連合的最高領導人和日本內閣的主要成員。[7]
由于許多國家存在多個總工會和多個雇主協會,因此,參與三方協商的工會和雇主方的組織可能有很多個。例如,韓國1998年成立的“三方委員會”,其參與者包括政府成員、三大政黨成員、兩大雇主組織的人員以及兩個最主要的工會聯盟的成員。[8]
三方協商委員會中經常會包括“獨立的專家”(例如意大利、荷蘭)以及經濟和社會利益以外的其他勞動和資本的代表。例如,西班牙的經濟和社會委員會雖然是三方機構,但也有一些轉變。它包括三個群體的代表:前兩個是工會和雇主機構,第三個是由一系列其他利益群體(農業、漁業、消費者、合作社)的代表和專家組成。日本設有數量眾多的咨詢委員會,例如中央勞工標準委員會和中央就業穩定委員會,參加這些委員會的除了日經聯和連合的代表,第三方并不是來自政府部門的人員,而是一些代表公眾利益的人士,有大學教授和律師。韓國也有類似的安排。韓國的勞動法審核委員會包括來自韓國總工會(FKTU)的三名成員,來自韓國雇主協會(KEF)的三名成員,另外還有十名專家,也是由大學教授和律師組成。[9]
隨著社會對話或者說三方協商的范圍越來越廣,從政府這個主體看,很多國家不再單獨由負責勞動事務的政府部門充當政府的代表,還有其他的部委加入,例如財政部、教育與培訓部門以及商業部等。在奧地利的工資和價格聯系委員會中,政府代表來自農業部、經濟事務部和社會事務部。澳大利亞的發展建議委員會就包括財政部的代表。喀麥隆的新的國家勞動咨詢委員會包括國家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國民議會以及最高法院的代表,另外還有雇員、雇主的代表和勞動部。在津巴布韋,財政、商業、工業、采礦、農業等部門的代表也參加勞動咨詢委員會。在有的國家,參加社會對話的不僅有相關部委的部長,甚至國家元首也參加協商會議,愛爾蘭就是這樣,日本也有這樣的做法,即由首相或者副首相參加三方會議。
由于各國非工會化部門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需要吸收NGO組織以及其他一些利益群體,例如婦女組織、青年和失業者組織的參與。一些國家已經把農民(例如比利時、印度、西班牙)、小企業的業主或是從事某些職業的人員(如比利時、荷蘭)、自由職業者(如法國)、合作社的代表(如丹麥、葡萄牙)、社會團體的人員(如澳大利亞)、消費群體(如丹麥、西班牙)、環境協會(如葡萄牙)以及家庭協會的人員(如法國、葡萄牙)等吸收到三方會議中。因此,和“三方”合作相比,這種經濟和社會機構更應該稱為“多方”合作。[10]
二
世界各國如此廣泛地應用三方協商機制來應對各種各樣的勞動關系問題,是因為在一個利益多元的社會中,需要三方協商機制來協調勞動關系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
在勞動關系的基本理論中,勞動關系的主體由“三方”構成,即勞方、資方和有關的政府機構。約翰·鄧洛普認為,勞方這個主體包括非管理人員的雇員及其代表組織工會;資方是各級管理人員及其代表雇主協會;有關的政府機構不僅是勞動行政部門,更包括代表國家意志的立法和司法機關。[11]國際勞工組織是這一三方性的最好說明。各成員國的代表團由勞、資、政三方組成,三方都參加國際勞工組織的各種會議和機構,獨立表決。
更重要的是,勞動關系的三方主體所追求的目標并不相同,利益也不完全一樣。哈里·凱茲和托馬斯·寇肯就明確指出,勞資之間從根本上存在利益沖突,他們擁有“不同的經濟利益”。這種觀點在勞動關系理論中被稱之為多元論,是勞動關系理論的主流,也可以說,它是勞動關系規范分析的基石。例如工資和福利,對工人來說是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的收益,而對于資方來說則是需要控制力求最小化的勞動成本。在引進新技術這樣的具體事件上,勞方和資方的利益也可能產生矛盾。新技術的引進能讓企業保持競爭力不被市場淘汰,但對工人來說則可能意味著喪失工作崗位。因此,有學者認為,勞動關系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要平衡三方的利益。[12]
協調三方利益沖突的機制有很多種。根據參與方的數量可以劃分為單方機制、雙方機制以及三方機制。例如,勞動法即是政府這個主體單方面協調勞動關系的一種方式,而集體談判機制是勞資雙方協調勞動關系的最著名方式。
以三方機制協調勞動關系既反映了三方主體利益的差別,同時更說明了決策的民主思想:在決定某些人命運的過程中,應該允許那些受決策影響的主體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力求在決策中體現他們的利益訴求。因此,在政府就勞動問題的決策中,應該允許有關利益主體——勞方和資方參與其中。由于直接民主的方式成本太過高昂,所以勞資一般通過其代理人工會和雇主協會參與政府有關勞動問題的決策過程。政府通過三方協商進行決策雖然不得不放棄一些權力和便利,但可以換取勞方和資方對政府所實施政策的支持,實現社會和諧。通過三方協商,政府也可以把矛盾轉移出去,讓勞資團體共同分擔和化解勞資沖突。
從三方機制的發展也可以看出,各國三方機制的引入是因為存在這些社會需要。在20世紀60年代,困擾很多國家的是通貨膨脹問題,各國政府為控制物價而實行收入政策。這一政策肯定會影響到勞方和資方的利益,同時收入政策的有效實施也需要這兩大利益主體的支持,因此,在這一時期,這些國家就收入政策與勞方和資方進行了三方協商。例如,在丹麥和荷蘭,工會接受了工資限制以協助抗擊通貨膨脹。[1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戰時勞工委員會這個三方機構的產生也是社會需要的結果。當時美國的形勢嚴峻,既要保證戰爭所需的產品的產量,又要避免罷工,避免工資與物價的上漲。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羅斯福政府于1942年成立了美國戰時勞工委員會。戰時勞工委員會是一個三方機構,包括勞方和資方代表,而委員會的主席是中立人士。這個機構在當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從1942年到1945年,戰時勞工委員會成功地解決了2萬多起勞資糾紛。戰時勞工委員會還利用它的各個辦事處使集體談判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同。戰時勞工委員會還充當了培訓機構,培養了許多帶頭的調解人、仲裁人和政府顧問。這些人在戰后的幾十年里,對集體談判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些專業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美國式的集體談判模式,一種政府直接干預很少的談判模式。[14]
1997年,韓國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解決方案引發了裁員潮和大規模失業現象。為解決這一問題,韓國政府和韓國的雇主及工會組織進行了三方協商,并且于1998年1月15日簽署了“社會契約”。政府和雇主方承認工人的基本權利,承諾采取一些社會保護措施,而勞方同意削減工資并且在雇傭上給予資方一些靈活性,接受新的解雇制度。這份社會契約被認為對韓國經濟的復蘇起了重要作用。[15]
三方協商機制在今日的中國具有其他制度無法取代的作用。作為一個轉型國家,我國已經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開始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在未來的若干年,我國還必須走完工業化的過程。轉型時期的特點是新問題層出不窮,卻沒有既定的法律對這些問題進行規范,因為法律具有明顯的延遲性。只有當一個新問題成為普遍性的問題,并且在實踐中已經找到有效的處理方法時,才可能經由法律將這一處理方法強制在全國推行。很多勞動關系學者推崇集體談判制度,認為它可以平衡勞資力量的不對等,改變“強資本,弱勞動”的態勢,但是,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有賴于工會在企業層面的獨立,工會能形成一種與資方力量相抗衡的集體力量。集體談判的本質是一種雙方的決策。而協商包括信息的分享、意見的咨詢、利益的表達,有時候也能做到共同決策。集體談判通常有明確的談判事宜,例如工資或者工時等,而協商的主題卻可以多種多樣,其形式也多種多樣。可以說,靈活性賦予協商更強的生命力。如果協商都無法進行,又何來談判?
三
我國的三方協商機制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隨著1986年勞動制度開始改革,勞動關系多元利益分化逐漸明顯。在“砸三鐵”、“優化勞動組合”、“國有企業改制”、“裁員”等多項經濟體制改革和勞動體制改革措施中,勞資沖突逐漸顯性化。一些省市為了緩和勞資矛盾,首先嘗試通過三方協商機制來協調勞動關系。這些敢開先河的省市是山東、山西和遼寧等。[16]例如,1998年,遼寧省作為老工業基地,為了解決在企業轉軌中出現的問題,建立了一個由政府、工會和企業組成的稽查機制。
1990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ILO的《三方協商促進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公約》。我國遵守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在修訂的《工會法》第34條第二款中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同級工會和企業方面代表,建立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系方面的重大問題。”這為三方協商機制在我國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2001年8月3日,“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成立暨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標志著我國開始在國家層面建立正式的三方協商機制。隨后,各地在省、縣甚至街道等各個層面紛紛創建三方協商機構。到2009年底,全國已經建立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1.4萬個。其中,省級31個,地級313個,縣級2 531個,縣及縣級以上地方共建立三方協調機制2 875個。[17]
在國家層面上,我國建立了“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制度”,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三方組成。三方各自確定相對固定的機構負責人作為三方會議成員,不定期召開會議。自2001年到2011年6月底,共召開過15次會議。國家三方會議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關系司(原來在勞動工資司)設立了辦公室,負責三方會議的日常工作,并于2006年決定成立勞動關系法律政策研究委員會、薪酬咨詢委員會、集體協商指導委員會、社會保障政策咨詢委員會以及勞動標準研究委員會五個專業委員會。但這些專業委員會并沒有實際運行。
十年來,國家三方會議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了作用:
首先,推動了我國集體協商制度的發展。國家三方會議在前13次會議中有10次會議涉及集體協商問題。第三次會議結束后,三方分別就《集體協商規則(草案)》征求了修改意見,在第四次會議上提交討論,達成基本共識。會議原則通過了《集體協商規則》。三方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通知》、《關于貫徹實施〈集體合同規定〉的通知》和《關于進一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其次,三方為一些勞動法律法規的制定與修改提供了意見和建議。這些法律法規包括《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最低工資規定》、《集體合同規定》等。[18]
第三,推動各地進行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的活動。這一活動非常具有中國特色,是我國的三方協商機制搞得最熱烈、最受歡迎的一項活動。這一活動弘揚了先進,客觀上對協調勞動關系具有積極的作用。
第四,建立了信息分享制度。國家三方會議辦公室不僅在會后編寫《會議紀要》抄送有關各方,還定期編寫《信息交流》,介紹各地落實國家三方會議精神、推行各種措施的情況等。例如,在第15期的《信息交流》上,先介紹了福建、北京、江蘇、河北、廣東等地“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穩定勞動關系的工作意見”,然后是蘇州、連云港的一些具體做法,最后重點介紹了吉林省總工會開展的“共同約定”行動。這些信息的分享有助于各地建立健全三方協商機制,互相學習借鑒。[19]
地方的三方會議相較于國家層面的制度更具有靈活性。參加三方協商的主體除了勞動行政部門、企聯/企協以及工會外,在一些地方也有國資委、經委等機構代表資方參與協商,如寶雞市。遼寧省把工商聯和外企協會納入資方代表中。在上海市,法院始終參與勞動關系的協調工作。在上海市的區一級三方協商會議上,有一些著名的企業家代表資方參加。在寶雞市,三方辦公室設在勞動保障局的法規科。陜西省成立了勞動關系協調領導小組,由主管副省長擔任組長。在很多地方,三方會議定期召開,如廣東、西安、遼陽等地。
地方的三方會議也更有實效。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要經過三方會議的討論通過。筆者到陜西省調研時,有關方面介紹說,2008年在陜西省第七次三方會議上,各方就最低工資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在會上還發生了激烈爭論。廣州市的三方會議對最低工資標準要先進行協商,然后由政府頒布,協商過程中三方辯論激烈。上海市的三方協商機制作用之一是化解和預防重大的勞動糾紛,在一些欠薪案件中,三方協商機制有效地化解了沖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正式的三方協調會議,在我國還存在一些準三方協商機制。第一種是多方參與的協商制度,例如山東省的“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參與會議的除了黨政機關、工會外,還有團委、婦聯、人行等機構和組織。類似的還有“發展家庭服務業促進就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第二種是政府與同級工會組織召開的聯席會議,這些會議由省長或主管副省長主持召開,議題廣泛,涉及從支持工會工作到就業、最低生活保障、民主管理等多方面問題。與三方協商機制不同的是,這些聯席會議一般沒有雇主協會的代表參與。
四
我國三方協商機制的建設明顯處于發展的最初階段。[20][21]它沿襲了政府主導的協調勞動關系的傳統方式,在勞方和資方的代表組織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職能過窄,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不能有效協調勞動關系主體的不同利益。
在我國的三方協商機制中,政府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三方會議“由政府部門的執行主席牽頭(主持會議)”,辦公室設在政府部門。因此,三方會議的工作,從計劃到落實再到最后的總結,都由政府部門主導。三方協商會議討論的議題,如集體協商、和諧企業、勞動監察等等,都是政府所定義的“勞動關系”工作,也就是說,這些都是三方辦公室所在的司局要開展的相關工作。在多方或政府與工會的聯席會議中,政府的主導性更加明顯,既沒有資方代表參與,勞方代表的人數與政府人員相比也少得可憐。
政府的主導性得以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勞資代表組織的不完善,其獨立性與代表性都受到了質疑。[22]《三方協商促進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公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參與協商的“代表性組織”是指“享有結社自由權利”的雇主和工人組織。正是從這一前提出發,勞動問題專家將結社自由視為三方協商的基本條件。雇主和工人組織只有在具有“代表性”的前提下,才能夠代表他們所代表的群體的利益行事,三方協商的結果才能夠經由這些組織貫徹執行下去。
然而,我國的工會依然保留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基本職能沒有進行改革。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國家實行全國統一的勞動制度,勞動者的就業待遇和就業條件由國家統一決定,使工會喪失了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必要性,僅成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這一角色的基本定位并沒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發生改變。在2008年修正的《中國工會章程》中,仍然保留著“橋梁和紐帶”的用語。雖然工會宣稱自己“是會員和職工利益的代表”,但基層工會的建立絕大多數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各級工會領導人的任免絕少取決于會員的意志。有些工會主席雖然通過選舉產生,但選舉仍流于形式。在工人與企業的勞動爭議中,還能見到在一些案例中工會主席充當企業方代表的事例出現。陳峰教授用“四方”來表達工會與會員關系的割裂,很具有說服力。[23]
在國家三方協商機制中僅由企聯/企協充當雇主組織的代表也是不足的。企聯/企協的成員多為國有企業,其領導人員多為退休的主管過經濟工作的政府官員。由于其性質確定為“非營利的全國性社會團體法人”、“國際雇主組織的中國唯一代表”,其資金來源受到很大限制,影響了它的協商能力。多年來,另外一個組織——工商聯一直在謀求成為雇主組織的代表,能夠參加國家三方會議。在2011年5月召開的“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第一次執行主席會議”上,三方已經原則上同意增加工商聯作為雇主代表參加三方會議。工商聯的加入能彌補企聯在私營企業上的代表性,但對于成員企業的影響有限,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雇主組織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另外,我國的三方協商機制已經從國家到街道在各個層面得以建立,但在縣以及縣以下的行政單位中,雇主組織普遍不健全,一些地方不得不用國資委、經貿委、個體企業協會等組織來代替。這樣的“資方”代表如何與政府和工會進行平等協商呢?
工會或資方代表性不足會直接影響到三方協商機制的有效性。這一點世界各國均是如此。英國之所以對三方合作失去信心,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國的總工會“不能成功地傳達”三方協商的結果。[24]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工人組織的代表只有韓國總工會的人員,事實上,韓國在當時還有一個規模較小但比較具有戰斗精神的工會聯盟——韓國工會聯合會。由于不能參加三方協商,韓國工會聯合會對社會對話多持批評態度,直到1996年受邀參加韓國的產業關系改革委員會后,其態度才發生轉變。承認韓國工會聯合會是一個社會伙伴這一舉措被韓國學者認為是韓國邁向真正的社會對話的一大進步。[25]
在我國也不斷有學者質疑三方協商機制的實際成效。在國家層面上的三方會議,會期只有一天,開會的次數也沒有按照最初的設計開滿過四次或三次的會議。[26]從會議紀要看,這為期一天的會議每次都有三方領導人的講話、工作匯報以及人員變動的說明,留給三方進行討論和磋商的時間非常有限。以《勞動合同法》為例,在國家三方會議第十次會議的紀要中這樣總結道:“三方積極主動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好有關立法工作,在修改《勞動合同法》草案、起草《勞動爭議處理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媒體的報道卻是“兩大外商組織——歐盟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同時將各自的建議和意見遞交給全國人大”,并且威脅“撤資”。國內的企業在無法發出聲音的情況下,紛紛規避法律:華為公司出現了“辭職門”,中央電視臺解雇了大批臨時工,勞務派遣意外地在《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后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這說明三方會議就《勞動合同法》的協商并不那么有效。
我國三方協商機制的另一個問題是協商會議的職能過窄。在2008年制定的《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制度》中具體說明了三方會議的工作內容,包括:推進和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企業改制改組過程中的勞動關系;企業工資收入分配;勞動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勞動爭議的預防和處理;企業民主管理;工會組織和企業聯合會組織的建設以及其他問題共七大項。一些重要的勞動關系問題并沒有列入其中,例如就業問題、群體性事件的處理等等。在三方會議的實際運作中,這些列入“制度”的項目還有很多項沒有進行實質的協商。例如,在勞工標準中,除最低工資標準在某些地方的三方會議中進行過協商之外,其他如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保險福利待遇、職業技能培訓等均無所作為。
從國家三方會議參會人員的構成中也能反映出協商會議的職能過窄的問題。政府方的參會人員在前12次會議中主要是三方協調辦公室所在司局的人員。當三方辦公室由勞動工資司更改為勞動關系司時,參會人員也隨之變為主要是勞動關系司的人員了。在制度設計上,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除勞動關系司之外應該有“辦公廳、法規司、調解仲裁管理司、勞動監察局、國際合作司等相關司局負責人”參加會議,但實際情況是從沒有出現所有這些司局負責人同時出席會議的情況。[27]結果是,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不僅由政府主導,而且僅僅由政府中的勞動行政部門主導,進而由其中的勞動關系司主導,其效果可想而知。
如果對比國外的情況,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更加明顯。有些國家最主要的三方協商組織名為經濟與社會協調委員會或者類似的名稱。這類組織一般處理的是比較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例如,在奧地利,社會對話的領域包括收入政策、社會政策、物價與工資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社會福利、勞動法、工作創造與培訓、就業政策等。這些廣泛的經濟社會問題包括以下幾類: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以及經濟增長問題;經濟結構的轉變問題;工資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及財政政策;就業政策;性別平等;教育和職業培訓;生產率與經濟競爭力;稅收和財政政策;社會福利、社會保障與社會保護;處理來自外部壓力要求改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例如向市場經濟轉移、地區一體化、結構調整和減低貧困的政策等。[28]
很顯然,我國三方協商機制所存在的問題根植于我國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對勞動制度進行全面改革,要對一些勞動法律法規進行修訂。這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然而,即便是在不改變現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我國的三方協商機制也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教訓進行某些改革:
首先,適當調整三方會議辦公室的設置單位,可以考慮將其放到具有綜合行政職責的部門。因為勞動問題的解決可能涉及的不僅僅是勞動行政部門,還可能涉及財政、教育等多個部門。目前,該辦公室全部為兼職人員,應當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撥付專門的經費,設立獨立的人員編制。這樣,也可以將三方協商的主題適當放寬到就業、工資等勞動問題上。
其次,對于政府在三方協商中主導性過強的問題,可以參照日本和韓國的經驗,讓律師或者學者充當公眾利益的代表,與勞方和資方的代表進行討論和研究,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咨詢意見;也可以參照歐洲某些國家的做法,強化三方機制的研究能力。在開會討論某些問題之前,應組織專家學者進行調查研究,為三方的協商提供準確的事實和材料。
再次,適度強化高層面的三方協商功能,沒有必要要求在各個層面都建立三方協商機制。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較大,應當允許各地進行嘗試,不必要求所有地方都遵循同一模式。
最后,在國家層面上,參加三方會議的人員沒有必要事先作出明確的規定,應該根據所討論的議題由各方自行確定參加會議的具體人員。如果各方能就有權參加投票的人數達成一致,對于各方參會人員的數量限制就沒有必要遵循對等的原則。
總之,我國的三方協商機制尚處于發展的最初階段,但它邁出了走向社會對話的第一步。我們相信,協調勞動關系主體利益沖突的社會需要必將促使它不斷走向完善。
[1]國際勞工組織:《國家一級有關經濟與社會政策的三方協商》,國際勞工大會第83屆會議,報告六,國際勞工局,日內瓦,1996。
[2][5][13][24]Treblicock,Anne(ed.).Tow ards Social D ialogue: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N ational E-conom ic and Social Policy-m aking.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94.
[3]Ludek Rychil,Rainer Pritzer.“Social Dialogue at National Level in the EU Accession Countries”,wo rking paper,ILO,Geneva,2003.
[4][7]Suzuki,Akira.“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union Wage Coordination and Tripartite Dialogue in Japan”.Harry C.Katz,Wonduck Lee,and Joohee Lee.Ithaca(eds.).The New Structure of Labor Relations:Tripartism and Decentralization.New York:ILR Press,2004.
[6][14]哈里·C·卡茨:《集體談判與產業關系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
[8][9][15][25]Choi,Young-Ki.“Experiencesof Social Dialogu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the Republic of Ko rea”.working paper,ILO,2000.
[10][28]Ishikawa,Junko.Key Features of N ational Social Dialogue:A Social Dialogue Resource Book.ILOGeneva,2003.
[11]Dunlop,John T.Industria l Relations Systems.Boston,Ma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
[12]約翰·巴德:《人性化的雇傭關系——效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6][20]喬健:《中國特色的三方協調機制:走向三方協商和社會對話的第一步》,載《廣東社會科學》,2010(2)。
[17]全國總工會研究室:《2009年工會組織和工會工作發展狀況統計公報》,載《中國工運》,2010(5)。
[18]汪洋:《我國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現狀、問題及改革思路》,載《經濟研究參考》,2006(44)。
[19]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辦公室編:《信息交流》第15期。
[21]Shen,Jie,Benson,John.“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 China:A First Step towards Collective Bargaining”.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2008,147(2/3).
[22]Simon Clarke,Chang-Hee Lee.“The Significance of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 China!”.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08,Vol.9,No.2(Winter).
[23]Chen,Feng.“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 Processof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10,201.
[26][27]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辦公室編:《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紀要》(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