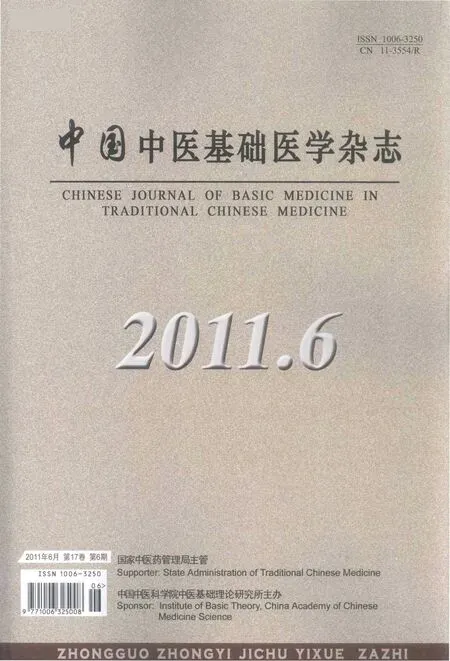從《中醫病理學概論》看任應秋“辨證論治”學術思想*
李 菲
1957年2月,上海衛生出版社出版了任應秋先生編著的《中醫病理學概論》一書。這本書主要針對中醫的病因學、病機學以及辨證理論從“病理學”的角度進行了描述,并介紹了中醫診療特色。任老在書中十分詳細地闡述了他的“辨證論治”觀,這些觀點也是“辨證論治”作為中醫學主要特點的學術基礎。
該書的問世,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1954年,國家對中醫提出了“系統學習,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針,強調了西醫學習中醫的重要意義。任應秋在上海就讀期間,曾受誨于“中醫科學化”的倡導者陸淵雷先生,對陸氏之談大加稱允,遂效其法,以“中醫科學化”為己任。該書致力于對中醫的辨證論治過程作出科學化的病理學描述,使得中醫理論更加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便于西醫學習中醫,也是對于中醫深奧理論的簡要詮釋。
1 “辨證論治”的概念:辨識性質
任應秋這樣定義“辨證論治”的概念:“中醫辨證論治的方法,是依據機體病理變化的若干證候群,辨識為某種性質的證候,而確定其治療,因為它認為構成證候的證候群,就是病理機轉的具體征象,而證候就是病理機轉征象的總和,也就是對疾病總的觀察和認識,根據總的觀察、分析和認識,進行治療,便是辨證論治。[1]”認為所謂“辨證論治”辨的是“證候”,而證候是對疾病性質的一種描述方法。而辨證論治實際上就是將臨床搜集的各種信息的總和——“機體病理變化的若干證候群”進行“辨識”,最終統合成為一種疾病的“性質”的過程。而他所描述的“證候”,也更加偏重于表示疾病的“性質”,與我們今天將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等多重因素組合成為一個證候的方法有所區別。
2 辨證論治的范疇:八綱辨證
任應秋認為:“中醫的辨證論治,是注意于生體病變的全身證候,務使身體的生活機能恢復其正常狀態,也就是說要把病體整個病理機轉一變而為生理機轉。例如體溫放散過少,以致郁積成熱的(發熱無汗),便發汗以解熱,體溫形成多,以致放散不及的(發熱自汗),便涼解以平泄;生活機能過于亢進的(陽證熱證),消之使不亢進;生活機能過于衰弱的(陰證寒證),溫之使不衰弱;全身細胞生活力減退的(陽虛),便宜興奮,即所謂‘溫經回陽’;全身細胞原形質缺損的(陰虛),便宜補益,即所謂‘養陰補血’,其間斟酌損益的微妙處,全在這辨證論治。[2]”由此可見,任應秋將辨證論治中“證”的范疇主要界定在“陰陽表里虛實寒熱”的范圍之中。該書第五章的題目為“辨證論治的體系”,又分為“陰陽的含義”、“表里的含義”、“寒熱的含義”、“虛實的含義”4部分內容介紹八綱的主要內容。
對于八綱在辨證論治中的意義,他做出了這樣的總結:陰陽在醫學上的應用,就在窺測其兩種(陰陽)機轉偏盛偏衰之所在而趨于平衡。抓住機體抗力及時抵抗疾病,隨表而出,是表證以解表為第一要義的所以然。里證有二義,即病變的亢進和機體內在器官病變。證候上的寒和熱,以寒來代表生理的生活機能的衰減,熱來代表生理或病變機轉的亢進,已多半不屬于物理作用的范圍。虛實是限于辨證論治而言的概念,虛多半是指生理機能(正氣),實多半是指病理變化(邪氣),可以作為臨床治療的主要依據[3]。由此可見,“八綱”的實際意義,是用以描述疾病基本的盛衰變化等特點,是從病理學的角度對疾病性質的認識。因此,中醫學的辨證論治學問就具有“中醫病理學”的基本含義,而八綱就是中醫辨證論治的主要范疇。
3 辨證論治的實證:六經界說
任應秋在“辨證的體系”的章節中特別增加了“六經的界說”一節內容,將《傷寒論》的六經辨證體系,作為八綱的實際運用舉例,更加深入地對八綱的具體運用方法作了介紹。
他認為:“‘六經’是中醫辨證論治的綜合概念,也就是陰、陽、表、里、寒、熱、虛、實‘辨證’的綜合產物。[4]”“六經辨證”,是綜合運用“八綱”進行臨床診療的一個實例。他說,“為什么說它是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的綜合產物呢?因為在臨床辨證時,太陽、陽明、少陽都為陽性疾病,太陰、少陰、厥陰都為陰性疾病,太陽、陽明、少陽都代表熱性疾病,太陰、少陰、厥陰都代表寒性疾病,太陽、陽明、少陽都屬于實性疾病,太陰、少陰、厥陰都屬于虛性疾病。這陰、陽、寒、熱、虛、實之中,又有在表在里和在半表半里的不同。[5]”
對六經病進行簡單的性質分類之后,他還分別對“六經病”的主證逐一進行了病理學闡釋。認為太陽病是表證,是一切疾病前驅的先兆證。陽明病,是體液耗散的結果。少陽病階段病理特點是過敏,是病邪可出可入的階段。太陰病是消化器官病變機轉逐漸走向衰減的胃腸肌遲緩的表現;少陰病就是心臟和神經衰弱的表現。體溫低落而“發厥”,這是“厥陰病”的主要表現。而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六經是由表、里、寒、熱、虛、實六變所形成,也就是‘六變’在臨床上錯綜復合出現時的6個界說,也就是范圍‘六變’的6個系統,它的性質是經常變動的,而不是靜止的,在臨床上他幫助我們認識疾病有極大的便利,通過它可以認識整個病變機轉的性屬。[6]”
作者對《傷寒論》“六經”的界定,具有重要的辨證意義。在其對傷寒六經病諸證候進行的“病理學”詮釋中,簡明地闡述了中醫的證候學說與西醫學病理科學之間的對應關系。他繼承了陸淵雷將中醫科學化、實質化、病理化的研究方法,開始對中醫的“證候”進行了西醫病理學模式的描述,是中西醫匯通的另一個高潮,也是在中西醫結合方面的一大創新。
任氏這樣定義了“病理學”的概念:“病理學是究明疾病的發病條件,發病經過及其結果的學問,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體。人體是生理的生活現象和病的生活現象的統一體。人類隨著年齡的增加,病的生活現象勝過生理的生活現象時就成疾病。[7]”因此,他對“病理學”的認識是寬泛的,并沒有摻雜中西醫學間的分別。在他看來,西醫學有西醫病理學,中醫學也有獨立的中醫病理學。因此任應秋將該書命名為《中醫病理學概論》,而實際上,這基本上就是一部研究中醫診療過程和方法的“辨證論治”著作。
4 辨證論治的應用:癥狀審辨
任應秋在該書的“癥狀的審辨”一章中說:“中醫的診斷和治療,不可能對病,而是對證,尤其最主要是對證候……但證候是建筑于各種證狀上的,要想辨識清楚證候,便得先行把各種不同和類似的證狀審辨清楚,才能給辨識證候打下基礎。[8]”本章中,他介紹了發熱、惡風、惡寒、汗等20多個主要癥狀診斷與鑒別診斷、辨證方法,并對其進行了病理學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證(癥)狀”的臨床辨析過程時,他使用了“審辨”一詞,其中包含了“審查癥狀”和“辨別證候”兩個層面的含義。這也是中醫學的重要特色。西醫學的病理學描述是以單一癥狀為分析對象的,每一個癥狀都擁有獨立的病理學描述,各自并無嚴格意義上的交合,其治療也是針對各個癥狀進行的。而中醫學對疾病的認識則與此完全不同,癥狀只是作為對辨證論治的基本素材,真正對疾病的認識要通過對全部癥狀的綜合提煉,才能得出辨證的結論。因此,從中醫學的角度認識“癥狀”,對于每一個癥狀的認識都是一次辨證論治的過程。
任應秋先生針對這一中醫學的重要特色,進行了精致而詳盡的敘述。
5 辨證論治的優勢:發展變化
通過對《中醫病理學概論》一書中“辨證論治”觀點的解析不難看出,該書的立意可以算作是檄文一類,也是任應秋先生在面臨西醫學對中醫學的沖擊,為“中醫學不科學”的說法進行辯護而著述,有明顯時代烙印的著作。
他以“腎炎”為例,闡述了其認為西醫學并不全面的觀點:“如有些腎臟的疾病,在病理形態學上說在腎小管、腎小球方面沒有病理的改變,但是病人有蛋白尿,他們叫這一類情形為官能性的改變,但是究竟這些官能性的改變本質是什么,從細胞病理學上便找不到答案了。原因就是在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病理學,忽略了疾病是人這個有機體所表現的現象之一,并且是在發展著的、變動著的現象,決不能把它從整個有機體孤立起來加以片斷的了解,更不是僅僅從病理形態學上考察就能有全盤的了解。所以時至今日,用傳統的切片、染色等方法來研究疾病的形態學,幾乎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對于疾病的治療,卻表現出異常的貧乏。[9]”
同時,他又指出了中醫學在整體觀察、辨證論治的基礎上所體現出來的全面、系統的絕對優勢,強調了“證候”在“中醫病理學”中的重要意義:“祖國醫學卻把證候認為是機體生理和病理斗爭不同的反應,凡證候愈猛,證明生理與病理斗爭的激烈,生理的戰斗力亦愈提高,這時病人自覺證狀的痛苦雖甚,并不等于疾病發展到危險階段;相反的疾病日久不愈,證候的自覺減輕,痛苦不大,這實質上是生理的戰斗力日趨下降,使病理占了優勢,病人身體就會日漸衰憊,因體內物質基礎消耗太大,這才使病步入危險階段……疾病是隨時發展著的,變動著的,證候也是極復雜而變化的,這樣證候與治療密切配合的病理知識,有它現實的實踐意義,能夠通過實踐的知識,便有它不可磨滅的真理存在,更有它不斷變革、升華發展的前途。[10]”
可見,任應秋先生對中醫學“辨證論治”的內容極為重視,認為這是中醫學的一大特色而努力發揚。由此我們也應該注意到,50年代學者們所提出的“證候”的概念與今天的差異,正應該溯本求源,研究這一差異形成的過程和概念演變的規律。
[1]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45.
[2]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32.
[3]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46.
[4]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42.
[5]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42.
[6]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46.
[7]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1.
[8]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47.
[9]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序言1-2.
[10] 任應秋.中醫病理學概論[J].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序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