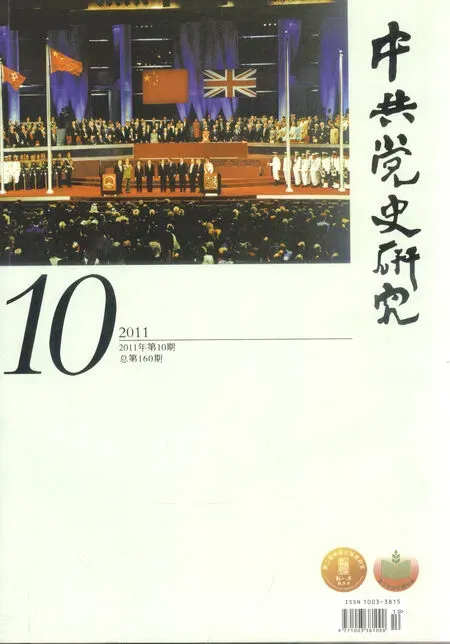從抗戰時期國民黨處理中共問題的政策思路看國共磨擦
同書琴
抗戰時期的國共關系一直是一個研究熱點,但以往的研究,或多從中共黨史的角度分析,或多將論題集中于國共合作。本文擬以國民黨解決中共問題的政策為視角,以三次較為嚴重的軍事磨擦為中心,探討抗戰時期國民黨為何一再挑起國共磨擦及其事后的應對處理,以期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進行另一角度的思考。
一、從力促國共合并到防共限共
(一)力促國共“溶成一體”
眾所周知,國共磨擦是貫穿于抗戰始終的。不過,在抗戰初期,國共關系總體上還是比較融洽的,雙方在軍事上頗多配合,也幾乎沒有發生引人注目的沖突。這種融洽關系與日寇大舉入侵、抗戰前線吃緊有關,同時,也與蔣介石在這一時期力促國共合并的政策取向不無關系。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方針,卻沒有令其根本放棄取消中共組織、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政治意圖。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中。該決議案提出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最低限度之辦法”是徹底取消紅軍與蘇維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傳、根本停止階級斗爭等①參見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435頁。。而此前數日,中共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作出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并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等四項政治承諾②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385—386頁。。這是中共為盡快促成國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原則性讓步,卻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國民黨的“最低限度之辦法”。國民黨人歷來以正統自居,盲目自大,又不能理解共產黨人為民族大義與抗戰大局而甘愿妥協的博大胸懷,難免視中共的重大讓步與真誠合作為“輸誠”①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434頁。。蔣介石在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講話稱:“共產黨過去因為不察國情,企圖消滅本黨,以致遭受許多事實的教訓。他們察前思后,一定已經知道他們以往為中國革命造成多少嚴重的錯誤,使中國革命力量無故受了多少的犧牲,他們當不是全沒有理智的,現在中國的環境怎么樣?國際形勢怎么樣?我想他們總能度勢識時,履行他們對本黨的宣言。”他明確要求共產黨“一定是要受本黨的領導”,而且要“消融于三民主義之下”。②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8頁。加之這一時期抗戰處境艱難,蔣介石便設想將國共兩黨組織合并,“溶成一體”③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262—263頁。,將共產黨完全納入到其黨統和法統之下,通過政治途徑根本解決中共問題。
1937年6月廬山談判中,蔣介石提議“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干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目之干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關于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討論決定。”“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以達成兩黨徹底合作。④《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514頁。中共積極回應國民黨的合作誠意,建議“國共兩黨合作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或“由兩黨組織各級的共同委員會來進行兩黨合作的事宜”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第700頁。。不過,中共的建議與蔣介石的想法顯然相去甚遠,中共注重在合作中保持自身的獨立性,蔣介石強調的是“溶成一體”。為此,蔣介石于1938年12月6日、12日及1939年1月19日、20日先后數次約見周恩來等,談兩黨合并之事,一再表示不同意用跨黨辦法來處理國共兩黨合作關系,說:“中共既然實行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并成一個組織。”“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第5—7頁;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第269—270、272頁。
理所當然地,蔣介石“溶成一體”、組成一個大黨的建議被中共于1939年1月25日復電正式拒絕了。
(二)國民黨人的防共心態
就在蔣介石力促兩黨“溶成一體”的時候,國民黨內卻有人對中共處處加以防范。1938年6月,國民黨人張允榮擬訂“今后關于華北共黨之對策”四條,提出應“在晉及晉東南建立華北軍事根據地……此對日對共均有極大意義與作用”;“在華北受共軍摧殘而失敗歸來之將領,應設法優待,以勵來者”;宜“深入民間,加強組織,撤散其(指中共——筆者注)外圍,綱[網]羅中間人材。對于民間武裝,更應加強爭取,如幫會之運用,舊日民間武裝組織之吸引等……即如現在之冀魯交界處共黨勢力尚弱,正宜在此等處所推行此項政策”等建議,國民政府軍委會即令軍令部“就主管范團[圍]參考核辦”⑦《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2),第7—8頁。。1938年12月,陳立夫指示河北省主席鹿鐘麟在民運工作中“總以防止共產勢力之擴張為主”⑧《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2),第11頁。。陜西省黨部也一直在做防范共產黨影響的各種工作⑨參見楊奎松:《國民黨走向皖南事變之經過》,《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4期。。
如此防范,顯然反映了國民黨人對中共的不信任態度。事實上,蔣介石力促國共合并,僅僅是他通過政治途徑解決中共問題的一個策略。多數國民黨人,包括蔣本人在內,不信任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真誠合作,即使是在抗戰初期這一國共關系史上較為融洽的時期。時任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幾次報告蔣介石,認為中共“一切絕對無誠意,不過藉此擴張其勢力”①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90頁。。蔣介石也深感“共黨乘機擴大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②轉引自金沖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4頁。。這種不信任心理就是在國民黨官方文件中也不難發現。如1937年11月,國民黨中央特種研究委員會報告稱,對蔣介石關于今后要對中共“一視同仁”的講話“敬謹接受”,“惟為防止基層黨政機關及人民誤解起見,應由國民政府發表文告,在我國境內,無論其為何人及其何種名義,凡有私自組織軍隊,企圖割據地方;違反國家紀綱,擾亂社會秩序等情事,皆為國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務望均能徹底覺悟,服從法令,遵守紀律,精誠奉行三民主義。誠能如此……政府當一視同仁”③《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2),第3頁。。可見,對中共的不信任確是當時國民黨人的一種普遍心態。
這種心態,當與國共兩黨深深的政治歧見大有關系。國共之間因信仰、綱領及利益等方面的不同乃至對立而形成的政治歧見是如此之深,長達十年的殘酷戰爭和反共宣傳可見一斑。這一切,無疑會在國民黨人心中刻下難以磨滅的烙印。時至于此,國民黨被迫聯共抗日,但國民黨人心中這種深深的烙印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這些動輒以黨國代言人自居的國民黨人,恐怕難以輕易相信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敵在一夜之間歸順國民黨的誠意。
(三)走向防共限共,磨擦日漸激化
國民黨人的不信任態度及由此導致的防范心理,在中共斷然拒絕兩黨“溶成一體”的建議后,無疑被有力地強化了。此后,蔣介石和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
當然,促成這一變化的根本因素,應該說還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創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迅猛發展。以八路軍為例,1937年8月改編時4.6萬人,到年底發展到8萬人,1938年底進一步擴展到15.6萬多人④參見柳茂坤:《八路軍發展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457頁。。其活動區域,由陜北入山西抗戰,繼而出擊河北、綏遠,再入山東,在敵后創建了一個個抗日根據地,建立起名義上隸屬于中央政府、實際上獨立自主的地方民主政權,動員群眾,建立武裝,在華北敵后取代國民黨,成為除日本侵略軍以外最具影響的一支力量。
中共軍事力量、活動區域一年之間擴展如此迅猛,在客觀上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人。按照他們的邏輯,既然國共合作抗戰,中共及其軍隊自應服從中央,全國政令軍令統一;而中共既不愿“溶成一體”,又要獨立自主地發展,不受控制地四處擴張,不是恰恰證明了中共對合作絕對無誠意嗎?“共產黨的企圖,(就是)在抗戰期間,利用統一戰線的口號……盡量發展勢力”,⑤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376頁。國共合作不過是其發展勢力的一種策略而已。國民黨人的不信任態度和防范心理,再一次被大大地強化了,放大了。
既然對中共的合作持這種心態和看法,眼見中共以獨立自主的姿態迅猛地發展,國民黨人的神經自然高度緊張,蔣介石驚呼:“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發展”⑥轉引自金沖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第14頁。。于是,限制中共力量進一步擴展自然成為蔣介石和國民黨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了。
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國民黨對中共政策的轉折點。會議初始,蔣介石就基于共產黨勢力迅猛發展的現實,檢討國民黨自身不足,以激勵國民黨人的自省與發奮,更希望找到抑制共產黨的辦法。他明確提出,對中共必須“以嚴正的態度來教訓管理他”,希望國民黨拿出“有進無退的革命辦法,來對付他”。出于對共產黨發展的擔憂與恐懼,相當一部分代表對蔣介石的建議予以響應,紛紛自省,討論辦法,國民黨中宣部還介紹了與中共斗爭的經驗。①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09—410頁。最后,根據大會代表們的要求,經蔣介石同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迅速擬訂《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并下發執行,還進而要求各地各部門分別擬具適合本地本部門需要的應付異黨之對策與辦法。于是,軍事委員會之《處理河北問題六項辦法》、宣傳部之《糾正共黨不法行為宣傳辦法》、戰地黨政委員會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陜西省政府之《陜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防共限共法規文件紛紛出臺。
一邊是中共力量獨立自主地迅猛發展,一邊是日漸強化的防共限共措施,“縱因此而發生磨擦,設非出于本黨之過分與不是,亦應無所避忌”,②高軍等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資料選輯》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8頁。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進入1938年以后,國共之間就磨擦漸起了,如陜甘寧邊區一些地區因出現雙重政權而沖突不斷,南方因共產黨人和新四軍留守人員問題也常起糾紛,往往是“一面解決又一面逮捕”③湖南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湖南地下黨歷史文獻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頁。。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后,防共限共辦法紛紛實行,本就磨擦不斷的國共關系不可避免地更趨緊張,由一般性的查沒報刊、封閉社團、逮捕人員,迅速發展到軍事沖突的地步。秋冬以后,軍事沖突在頻繁和激烈的程度上日甚一日④參見費正清著、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17頁。,最終在1939年冬1940年春,在陜甘寧地區、山西和太行山地區形成了大規模的嚴重軍事沖突。
但除了在平江、確山等少數幾個地方使中共遭受較大損失外,國民黨在它挑起的這場沖突中并沒有撈到多少便宜,反而一再兵潰地失。在陜甘寧邊區,國民黨襲占了淳化等五縣,卻丟掉了綏德等五縣;在山西,閻錫山妄圖以武力奪回對新軍(即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的控制權,制造晉西事變,反而使新軍大部公開脫離閻的統轄,事實上成為八路軍之一部,還丟掉了晉西北的地盤;在太行山地區,石友三、高樹勛、朱懷冰等部均被擊潰,殘兵被趕出河北,退往山東、河南等地。結果,國民黨失掉了在華北的優勢地位。而后,中共主動提出談判,閻錫山、衛立煌⑤這一時期的國共磨擦主要表現為“地方性”的。衛立煌、閻錫山分別為第一、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負責冀省及魯北、晉察冀的戰事指揮。無奈,分別與中共達成休戰協議,劃定各自活動區域,國共激烈的軍事磨擦告一段落。
二、局部剿共政策及對其后果——皖南事變的處置
(一)局部剿共政策,致生皖南事變
國民黨千方百計防共限共,不惜挑起國共激烈的軍事磨擦,卻導致中共力量更加壯大。這一結果恐怕是國民黨人始料未及的,其內心的沮喪與不甘可以想見。于是,晉西事變后不久,在日軍攻勢已停的情況下,國民黨內主張用軍事手段解決中共問題的呼聲日漸高漲⑥楊奎松:《國民黨走向皖南事變之經過》,《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4期。。蔣介石也躍躍欲試,自信具備了“抗倭剿共,盡可雙管齊下”的實力,只是,在一番審時度勢后,他明白此時還“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勢”和“局部斗爭”⑦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18頁。。
考慮到華北八路軍已占優勢,國民黨難有作為,蔣介石和國民黨便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華中地區(主要指江蘇和安徽兩省)。該區位于中國心臟地帶,又系交通樞紐,為國民黨歷來所重之地。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定“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后,新四軍在這一帶迅猛發展,到1940年底,主力部隊已近9萬人,相較于剛組建時的1.03萬人,增長8倍以上⑧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43、467頁。。國民黨人深為恐慌,從1940年春天起就加緊制造軍事磨擦,繼而在蘇北蘇中形成了尖銳的對峙局面①參見費正清著、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2部,第723頁。。
為避免在華中重蹈華北覆轍,國民黨想出了一個方案,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地區,并據此擬訂了與中共談判的《中央提示案》②皖南事變編纂委員會編:《皖南事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第79—80頁。。在國民黨看來,這一方案既可保住華中地區,又可免去與中共軍隊雜處致生磨擦,還迫使中共軍隊與日偽軍直接交鋒而消耗其實力,可謂一石多鳥。1940年7月,國共兩黨展開了以劃分作戰區域為中心議題的談判,國民黨態度強硬地要求中共接受《中央提示案》。中共雖不反對軍事劃界的辦法,卻不能接受國民黨劃定的狹小區域。但為顧全抗戰大局,中共作了一些讓步,答應皖南新四軍“遵令北移”③《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頁。,但對國民黨其他要求毫不讓步,談判在秋天陷入僵局。
在此前后,蘇北接連爆發了兩場激烈的大規模軍事沖突。先是在10月間,蘇北最主要的國民黨軍韓德勤部發動黃橋戰役被新四軍一舉擊潰,損失慘重;旋即,新四軍打響了以消滅韓德勤部為目標的曹甸戰役,盡管未達到作戰目的,卻進一步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人的神經。國民黨內以武力“清剿”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的主張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占據支配地位。④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24頁。
不過,就蔣介石本人而言,他內心里還是希望盡可能避免采取軍事解決的辦法,也就是通過政治途徑兵不血刃地將八路軍、新四軍趕過黃河去。因此,他在下達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北移的命令后,又于1940年12月底接見周恩來,以“極感情的神情談話”,提到“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難的日子”,勸說“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太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我弄得沒有辦法,天天向他們解釋”。“我難道愿意內戰嗎?愿意弄塌臺嗎?現在八路新四軍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么要自相殘殺?”“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⑤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21—122頁。。
但在武力“清剿”已成為國民黨內主流意見的情況下,蔣介石畢竟開始準備軍事行動了。在他批準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后,第三戰區顧祝同軍開始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為武力驅趕新四軍北渡做準備。國民黨人沒有料到的是,新四軍皖南軍部在規定的最后期限未到以前,就開始“遵令北移”了。只是,由于擔心受到日寇和國民黨軍的阻擊,新四軍沒有直接向北渡江,而是選擇了先向南再伺機向東向北的迂回路線。這條路線與北渡命令在方向上南轅北轍,所以當新四軍意外地鉆進了國民黨軍正在形成中的包圍圈后,顧祝同想當然地認定“葉挺、項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而是“企圖竄據蘇南,勾結敵偽,挾制中央”,于是“決予進剿”,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2),第531頁。皖南事變就這樣發生了。可見,皖南事變的發生雖有一定偶然因素,但卻與國民黨的局部剿共政策直接相關,或者說,是這一政策直接導致的后果。
(二)定性軍紀問題,處置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共關系驟然緊張。蔣介石雖無心理準備,卻不得不設法處置應對。國民黨高層經過幾天的緊張磋商,于1941年1月17日傍晚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了一道命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挺著即革職,交軍法審判。”軍委會發言人同時發表談話,稱“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⑦《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70、171頁。筆者分析,這一處置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其一,新四軍“抗命叛變”,應予撤銷番號之懲處;其二,事變的責任在新四軍,國民黨軍“進剿”是維護軍紀的正當行為;其三,事變只是純粹的軍紀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涉及共產黨,不涉及八路軍。這里,蔣介石采取了一種兩面手法,一方面刻意表現強硬,撤銷新四軍番號,打壓中共;一方面又不涉及八路軍,對事態加以控制,以避免全盤破裂。應該說,這一處置展現了蔣介石老謀深算的政治手腕。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和以黨國領袖自居的蔣介石是不可能認錯的,板子既然打了,便要證明打得對,所以蔣介石必須表現強硬,強行撤銷新四軍番號;但他清楚地知道此舉有可能導致兩黨關系破裂,而這是抗戰大局所不容許的,因而必須控制事態,是以將事件定性為純粹的“軍紀問題”。
然而,中共堅決不接受蔣介石對事變的處置。正在忠實執行北移命令的新四軍不但被無情剿滅,還被誣為叛軍,中共當然不能就此罷休。但為抗戰大局,中共選擇了“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策略,發動了政治大反攻,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了與重慶1月17日命令針鋒相對的命令:“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并向國民黨提出以“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為核心的“十二條”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1、775頁。,同時,揭露事變真相,發動輿論攻勢,組織全國性的抗議運動。
中共的政治攻勢很快奏效。雖然在國民黨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下,中共的宣傳對一般民眾影響有限,但在國民黨內部、民主黨派和國際輿論方面引起了極大反響,令蔣介石倍感壓力。剿滅黃河以南共產黨軍隊計劃,主要是國民黨內軍事高層參與其事,其余多不知情。被中共揭破后,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孫科、張治中等或致函致電,或上書陳詞,對國民黨處理中共問題的失策表示不滿,譴責“剿共”內戰違背民心,對時局表示憂慮。各民主黨派對蔣介石也表示不滿和憤慨,章伯鈞等甚至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民主黨派與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議。海外華僑也反對分裂。國際上,不僅蘇聯反對,美英等也不滿,尤其是美蘇兩大國先后出面干預,美國甚至表示美援與國共合作互為聯系。②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下冊,第575頁;鄧野:《皖南事變之后國共兩黨的政治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這是蔣介石最為顧忌的,因為美蘇特別是美國的援助是國民黨抗戰勝利的寄托,美蘇的支持又是蔣介石提高自身及中國國際地位的重要籌碼。總之,來自各方的不滿與壓力匯集到一起,令蔣介石陷入到“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的狼狽境地③《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29頁。,加之日軍也在事變后突然發動豫南戰役,向湯恩伯部隊發起打擊,客觀上牽制了蔣的反共政策,不得已,蔣介石只得設法盡快了結。
其實,前述蔣介石對事變的處理考量就決定了他在懲處新四軍之后,必會設法息事寧人,確保國共合作不破裂。他正是這么做的。1月18日,周恩來通過《新華日報》刊出“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議題詞,蔣介石不僅在第二天就釋放了被抓的新華日報營業部主任,還下令不準以武力進入新華日報社。23日,國民黨中宣部、軍委會政治部、三青團中央團部受命指示各相關單位,對事件的說明要嚴守范圍,“此次事件……乃純粹軍紀問題,決不含政治的或黨派斗爭的意義”;“此次違抗命令,破壞軍紀者,只新四軍。各言論機關,如有評述,應以新四軍為范圍予以評述,對中共及十八集團軍可勿涉及”④《中國國民黨中宣部等頒發制造皖南事變宣傳要點電》(1941年1月23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2),第552頁。。國民黨官方輿論《中央日報》《掃蕩報》等也為1月17日命令作解釋,稱為“斬馬謖”⑤轉引自鄧野:《皖南事變之后國共兩黨的政治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甚至蔣介石于1月27日親自發表講話,公開強調“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遍。”“除此以外,并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在其中。”“現在新四軍番號既已取消,這個問題自然是完全解決,再沒有其他問題了”①《皖南事變》,第239、245頁。。蔣介石要中共接受既成事實,就此了結。但中共拒絕就此了結。
此時,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開幕(3月1日)在即,因會期恰逢皖南事變后的政治敏感期而具備了檢驗國共關系的特殊功能。蔣介石當然明白這一點,故希望“求得個妥協辦法”將國共裂痕敷衍過去,以期就此順利收場。
不料毛澤東早已洞穿蔣介石心機而先著一步,展開新一輪更強大的政治攻勢。2月25日,中共七位參政員致電參政會秘書處,重申延安軍委會發言人所提之“十二條”,聲言“在政府未予裁奪前,澤東等礙難出席”②《皖南事變》,第211—212頁。。為表“仁至義盡”,中共作出重大讓步,于3月2日又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中共這一擊恰中國民黨要害,因為中共如不出席參政會,不但不能如蔣所愿彌合國共關系,反而將國共裂痕昭示天下,國民黨將承受更大壓力。國民黨立即行動起來,動用一切力量,軟硬兼施,壓中共參政員出席。蔣介石一面厲言中共如不出席“惟有根本決裂”,一面開出將周恩來列入主席團候選人名單這一在黃炎培看來“往時求之不得”的“優厚”條件,還請出第三方面名流黃炎培、梁漱溟、沈鈞儒、左舜生等充當說客往返斡旋。③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黃炎培日記摘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第5輯),中華書局,1979年,第23—24頁。
但中共頂住了壓力,終未出席。因為,中共的“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而在于以攻勢打退攻勢”④《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30頁。,揭破事變的政治性質。結果,“蔣被打得象落水狗一樣,無精打采的講話”⑤《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225頁。,并于3月6日重申,“剿滅”新四軍并非“剿共”,表示他“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于中國歷史之中”,“而且以后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⑥蔣中正:《政府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問題的態度——1941年3月6日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演說》,孟廣涵編:《國民參政會紀實》(下),重慶出版社,1985年,第886—887頁。。參政會還在董必武缺席的情況下選董為駐會委員。蔣介石終于無計可施,無奈“退兵”了。
毛澤東說:“對于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進攻了,國共暫時緩和的可能性就有了。”⑦《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30頁。果然,參政會閉幕不幾日,3月14日,蔣介石約周恩來談話,不再提及中共軍隊北移問題,只是表示“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以緩和對立空氣。隨后,中共表示,“愿意同國民黨繼續團結抗日”。⑧《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235—236、240頁。不久,雙方恢復對日協同作戰,中共也參加了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國共兩黨因皖南事變而劍拔弩張的關系終于逐漸緩和下來了。
三、重回政治解決之途
(一)國共方案,差之千里
皖南事變后,蔣介石一度相信和平解決共產黨問題已無可能。還在二屆一次參政會期間,蔣介石就曾秘密召集國民黨參政員訓話,言明“國共總要分裂,不必懼怕”,“單從軍事上,三個月可以消滅共產黨”,但目前還不是時候,只能“政治防御”⑨《(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會議日志》,孟廣涵編:《國民參政會紀實》(下),第834頁。。此后,蔣介石開始對中共各根據地進行全面封鎖,試圖阻斷中共與外界的一切聯系,限制其發展,而對早已封鎖的陜甘寧邊區,更是構筑碉堡,以為將來推進之準備。
不久,國際局勢大變,蘇德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蔣介石和國民黨深感慶幸,倍感釋然。在他們看來,蘇德戰爭使蘇聯自顧不暇,也意味著中共失去了國際靠山;美國參戰,為牽制日本,加強了對中國援助,國民黨力量大為增強。兩黨力量,一消一長,中共在短期內不再可能危害國民黨了,國民黨的地位從此無虞矣。
蔣介石進而對中共轉變態度產生了些許期待,因為一直在蘇聯治病的林彪突然回國并大談國共合作。確實,國際大勢的劇變同樣促使毛澤東重新考慮國共關系,社會主義蘇聯與一貫反共的美英結成反法西斯聯盟,預示著戰爭可能很快結束,中共必須考慮戰后不得不繼續與國民黨合作的局面。同時,蘇聯為確保日本不會從東線發起進攻,也急于促使國共緩和關系,推動中國抗戰。加之這一時期抗日根據地在日軍“掃蕩”和國民黨封鎖下極度困難,中共開始考慮轉變對國民黨的策略。
這樣,國共兩黨于1942年7月恢復了接觸,雙方均反應積極,高度重視。蔣介石于7月、8月兩度接見周恩來,并約毛澤東會晤。毛澤東甚至一度決定去見蔣介石,因黨內反對,改派林彪前往,而林彪重慶之行也在表面上緩和了兩黨關系。①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頁。在這種氛圍下,政治解決中共問題又重新回到國民黨的政策考量范圍之內。1942年10月,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及國民黨人都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以代替全面的軍事破裂②參見黃修榮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1931—194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548頁。。中共當然希望政治解決。1942年12月24日,周恩來、林彪正式向國民黨提出中共的談判方案,要求共產黨合法化、軍隊給予編制、承認邊區現狀等。然而,國民黨仍然頑固地堅持以《中央提示案》為談判基礎。雙方條件差距太大,談判遂拖了下來。
國共兩黨都抱著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愿望,開出的條件何以差之千里?原因就在于國共雙方對“政治解決”的理解或者說期待是不同的。中共著眼于戰后爭取與國民黨建立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協商關系,重點在緩和兩黨表面上的關系,重開談判大門,因而只談大的原則,不及具體問題。③參見黃修榮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1931—1945),第548—549頁。
這當然不是自認為局勢對己有利的國民黨所希望的政治解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就中共所提條件向蔣介石呈報了書面意見書,認為中共所提四項,“系根據本黨所示寬大政策而來,其目的在對于黨政軍各方面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認為有悔過誠意。”而“本黨寬大政策之真正作用,應為瓦解中共,絕非培養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項,不能做為商談基礎。”“如須商談則應以下列原則為基礎:(1)中共不應有軍隊,其軍隊須……編遣整訓……不得再自立系統及保留變相武裝;(2)中共不應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組織須一律取消……(3)以上兩項辦到后,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④黃修榮編著: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1931—1945),第552—553頁。。稍后,1943年3月,蔣介石在其出版的新著《中國之命運》中明確表示:“我是始終主張國民政府對國內的各種意見,和各種糾紛,都要用很寬大的態度來容納,和很合理的方法來求得解決。”“只要他不割據地方,反對革命;不組織武力,破壞抗戰;只要他對于國家民族和革命建國真有利益;我不但沒有加以妨礙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發展,亦能成功。”“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是無論怎樣寬大,決不會發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辦法了。”⑤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平津支團部,1946年,第146—148頁。盡管軍令部的意見書和蔣介石的“主張”在表達方式上不相同,但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中共交出軍隊、撤銷邊區政府,然后給予中共合法地位。這就是國民黨政治解決方案的核心內容。
顯而易見,中共提出的談判條件與國民黨的希望相去太遠,沒有討論余地。盡管蔣介石注意到1941年以后中共根據地極端困難,不過他意識到徹底解決中共問題的時機仍未成熟,乃仍以《中央提示案》為談判基礎,藉以拖延,以待時機。
(二)“閃擊延安”,企圖迫中共就范
1943年5月,共產國際突然宣告解散,國民黨人大受鼓舞,不少人認為徹底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時機已然到來。蔣介石也不免幻想起來,在作出日軍很快將會進攻蘇聯的判斷后,即提出應爭取使共產黨“將軍權、政權統一于中央”。5月27日,軍委會黨政軍聯席會議專門“討論第三國際解散后本黨對中共之態度”①《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59—360頁。。6月7日,張治中與周恩來、林彪談話,說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曾研究對中共的辦法,有兩種意見:一是中共交出軍隊、政權,組織合法化;一是同國民黨合并,現等中共意見②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69頁。。6月13日,張治中再次與周、林談話。蔣介石又通過張治中,請即將返回延安的周恩來、林彪帶信給毛澤東,希望毛澤東能到重慶來“當面談一切問題”③《張治中回憶錄》,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685頁。。國民黨宣傳部門還受命鼓動其主持下的各種社會團體群起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解散組織,放棄政權與武裝,統一到國民政府軍令政令之下。至8月中旬,“各地參議會新聞、文化、婦女等團體請解散中共電,已有十多處”④《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頁。。軍事上,蔣介石也部署起來,于6月29日指示早已準備伺機奪取囊形地帶(即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的胡宗南“切實準備,但須俟有命令方可開始進攻,否則切勿行動,并應極端秘匿,毋得聲張”⑤《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66頁。。一時之間,政治軍事,多管齊下,其勢甚猛。看起來,蔣介石確實打算乘共產國際解散的大好機會徹底解決中共問題。
孰料事機不密,“閃擊延安”軍事行動計劃在7月初被中共偵知。中共當即予以揭穿,在政治上“迎頭痛擊”。短短幾天時間,中共幾番電報質問、開群眾大會通電全國,還借助美英蘇等國際力量施壓,全國上下、國內國際很快形成“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強大輿論壓力,這令以愛國抗戰相標榜的國民黨不能不有所顧忌。尤其在國際輿論和外交方面,外國記者紛紛起而質問,美蘇等國的輿論也多有抨擊;美英蘇各大使緊急開會,警告蔣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停止援助。⑥參見張培林:《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策動與夭折》,《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182頁。這一切,使蔣介石和國民黨煩惱異常,不得不“竭力否認,盡量敷衍”⑦《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9頁。,改變計劃,7月10日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日復電中共謂無意進攻,12日胡宗南下令開始撤退。
然而,中共認為這只是國民黨“稍示和緩”,它決不會就此輕易罷手,“實際上目前軍事準備決不會放松,政治壓迫亦必會加緊”,⑧《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9頁。乃決定加大政治火力,以蔣介石新作《中國之命運》為靶子,發起了一場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大批判運動。
中共對蔣著的激烈批判,依蔣之個性,其惱怒不難想見。不過,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蔣介石決不會憑一時沖動魯莽行事,必然反復權衡掂量。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開幕(9月)前后,蔣介石對“中共問題苦思甚切,以其關于各方面甚復雜而重要,不容絲毫疏忽也”,最終決定不用武力,而是“采取守勢,圍而不剿,用側面與非正式方法以制之為宜”⑨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82—483頁。。他在全會上正式表態:“中共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強調“這是這次大會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時所應遵循的原則”。○10《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上關于反共問題的指示》(1943年9月13日),彭明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5冊下(1937—194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97頁。
客觀地說,從蔣介石對軍事行動緊急叫停,到下定決心“對共不用武力討伐”,除了中共政治攻勢對其造成內外一致指責的壓力外,從根本上說,乃是這時蔣介石的基本方針仍是要通過政治手段解決中共問題。蔣介石在提出爭取使共產黨“將軍權、政權統一于中央”的同時,曾特別指示:“對中國共產黨問題,我應盡力向政治解決之途為最大之努力;在宣傳上尤不可造成政府準備以武力解決之印象。”①《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78頁。國民黨軍委會黨政軍聯席會議的討論意見也主張政治解決,盡管在解決的具體方式上有所爭論。蔣還認為,“共產黨之宣傳攻勢……乃奸黨內部動搖,故造作謠言,希挑起戰爭,以促其黨內之團結”,他們“是決達不到目的的”,②《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59、363、369頁。也就是說,自己是決不會上中共的圈套的。從蔣介石的行動部署來看,其主要目標在于壓迫中共在政治上就范,軍事行動和輿論宣傳不過是輔助手段而已,否則,就不必找周恩來、林彪,又是談話又是帶信。而中共對蔣介石的心思也看得很明白。5月30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蔣有幻想,可能對我們又要采取組織上的溶共政策。”6月4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會議,估計國民黨可能“抓緊時機采取政治解決辦法,輔之以軍事壓迫”。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68—569頁。“閃擊延安”行動曝光后,毛澤東也指出:“蔣企圖以宣傳攻勢動搖我黨,以軍事壓迫逼我就范。”④《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9頁。總而言之,應該可以斷定,蔣介石在這時確實沒有軍事解決中共問題的打算和準備。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事機泄露、中共痛擊、天下指責的情況下蔣介石“竭力否認,盡量敷衍”,并最終讓中共問題還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的原因。
中共對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作出了積極回應,表示“在蔣先生和國民黨愿意的條件下,我們愿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⑤《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6頁。。這樣,雙方逐漸恢復接觸,重啟談判。此后,直到抗戰勝利,國共兩黨的斗爭,主要集中表現在談判桌上的唇槍舌劍,再也沒有爆發嚴重的軍事沖突和磨擦了。
四、國民黨人的無奈與糾結
縱觀抗戰時期國民黨解決中共問題的政策思路,從力促兩黨合并,到防共限共,乃至局部剿共,最后重回政治解決途徑,其間雖有搖擺,但基本上還是以政治解決為主,而且始終沒有打出“剿共”招牌,即便是在皖南事變前后國共激烈對抗的時期。這是因為,抗戰時期,民族危亡,軍事解決的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抗戰大局不許,國人不許,外交不許,就是國民黨內的進步力量也不會允許。國民黨被迫聯共抗日,但兩黨的政治歧見絲毫未曾化解,中共仍是國民黨心頭大患,必欲解決而后快。無奈之下,只有政治解決了。
中共始終是歡迎政治解決的。然而,國共雙方對政治解決的理解或者說期望相差千里。中共期望的是民主合作與平等協商;國民黨的方案,不同時期側重點雖有不同,但從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最低限度之辦法”到共產國際解散后的“將軍權政權統一于中央”,無論是軍令部意見書,還是蔣介石本人在《中國之命運》中所表達的“很寬大的態度”和“很合理的方法”,其基本精神始終是一致的,即如周恩來所指出的, “決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協商”,而“是我們聽命(服從調遣、統一編制、奉行法令等)于他們的領導”,一門心思要解決中共的政權和軍隊。⑥參見黃修榮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1931—1945),第548頁。雙方之間的鴻溝如此之深,如何彌合?政治解決的結果只能是政治無法解決了。
既不能軍事解決,又無法政治解決,耳聽中共獨樹一幟的言論,眼見中共迅猛發展的力量,蔣介石與國民黨人不免憂心忡忡,焦慮不安,終至坐臥不寧了。若任其“實力坐大,危險愈甚”⑦《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77頁。。然又不能軍事解決,萬般無奈,還是得在政治解決的軌道上設法。乃根據局勢變化,或以許多名目限制中共力量發展以待將來,或以各種手法逼壓中共“政治解決”。于是,《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出臺了,《中央提示案》提出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下達了,閃擊延安軍事行動秘密部署了,磨擦與沖突也就無從避免了。
由此可見,不斷地挑起兩黨磨擦,實際上反映了國民黨人在面對中共力量迅猛壯大情況下,想要解決中共問題卻又不能有效解決、明知不可為而又不得不為的一種極度焦慮、矛盾與糾結的心態。它明知應以抗戰大局為重,聯共抗日,卻又害怕中共在抗戰中壯大最終危及自己的統治而不斷發動反共磨擦,以限制和削弱其力量;然而日寇的瘋狂進攻又使它意識到不能發動內戰,必須聯共才有可能取得抗戰勝利,因而又不愿意國共完全破裂;蔣介石和國民黨還要把自己打造成民族領袖與抗戰先鋒,當然不能背負破壞團結、破壞抗戰的罪名,所以它在發動軍事磨擦時總要掛上其他招牌。一句話,國民黨扛著聯共抗戰的鮮亮招牌,干著防共限共反共、破壞團結抗戰的不光彩事體,打著既限制消耗中共實力、又不背負破壞團結抗戰罪名、還不要國共關系全面破裂的如意算盤,執行著奇怪而矛盾的兩面政策,從而使它在制造磨擦時總給人一種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欲“反”還“罷”的感覺。這就能夠理解為什么國民黨以山西新軍“叛變”為名發動晉西事變、在失去對大部新軍的控制權和晉西北地盤后卻沒有對中共大肆討伐;為什么將皖南事變定性為純粹的“軍紀問題”、軟硬兼施要中共出席參政會并不得不“保證”以后不再有“剿共的軍事”;為什么閃擊延安行動先是“極端秘匿,毋得聲張”,繼而“不得不竭力否認”并最終決定“對共不用武力討伐”。這也是當國民黨圖謀被戳穿后,反而使自己一再陷入到“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的尷尬境地的原因所在——它在中共和全國人民及國際社會面前輸了理,它的所作所為和中共處處以民族大義、抗戰大局為重的博大胸懷形成了鮮明對比。僅此一點,便注定了國民黨挑起的一次次磨擦最終只能是枉費心機。而造成上述焦慮、矛盾與糾結心態及兩面政策等等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復雜化形勢下,國民黨當局始終把維護它的專制獨裁統治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而把中華民族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這是其全部政策的根本出發點。
當然,無論磨擦的程度如何,得失怎樣,國共磨擦畢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磨擦,國共關系仍要受抗戰大勢制約,國共雙方最終都要暫時將自身的階級利益服從于抗日的民族利益。因為,“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81頁。。所以,盡管國民黨內心存“剿滅”中共想法者大有人在,但在發生嚴重的磨擦時,國民黨不能不對自己的行動加以控制,甚至著意防止事態惡化;同樣,中共在遭受巨大損失后,也不能不考慮到國民黨仍在抗日這個事實而盡可能地維持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也就是說,國共磨擦無論激烈到什么程度,最終都不能不走向妥協,雙方在確保合作不破裂這一點上是有著政治默契的。這在對皖南事變的處置應對中得到了最好的詮釋,正如日本學者片岡徹也所說,如果像黃橋之戰、皖南事變這樣大規模的國共軍事沖突都沒有導致對日和解與全面內戰,那么,這恰恰不是統戰的結束,而是對它的效果的基本證明②轉引自費正清著、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2部,第7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