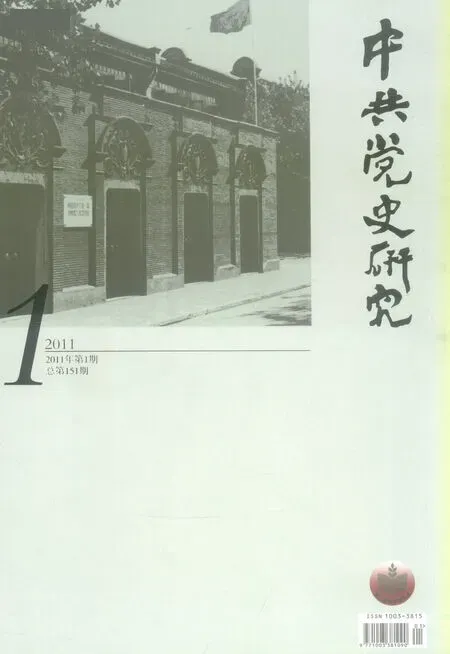從冷漠到投入:冀東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政治參與
朱德新
從冷漠到投入:冀東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政治參與
朱德新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的環境封閉等因素,導致冀東農民具有冷漠的政治傾向。以日軍的入侵為契機,以中共艱難的動員為“催化劑”,抗戰時期冀東農民的政治態度實現了從冷漠到踴躍參與的轉變。他們積極參與反抗日偽政權統治,掩護抗日干部脫險,加入各種社團,全力支持抗日的各種社會政治活動。在抗日軍隊弱小與日偽軍事力量強大的冀東特殊環境中,農民的政治參與,成為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奪取冀東抗戰勝利的重要條件。
抗戰時期;冀東農民;政治參與
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冀東①冀東是指河北省東部地區,舊制包括遵化、豐潤、昌黎等22個縣和唐山礦區、秦皇島港。它北據長城,南瀕渤海,西控平津,東臨山海關,是華北通向東北的橋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冀東境內的北寧鐵路、開灤煤礦和塘沽、秦皇島兩大海港都具有特別重要的軍事意義。農民的政治參與,經歷了從冷漠到投入的演變軌跡。這種轉變既是抗日根據地創建以及奪取冀東抗戰勝利的前提條件,也是推動政治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因而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啟示作用。目前,史學界雖對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政治參與進行了研究②主要研究成果有:翁有為:《論抗日根據地的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山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張鴻石:《論抗日戰爭時期華北根據地農民的政治參與》,《河北學刊》2002年第2期;孫蘋:《抗戰時期根據地婦女政治參與探析》,《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陳莉莉:《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等。,但缺少對其在抗戰前政治態度的探討以及參與行為演變過程的比較分析。就本文涉及的主題來看,冀東農民在抗戰前后為何有從冷漠到投入這種性質不同的轉變?這種轉變的作用、特點以及帶來的啟示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運用政治參與理論進行探討的問題。
一、封閉環境:導致抗戰前的政治冷漠
政治參與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中外學者有關論述很多,但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政治參與理論影響較大。亨廷頓認為,“個人所處的群體環境,對于決定他參與的范圍和性質,通常也比其特定的社會背景特征更為重要”①〔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著,汪曉壽等譯:《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83頁。。冀東農民所處的群體環境是分散在大小不等的平原或山地、各自孤立且內部相對松散的村落。抗日戰爭爆發以前冀東農民的經濟生活,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頁。。這種經濟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男子耕作,婦女佐之,老者守戶,幼者畜牧,小女攜籃采桑,回家自織。絕大部分人在多數時間里,一般不超出自己經營的土地范圍,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亦在本鄉集鎮銷售。③據有的老人回憶,即使在集鎮大街上傳遞和接收的信息也不多,因為1932年才開始有收音機,人們稱其為“電匣子”,覺得很新鮮。1992年5月25日在北京南至秦皇島的309次列車上訪問原冀東抗日村政權干部孟吉輔、佟玉柱老人的記錄。農民每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農民的其他活動,如完糧納稅、人際糾紛、社交往來等,亦以本村莊為主要場地,就連婚姻關系亦大多數在本村范圍。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由于“人口流動率小,社區間的往來也必然疏少”; “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④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頁。。這就出現了“村落社會和平靜穆猶如一潭死水,大多數農民對離家門30里地以外的事大都不知道,更談不上了解國家大事”的現象⑤1992年5月25日在北京南至秦皇島的309次列車上訪問原冀東抗日村政權干部孟吉輔、佟玉柱老人的記錄。。上述群體環境,決定了冀東農民政治參與的觀念和性質。
第一,屈從命運,逆來順受。“福來則歸功于天,禍至則諉之以命”是農民的處世哲學。他們認為地富剝削是“天經地義”,對現實生活“呈麻痹狀態”⑥1992年10月委托中共遵化縣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李永春代訪資料。。既有濃厚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利與我何有哉”的傳統心理,又有“皇帝與總統不分”、“誰做皇帝都照樣交糧納稅”等“安于命運”的模糊觀念。農民們誠望天下太平,自己“寧為治世犬,不做亂世民”。從而以超常的毅力忍受官府與土豪劣紳的欺詐剝削,借此換取鄉村的寧靜。這種情形類似于馬克斯·韋伯所揭示的“麻木的習慣”,即“出于絕對的漠然或者無力認識行動的可選擇過程”⑦〔英〕弗蘭克·帕金著,劉東等譯: 《馬克斯·韋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頁。。
第二,回避官員,忌打官司。統治階級愚民政策的欺騙,農民文化知識貧乏以及處于饑寒交迫的封閉環境等因素,致使農民產生避官、畏官現象。農民即使偶然遇到官員,也抱著“鄉下佬見太爺,多磕頭少說話”的態度。同時,一些鄉間公正士紳擔心招致怨尤,不愿參與基層政治,導致土豪劣紳霸占職位,農民敢怒而不敢言,對官員更是避而遠之。千百年來,農民將打官司的經驗歸結為: “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餓死不做賊,屈死不告狀”。這是因為農民們深知除打官司要消耗大筆費用之外,還認為社會上官官相護,官富相護,到頭來敗訴的仍是窮人;加之“一朝經官,十輩子結冤”,無論和誰打官司,對從不介入政治的農民而言,都會將雙方矛盾公開與激化,與對方結仇,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所以,為避免打官司,農民們遵循“東家長,西家短,人家的事情你別管”的原則,對一切事務都不去過問。即使有任何想法,也要“緊睜眼,慢開口,話到舌前留半句”。
第三,固守成規,封建保守。農民們身處僵化的空間和凝固的時間內,祖輩移交的經驗便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唯一的信息來源,世世代代就是憑此來處理一切事務的。筆者在調查中得知,盡管一些村莊也有鄉規民約,大意是交糧納稅,濟貧防匪,鄰里相助,積德為最。此約不議論不通知,雖然貼出來,但“基本無人看”①1991年10月29日在昌黎縣西沙河鄉訪問原中共晉察冀分局十三地委駐昌黎地下工作人員蘇振寰老人的記錄。。關于農民的政治行為,有的冀東農村老人回憶道: “他們只知道殺人償命,完糧納稅”②1991年10月18日在遷西縣白廟子村訪問谷世榮老人的記錄。。由此可見,冀東農民頑強地保持自己的生活習俗和傳統習慣,村落社會的秩序正是依靠這些傳統信念、倫理思想以及長輩們的威望調節和維護的。例如,農村倘有吵嘴扯皮之事,當事人把對方一拉吼道:走,找同族或街坊中某某大爺或大伯評理去。而這些長輩們連罵帶講理地“一陣轟,便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③1991年10月14日在遵化縣西三里鄉小劉莊村訪問劉歡老人的記錄。在關于各級官吏產生的途徑方面,農民們認為,任何官吏均為“真命天子”所委派,至少在“縣里打開冊子有紅名”,對這些人不能采取選或改選的方式,否則有違皇帝旨意,更是大逆不道④1991年10月25日晚在豐潤縣城關訪問曹兆榮老人的記錄。。
上述狀況⑤由于無法找到抗戰前有關冀東農民政治參與的報刊和檔案文獻記載,筆者主要利用1991年至1992年兩次赴冀東農村調查采訪的口述資料。猶如恩格斯在1894年寫成的《法德農民問題》中所揭示的:“作為政治力量的因素,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表現出他們那種根源于農村生活隔絕狀況的冷漠態度。”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5頁。
二、中共動員:從冷漠往參與方向轉變
1933年初,中日軍隊在長城關隘激戰的槍聲劃破相對沉寂的冀東天空,給農民帶來極大的震驚。尤其是日軍入關后的燒殺搶掠,使離鄉背井的村民感覺到了與根深蒂固的鄉土意識大相徑庭的困惑,這種無法接受的現實逼使冀東農民武裝組織即“山大王”奮起保“家”。例如盤踞在遵化、興隆一帶以“天下第一團,富人都獻錢”為行動綱領的“山大王”楊二,原興隆縣黃花川民團團總孫永勤領導的“天下第一軍”,都將其“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號,改為“打日本,保家鄉”的目標。孫永勤還將其武裝組織改稱為“民眾軍”,向日軍發動攻擊,被家鄉父老譽為“及時雨宋江”。
對包括上述農民武裝在內的華北各種民眾武裝組織 (紅槍會、天門會、聯莊會等)的行為,劉少奇在1938年作過總結。他認為,這些農民武裝組織一切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無論是日偽軍還是其他軍隊等,誰去騷擾掠奪,他們就反對誰。劉少奇強調,他們的政治立場中立,要將其引導到抗日道路上打游擊,為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作艱苦奮斗,犧牲自己,那是不容易的。⑦劉少奇: 《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解放》1938年第43—44期合刊。
為改變處于政治冷漠狀態中的農民,冀東共產黨組織采取了“喚醒民眾”、“發動民眾”的社會動員策略。冀東的共產黨員大多以小學教員的職業為掩護,向農民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有些則裝扮成小商販,以串鄉售貨的方式,大量發展“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冀東分會”的會員。1934年5月,中共京東特委成員王平陸來到孫永勤“民眾軍”的駐地,向他宣傳中共關于抗日的方針政策,并建議他把“民眾軍”改稱為“民眾抗日救國軍”。孫表示愿意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懇求京東共產黨組織早日派人前來指導工作。他高興地稱贊增加“抗日救國”四個字“方向明,旗幟新”⑧《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1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6頁。。在此期間,楊二等也在中共的幫助下,將“保衛家鄉”的地方性農民抗日武裝整編成統一的“民眾抗日救國軍”。
冀東共產黨組織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動員農民參與的初步成效,其標志是冀東人民武裝抗日大暴動 (亦稱起義)的發生。這是中共在敵后發動農民,組織農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一次偉大壯舉。1938年7月,隨著八路軍第4縱隊向冀東挺進,在冀東20多個縣的廣大地區,農村中青壯年大部分手持棍棒、梭鏢隨呼或尾追其后,爭相參加“便衣隊”。據此次大暴動的領導人李運昌回憶:遍地都是趕來參軍的群眾,歌聲、笑聲、口號聲夾雜著零星的槍聲,真令人激動!①《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1輯,第37—82、42—43頁。農民踴躍參與,很快組成20萬人的抗日隊伍,并與八路軍協同作戰,摧毀了除鐵路沿線以外的所有日偽政權,占領了興隆、昌平、薊縣等9座縣城以及所有重要集鎮;并將唐山至昌黎的100多公里鐵路截成數段,迫使北寧鐵路中斷行車半個月之久。但遺憾的是,大暴動在堅持兩個多月后失敗。
列寧在分析俄國農民特點時指出,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到了尖銳化的時候,到了一切社會關系急劇遭到破壞的時候,“農民很自然地表現出由一邊倒向另一邊”, “動搖不定,反復無常,猶豫不決等等”的特點②《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頁。。冀東的情況與此類似。大暴動失敗后,日偽強化編10戶為甲,編10甲為保,然后聯保成鄉的保甲制度;采取1人或1家“為匪、窩匪與通匪,則1甲內之住民必連帶施以懲罰”的“連坐”方法,實施人身管制;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和宣傳,全方位強化對冀東農村的控制,給農民帶來思想上的混亂③參見拙文:《本土色彩掩蓋殖民統治——淪陷時期日本對冀東農村的控制》, 《史學月刊》2010年第5期。。農民們雖然不與日偽同流合污,但抗日情緒明顯低落,政治參與熱情立即回到抗戰前的冷漠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 “一個自稱為革命者的精英,如果不去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那么,他不是自取失敗就是在隱瞞他的真實目的”④〔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著,汪曉壽等譯: 《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第177頁。。因此,冀東共產黨組織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秘密深入村戶,開展了更深入的社會動員。據李運昌回憶,除通過各種渠道廣泛宣傳中共關于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促進農民提高思想覺悟之外,還實行了“隱蔽開辟”的方法,即“開始是幾個人帶著少量武器,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工作關系跳到敵占區。工作時一方面利用我們干部好作風的影響,另一方面打特務,除土匪,改造壞人二流子,以這些具體活動爭取最廣泛階層的社會同情,為工作創造最好的條件”⑤中共豐潤縣委黨史研究室1961年在北戴河訪問李運昌記錄,原件存該室數據第10卷。。在西部盤山,大小幾十股土匪借抗日之名四處敲詐勒索,為當地農民所痛恨。共產黨根據農民的意愿,帶領八路軍首先整頓當地武裝,對作惡多端的土匪蔣德萃、白老八之流予以鎮壓,“這件事大得人心,使群眾的抗日熱情高漲起來”。在中部豐玉遵地區,也是從消滅土匪和“白面兒鬼” (即吸毒者)入手,安定社會秩序,得到群眾擁護的。在東部豐灤遷地區,八路軍首先消滅了以借抗日之名胡作非為的高奎武部隊,接著進行鋤奸滅匪,處決了破壞抗日的惡霸地主侯老七,鏟除慣匪郭滿等,為民除了大害。所以,有的村莊連夜“唱影” (即唐山皮影戲)來表達對八路軍的感激。八路軍在上述地區站住腳后,便著手開辟更為隱蔽的活動區,并逐步把日偽農村基層政權改造成公開應付日偽、暗中支持抗日力量的“兩面政權”,進而“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革命勢力擴展到敵人統治森嚴的占領區”⑥《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2輯,第107—108頁。。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也隨之被調動起來。
亨廷頓對各種參與模式進行比較后認為,以階級取向動員為基礎來尋求窮人支持的政黨,“為了克服窮人參與的障礙,必須做出更明確且更有意義的努力”⑦〔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著,汪曉壽等譯:《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第133頁。。冀東共產黨組織對農民參與的動員與亨廷頓的分析大致吻合。抗戰爆發后,中共明確將“發動民眾”列為開辟抗日根據地必須具備的三個基本條件之一⑧《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4頁。。冀東共產黨組織遵循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按照冀東實際“做出更明確且更有意義的努力”,即將農民的具體利益與對敵斗爭相結合,通過武力手段為民除害,使農民切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獲得農民擁護,并在此基礎上依靠農民通過政治參與釋放出來的創造力,支持中共及抗日軍隊的對敵斗爭。
三、付諸實踐:抗戰時期產生巨大效能
經過中共廣泛而深入的動員,冀東農民改變了抗戰前政治冷漠的狀態,積極投身于抗日戰爭,產生出巨大的參與熱情和參與效能,使冀東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政治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參與反抗日偽政權統治的活動。例如豐潤縣潘家峪、灤縣潘家戴莊的農民拒絕向日偽繳納糧款和物資,并將日偽警察分駐所為建立保甲制度而發放的門牌、戶口冊、“良民證”等毀棄,寧死不做日偽的“良民”。農民反抗和抵制日偽統治的行為遭到日軍血腥屠殺的報復。1941年1月25日、1942年12月5日,日軍以搜查八路軍為借口,糾集重兵包圍這兩個村莊,村民們面對日軍的槍口毫不屈服,拒絕透露任何有關八路軍及其機關、物資隱藏地點的信息。日軍在這兩個村莊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潘家峪慘案”、“潘家戴莊慘案”,分別殺害手無寸鐵的村民1237人、1280人,燒毀房屋1100間、1030間。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正如李運昌等八路軍領導人所指出的:冀東廣大人民群眾,“如寧可犧牲全村人性命也不肯向敵人屈服,也不肯暴露我軍機密的潘家峪人民”以及與其他為革命捐軀的冀東英烈一樣,“他們的英名和業績將同我們的革命事業一起,千秋萬代永世長存”①《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2輯,第124頁。。
第二,用鮮血和生命掩護抗日政權的干部脫險。國外有研究政治學的學者將“與政府官員或政黨領袖聯系”看做是政治參與的“過渡活動”等級②〔美〕安東尼·M.奧勒姆著,董云虎等譯:《政治社會學導論——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8頁。。而冒著生命危險或用生命作代價去換取抗日政權干部人員的安全,應可算做更高層次的政治參與。因為農民在這方面的活動,對抗日政治秩序的連續性和鞏固性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窺冀東中部的白峪村一例便可見全斑。日軍包圍該村搜查抗日政權的干部,村民均遭毒打,以被打死十幾人的代價換取被包圍在人群中的抗日區政權干部毅然、石更等人的安全。村民們說:“抗日干部的腦袋在褲腰帶上掖著,為老百姓打鬼子除漢奸,咱們就要豁出命來保護他們。”事隔40多年后,抗日戰爭歲月多次遇險后生還的這些干部仍然感慨萬千,他們深情地說:“離開群眾,我們一步也不能行動,不能生存。我們地方干部活動在群眾之中,對這一點感受尤深”。正是在廣大群眾這堵銅墻鐵壁的掩護下,抗日斗爭才得以堅持。“這種革命情誼,勝過母子之情,手足之誼,是我們畢生也不能忘懷的”。③《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2輯,第213—216頁。
第三,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經過共產黨的啟發教育和抗日戰爭硝煙的洗禮,農民們提高了政治覺悟,普遍關心時事,密切關注抗日斗爭勢態的發展,并且“提高了政治意識,不明白的立即打聽”④《一九四四年第四專區豐灤聯合縣村政權改選經過情形登記表》,豐潤縣檔案館藏,永字第1號卷宗。。對八路軍也有了正確的認識,有的農民稱其為“祖國人”⑤1984年11月27日,田益廷等人訪問抗戰時期“潘家戴莊大慘案”的幸存者之一、姚福的妻子 (慘案發生時31歲)。她回憶:慘案發生的當天早上,她父親招呼她們快起來,說“祖國人來了”。“我爸沒有說是八路軍,而說成祖國人。我們都起來了,幾個祖國人就進到我媽的房里”。轉引自田益廷等:《潘家戴莊慘案》,左祿主編: 《侵華日軍大屠殺實錄》,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250—251頁。。1944年,豐灤抗日聯合縣政府在區長聯席會議紀要中指出,在“環境緊張的地區 (如二區、四區),農民多傾向咱們,農民天天‘跑返’ (即敵人來農民走,敵人走農民返——筆者注),對部隊與政權干部非常擁護與歡迎”⑥《第四專區豐灤縣區長聯席會議記錄》 (1944年),豐潤縣檔案館藏,永字第1號卷宗。。農民們還痛恨漢奸,自動擔任防特鋤奸任務,看到“政權掌握在舊辦公人手里即要求改選”⑦《一九四四年第四專區豐灤聯合縣村政權改選經過情形登記表》,豐潤縣檔案館藏,永字第1號卷宗。。農民用票選、豆選、碗選等方式,一絲不茍,認真負責地把那些真正為民謀利益,忠誠抗日事業的積極分子選拔進入抗日根據地基層政權的領導崗位。
第四,踴躍參加各類社團組織。農民們響應冀東共產黨組織關于“要報效國家,不給敵人辦事”①中共遷西縣委黨史研究室于1981年12月25日訪問李運昌記錄,該室數據第10卷。的號召,自動參加了諸如農民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報國會、兒童團之類的抗日群眾組織,積極配合八路軍開展抗日工作。當日軍進村時,這些組織的農民有的又搖身變成日偽保甲體系內“反共自衛團”屬下的成員,以敷衍應付日偽。抗日群眾團體的政治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擇其年齡最小的兒童團來看,都有濃厚的參與意識。少年兒童們站崗、放哨、送信,給抗日部隊當向導等,許多英勇少年為國捐軀。當時在冀東抗日根據地擔任記者的管樺所寫的小說《小英雄雨來》,正是抗日戰爭年代冀東少年兒童的一個縮影。
第五,全力支持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戰爭。抗戰期間的冀東農民突破了此前保衛家鄉的局限,將抗日、保家與祖國的命運相結合,自覺投身到保衛祖國的斗爭,展現出“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以堅持灤東抗日斗爭的八路軍第12團為例,1942年,它開到灤東時僅1300人,1年后消耗了900人,但由于群眾踴躍參軍,部隊始終處于超編狀態,到抗戰結束時仍超過1800人。據統計,在八年抗戰中,僅遵化縣就有3144人先后參加抗日隊伍,其中1985人光榮犧牲。②《遵化黨史資料》第2輯,第124—131頁。八路軍將士不僅是冀東農民子弟兵,而且在物資上也全依賴農村。李運昌等冀東八路軍領導人對此均有贊詞,認為在那血雨腥風的年代,人民覺悟很高,抗日政權在財政上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給多少,不折不扣,不用費力,應時供給③《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3輯,第113頁。。除錢糧外,農民還為八路軍提供服裝,許多村莊每月都要組織幾十名婦女為八路軍趕制衣服鞋襪,僅1940年,遵化縣的婦女就做鞋39萬雙,軍衣、軍被8.5萬套④《遵化黨史資料》第2輯,第54頁。。
冀東農民的上述參與對抗日戰爭起到了重大支持作用,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井門滿明少佐對此也不得不承認:“敵人 (指抗日軍隊——筆者注)以民眾為叢林,潛伏其中進行抗戰。”⑤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0頁。冀東日酋岡村寧次也看出: “八路軍的勢力表面上似乎看來平靜,實際上一揭開表皮就露出紅色的實質”⑥轉引自《遵化黨史資料》第2輯,第383頁。。
四、參與行為:戰爭環境呈現多重特征
抗戰時期冀東農民的政治參與,不僅是在抗戰前政治冷漠基礎上產生的,而且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展開的。在中華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在血與火特殊條件下啟蒙和養成的農民政治參與意識與行為,既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戰爭環境的烙印,又與和平時期的政治參與有著很大的區別。
第一,冀東農民的政治參與是一種外力推動下的被動參與。在亨廷頓的政治參與理論體系中,政治參與內容不僅包括自動參與,而且包括受動員而產生的參與⑦〔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著,汪曉壽等譯:《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第5—7頁。。從冀東農民由冷漠到投入的政治參與演變過程中可以看出,迫使其發生這種性質變化的契機是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催化劑”則是中共的引導。很顯然,倘若離開中共的組織、動員和引導,僅靠冀東農民自身的努力是無法實現這種界限超越的。
第二,與從冷漠到投入的轉變過程相對應,冀東農民的參與行動也經歷了從抗戰前的“保家”到抗戰爆發后“保國”的升華過程。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前述日軍入關后冀東農民多次武裝反抗,都與歷史上農民起義一樣,目的仍是為了“保家”而戰。抗戰爆發后,經過中共的動員和引導,冀東農民武裝組織實現了從“保家”到“保國”的轉變。根據亨廷頓的政治參與理論,這種轉變體現出一種個人對國家的認同趨向于超過其他方面的忠誠,具有“公民權的概念”,超越了社會階層和社區群體之間的界限,從而為大眾性的政治參與奠定了基礎①〔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著,汪曉壽等譯:《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第48頁。。
第三,冀東農民的政治參與是在敵強我弱的特殊環境中開展的,因而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抗戰爆發后,為確保冀東這一日軍“華北兵站基地”的“心臟”和通往“滿洲國”“咽喉要道”戰略地位的暢通無阻,日本一直在此投入重兵。與日偽軍事力量相比,抗日武裝力量始終處于劣勢地位。1938年冀東抗日大暴動后僅存武裝3000余人,經浴血奮戰,到1941年春才開辟出初具規模的根據地,主力部隊擴充至4000余人,縣區游擊隊發展到3000多人。但此時日軍約2萬人,偽軍約7萬至8萬人。八路軍在1941年反“掃蕩”中又遭到很大損失,根據地幾乎全又變成游擊區。②《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第2輯,第108頁。在這樣一種八路軍與日軍力量懸殊的農村環境中,如果沒有農民的參與作依托,抗日戰爭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抗日武裝力量只能浮游于各地,無法生存和發展。因此,農民的政治參與,對冀東中共及其軍隊的抗日戰爭就顯得更為重要。
第四,冀東農民的政治參與仍有抗戰前政治冷漠思想迷霧的籠罩。對于身處封閉環境并且長期受封建專制體制束縛下的農民,要求其在戰爭環境中的政治參與言行“一刀切”式地全朝正確方向發展也是不現實的。也就是說,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行動還存在不少錯誤現象:一是對民主概念的認識存在誤解。在1944年豐灤抗日聯合縣的一次區務會議上,有的區干部反映,一些農民把自己不愿干的事當成講民主,有些農民不去挖溝,自認為此乃講民主。如果一定要他們去,他們便說受到抗日干部的壓迫,也就是抗日干部不講民主。③《第四專區豐灤縣二區區務會議記錄》 (1944年11月1日),豐潤縣檔案館藏,永字第1號卷宗。二是對政治仍持不介入態度。對于參加選舉等方面的政治活動,部分農民存在著“誰吃公糧誰負責”,“不吃公糧就不辦事,凡事與我無關系”的言行④《第四專區豐灤縣二區區務會議記錄》 (1944年11月1日),豐潤縣檔案館藏,永字第1號卷宗。。三是還有“認命”的思想。一些佃戶以為自己的地租被減免是“命好”,上級的“恩賜”。另一部分農民則不敢接受地租被減免的現實,對此誠惶誠恐,有退租現象,導致“明減暗不減”的后果。⑤昌黎縣抗日政府: 《一九四五年工作的檢討與今后方向》,昌黎縣檔案館藏,永字第1號卷宗。
但就冀東抗日根據地的整體形勢來看,抗戰前農民政治冷漠和一盤散沙的狀態已成為歷史,政治參與的奇葩已在日偽重點統治的地區盛開,并實現了量與質的飛躍,農民破天荒地第一次品嘗了當家做主的滋味,由此煥發出蓬勃生機與活力,并轉化成克服困難戰勝入侵者的巨大物質力量。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一個社會卷入一場規模巨大、傷亡慘重的戰爭時,會導致政治參與水平顯著提高⑥〔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著,汪曉壽等譯:《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第57頁。。通過高水平的政治參與,冀東農民不僅用自身寬厚的肩膀支撐了八年抗日戰爭的開展,而且使自己的家鄉熱土成為抗戰后期共產黨和八路軍先機挺進東北的基地。
今天,我國已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時代,農村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現代轉型。抗戰時期中共動員冀東農民政治參與的歷史經驗對于改善目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提高農民政治參與意識,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只有通過運用一切手段,充分調動9億農民類似抗戰時期潛在的無法估量的參與積極性與創造性,踴躍開展有序的政治參與,才能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步伐。
(本文作者 澳門理工學院客座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責任編輯 王愛云)
From Indifference to Enthusiasm: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Peasants in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Bases of Eastern Hebei Province
Zhu Dexi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the peasants in the eastern Hebei Province were indifferent to politics due to the closed environment.However,the invasion of Japanese army and the mobiliz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changed their political attitude.The peasants were no longer apathetic about politics,but actively get themselves involved in many kind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such as opposition to the rule of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s,prote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cadres,joining different kinds of associations,and support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Under the special conditions in eastern Hebei Province with weaker anti-Japanese forces vs.stronger Japanese and puppet army,the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Japanese bases and winning the victory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eastern Hebei Province.
D231;K265.1
A
1003-3815(2011)-01-008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