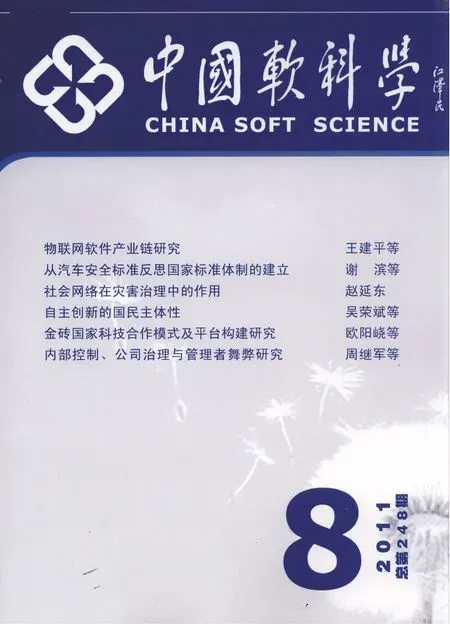市場統一基本制度之構造與實施
鄭鵬程
(湖南大學 法學院,湖南長沙 410082)
市場統一基本制度之構造與實施
鄭鵬程1
(湖南大學 法學院,湖南長沙 410082)
稀缺資源只有在統一市場才可獲致最優配置,大國中政治性分權與經濟性統一的制度悖論必將產生市場分割問題,財政聯邦制、司法調節等難以解決此種頑疾。自由流動規則、競爭規則是克服市場分割、維護市場統一之基本規范。中央應從戰略高度重視兩類規則之構造,在憲法中增設自由流動條款;擴大競爭規則適用于政府行為的范圍。
市場分割;市場統一;自由流動規則;競爭規則;行政調解
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稀缺資源只有通過市場機制才能獲致最優配置,因此,建立并維護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區域性國際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就成為各個國家、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乃至全球性經濟組織努力奮斗之重要目標。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確立以來,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實現國內市場統一,促進各類資源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成為中央政府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經過30多年的持續改革,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但整體考察,國內市場尚未獲致真正統一。拋開兩岸四地間的各種貿易壁壘不說,單就內陸市場而論,商品、人員、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還面臨諸多制度性障礙。有經濟學家曾經測算,中國的國內貿易壁壘遠遠高于國際貿易壁壘。而在金融危機或市場疲軟等經濟不景氣時期,地區壁壘與市場分割往往更為突出和嚴重。市場分割的危害極其廣泛且深遠,用美國聯邦黨人的話來說,它會成為國家“不和與沖突的重要原因”,“會助長無休止的仇恨”[1]。因此,中央政府應當時刻警覺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問題。本文試圖就中國這樣的大國如何構建既能保障地方自主權又能防止、規制地方保護主義,使地方利益與中央利益(統一市場)實現有機平衡的制度進行探討。雖然論文討論的主要內容是如何用法律手段規制地方保護主義,但一方面,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市場統一,倡導維護市場統一比主張打擊地方保護主義能獲得更廣泛的認同,另一方面,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損害市場統一比判斷其是否構成地方保護主義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論題定為市場統一基本制度之構建與實施。
一、市場分割:政治性分權與經濟性統一制度悖論的必然產物
對于任何大國或一個國際經濟組織,其建立或維護內部統一市場之努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它必須與阻礙內部市場統一的各類保護主義勢力和行為作長期而艱苦的斗爭。自1824年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第一起地方保護主義案件吉本斯訴奧格登案開始,美國同地方保護主義行為的斗爭歷史已有180余年,迄今仍未停止①200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鄂乃德與赫基馬固體廢物案中就地方保護主義問題作出裁決,參見:United Haulers Association,Inc.,et al.v.Oneida-Herkimer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uthority et.,Decided April 30,No.05-1345.2007.。歐洲人為了建立歐洲內部統一市場奮斗了50余年,雖然取得的成績令世人矚目,但成員國相互間關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指責或指控從未間斷。自1948年關貿總協定生效之后,國際社會就致力于“取消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以達到“擴大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發展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目的,但迄今為止關貿總協定及其后繼者WTO所取得的成績與其所標明的宗旨相比,差距甚遠,而且目前每一種削除貿易壁壘的新的嘗試和努力都遇到了重重困難。自墨西哥坎昆會議無疾而終之后,新的一輪WTO多哈多邊貿易談判毫無進展。而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使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多哈談判雪上加霜,前景更加黯淡。
市場統一任務之所以長期和艱巨,源于市場統一進程中作為個體利益的成員利益與作為整體利益的共同體利益既相互依存又存在沖突。任何經濟共同體都是由若干成員如主權國家、主權州或地方政府組成的。在一個經濟共同體中,構成該共同體的成員一方面必須依據條約或法律的規定承擔維護共同體市場統一(共同體利益)的義務,另一方面必須增進其轄區內選民或居民的福利,對其轄區內選民或居民的利益(成員利益)負責。
從長遠來看,共同體利益與成員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因為,不管一個經濟共同體是國家,還是區域性國際組織,抑或是WTO這樣的國際組織,其統一內部市場,實現資源帕累托最優配置的目的,都必須通過其成員及其成員所轄區域內居民在開放市場中的公平競爭才能實現。沒有共同體成員及其成員所轄區域內居民這些獨立利益主體的參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從此角度考察,成員利益的最大化就成為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條件。反過來考察,共同體市場范圍越廣闊,市場統一的程度越高,共同體所掌控的有限資源的最優配置的可能性或者說共同體成員整體福利最大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成員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機會也會越多。共同體利益與其成員利益的這種一致性,為作為獨立個體的成員加入各種經濟共同體提供了激勵。
共同體利益的最大化必須借助其成員之手來實現這一機制,內在地、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無法調和的矛盾。由于共同體利益的最大化必須通過各成員利益之最大化才能實現,所以,不管一個共同體對統一其內部市場的愿望多么強烈,它首先得承認并在法律上盡力保護其成員及其成員所轄范圍內各類機構的獨立利益(包括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主體地位。在一個統一的市場內,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共同體各成員之間必須為其轄區范圍內各個獨立的利益主體(居民或企業)爭取有利的交易條件而展開競爭,這也正是共同體所期望的。不過,共同體成員所采取的競爭方法和手段與其居民或企業所采用的競爭方法和手段根本不同。企業最常用的競爭手段是價格,即通過優質低價策略爭取市場份額。而共同體成員,不管是享有主權的成員,抑或是不享主權的成員,一般不直接購買或銷售產品(服務),所以,價格不是其主要的競爭手段,共同體成員最常用的競爭手段,是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制度,即經由制度降低本轄區范圍內各利益主體的交易成本或增加轄區范圍外各利益主體的交易成本,以此保護、提升其轄區范圍內居民或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競爭,我們稱之為制度競爭。制度競爭,特別是與經濟交易活動密切相關的制度的競爭常常會產生顯著的負外部效應,即對他人帶來不能用市場交易衡量的不利影響[2]。例如,如果一個地區的稅收優惠措施只給予本地企業而不給外地企業,則外地企業在本地的市場競爭會受到經營成本高的不利影響。這些不利影響,從市場統一的角度考察,構成了市場壁壘。所以,只要在一個共同體內部存在著各種成員利益,成員利益就必定會與共同體利益發生沖突。
不管是在疆域上,還是在人口上,中國都是一個大國,但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既沒有市場觀念,也不承認作為政治共同體組成部分之各級地方政府的獨立利益主體地位。雖然上個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經強調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3]。但這種主張在當時并沒有上升為法律,所以,長期以來中國并不存在大國通常有的市場分割問題。基于對不承認地方利益、不承認市場經濟的教訓的切身體悟,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政府不但承認了地方利益的合法性、接受了市場觀念,而且將地方利益、市場經濟理念寫入了憲法。1982年憲法關于“中央與地方應有職權劃分”的規定及1993年憲法修正案關于“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定,將我國的經濟推向了快速發展軌道。目前經濟領域所取得的各項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于地方政府競爭機制的引入。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仍將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但實施市場經濟體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告誡我們,不能再回到原來大一統的集權主義時代。作為現今世界上唯一沒有實行聯邦制的大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實行適當的政治性分權,以促進地方競爭,可能成為將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選擇方向。雖然中國的地方政府不同于美國的州政府,更不同于歐盟的成員國,中國的地方政府不屬于主權單位,但是有地方競爭,就必須承認地方利益,而有地方利益,就必然會產生地方保護主義,即使中央政府具有高度的權威性,也不能為了根除附在地方利益之上的地方保護主義而將作為市場統一發動機之一的地方利益根除。因此,如何在承認并保護地方利益、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的前提下,防止市場分割、維護市場統一,成了中央政府的一大難題,也成為中國學術界長期關注和討論的話題。
二、市場統一觀評介
學術界對市場分割問題的關注始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迄今為止所提出的克服市場分割、整合國內市場的主要觀點有分權觀、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改革觀、司法調節觀等。
(一)分權觀
分權觀也稱為“財政聯邦主義”,主要是經濟學界提出的觀點。許多經濟學者指出,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是地方政府財政激勵之結果,是財政“分灶吃飯”體制刺激了地方政府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在財政激勵下,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不惜“以鄰為壑”[4]。基于這種認識,他們提出的促進市場統一的具體對策是完善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稅體制[5],實行“經濟性分權”[6],建立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以換取地方政府放棄地方保護行為”[7]。而分稅制的完善,首先必須解決事權與財權不清的問題,認為“以事權為基礎劃分各級財政的收支范圍以及管理權限,使事權劃分與支出相一致并和財力相適應”是“建立完善、規范、責權明晰的分級財政體制的核心”[8],政府間事權劃分應遵循效率性、公平性和經濟穩定性三個基本原則,“凡是關于國家整體利益、全局利益的事務……應由中央處理;凡是關于地方局部利益和地方自主性、地方自主發展的事務歸地方處理”[9]。
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對于構建穩定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將其作為規制地方保護主義、統一國內市場的主要措施則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很難界定,而這正是合理劃分政府事權與財權的前提條件。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時期,政府只需要做三件事:界定產權、保障交易安全、解決私人紛爭。然而,這種理論已經不適合于混合市場經濟時代的需要。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與市場之間、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已經結成了彼此不可分離的聯盟,在這種聯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10],對政府與市場邊界的界定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果不能獲得合理界定,則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就是一句空話。
其次,即使解決了事權與財權的劃分難題,地方保護主義也不能得到有效規制,因為,政府間事權與財權的劃分并不否定分權,而是強化分權、規范分權。強化分權可能導致“一個嚴重的悖論”,即“當中央權威被削弱之后,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變成'掠奪之手'而不是'幫助之手'”,進而使市場更難統一。此外,“在一個存在具有文化、民族差異的國家,如果政治和(或)經濟分權程度過大,那么地方政治家就很可能選擇分裂主義政策……如果中央既無財力收買分立主義傾向的地方,又缺乏強大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很可能幫助本地企業逃避中央稅賦和管理來發展本地經濟,進而削弱中央維護法律秩序、征稅和管理社會經濟的能力,最終危害整個社會福利”[11]。
(二)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機制改革觀
部分經濟學者運用博弈理論,從政府官員晉升激勵的視角對市場分割的原因進行了詮釋[12],認為當下中央政府建立的考核機制導致市場難以統一。這些學者指出,自1980年代初開始,地方政府官員的選拔和提升標準由純政治指標轉變為經濟績效指標,尤其是地方GDP的增長,不同地區的官員不僅在經濟上為GDP和利稅競爭,而且也在“官場”上為政治晉升而競爭。同一行政級別的地方官員,無論是省、市,還是縣、鄉(鎮),都處于一種政治晉升博弈。在這種博弈中,因為只有少數人可獲提升,一人獲得提升將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機會,一人所得構成另一人所失,所以參與人面臨的是一個零和博弈。“官場”競爭的邏輯,深刻地改變由官員所主導的經濟競爭的方式和內容:參與人只關心自己與競爭者的相對位次,不僅有激勵做有利于本地區經濟發展的事情,而且也有同樣的激勵去做不利于其競爭對手所在地區的事情。這就是為什么處于政治晉升博弈中的政府官員不愿意合作卻愿意支持“惡性”競爭的基本原因[13]。基于這種認識,這些學者建議,市場整合必須改革傳統的政績考核機制,淡化GDP指標、強調綠色GDP概念或“根據不同地區采用不同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機制或在相同的政績考核機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14]。
如果說改革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機制對市場整合有積極作用,那么這種作用也是極為有限的。首先,只要存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考核的機制,則不管其考核的標準或內容是什么,不管是純粹的經濟增長,還是綠色GDP,抑或是社會、文化發展等其他指標,都同樣會導致市場分割,因為現實中有些市場封鎖行為就是以保護本地生態環境和居民身體健康為借口的。
第二,即使中央政府不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考核,地方保護、市場分割也可能不會有所減少。從比較的角度看,許多國家的中央政府譬如美國并未建立考核地方政府官員的機制,也不存在前述學者所說的地方政府官員政治晉升博弈問題,但這些國家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也很突出。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機制只對極少數人有激勵作用,只能保障極少數人對中央政府的忠誠。目前政制下中央政府用以穩定維系地方與中央關系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向地方政府推薦、委派、任命主要干部擔任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并由其傳達、貫徹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旨意,以確保地方與中央步調一致。但這種制度并不是沒有挑戰。根據現有的制度安排,地方行政長官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顯然,中央推薦、委派與地方選舉之間存在一種不可避免的張力。另外,在這種制度下,中央政府能夠直接控制的只是那些流動較強的地方官員,而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官員的流動性不強。他們與地方利益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在強烈的地方利益面前,中央政府的代理人難以確保中央政府的政令統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政令不統一的真實寫照。
第四,雖然該觀點所揭示的地方政府官員政治晉升與地方政府GDP指標之間的關系確實存在,但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所揭示出的這種關系的性質即地方政府官員的職位升遷與地方經濟增長率正相關的結論經不起經驗檢驗,有學者通過經驗數據研究得出了地方經濟增長和地方官員升遷“負相關的計量結果”[11]。
(三)司法調節觀
與經濟學界的觀點不一樣,政治學、法學界的學者主張通過司法方式解決市場分割問題。他們認為,通過立法、行政方式化解或消滅中央和地方的權力沖突“不見得有效”,而用司法方式調節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通過裁決個別糾紛間接協調政府間關系有“不為人注意的重大好處”,因為地方保護主義措施經常涉及私人利益,“這種私人利益可以抵制地方用各種措施損害全國性市場的統一”。“如果能為合法的私人利益提供有效的救濟”,則“在千百萬人對自身利益的關注中,在眾多法院司法過程中,在無數的案件中,地方政府的行為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審查,使得所有法院都成為統一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守護者”[15]。有學者還主張設計出一套包括撤銷地方政府違法行為、變更地方保護行為的內容、補償受害人遭受的經濟損失、施加懲罰性賠償責任、追究地方政府決策者的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等在內的法律責任體系,以抵消地方保護行為實施者和受益者從這些行為中所獲得的利益[16],進而達到維護市場統一的目的。
確實,從法理層面分析,司法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關卡,大凡不能通過其他手段得到有效解決的糾紛,最終都希望能夠通過司法途徑獲致解決。所以,理論上,司法是調節中央與地方關系,維護市場統一的最有效手段,實踐中也有這樣的范例,如美國對地方保護主義的規制就是經由司法審查實現的。然而,一旦回到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通過司法方式來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并不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情。“因為我國的法院系統是高度地方化的,法院不能在判決中宣布地方性法規的無效,不能審查抽象行政行為。受到侵害的當事人不指望從法院獲得救濟,目前我國的法院也不能提供這種救濟”[15]。顯然,寄希望于一個本身就有缺陷、就需要進行重大變革的制度去遏止另一種制度弊端,不僅缺乏邏輯自恰性,而且在實踐中也會產生危害,即將原本有一點獨立品格的司法機關拉入“司法地方保護主義”之泥潭。
其次,對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提出訴訟,以人們能夠發現地方政府的違法行為即容易舉證為前提條件。但我國的地方保護主義有很多隱性措施,往往是只做不說,故意拖延等。行政措施公開性不強、透明度不高,證據難以獲得,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功能的發揮。
第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對地方保護主義的司法遏制主要靠私人當事人的力量,靠“千百萬人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不是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間的對抗來實現的。那么,是否有“千百萬人”關注自身利益的人愿意“挺身而出”,就成為司法遏制地方保護主義是否有效的關鍵性因素。根據歐、美的經驗,凡對政府提出訴訟的,都不能從政府手中獲得損害賠償(因為這將威脅到政府的財政而影響其公共服務能力),只能獲得禁令救濟。易言之,提出這種訴訟的私人當事人并不能從這種訴訟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實惠,甚至可能會因提出訴訟而遭受財、物、時間方面的損失。顯然,這可能是一種得不償失的公益訴訟。
第四,禁令救濟無論是對于地方政府還是其所屬官員都不是嚴厲的救濟措施,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違法行為人對法律的尊重。如果當事人不遵守禁令(在我國可能較為普遍,如不執行法院的判決)而又沒有相應的制裁措施,則這種救濟措施也是沒有很大用處的。
上述三種觀點分別涉及財稅法(分稅制)、行政法(公務員制度)、訴訟法三個法律層面,除司法規制觀直接指向市場分割行為之外,其他兩種觀點雖然主觀上具有標本兼治、徹底根除地方保護主義之目的,但事實上對地方保護主義的規制只具有間接意義。所以,目前學術界對規制地方保護主義措施的研究仍然是不夠全面、不夠深入的,有必要進一步深化。
三、市場統一基本制度之反思和重構
理論上,具有中立、開放品格的競爭法律制度是維護市場統一最直接、最有效的因而是最理想的制度,因為,競爭法是市場經濟之基本法,它以維護市場自由競爭、公平競爭為其主要價值訴求。而自由競爭、公平競爭只有在一個統一的市場中才能實現,市場分割毫無疑問損害了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進而違反了競爭法律制度,所以,競爭法律制度可以而且應當對市場分割行為進行規制。我國目前主要是依靠競爭規則來維護市場統一。早在1980年,國務院就頒發了《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已廢除),以“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條和第30條對地區封鎖作了禁止性規定。2001年,國務院又專門頒發了《關于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國務院第303號令),對地區封鎖的具體表現形式進行了細化。2007年頒布的《反壟斷法》也對如何規制地方保護主義作了明確規定。上述四個法律文件,盡管頒布的具體時間背景不同,但對那些公開的明目張膽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特別是地區封鎖行為都構成了有力威懾。不過,從經驗層面考察,這些規則在維護市場統一方面還存在明顯的缺陷:首先,上述四個法律文件都沒有明確將保障自由競爭、維護市場統一作為其立法目的;其次,這些法律文件主要適用于商品(包括服務)流動,沒有涉及人員、資本等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問題;第三,對政府行為的規制只限于政府的作為,而不規制不作為。正是由于立法存在前述缺陷,諸多國內貿易壁壘特別是人才流動壁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消除。所以,要使包括兩岸四地在內的全國市場獲致真正統一,有必要重構市場統一基本規則。
從比較法的角度考察,歐美用以維護市場統一的基本制度有自由流動規則(free movement rule)和競爭規則(competition rule)。其中前者以禁止各成員制定妨礙共同體內部市場統一的歧視性措施,如對共同體內商品、服務、人員、資本的流動施加數量限制或征稅為已任,后者則側重于規制政府機關或市場主體限制競爭、分割市場的行為。這兩類規則往往并存于一個共同體的同一部法律文件尤其是憲法性文件之中,但實踐上各有側重。美國主要依靠自由流動規則即憲法第1條第8款第3項中的“隱性商業條款”(dormant commerce clause)保護市場統一,其競爭規則雖然也在打擊地方保護主義方面發揮了作用,但商業條款是競爭規則的法源,故商業條款是美國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主要法律依據[17]。而歐洲的情況恰好相反,雖然《歐共體條約》第一編、第三編中的商品、人員、勞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規則也在統一市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歐共體的市場統一主要是通過其競爭規則即《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82條、第86條來推動的。美國學者格伯爾曾經指出,在歐洲,競爭法是“規范經濟和政治關系”的“核心手段”,是歐洲一體化過程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一體化和讓人們對歐洲制度產生信心的'發動機'”[18]。競爭規則之所以在歐共體市場一體化過程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為競爭規則所具有的中立、開放品格,贏得了成員國的尊重和服從[19]。我們可以借鑒歐美維護市場統一的成功經驗,重構市場統一基本制度。
(一)在憲法中增加自由流動條款
自由流動條款,是用以保障商品、人員、資本、服務在共同體內部市場能自由流動的法律規則。商品、人員、勞務、資本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因為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而競爭的基本含義一是自由,二是公平,因此,競爭得以展開的首要條件就是商品、人員、資本、服務能夠自由流動。只有商品和其他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其效用才能被最大化,市場實現稀缺資源最優配置的目的才能實現。另外,商品、人員、資本、服務自由流動本身也是市場經濟所追求的一種價值。雖然多數人特別是經濟學者將市場經濟作為促進經濟增長和進步的最理想機制,但市場經濟所追求的目標絕對不只限于經濟增長,它還包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政治自由等多重目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經指出,“市場機制對高速經濟增長和全面經濟進步做出貢獻的能力”已經得到廣泛、正確的承認,但如果“僅僅在衍生的意義上理解市場機制的地位”,則“是一種錯誤”,“交換和交易的自由,其自身就是人們有理由珍視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市場機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當然是重要的,但與交換自由—詞句、物品、禮物—的直接意義相比,它只是次要的”[20]。我國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直接動因或近期目標也許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但伴隨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社會公眾對自由價值的認知和關注將超越其工具性意義,而逐漸轉向于尊重自由的目的性價值,并最終轉換成為法律上的訴求。
1.自由流動規則的地位。自由流動規則應當在憲法性文件中加以規定,這是各經濟共同體較為一致的做法。歐共體中的自由流動規則規定于《歐共體條約》第三部分“共同體政策”的第一編“商品的自由流動”和第三編“人員、勞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之中,而美國關于自由流動的規則即“商業條款”規定于聯邦憲法第1款第8款之中。除美國、歐共體外,還有其他一些國家如土耳其也在其憲法中(1982年憲法第167條第2段)制定了自由流動規則:國家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提供并改善正當的運轉正常的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信貸與貨幣市場,并為了實現該目的,避免市場中出現實質的或契約性的卡特爾協議與壟斷[21]。我國也有學者指出,“建立地方政府競爭秩序的關鍵是應該在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中明確寫入維護國內統一大市場,即維護國家內部的產品、勞務、人員和資本四大自由流通”[7]。之所以要將自由流動規則作為憲法規則加以規定,一方面是因為自由流動規則所保護的自由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也只有將商品、資本、人員、服務的自由流動上升為憲法權利,才有可能對分割市場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進行有力規制。基于此,本文建議將憲法第15條第3款修改為:“國家保障商品、人員、服務與資本的自由流動,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這樣一方面可以彌補我國自由流動規則缺位這一缺陷,另一方面也可為競爭規則的有效實施提供憲法保障。
2.自由流動規則的基本內容。自由流動規則的核心內容,即禁止地方政府限制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妨礙市場統一。這里所說的“地方政府”,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級各類地方機構,也包括特別行政區。目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雖然在政治上已回歸祖國,但在經濟上,兩岸三地尚未形成統一市場。譬如,內地居民不管是去港澳,還是去臺灣旅游,都必須繳納相關費用,辦理證件。所以,應考慮通過自由流動規則將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市場建成全國統一市場。這里所說的“限制”,既包括直接禁止,如交通封鎖,也包括間接限制,如對外地商品、人員、服務或資本施加額外的稅收負擔、收取額外費用,或給本地商品、人員、服務或資本以稅收優惠等,既包括作為,也包括不作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地方政府實施的公開的、直接的、有形的限制逐漸越少,而暗中的、間接的、無形的限制卻在不斷增加。自由流動規則的內容必須體現這種變化。
自由流動規則包括商品自由流動規則、服務自由流動規則、人員自由流動規則、資本自由流動規則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雖然同屬于自由流動規則體系,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和交叉,但也有其相對獨立性。商品的自由流動,一般通過競爭規則來保障,而服務的自由流動,有些可由競爭規則來保障,有些可以由資本流動自由規則來保障,可能還有一些需要專門的服務自由流動規則來保障,所以,在服務領域,會較多地出現法規競合的現象。資本的自由流動,主要是通過銀行法、證券法、投資法等法律制度來保障實現。目前,在商品、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三個方面,我國都制定有相關的法律制度,當然,這些法律制度還需要不斷修改和完善。這里要特別強調制定人員自由流動規則的重要性。人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員的自由流動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之所以能夠保持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每年有近1/5的人口在搬遷,各類技術人才和大批年輕勞動力在源源不斷地自由流動。其它發達國家如日本、法國、德國等每年的人口遷移率也至少在10%以上,而我國的人口遷移率只有4.99%[22],不到發達國家的一半。究其原因,是因為在人才流動方面,我國存在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有一項調查表明,在42種地方保護形式中,阻礙人才流動是最為嚴重的保護形式[23]。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勞動力資源的合理定價和優化配置,需要以人口的遷徙自由來保證。農村與城市之間巨大貧富差距的縮小必須以遷徙自由來保障[24]。因此,修改《公務員法》、《就業促進法》,制定保障人才自由流動的規則,既是完善促進市場統一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人才強國戰略必不可少的舉措。
3.自由流動規則的例外。正如同自由本身將受到限制一樣,商品、人員、服務、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并不具有絕對性,因為在一個共同體內部,還有其他一些價值如公共安全與秩序等比自由更為重要,所以商品、人員、服務、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必須受到限制,譬如在發生重大疾病如SARS、禽流感這類疫情時,政府可以對商品、人員等的自由流動進行限制;在國際貨幣收支嚴重失衡時,資本的自由流動也必須受到限制。這就是自由流動規則的例外。為了防止自由流動例外規則的泛化,立法必須明確列舉自由流動規則的例外情形,如(1)基于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的需要;(2)基于環境保護的需要;(3)基于維護公序良俗和文化的需要,等等。同時對自由流動例外規則的適用也應施加諸如比例原則等原則性限制。
(二)競爭規則
如前所述,在統一市場方面,競爭規則在不同共同體內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歐洲市場統一的過程中,競爭規則起著核心作用,所以,不管是原來的成員,還是新加入的成員,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歐共體競爭規則,即《歐共體條約》第81條和第82條的約束。美國維護市場統一的主要法律規則是憲法中的隱性商業條款,大部分破壞市場統一的地方保護主義案件都是根據隱性商業條款來處理的。美國的競爭規則—反壟斷法根據隱性商業條款制定,雖然在規制地方保護主義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還是有限的。我國尚未在憲法中明確制定自由流動條款,因此,目前維護商品、服務、資本自由流動的任務主要由競爭規則來承擔。由于實務部門、學術界對競爭法規制政府行為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沒有達成高度一致,所以,目前關于規制地區封鎖、市場分割行為的競爭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強,需要進一步完善。
1.擴大競爭規則適用于政府行為的范圍。《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都適用于政府行為,不過兩法的規定并不完全相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規定的是“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反壟斷法》所規定的是“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兩者雖然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別,但其共性都只約束行政權力,而對立法權與司法權沒有約束,另外兩者都只禁止行政作為,而不禁止行政不作為。這種過窄的規定不利于對政府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進行全面規制。因為,有些限制性規定是由立法機關特別是地方性立法機關作出的決策,如果法律只禁止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而不禁止地方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濫用,則難以發揮其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用;另外,在企業等市場主體限制、排除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時,如果地方政府不主動制止這種排除行為,則雖然這種行為是由企業作出來的,但其效果與政府的行為一樣,所以,競爭規則應當擴大到規制地方政府的不作為行為,即如果政府不主動,或在接到舉報之后不采取措施,則視同違反了國家的競爭規則。
2.明確判斷政府行為違反競爭規則的標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促進或保護公共利益,政府對競爭進行限制是經常發生的,但并非所有的對競爭的限制都構成違法。究竟哪些行為損害市場統一,哪些行為對市場統一沒有損害,法律必須明確規定一個判斷的標準。考察域外經驗,在判斷政府行為是否損害市場統一方面,一般有兩種方法:平衡分析法和歧視分析法。平衡分析法,也稱為不當負擔法,就是對限制競爭的法令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法令所創造的公共利益大于其限制競爭帶來的不利影響,則該法令是合法的,反之則是非法的。由于平衡測試法所要考慮的因素過于靈活,在實踐中難以把握,所以很少被人使用。所謂歧視分析法,就是將政府行為對本地和外地企業的影響進行比較,如果政府行為給外地企業增加了額外負擔,或為本地企業給予外地企業不能享受的優惠,這種行為就是歧視性行為。雖然歧視分析法所運用的基本手段也是比較,但這種比較分析涉及兩個不同的客觀存在的空間,即本地與外地,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國務院第303號令與《反壟斷法》中有許多禁止歧視的規定,但并未將歧視作為判斷政府行為違反競爭規則的核心標準,有進一步修改的必要。當然,歧視標準的可操作性也是相對的,由于地方政府可能會采取一些策略性行為規避法律的制裁,所以,在運用歧視分析法時,不能僅僅著眼于地方政府行為的表面,如立法文本,還要深入分析政府行為的目的與結果,即要將歧視審查標準深入至目的歧視與結果歧視層面。
3.建立政府行為豁免適用競爭規則的制度。在對地方政府適用競爭規則時,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是,是否有必要建立地方政府壟斷豁免制度。美國反壟斷法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就是州行為主義(state action doctrine),即對州政府限制競爭的法令原則上不適用反壟斷法。歐共體競爭法中也有國家行為抗辯制度。州行為主義、國家行為抗辯制度的法理依據是主權原則。而對不享有主權的政府機關,如美國的地方政府、歐盟成員國的某些管制機構,則不能享受反壟斷法的豁免。我國屬于單一制國家,主權由中央政府享有,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附屬機構,各級地方政府包括省級人民政府在內從來就不屬于主權單位,即使是民族區域自治機關,其享有的自治權也是有限的,所以,從主權理論角度考慮,斷無豁免地方政府的理由。
但中國是一個大國,其領土比歐盟要廣闊,人口比歐盟要多,而且各個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社會風俗習慣都有很大差異。從政治學上分析,這樣的大國應當實施聯邦制,因為聯邦制不僅更容易滿足地方自治的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促進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進而推動宏觀經濟高速增長、提高地方公共產品質量與效率、推動市場化改革過程[25]。然而,我國并不具備建立聯邦制的歷史、文化條件,有限的幾次建立聯邦制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為了調動單一政制下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中央政府在許多方面都賦予了地方政府自主權,并在立法上予以保障。如《預算法》承認各級地方政府有自己獨立的預算,《立法法》第63、64、66條明確規定,省級(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上位法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規。《稅收征管法》規定,省級人民政府可以決定減征或者免征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稅收。《價格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有權按照中央定價目錄規定的定價權限和具體適用范圍制定地方定價目錄。現實中,大量服務性的收費標準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既然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與法律上承認了地方政府屬于獨立的利益主體,那么,對于地方政府的某些行為,即使具有歧視性,也應予以容忍。
第一,市場參與者例外。這里不妨先舉一個具體的事例,媒體間或批露,某某市政府出臺文件,凡是動用本級財政購買公務用車,必須購買本地企業產生的汽車,或凡是本市所屬單位的公務接待用餐,必須購買本地企業生產的白酒,媒體往往將此作為負面新聞地方保護主義案件予以報道。學界對此亦多持批評態度,認為此類文件對于外地的競爭者來說不公平。單從公平競爭層面來評價,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不難發現,此時的地方政府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消費者在市場上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作為一名消費者,他有權決定購買誰的商品,旁人不得強迫和干涉,即使消費者主體是政府也一樣,此即消費者的選擇權。再換一個角度考慮,地方財政本來大多源于本地企業的稅收,原本就是為了促進地方公共利益的,地方政府用來自本地企業的稅收形成的財政,去購買本地企業的產品,增進本地的公共利益,符合市場經濟中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所以,如果政府作為市場參與者作出了優先購買本地商品的決定,那么它可以同私人消費者一樣不受競爭規則的限制,這在國外叫做市場參與者例外規則。市場參與者例外,只適用于政府自身作為市場參與者之情形,如果政府通過政令的形式要求別人用他們自己的錢購買其指定的商品,如要求市民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生產的防盜門、強迫購買其指定的企業的香煙,這種情形不能叫做市場參與,而叫做市場規制。在市場規制情形下,如果其規制目的、規制行為或規制結果具有歧視性,則不能豁免適用競爭規則。顯然,在適用市場參與者例外規則時,分清政府何時是市場參與者,何時是市場規制者十分重要。
第二,國有經濟例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跟市場經濟相結合,“最大的難點就在它的核心部門—作為經濟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跟市場經濟相結合”[26]。此語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改革開放3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實踐難題。一方面,現行憲法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國有經濟又往往成為市場條塊分割的重要動因,成為行業腐敗的重要根源。實踐與理論的這種反差似乎表明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契合具有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但理性地反思,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并不存在理論上的悖論。兩者的有機結合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來實現。這種制度創新就是競爭法律制度的合理運用。首先,對于那些競爭性的國有經濟(工程機械、房地產、汽車制造等),國家能夠退出的應當盡可能退出,如果不能退出,就必須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一樣,平等地適用競爭規則。其次,那些關系國家安全與國計民生行業的國有經濟,往往具有自然壟斷屬性,即具有不可競爭性,對于這類國有經濟,法律可以允許其采取某些限制競爭行為,豁免適用競爭規則。不過種豁免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第一,此類限制性行為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這種授權并不一定是法律強迫國有經濟一定要從事某種限制競爭行為,只要法律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可以采取某種限制行為即可。即使這種法律是某些企業或利益集團尋租立法的結果,該條件也算得以滿足。第二,必取有一個明確的政府機關對國有經濟的這種行為進行主動監督。所謂主動監督是監督管理機構采取了積極的作為行為,被動、依申請的、或不作為的監督,不能算符合該標準。第三,此類國有企業的財務必須透明。包括高管工資,國家補貼等。只有同時滿足了這三個條件,國有經濟才能獲得豁免。《反壟斷法》第7條關于“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的規定與反壟斷法中的其他規范并不協調,因為,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是反對壟斷、促進競爭,而不是反對競爭、保護壟斷。從比較法的視角考察,也很少有國家在反壟斷法中明確表示保護國有經營者,因為這種規定不僅沒有任何可操作性,反倒使人覺得立法者在有意偏袒國有企業,甚至是在為國有企業濫用其壟斷行為提供某種借口。為了消除社會各界對《反壟斷法》第7條的誤解,有必要將該條修改為國有企業適用除外條款。
四、實施市場統一基本規則應重視的幾個問題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得到有力實施,則不過是供人觀賞的“花瓶”。然而,在實踐層面上,法律規則的實施往往比規則的制定更為困難。特別是,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直接以地方政府的規制行為為規制對象,因而這種規制的實施更是難上加難。究竟怎樣才能使市場統一規則得到有效實施,學術界曾經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筆者基本贊同,在此不再贅述,但想強調以下幾點:
(一)要用戰略眼光看實施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的重要意義
穩定維護地方與中央關系的平衡,對于鞏固和穩定一個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對于大國的長治久安是至關重要的。當前政制下,維護地方政府積極性與中央權威之間平衡的杠桿主要有兩個。一是人事,即由中央向地方委派、指派地方行政長官來保障地方對中央政府的忠誠;二是財政,即中央政府通過掌握財權來控制事權。這兩種手段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障中央的權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當經濟不能實現持續發展,中央財力減弱時,中央政府調控地方的能力也可能會隨之削弱。所以,雖然控制人權與財權是維護中央權威,進而統一市場的重要手段,但仍不是長久可靠的手段。市場統一基本規則具有穩定平衡地方與中央關系的功能,是加強中央政府影響力和權威的新舉措。通過市場統一規則的實施,中央政府不僅可以將地方政府間的紛爭納入法治軌道,提高中央政府依法解決地方政府間紛爭的能力,而且通過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行為合法性的評價,樹立了中央政府依法解決地方保護主義的權威。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政府職能不斷轉變,地方政府人權、事權、財權等逐步擴大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建立新的加強自身權威的方式,不斷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無疑具有戰略意義。另外,在臺灣與大陸難以就統一事項達成政治性一致的情況下,客觀、中立、開放、具有促進資源最優配置功能的市場統一基本規則,對于促進兩岸統一的意義也是重大的。基于此種分析,中央政府對市場統一規則基本作用的認識,不能再停留在市場規制手段這一層面上,而應當有更長遠、更深刻的認識,應高度重視市場統一規則實施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二)市場統一規則之最高實施機構應當具有唯一性
市場統一基本規則最高實施機構的唯一性,是由該類規則所欲達致的目標決定的。不管是自由流動規則,還是競爭規則,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禁止市場分割、促進市場統一。市場統一,客觀上要求由同一個機構對市場統一基本規則進行解釋和適用,否則很有可能政出多門,產生新的市場分割即部門分割問題。所以,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的執行權在性質上是不可分的。現行立法顯然不符合唯一性要求。國務院頒布的第303號令所確定的執法機關有近10個,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所確定的“上級機關”也不是唯一的。多頭執法局面的出現可能有兩種原因:或者是立法當局沒有認識到市場統一基本規則之最高實施機構的唯一性要求,或者雖然認識到了,但不愿意觸動現有的利益結構,其中,后一種可能性更大。
要真正建立兩岸四地統一市場,就必須下定決心在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的實施方面解決多頭執法問題,建立統一的執法機構。憑空設想出一個新的執法機構在實務部門的專家看起來可能是幼稚可笑的。順著立法機關關于分步解決反壟斷執法機關設置問題的立法思路,由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負責市場統一規則的實施可能較為合適,畢竟其地位要高于地方政府(反壟斷委員會的主任由一名副總理兼任)。不過目前的反壟斷委員會在性質上只是一個議事協調機構,難以真正擔當實施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的重任,所以,必須對反壟斷委員會進行重大變革。其中有兩點變革必須首先予以保證:第一,反壟斷委員會由非常設的議事協調機構改為常設的行政機構;第二,全國人大或其常務委員會授予或委托反壟斷委員會審查規范性文件并宣布違反市場統一規則的規范性文件無效之權力。
(三)溫和執法應成為市場統一規則之實施基調
市場分割的成因與動機較為復雜,無論是其主觀態度,還是客觀結果,在倫理上難以找出太多的責難理由。對抗式的糾紛解決方式,過于嚴厲的法律責任,不僅不利于地區封鎖問題的解決,反而有可能激化其他矛盾,損害地方政府及其官員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積極性。所以,市場統一規制之實施應以溫和為基調。溫和執法要求:
第一,不主動審查違反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的抽象行政行為。違反市場統一基本規則之行為可以分為抽象行為和具體行為兩類。如果對市場統一基本規則的違反只停留在文件上,而沒有得到實施,那么,這種違反只具有抽象行為意義,并不會對市場產生實際上的損害后果。所以,對此類行為,執法機關不必理會,這一方面可以節省辦案經費,另一方面也可避免不必要的對立。
第二,處理紛爭以行政調解或行政勸告為主。對市場統一規則的違反如果已經從抽象行為層面轉化為具體行為層面,并有確定的受害人,則應當應受害人(不管是政府還是私人)的請求,對具體行為與抽象行為進行審查,受害人只就具體行政行為進行投訴,執法機關應主動對抽象行為進行審查。對于受害人與違法者之間的紛爭如營業損害或財產損害糾紛或其他糾紛,應以調解為主。對于抽象違法行為,以行政勸告為主。行政調解或行政勸告,不僅有傳統“集體本位”文化的支持,也契合現代和諧社會理念,還可以克服執行難問題。
第三,法律責任以發布同意令為主,輔之以禁令。目前立法規定的責任形式有“責令改正”,或給“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行政處分。有人指出,這種責任形式不足以對違法行為人構成威懾,因而主張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并舉。考察域外立法經驗,既有要求承擔民事責任的如美國,也有追究行政責任的如歐共體,還有追究刑事責任的如俄羅斯,但基本沒有三責并舉的立法例。總體考察,歐美對違反市場統一規則所設置之法律責任以禁令為主,民事賠償或行政處罰為輔。這種立法安排,主要是為了防止過重的行政責任或財產責任損害地方政府及其官方為其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主動性、創造性與服務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因害怕擔責而不愿提供對居民有益卻可能(哪怕這種可能性很少)受到市場統一規則審查的服務,則地方政府的地方服務功能將會受到很大的損害。所以,除了民事賠償之外,對違反市場統一規則的法律責任的設計應盡量避免使用財產責任,也應盡量避免使用懲罰性責任,應以恢復自由市場為其主要功能。如果通過行政勸告等方式能使違法行為人主動修改或廢除相關文件,則可以以同意令形式結案。對不聽從勸告的,可以發布禁止令。對拒不執行禁止令的,再追究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五、結語
自由流動規則與競爭規則是市場經濟大國維護市場統一不可或缺的制度。它們不僅具有保障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而且對于文化融合與政治融合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作為當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實施聯邦制的大國,制定完善的市場統一規則并保障其得以有效實施,對于建立長久穩定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實現包括兩岸四地在內的全國市場的真正統一,意義重大。雖然目前我國基本建立了維護全國市場統一的制度,但該制度從文本到運行都還有很多缺陷,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予以重構、完善。本文雖然提出了一些個人拙見,但研究視角、所提觀點可能有點片面或理想化。譬如本文雖然將論題定為市場統一,卻將研究對象限定在地方政府行為層面,而對如何規制中央政府特別是國務院各部門妨礙市場統一的行為(這無疑是我國市場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沒有作任何正面的討論。筆者的觀點是,中央政府各部門出臺的限制性規定絕大多數最終得由地方政府來實施,所以,對地方政府的行為進行規制可以達到間接規制中央政府各部門行為的目的。這種想法是否正確,有待于實踐檢驗,也期待同行指正。
[1]漢密爾頓,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M].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07,216-217.
[2]鄭鵬程.論經濟法制定與實施的外部性及其內在化[J].中國法學,2003,(5):114 -123.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7.
[4]沈立人,戴園晨.我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J].經濟研究,1990,(3):12-19.
[5]銀溫泉,才婉茹.我國地方市場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經濟研究,2001,(6):3 -12.
[6]樓繼偉.解決中央與地方矛盾的關鍵是實行經濟性分權[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1,(1):16-20.
[7]周業安,馮興元,趙堅毅.地方政府競爭與市場秩序的重構[J].中國社會科學,2004,(1):56-65.
[8]閆坤.財稅改革30年:分稅制改革的評價與展望[J].經濟要參,2008,(51).
[9]周波.我國政府間事權財權劃分的方式演進、面臨問題及對策建議[J].改革,2008,(3):58-64.
[10]里斯本小組.競爭的極限:經濟全球化與人類的未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103-111.
[11]楊其靜,聶輝華.保護市場的聯邦主義及其批判[J].經濟研究,2008,(1):99 -114.
[12]何智美,王敬云.地方保護主義探源—一個政治晉升博弈模型[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29(5):1-6.
[13]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J].經濟研究,2004,(6):33 -40.
[14]皮建才.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下的區域市場整合[J].經濟研究,2008,(3):115 -124.
[15]劉海波.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關系的司法調節[J].法學研究,2004,(5):36 -44.
[16]吳睿,唐麗寧.論地方保護行為的法律責任之設定[J].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4(3):47-52.
[17]鄭鵬程.美國規制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制度研究[J].中國法學,2010,(2):91 -102.
[18]格伯爾.二十世紀歐洲的法律與競爭[M].馮克利,魏志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2.
[19]鄭鵬程.歐洲統一市場的建立與對國家干預的規制[J]. 現代法學,2009,(5):175 -181
[20]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4.
[21]O Z Gamze.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Turkey[J].E.C.L.R.,1999,20(3):149 -158.
[22]楊云彥.中國人口遷移的規模測算與強度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6):97-207.
[23]李善同等.中國國內地方保護問題的調查與分析[J].經濟研究,2004,(11):78 -84.
[24]孟楨堯.讓“遷徙自由”縮短貧富差距[N].中國青年報,2006-01-19.
[25]劉亞平.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38-144.
[26]黃范章.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三十年—兼論創立中國特色的轉軌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4):5-11.
On Building and Application of Basic Rules for Market Unification
ZHENG Peng-cheng
(Law school,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Only in an open and unified market can the rare sources be optimally allocated.However,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quirement of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single market inevitability generates local protectionism in a big country.Academic viewpoints on how to overcome Chinese local protectionism such as establishing fiscal federalism doesn't get the rules which can directly strike against protectionism,and some viewpoints like judiciary's intervention are obviously unrealistic.Free movement rules and competition rules which are of both open and neutral might be the most suitable means that overcome market separation and keep the market unification.Consequently,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reconstruct and reform the rules of market unification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general,and should add a free movement clause in 1982 Constitution,extend the cover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governmental behavior.
market blockade;market unification;free movement rules;competition rules;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DF411
A
1002-9753(2011)08-0001-13
2011-03-16
2011-06-02
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競爭法與競爭政策。
(本文責編:辛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