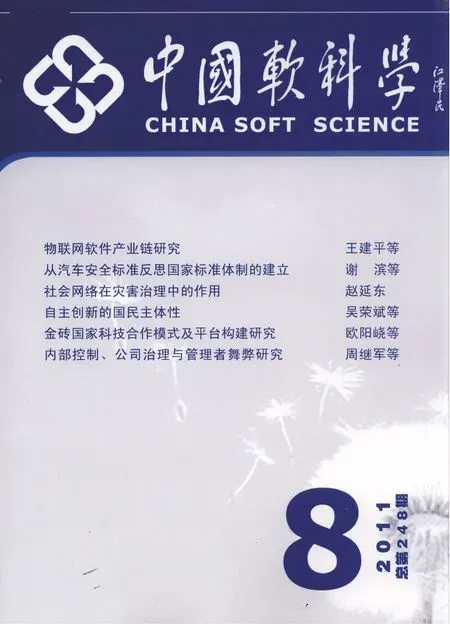自主創新的國民主體性
吳榮斌,田志康,王 輝
(1.華中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4;2.湖北省科技廳,湖北 武漢 430071;中國地質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自主創新的國民主體性
吳榮斌1,田志康2,王 輝3
(1.華中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4;2.湖北省科技廳,湖北 武漢 430071;中國地質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本文針對自主創新的爭論,首先從概念上挖掘了自主創新隱含的主體,并對自主創新進行了定義。認為自主創新是國家或民族企業或民族資本主導的、可持續的技術創新,它以中國國民主體性為基礎。然后從政府R&D性質、外資R&D機構的國家屬性、稀缺資源分配、R&D國際化、R&D國際合作等方面對自主創新的國民主體性進行了界定和闡述。其三,提出了堅持自主創新主體性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并對此進行了簡要討論。作者認為,自主創新的主要問題是R&D屬性問題,而決定R&D活動的主體屬性應是國民性。明確自主創新的國民主體性對我國的自主創新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意義。
自主創新;國民;主體性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在新世紀召開了第一次科技大會。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自主創新不僅出現在領導人的講話中,而且以文件、政策的形式,寫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在《綱要》中,自主創新是我國科技工作12字指導方針的第一位: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自主創新從一般微觀企業層面、從與單純技術引進的對立層面,第一次上升到宏觀、國家戰略層面。但圍繞著自主創新的主要性質問題,即主體性問題,還沒有解決。中國自主創新政策,特別是自主創新產品采購政策出臺后,一直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的反對。開始此項旨在針對內資的國家自主創新政策,由于以美國商會和歐洲商會的反對,不得不申明在自主創新產品認定等方面內外資一視同仁①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對在中國境內依法設立的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凡是在中國境內依法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的產品生產單位均可自愿申請認定。科技部就2010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答問。新聞中心-中國網news.china.com.cn 2010-04-12,外國在華企業視同本土民族企業,主張要以“全球化思維方式看待企業問題”,“外資企業是我國企業并保證其享有國民待遇”。“一家外商投資企業經中國政府批準成立以后,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管,向中國政府交稅,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它就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企業。如果始終將外資在華企業看作是外國企業,中國就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外開放的良好體制環境”。歐盟商會政府采購工作組主席吉爾伯特·范·克卡霍夫(Gilbert Van Kerckhove)認為,根據原產地標準,對本國產品的界定不應考慮生產企業的屬性,不應區分內資外資企業,原則上應當包括依法在本國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所生產的符合相關認定標準的產品,即按屬地原則界定本國產品,此觀點獲得一些人的認可②參見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王志樂有關言論。。在政策上,“鼓勵中外企業加強研發合作,支持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研究機構合作申請國家科技開發項目、創新能力建設項目等,申請設立國家級技術中心認定”[1]。關于自主創新產品認定規定是將外資企業視同內資民族企業的邏輯結果。一度有人建議取消自主創新中的“自主”二字,以避嫌[2]。最近,科技部在網上征求對有關政府科技計劃,包括863(含國防)計劃管理辦法的修改意見,其中,修改了原先的資格條件,將在華的法人均納入符合資格范圍[3]。
外資在華企業的“中國法人”與民族企業一樣是自主創新的主體嗎?他們可以享受自主創新產品研發的政府資助,自主創新產品的首購、訂購政策嗎?自主創新的主體是誰?是我們。而我們又是誰?在今天開放的環境下,它是一項普惠的政策嗎?還是導向封閉?從WTO國民待遇原則,本文不否認外資企業的國民屬性,但從自主創新及科技發展和主要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本文認為,在有關政策上要區別對待。以下從自主創新定義、政府R&D性質、外資R&D機構的國家屬性、稀缺資源分配、R&D國際化、R&D國際合作等幾個方面作簡要分析。
二、“自主創新”的定義及隱含主體
國家沒有明確定義自主創新的概念,僅對其內容表述為:自主創新包含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張煒、楊選良(2006)對此概念的歷史和涵義演變作過簡短討論[4]。但是,這些定義和內涵解釋隱含或忽視了一個重要表述,即它的主體性。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只是“自主創新”的內容概括和實現方式,不管是否“自主”都需要這些內容。或者說,這些內容只是創新的注解,非“自主”的解釋。跨國企業在中國國土上,也按照此內容,或原創,或集成,或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我們在討論這些定義時,也許在潛意識中將“自主”指我們,但“我們”沒有定義。或者在討論時,因不方便,或怕刺激外資,怕他們指責我們奉行封閉主義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自主”的主體。
在“自主創新”的英譯中,有多種表述,即“Independent innovation”,“indigenous innovation”,“self-innovation”或“self-determination and innovation”和“proprietary innovation”,后者是科技部的正式譯法。張煒和楊選良(2006)建議放棄“independent”或“independence”,在對外媒體中使用“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或“innovation”,或學術研究中用“self-oriented innovation”,或相近的譯法。但此建議不妥,因它沒有反映我國的科技政策基點。科技部的正式譯法:proprietary innovation,較好地表述了我們已解釋的內容,以取得知識產權為目標的產權或權利創新。但此譯法也有泛主體之嫌。我們是WTO成員國,要實行“國民待遇”原則,這樣,“自主”創新的主體是誰就成為問題,難怪在一次研究自主創新指標研討會上,一位專家反復提問“我們是誰”。此概念的“主體”天生或預設或忽略于所表述的概念中。因是預設,隱含而沒有清晰陳述,導致理解各取所需。
科技部前部長徐冠華院士在其《關于自主創新的幾個重大問題》(2006)[5]中闡述了為什么要強調自主創新。他的理由我們理解為:①此處沒有按小標題歸納。第一,因傳統比較優勢的喪失和產業領域對外技術依賴而阻礙國家競爭力持續提高。第二,技術創新能力是內生的,技術引進是外生的,外生的技術引進只有通過內生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消化、吸收,才能轉化為自主知識產權,才能轉化為核心技術的競爭優勢。第三,在國際競爭中,因國防安全、經濟安全、技術壟斷,通過正常貿易,技術要素的市場化轉移,后發國家很難得到核心技術。因此為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獲得核心技術,提高國家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優勢需要自主創新。也就是說以資源稟賦為主的傳統比較優勢要向以技術為主的核心技術競爭優勢轉換,此轉換需要自主創新。但怎樣獲得自主創新呢?這就是通過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來實現。而技術創新能力是內生的,需要建立自主開發的平臺,培養鍛煉自己的技術開發隊伍。在國外②包括在華的外國公司。對中國核心技術封鎖的情況下,就要培養中國國民技術人才,增強中國政府和公民掌握的經濟和科技組織的研究能力,它是內生的,是一國可以長期依靠的組織和人才,否則很難是“自己”的。在徐冠華院士的文章中,通篇沒有說利用外國公司、外國公民來進行自主創新,當然可以利用,但不是主體。這里隱含著排斥的對象。從他的闡述中可歸納出自主創新隱含的主體,即中國國民③此處是一普通概念,不包括外國獨資研發機構中中國公民的創新,理由后述。的自主創新。徐冠華院士此文章可以說是對自主創新的注釋。回過頭來,我們再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2006年1月26日)(以下簡稱《決定》)。《決定》雖沒有直接給出自主創新的主體性概念,但其內容直接、明白無誤地說明了自主創新的主體。
《決定》把增強自主創新作為國家戰略,在表述此戰略的意義時,強調實施此戰略以“激發全民族創新精神”,“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改變關鍵技術依賴于人,受制于人的局面”,“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民族”、“國家”和“愛國主義”是自主創新戰略主體的內涵。
《決定》在闡述自主創新的任務時,強調要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自主知識產權”構成了國家核心競爭力的要求,是自主創新的重要標志和任務。而自主知識產權只能是中國公司、公民或政府組織能控制、掌握使用的產權,否則談不上“自主知識產權”。怎樣培植自主創新,《決定》提出要創新體制機制,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深化科研體制改革等。在這些措施中,自主創新的主體地位再明確不過。它是通過調整我國國內經濟、技術資源配置,以獲得自有知識產權最大化為目的的“自主創新”。
但是在《決定》和徐冠華的闡述性文章中,均沒有直接給自主創新的主體下明確定義,這埋下了目前在實際政策制定和學術活動中的若干疑問,即外資在中國的獨立法人、外企中中國公民研究人員是否能參與我國自主創新活動,是否享受自主創新激勵政策,他們的成果是否算“自主創新”,“我國”是GDP概念、國土概念還是國民概念的問題。前面從徐文和《決定》分析中,在大的概念上不難得出結論,從知識產權的控制權角度,自主創新主體是國民范疇,當然它不排斥與國外的合作,因為它要利用全球資源。
依此,從國家層面對“自主創新”可下一狹義定義,即“自主創新”是指一國在國家主導下,本國國民和公私機構,通過自力更生與利用全球資源(資本、人力、設施設備等)相結合,開展以提高國家競爭力,實現國家意志,促進經濟繁榮和提高社會福利為目的的創新活動。它包括了“自主創新”的目的、途徑、主體和手段,這沒有涉及組織創新和市場創新。在微觀層面,“自主創新”可定義為:民族企業或民族資本主導的、可持續的技術創新。外購的產權,雖可控,如不能內化于企業持續創新和產業化之中,難以說做到“自主創新”。“自主創新”既是結果也是過程,僅對某次科技成果權利的控制是不夠的。
三、與自主創新有關的問題分析
回答自主創新的主體性問題,有必要討論政府R&D性質及主要發達國家政府R&D活動承擔主體、外資R&D機構的國家屬性、國家稀缺資源分配、R&D國際化與國際合作問題。一些人認為,外資在華企業也創造稅收,來自于稅收的政府R&D資助也應包括外資在華企業,跨國公司是國際公司,沒有國家屬性,R&D國際化了,在全球化時代,要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沒有必要強調主體性問題。事實是這樣嗎?分析表明,不管是從外國實際做法上,還是從政府R&D性質、跨國公司的屬性上,亦或是稀缺資源分配、R&D國際化以及國際合作上來看,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中國國民。
(一)政府R&D性質是積累人力資本和組織知識資本
討論與確定自主創新主體性的重要政策含義是決定政府R&D支出性質,以及相關的資助對象和范圍,而象產品等政策到是其次。如自主創新主體是國土范圍,或GDP意義上,那么在中國的外國機構和個人,即“中國法人”均可以獲得政府R&D資助,否則相反。即政府R&D性質決定著自主創新的主體性。
企業R&D支出,其目標是攜取壟斷或獨占利潤,獲取知識產權和競爭優勢。因知識產權(這里主要指專利及相關權利,如計算機軟件、植物新品種等)是私權,是排他性權利,因此私人企業R&D支出性質是封閉的,高度目的性和自我利益取向的。這里所說的封閉性是指R&D活動產出的排他性而言。一般來說,企業可以向社會上采取競爭性授予研究與開發經費,但產出成果是要受控制,①這里不討論特殊性企業公益性,或基礎性開放R&D支出,因它沒有一般性,而是有向社會捐贈性質。即它不會將產出成果,特別是與其產品競爭有關的成果無償地轉向對手,或無緣無故向社會公開。就是公開,在產業競爭領域,開發類研究,也是基于某種知識產權戰略。一般來說,大型或跨國企業傾向于在內部進行R&D活動,這是其R&D目的性的結果。
但是,由于R&D有正的外部性,其溢出效應使社會回報大于私人回報,企業研究與開發投入不能完全自收益中進行補償;企業R&D是沉沒的成本,由于不完全競爭和市場壟斷,使行業R&D水平總是相對不足(非最優水平投入);R&D活動充滿風險,不穩定,信息不對稱,對R&D的支出成本高昂。這就是阿羅(Arrow,1962)-納爾遜(Nelson,1959)[6]有關 R&D 投資的經濟學原理。按此原理,在競爭的市場中,企業沒有R&D投入的積極性,導致投入過少,不利于社會進步。但是競爭的市場也可能R&D過度投資,競爭者因R&D活動而產生的贏者通吃而產生負的外部性,一個公司可能沒有考慮其自己R&D活動對其他公司成功的可能性,這種負的效應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易產生過度投資。在實踐中,社會R&D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國外50%左右的支出是研究人員的工資和補貼①中國R&D人員支出大約在30%左右。,這使得所創造的知識資產部分是靜默的,并鑲嵌在人力資本中,如果這部分人員離開,相應的知識資產也會隨之失去。
阿羅-納爾遜的新古典市場失靈理論:知識產生結果的不確定性,知識產生本質上的不可分性,以及作為公共物品難以補償,為上世紀50年代至今的R&D政策的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7]:
R&D和知識的公共物品特征不能激勵私人從事R&D活動;競爭性體制產生較少的基礎研究;私人投資者厭惡風險,不會在結果不明確的重要技術進步中投資;公司的利益取向導致短期創新政策,不重視復雜研究項目的長期利益;自基礎研究中的利益很難專用;大多數中小型公司供養不起大的R&D部門,因此不能夠為他們的創新活動提供技術基礎;公共資助機構的基礎研究有外溢效果,它會刺激私營公司的研究活動;為了保證新技術擴散,并因而促進所有相關行業技術進步,一般公眾也應能獲取基礎研究成果;由于研究成果的私人占用,知識生產的秘密性阻礙技術擴散和經濟現代化。
與市場失靈的阿羅-納爾遜原理相對應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應對R&D活動提供資助或補貼,以產生對社會有益的知識。
市場失靈原理的優點是明了、清晰,它為政府干預提出了簡單的判斷標準,但它也有局限性,如它含蓄的假定,在所有相關技術活動中,市場機制對其他機制有競爭優勢,它沒有體現創新活動的多組織、多功能、多方向、多體系的特點,對發達經濟體系的動力學基礎陳述不當。因此作為技術政策的制訂的原理和指南,它有不足。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對此理論的局限性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制度失靈原理。公共干預的制度失靈原理把創新政策作重點,即通過建立創新基礎結構促進技術和創新機會的出現。創新政策領域包括教育、科學、技術、勞動市場和行業。比起市場失靈原理,它更復雜。市場和制度失靈原理不相互排斥,每種都有局限性和缺陷。在許多領域市場失靈仍是技術政策的基礎,它仍是目前政府R&D公共政策的基石。
這些原理雖然回答了為什么政府應干預R&D活動,但沒有直接回答一國R&D活動的主體性問題。我們認為,主體性問題仍包括在這些原理之中,即R&D活動是通過資助研究人員來進行的,R&D活動是一連續的過程,其部分知識、經驗積淀在人的腦海中,失去這些人就失去許多R&D積累,失去R&D的連續性,也就失去作為R&D活動目的之一,培養R&D研究人員的作用。作為國家來說,從事R&D活動的研究人員是有歸屬的(作為公司也如此),這就是為什么絕大部分國家,和國家的絕大部分R&D資助是面向本國國民的重要原因。這里我們把它稱之為R&D活動的人力資本積累原理。另外,現代社會R&D活動依賴于一定組織,它亦存在一定組織形式中,它的部分知識以知識產權(包括技術秘密和訣竅)形式貯存在R&D活動組織中,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將政府資助R&D活動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授予了承擔單位②美國80%左右的專利是以公司形式獲取的。,這些承擔單位(或組織)是有地域和版圖概念,由于世界經濟的國家競爭性,知識產權是經濟競爭力來源之一,因此這些組織是有國家屬性概念,而國家R&D活動的主要承擔者應是此國家所屬的組織,因此也可解釋一些組織招募外藉人員在此組織內承擔本國R&D活動原因,但此前提是其知識產權是歸屬于所在組織。如同個人一樣,組織是公共R&D活動的載體,是R&D知識的保存、傳遞、持續進行的場所,因此從R&D活動的知識產權歸屬和知識的傳遞、持續性來說,R&D主體屬性是國家以及國民控制的組織。這里我們將此歸納為R&D活動的組織資本-知識累積原理。由于知識產權的排它性,在競爭性市場中,R&D活動的人力資本和組織資本-知識的累積原理,決定了R&D活動的主體屬性-國民性。
為彌補市場失靈原理的局限性,在實際R&D活動中,出現了許多國際合作組織,出現了單邊或多邊合作協議,出現了國際R&D人員流動的競爭與促進政策,這亦是公共干預的制度失靈原理所研究的內容。但創新和R&D活動的這種趨勢并沒有改變R&D活動的主體性質,只是為強化這種主體性才存在這些單、雙邊或多邊合作協議,出現這些鼓勵、支持吸引R&D人員的政策。注意,這些政策或合約也是有限度的,除為彌補相對缺乏的知識、技術以及資金設施的不足外,大多數合作和外聘人員均有一定的知識產權制度安排。一國的R&D活動,從長期看均是為本國積累人才,創造屬于本國“支配”的知識產權。不排除少數有特定目的,以解決某一技術問題,或發展某一學科為目的而進行的 R&D國際活動,但主體應是明確的。
(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R&D活動承擔主體是其國民及其相應組織
許多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研究與開發大部分資助對象(包括間接的R&D采購)以本國國民為主。知識的獲取是開放性的,而資金的使用是封閉的。所謂自主性體現在對資金的使用和使用此資金所產生的知識產權的控制上。為保證這種自主性,通常采取如下措施。
1.項目申報單位所有權資格限制
幾乎所有重要的美國政府研究開發資助計劃,特別是針對企業或產業發展的計劃,如美技術創新計劃(TIP),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LR)、先進技術計劃(ATP),申報者須是美國公民所擁有的機構。如果申報機構由風險投資機構占有較大股份,此風險投資機構的實際控制人也須是美國公民①見美能源部科學辦公室:SBIR/STTR第一階段資助通知,2006.9.20;NIH資助政策聲明(2003.12);美國公法110-69-AUG.9,2007.121 STAT.593。。
美國“小企業創新研究”(SBIR)和“小企業技術轉移”(STTR)計劃,的主要資助對象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SBIR和STTR的區別在于一個僅是小企業自己的R&D活動,一個是與相應實驗室合作活動,目的主要是將美國有關實驗室研究與開發可以商業化的思想轉化為產品。該計劃對申請企業規定了明確的資格條件:資助的主要研究人員和其他人員不要求是美國公民,但機構所有者須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如NIH有關資助條件SBIR/STTR政策申明:
(1)位于美國,主要在美國運營,或通過交稅或使用美國產品、材料和勞力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的營利機構。
(2)合法的獨資、合伙、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資、協會、信托或合作社機構。如果是合資機構,外國機構份額不超過49%。
(3)按照聯邦法規匯編13,121.702(A)所提出的條款,企業最少51%的份額由一個或多個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擁有和控制,在合資企業的情況下,此合資企業的每個部分的51%必須由一個或多個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擁有和控制。
這個條件可簡述為美國人或美國人控制的機構才有權利申請和獲取資助。
美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在它的資助政策陳述(2003年12月修訂本)中對申請資格規定,一般來說,國內外公私營利或非營利組織都有資格收到資助。但由于法令、規章和政策限制,一些計劃或項目有資格限制,如對外國機構的限制。資格的決定包括確認申請者身份。要求申請者提交身份證明文件。除了檢查組織的資格,NIH還要考慮其它因素,它包括申請者在計劃項目中的任務、實施項目所在的地域、主要研究人員(PI)的任務、雇主和居民身份。如NIH在小企業研究資助項目確認程序中,要求列出主要或所有股東名單,包括風險投資公司,每個投資者或公司所持股份比例,并要驗明外國投資者或持股者。由受資助者所占用的研究場所不能與另一個組織共用,而且要在此研究者的控制之下。所有的資助項目必須要在美國境內的機構中實施。
2005年,美國在小企業創新計劃中,形式上放寬了此資格條件。即為了鼓勵風險投資,將被資助機構由美國自然人控制改為可以由公司控制,但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須控制此公司51%以上,實質內容沒有變。
2.研究人員身份限制
美國許多科技計劃雖說同意研究人員可以是來自外國的,但首席研究員須是企業聘用的美國人,如是外國人須經批準才許可承擔研究任務。一些研究計劃或協議,如美聯邦航空管理局與國家高技術中心的有關“下一代航空運輸系統”就明確承包商的每個雇員應是美國公民或合法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8]。由此合同所規定的外國人和外國公民必須在過去5年中有3年居住在美國,要接受安全篩查等。
3.所有權變化申報與審批制度
澳大利亞和以色列對此有明確規定。
如以色列1984年頒布(后又修改)的工業研究與開發激勵法[9],由以色列工業貿易和勞工部屬下的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監督實施。該法對接受資助公司的所有權變化申報與審批有明確規定,違反規定要判3年監禁(47A)。該法規定,有興趣投資以色列公司的外國公司,或尋求與以色列公司進行并購交易必須保證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 process),包括所并購實體是否得到OCS資助。如果目標公司的知識產權開發得到OCS資助,即使部分資助,其所有權變化、技術和生產權轉移要受到某些限制。按照法律,接受資助者的控制和所有權變化要通知OCS。特別是,接受資助的公司不僅要通知OCS控制權的任何變化,還要對其控制手段(包括投票權,任命董事或CEO權)轉移給非以色列人或實體要告知OCS。這種轉移會在接受公司中導致非以色列成為“權益持有人”。在某些情況下,沒有OCS的準許,接受資助的公司不能向外國或國內股東發行股票。當然,OCS的資助在以色列高技術公司中非常普遍,控制權變化需要獲得批準并不意味著對私募(private placement)、并購交易或公開發行構成障礙。受資助公司要想把自資助中形成的訣竅和技術轉移給第三方,不管是整體或部分都必須要獲得OCS的批準。在國內實體間轉移,只要承諾與資助相關的義務,包括轉移限制和特許使用費(Royalty payments),會得到批準;如受資助公司意圖將技術訣竅繼續商業化,就容易得到批準。然而,如果想將此技術訣竅在以色列轉給非以色列的實體,在一些情況下,要得到OCS批準,它有特定的限制和付款義務要求。這些限制會使外國技術公司收購以色列OCS資助的公司而得以生存下來,并可以防止以色列目標公司的源代碼(source code)和其他展示的訣竅轉移到它的新的非以色列母公司之中。
澳大利亞R&D Start(為工商企業研究與開發和商業化進行資助和貸款的計劃)和生物技術創新基金(BIF)的資助協議要求受支持者須向政府相關機構提交一份“控制變化”報告,在實際控制變化發生前要申請得到書面同意[10]。如沒有申請或申請還沒有同意,資助者的控制權發生了變化,資助協議會終止。如果對R&D start或BIF計劃目標造成或可能造成有害影響的話,會要求100%歸還資助款。該國法律(Commonwealth Corporations Act 2001)規定,控制權變化包括:接受資助公司出售給另一公司;設立一個新的海外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并且將R&D項目或知識產權轉讓給此公司;首次上市(initial listing on)交易股票或通過進一步公開發行股票(public share offerings);在證券交易所捆綁出售股票;或出售母公司。
4.地域限制
一是相關采購地域限制;二是R&D活動和所研發的產品及相關服務的地域限制。
如美國的在美國購買法(Buy America Act)和購買美國國貨法(Buy American Act),前者應用于美聯邦公共交通管理局(FTA)和聯邦公路管理局(FHWA),后者可以應用于所有美聯邦政府直接采購的商品。在美國購買法規定,由FTA和FHWA超過10萬美元與公共交通有關的采購要應用此法。它不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WTO政府采購協議范圍。它要求交通項目采購要使用美國材料和設備,鋼鐵及其制造的產品要求有100%的美國產品。按購買美國國貨法,所有美國聯邦政府機構購買的物品,其價值超過一定限度,就須遵守此法的規定(服務不應用于此法),即:所有公共使用的物品(用品、材料或供應品)必須是在美國生產的,所生產的產品必須用美國材料。美國許多州和市也有包括此內容的采購生產地域要求。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第10章和WTO政府采購協議,允許美國政府的這種采購優惠。
通常歐美各國政府資助均要求其相應R&D活動和所研發的產品及相關服務在國內進行。一般來說不資助境外的R&D活動。但如果研究材料或種質資源在國外,或為獲取某種知識或技術會支持某種國際合作研究,條件是要有知識產權安排。
5.采購例外與“其他交易”協議
美國是WTO政府采購協議(GPA)的簽字國。GPA是一個“多邊”協議,它要求所有簽字國遵從非歧視原則并執行所保證的采購程序,每個GPA成員都有權與其他成員政府合同競爭。為符合WTO政府采購協議的條款,并適用于雙邊協定,美國利用WTO的R&D規定,即R&D服務不包括在GPA中,把R&D服務采購—商業化前期產品或服務(pre-commercial)采購從公共采購中分開,把一個預先設定并日益增長的聯邦政府R&D采購市場留給中小企業(SBC)。它規定,所有低于一定數額的采購合同都要給了SBC,采購預算的2.5%(此比例有逐年遞增的趨勢)要留給SBC所進行的高技術創新R&D。美國小企業R&D采購采取“其它交易協議”程序。
“其它交易協議”與一些財政資助手段如撥款資助、合作研究協議不同,一般應用于采購[11]。但它只是一個合同工具,不是標準采購合同,與合作協議和財政資助有關的大多數法律不適用于“其他交易授權”所談判的合同。不適合管理程序合同的美聯邦法規。如他們不要求符合聯邦采購條例(FAR)及其增補要求,不要求符合采購合同的法律,如誠實談判法(Truth in Negotiations Act)和成本會計標準(Cost Accounting Standards)。其研發樣機計劃(R&D prototype programs)的“其他交易”被認為是沒有規則的政府合同。上文所述的有關“下一代航空運輸系統”的協議就明確,此協議是一種“其他交易協議”,不是一個采購合同、資助或合作協議,不得參照或暗示按任何聯邦法律或規章條款來解釋此協議。
6.比較利益與對等條件
怎么對待在美國的外國研發機構,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發生過激烈的辯論。首先,克林頓時期的勞工部長賴希(Robert Reich)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我們是誰”的文章,他警告,美國公司的運營越來越全球化,他們與美國的經濟聯系在很快消失,政策制訂者要區分美國經濟利益和美國公司的利益。美國是否能提供高工資的職業和支撐不斷增加的生活標準,并不憑籍美國公司的實力,而依賴于位于美國境內的經濟活動的競爭力和力量。1991年,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克林頓總統國家經濟顧問,第16屆白宮經濟顧問會議主席,總統國家安全會議和國內政策會議成員,是克林頓第一任期的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程序的設計師)在《美國展望》上回應“他們不是我們”。她認為,賴希所指的情景還沒到來,國家的經濟命脈仍然緊緊地與該國國籍公司的成功相連;賴希的國家經濟政策假設與現實的不符。許多外國市場被高度管制,常對美國不利。美國不能僅培養優秀勞動者,然后指望市場力量把高工資職位帶到本土。泰森認為美國跨國公司在重要程度上,仍是“我們”。而“他們”(外國在美子公司)不是“我們”。她主張的在美國內以國籍為對象的經濟與科技政策,對至今的政府研究與開發支持政策產生重大影響。針對在美外國子公司,以國籍為對象的科技政策,可簡單歸結為經濟利益和比較待遇原則。
如美國先進技術計劃/能源政策法(ATP/EPACT)規定[12],外國公司獲取美國政府R&D資助資格須通過經濟利益測試和非歧視測試。前者是了解美國政府資助外國公司申請者是否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后者是了解外國公司申請者的國家是否給予美國公司相同的待遇。
經濟利益測試:按ATP/EPACT規則,如果一個公司的參與會有助于美國經濟利益,此公司會有資格得到財政援助。經濟利益由下述證據證明:
(1)在美國研究、開發和制造業方面的投資;
(2)對美國就業有重要貢獻;
(3)同意在美國生產所形成的產品;
(4)同意自“競爭的”供應商那里采購零部件和材料。
比較待遇測試:此條款不應用于特殊公司,而是對其母公司的國家。即其母公司的國家必須提供給美國擁有的公司:
(1)類似于此法所許可的內容,與其他公司比較,有參與合資企業的機會(對應的R&D計劃條款);
(2)比較其他公司,有當地投資的機會(當地投資條款);
(3)“適宜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條款)。
概括說,按照經濟利益原則(亦稱經濟利益測試),如外國公司在美的子公司欲參與美ATP/EPACT或TIP(技術創新計劃)等科技計劃須要向美國有關審批機構提供其公司在美研發和生產投資證明,對美國就業貢獻證明,并同意有關資助所產生的科技產品在美國生產,在“競爭的”供應商那里采購供應品(零部件和材料)。前兩項強調公司過去的行為,后兩條是為未來的行為提供承諾(保證)。與此相關的是比較待遇原則(測試),它應用于申請參加美國有關科技計劃子公司的母公司所在國的行為政策。它由3個內容組成,其一,母公司所在國對美國子公司與其他公司一樣提供類似于參與美相應科技計劃的資助機會,提供在當地投資機會,提供適宜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即對應R&D計劃條款,當地投資條款和知識產權條款。就是說外國子公司欲參與美國有關科技計劃,獲取政府R&D資助須符合美國經濟利益,美國子公司在相應國家得到相應的“國民待遇”。
與經濟利益測試類似的如德國,它增加了永久設施條件。德國規定,如果外國公司想得到德國政府研究資助,必須符合下述條件:外國公司必須在德保持永久的R&D設施,證明在德國使用由此所產生的技術的主要意圖;充分利用此R&D的成果,將支持德國的生產能力;政府資助的R&D會有助于擴充公司在德的R&D能力,并作為工商業發展的地點,增加德國的吸引力;作為政府資助R&D的結果,外國子公司多少將會更獨立于他們的母公司。
7.R&D采購(商業化前期創新采購)
第一項(首發)產品或服務的原始(original)開發可以包括在有限生產或供應之中,以顯示應用試驗成果并在數量上證明生產或供應該產品或服務符合可接受的質量標準。它不擴大到為形成商業能力或回收研究和開發成本而進行的大規模生產或供應。即為首次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而進行的研發可以進行中試,或實驗性的生產,此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不在WTO政府采購范圍,而政府在首發產品或服務的研發階段就進行采購,以滿足WTO政府采購R&D例外條件:原始開發和應用試驗。美歐實行創新采購(R&D采購——商業化前期采購)政策,以將外國供應或生產者排除其創新產品或服務的政府采購市場之外,并促進本國公司的技術創新活動。
創新采購的核心是R&D采購。通常把一個新的想法變成一項商業產品或服務的研究和創新生命循環分4階段或4個步驟或水平,即初始思想,建議方案,樣品,商業前期產品/服務(所謂前產品/服務,前商業化產品/服務)(圖1)。
框圖中階段1不適用于GPA,階段2和階段3是一個評估和選擇的過程,到階段3后,才進入通常的公共采購范圍。WTO GPA簽字國,在此階段采購受此規定約束。政府R&D采購或資助就在R&D1-3階段。它可以有多個供應者,一般階段1在6個月左右,階段2和階段3均在2年以內。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美航空航天局以及引申的計劃,如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就使用政府R&D采購進行創新支持。歐盟創新前-商業采購專家組建議參與R&D采購參與條件為:營利組織;在歐洲經濟區有正規的R&D中心;首席研究員由建議公司雇傭;沒有雙重資助。雖說沒有像美國那樣要求建議公司有5 1%的所有權,但地域限制是非常明顯。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谷竣戰(2005)在其題為《世界各國科技計劃對外開放現狀和做法》的研究中認為,“對外國政府、機構或個人給了本國國民待遇,允許他們像本國的機構或個人一樣申請并承擔國家科技計劃的項目,這樣的情況極為罕見”。一些國家明確表示本國科技計劃不對外開放,一些國家雖說有某種程度上對外開放,但施加諸多限制,如屬地、合作、計劃類別、區域、渠道等限制。少數允許外國的科研機構,個人申請本國科技計劃的,需要本國的合作者,一些成果產業化需要在本地,一些開放的科技計劃僅提供差旅費、研討會費用。

圖1 創新生命循環圖
從政府R&D支出的目的及各國實踐上看,政府R&D支出具有明顯的國民性、封閉性(國際合作雙邊或多邊協議除外,此問題后面討論),而作為R&D活動結果或表現形式的自主創新其主體具有國民性。
(三)外資R&D機構仍有國家屬性
模糊自主創新主體性最重要因素是對外資R&D機構的國家屬性和法律地位的認識。這里包括對跨國公司的認識[13],對跨國公司在國外子公司的認識,對其涉外R&D機構的使命和任務的認識。
有人認為,跨國公司是一個國際公司,它追求經濟利益,基本上不受主權國家的制約,目前還沒有國際法制約。跨國公司的子公司與母公司往往不是統一法人,他們是分設的機構,按有限責任原則承擔義務與責任,遵守東道國的法律,向東道國貢獻稅收并創造就業機會。跨國公司子公司的R&D活動,在給東道國創造就業機會并吸引主體科技資源的同時,還提高在東道國子公司的產品市場競爭力,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因此跨國公司子公司應享有與東道國一樣的權利與義務。除公平、一致的稅收外,還應享有與東道國內資R&D機構的一樣權利與義務,獲取政府R&D資助,承擔一定的國家任務。再加之WTO普惠制要求以及對之片面理解,我國一些地方出臺的吸引外資R&D活動政策,就給了外資R&D機構的承諾。少數學者也力推給與外資R&D機構優惠政策,如建議出臺“研發提升計劃”,對一些外資研發機構給予資金資助,有條件吸收外資研發機構[14]。
這里要澄清幾個認識,一是跨國公司的國家屬性與責任,二是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東道國和母公司的關系,三是跨國公司子公司R&D活動根本屬性。
首先跨國公司不是沒有母國,除少數跨國公司外,均有明確的國家屬性,受母國政治制約,就是一些學者所提的沒有明確母國的跨國公司,他的出資人及主要所有者的國籍,決定他/她要受公民義務所制約,如是上市公司,還要受上市所在國的有關法律所影響,一些強國還以國內立法來影響他國公司的活動。從歷史上來看,跨國公司與母國是一個主體的兩個方面。母國政府往往為跨國公司在全世界的擴張創造條件,如推行自由市場理念、民主制度,要求開放市場(有時甚至不惜以武力為手段),而跨國公司在此基礎上擴張市場,創造利潤,甚至還強行推廣其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提高其母國經濟、政治實力。在許多發達國家外交隨行人員名單上,有大量跨國公司領導人。一些跨國公司是母國的政治、經濟象征。在一定概念上,一些跨國公司賦有母國國家的義務和一定政治使命,雖然追求利潤是其第一使命,但在一定時期,一定環境下,跨國公司的國家屬性盡現。
跨國公司子公司往往在東道國注冊成有限責任的獨立法人,遵守東道國法律。但要分清,表現為債務債權的經濟關系與所有關系,即屬地管理關系與屬人管理關系。母公司仍可通過屬人管理關系,來控制子公司。子公司須要體現母公司的意志,有限責任雖為子公司的經濟活動提供某種保障,但反過來,很難為子公司的一些行為追究母公司的責任,因此不能說子公司不受母公司影響、制約。子公司除完成其母公司,主要出資人的經濟目標外,必要時,還要完成其全球戰略目標。子公司的R&D機構類似,他們不僅為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產品的競爭力提供保障,而且許多還要為母公司的全球或區域戰略服務,這些R&D機構是設在東道國,但不屬于東道國,它只是利用東道國資源及基礎設施而己,如利用得好,東道國可以從中獲取一些外溢收益,利用不好,可能對東道國的長期科技競爭力造成影響。外資子公司R&D機構可以成為東道國創新體系一部分,但必須心中有數,可利用,不可依賴。一國的創新主體仍是一國自己,自己的人才、科研機構及一些關鍵民族公司。
(四)稀缺資源分配國民及其機構優先
確立自主創新的主體性,核心問題是稀缺資源的分配,就是外資R&D機構是否視同內資一樣享受稀缺資源的分配權。稀缺資源這里主要討論人才和R&D經費,特別是政府R&D經費。政府R&D經費包括財政各類科技計劃R&D資助、產業化資助(補貼)、政策性貸款貼息、稅收減免等。最重要的稀缺資源是人才,但因人才與經費支持息息相關,吸引人才就必須有經費支持,在一定的計劃項目中,就包含培養、吸引人才的內容,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目前最重要的稀缺資源是財政R&D經費,全世界沒有那個國家說他的R&D經費充沛。在一定制度與政策下,人才規模與質量是政府財政R&D經費規模的函數。在假定科研經費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一定情況下,提高政府和企業R&D支出規模,相應會提高R&D人才規模與質量。吸引穩定使用人才背后就是R&D經費支持程度。所以確立R&D稀缺資源優先分配主體性,就是確立R&D人才的優先培養主體性。R&D資源分配可分多個層次:
第一,財政性直接資助——法人主體有限定的R&D資源分配:1.R&D機構運行費;2.R&D機構常規人員聘用;3.國防項目;4.國家目標研究資助(競爭性或非競爭性)。此類資源分配是一國R&D活動中的核心,具有較強的國民性。并不是說其中一些項目不能委托給跨國公司,或進行外包,但從培養人才或積累知識、經驗角度,應以國人為主,這里應有戰略眼光。有時關鍵項目研發,外方不會與我們合作,不愿進行技術交流與轉移,但如果我們自主進行研發,反而有助于技術轉移與合作,最起碼會降低技術轉移成本,加速技術消化吸收。
第二,財政性補貼或成本分攤項目。此類項目對象以企業為主,主要是政府為減少企業R&D風險,減少R&D成本,鼓勵企業R&D支出而采取的獎勵性補貼項目,它面對的是一般競爭前市場,它基本上是以本國企業為主,不排斥,在一定條件下外資R&D機構參與其中(如支持在華企業增強其產品的全球競爭能力而給予一定補助)。
第三,利用間接財政支持的R&D項目,它的主要工具是稅收優惠(對企業R&D支出實行稅收減免、抵扣等)。這類項目受國際協定制約,實行普惠制。中國的獨立法人均享受此政策優惠,它的直接目標是激勵增加企業R&D支出,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稅收資源稀缺性在于明確劃分R&D支出范圍,只要不對正常稅收產生大影響,從長遠看它不屬于稀缺資源。如果作為一個政策工具,對企業領域進行區別性選擇實施,則它又為稀缺性資源。
第四,政府R&D采購、首購、訂購。政府R&D采購對企業自主創新將產生重大影響,我國先前出臺的企業自主創新產品采購、首購、訂購政策,由于受到外資的反對,不得不一再重申包括外資在華法人的“中國法人”資格。我國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府R&D采購政策。采購、首購、訂購政策對企業來說是稀缺資源,利用此項資源服務于自主創新的主體——具有中國國民屬性的企業,面臨著挑戰。對有重大影響或對國家國防、經濟實力有重大影響的技術,外方不會“供貨”,而一些普通技術產品,東道國也不愿培植非本國民族企業競爭對手,有時,它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第五,公共服務平臺資源。這里要分類,基礎性一般行業與技術領域可開放,非基礎性,關系到本國競爭力和研發優勢的不輕易開放,但可實行資源平等交換。這里要有政策運用的靈活性,掌握資源開放的節奏和對象。當某一領域本國不具備條件時,可與外方進行合作,開放一些研發平臺,以利培養人員,積累知識。對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的開發,在我方條件不具備時,要按照成果共享原則進行開放。
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全世界對人才的爭奪日趨激烈。人才的爭奪主要是對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以及對急需人才的引進上。人才培養和使用就需研究與開發項目和經費,這不僅僅是學校學習的問題。中國社科院在《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中認為中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怎么留人,靠事業留人,就是從事自主創新事業。為應付全球人才競爭,2008年底,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制定了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2010年國家發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各省市亦制定了相應高層次人才引進政策。人才引進的重要措施就是給予科研課題和經費,提供科研和生活條件。引進急需的海外高層次人才與自主創新的國民主體性不矛盾。他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實現自主創新目標的基礎。所引進的人才不是獨立的而是歸屬于本國國民R&D機構及企業之中,他是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一個部分。當稀缺資源分配優先性發生變化時,分配原則亦發生變化。
總之,稀缺資源分配要立足于本國國民R&D機構及企業,并且在具體運用時有一定靈活性,但主體不應有任何含糊。即最稀缺資源分配要以本國國家或國民所屬R&D機構為優先分配次序;在鼓勵、間接補助企業R&D支出上實行普惠制,對在中國境內注冊的所有企業(在華法人)均實行同類政策。
(五)R&D國際化與自主創新的主體性
1.R&D的國際化特點
傳統上,跨國公司僅在東道國進行生產、銷售活動,而將R&D活動留在國內,但近10年來,這種現象正在改變。R&D的國際化呈現如下特點①此節內容參考[美]《科學與工程指標 -2006、2008》[R];DG研究:關鍵數字2003-2004[R];聯合國貿發會議{R},2005。:
(1)R&D投資在傳統三方流動中極不平衡。在歐盟15國、美國和日本三方R&D投資流動中,美國吸引了來自歐盟15國公司1/3以上R&D,美國、英國是最大的R&D凈流入國。日本也是凈流入國,但規模較小。
(2)自1994年到2004年,美國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在海外所支出的R&D,比其母公司在國內支出的增長要快,而且占其總支出的比例上升。在區域分布上,美對歐盟、日本的投入下降,最大升幅是在亞太地區(不包括日本),這主要是新加坡、中國等國家。
(3)在發達國家,跨國R&D是一個普遍現象。在OECD的一些小國,外國子公司所支出的R&D占其工業R&D支出總數的50%以上(2001年),如匈牙利(78.5%,1998年)、愛爾蘭(65.2%)。許多發達國家也有非常高的比率,如澳大利亞(31%)、瑞典(38.2%)、英國(40.6%)、加拿大(30.5%),美國為14.3%。日本是最低的,外國子公司在其國內R&D支出占其企業總R&D支出的比率僅為3.4%。
(4)離岸①離岸(offshoring)指的是地點或活動轉向海外。它可以是由母公司在內部將服務轉向海外的子公司(有時稱此為“有控制的離岸”,它包括FDI,它的區別是自離岸到第三方)。外包總是包括第三方,但不必須是要轉移到海外。僅當所討論的活動被國際化地外包給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時,此兩個概念是重疊的。UNCTND:R&D全球化。和外企R&D 迅速擴展到新興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印度和中國R&D活動持續上升。近年來,中國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R&D活動增長最快的國家。
(5)少數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開始在國際上設立研發機構,其中以中國最多。中國最大的跨國企業設立的海外R&D機構主要在發達國家。但這些研發機構規模都很小,主要功能是情報收集和產品設計。
2.R&D的國際化動因
鞏固與擴大市場,減少R&D成本,攝取東道國R&D資源是R&D國際化的主要目標。R&D活動國際化的推力(創新的競爭壓力、人才短缺與母國成本高昂)與東道國吸引R&D及外國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的拉力(市場增長、人才積累、低成本)再加之東道國改善創新體系環境,為R&D活動提供激勵性政策,提供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接合在一起,形成了目前發達國家R&D國際化的格局。
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因自身的力量、市場、開放程度、對人才培養數量和對R&D的投資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成了跨國公司海外開展R&D活動的首選地。聯合國貿發會議調查,中國是最早提到的R&D目的地國家。為什么如此多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R&D機構?聯合國貿發會議引用美國工業研究所的研究認為,在中國進行工業R&D活動的優勢是:大量供給的人才;急望獲得資助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與頂尖中國高校締結知識產權協議的希望;大量的高技術園(即高新技術開發區);政策激勵;在R&D價值鏈的各階段具有成本節約的潛力。
這份研究強調,跨國公司擴大其在中國R&D活動除節約成本外,還有其戰略原因,即利用巨大的人才和思想儲備,在中國乃至亞洲日益成熟的市場中保持競爭力。認為這些實驗室會利用中國的技術和人才儲備從支持和適應型向全方位的R&D 活動轉變[15]。
3.R&D國際化對東道國影響
R&D國際化,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有兩種對立的觀點。正面的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R&D活動有積極的正面作用,通過擴散技術和管理經驗,凝聚人才,提升整個東道國產品技術而促進經濟發展。反面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R&D活動,與所在國經濟發展相關性不大(所謂“孤島”現象),還會造成另一種形式的腦力外流,擠占稀缺資源。但總的結論是正面影響大于負面影響。國內研究有兩個極端,但大多數持中肯態度,即跨國公司R&D對中國的影響,總體上是積極的。持極端的觀點認為,跨國公司搶奪中國科技資源,削弱中國科技安全基礎,利用技術標準和“技術鎖定”封堵中國技術創新領域和成長空間,削弱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利用專利戰略包圍堵截中國技術成果;壟斷國內市場,威脅中國市場安全;封鎖中國出口市場,損害中國產業利益。[16]目前,世界各國雖說對跨國公司R&D國際化有不同的看法,但國際上幾乎所有國家均采取鼓勵、吸引R&D國際化的政策。
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對跨國公司在國外的R&D活動意義進行了討論②正如該報告所說的,R&D全球化的影響,是很難測度的,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個新的現象,缺乏數據,現有的經驗基本上是發達國家的,R&D國際化和東道國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果關系還有賴進一步研究。。一般來說,跨國公司不同的 R&D類型,對東道國有不同的影響;R&D國際化的意義主要依賴于國家創新能力,創新的能力越強,正面影響意義越大。發展中國家自R&D FDI中獲得益處不是自動的,東道國吸引跨國公司的創新性R&D往往在已建立競爭優勢的領域(P197)。只有那些有較強的技術吸收能力的東道國才能自R&DFDI中獲益。就中短期來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能自R&D國際化中獲益,因為他們缺乏能力和制度來吸收外國R&D①見注[15]P198。。
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對外國子公司在美的R&D活動影響進行了評估,結論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任何國家,包括美國,不管R&D人員的國籍,都應該歡迎在它的境內進行R&D活動[33]。這個結論對我國也適用。
4.在R&D國際化中保持自主創新的主體性
作為一個開放的中國和WTO成員國,自主創新不可能是封閉的,不管你愿不愿意,科技進步的溢出和溢入總在發生,R&D國際化已成為潮流;除在少數領域和特定條件下,沒有一個國家僅靠自力更生單獨進行創新活動,這也是科技本身發展特性使然。但在此潮流中不能喪失自我,只有保持自主性,才能獲取R&D國際化的紅利。
這里首先我們要框定國家的政策取向,吸引R&D FDI(改革開放基本政策和國際協定),增加中國產品競爭力和整體創新能力,最大限度利用外資R&D溢出效應,減少不利影響,建設創新型國家,維護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即堅持自主創新的主體性,通過創新主體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吸引R&D FDI,在R&D的國際化中獲取最大收益。
在R&D的國際化中要強調以下幾點:
(1)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是吸引R&D FDI并利用其外溢的基礎。R&D國際化的基礎是東道國有一較完整的國家創新體系,在此體系內,基礎設施完善,科技人力供給充沛,在一些領域積累了大量知識基礎。R&D成本與資源是R&D國際化的重要依據。東道國自主研發力量與成效是國際化R&D FDI的重要目標②美國和英國分別占外國R&D流入的58.8%和47.1%。(世界投資報告2005)英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外國學生占其總數35%,在歐盟中是最高的,與美國水平差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干科學領域。。當前跨國公司R&D FDI向中國的流入與研究模式逐漸高端化也與我國多年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持續的科教投入有關。
(2)要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用外資R&D的外溢。外資R&D外溢通常是通過人才流動來實現的。人才流動,一是外資R&D機構研發人員出來興辦企業,政府給予資助和支持,使企業成功發展。二是國內政府研發機構吸引,而這種吸引亦是在政府和內資企業支持下實現的。除人才流動外,國內有關科研機構或企業與其對等進行交流也有獲取外資效應功效,此對等是在具備科研實力為基礎,而培養此實力是要靠自主創新。
(3)實現國家目標。跨國公司在東道國進行R&D活動,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其核心技術不會轉移給東道國,而且還要采取各種措施防止泄露,因此中國自己的國家目標,必須靠自己才能實現。就是要得到技術轉讓,外方通常看你是否有技術突破的可能,如有可能,他們才可能降價,或進行轉讓。在此種情況下,對方是被迫選擇的結果。前提條件也是自己的研發力量及其突破。加強本國戰略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只能靠本國自己的力量。
(4)減少R&D國際化的負面效應。自主創新與R&D國際化程度或吸引R&D FDI是一個雙向激勵和增強過程。一般來說,自主創新能力越強的國家,吸引外資R&D能力也越強,因為自主創新也為外資積累了供溢出或轉移的知識與人才。而從東道國來說,自主創新能力越低,從FDI R&D活動獲取的益處也越少。一定的自主創新活動,能使外資迅速轉移本國的R&D成果,即東道國的擠壓效應(好比說,如不轉移,就沒機會了);能最大限度獲取外資R&D活動的溢出能力,即消化吸收能力。反過來,外資R&D活動也逼迫東道國要加強自主創新活動,或說成是負反壓效應,由于隨著外資R&D活動的增多,東道國的人力資源,或公司R&D活動空間在沒有政府支持情況下會發生“擠出”效應,大量的人力“外流”,使東道國自己企業和研究單位高級人才短缺,為應付此種短缺,正常的反應就是須提高自主創新力度,消解此“擠出效應”。這正如聯合國貿發會議在其R&D國際化和發展中國家的文件中所說的,“沒有適宜的科學和技術基礎,吸引公司R&D并從中獲益,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挑戰而不是機遇。針對進一步邊緣化和增加R&D差距的風險,加重R&D政策的機會成本,是政策制訂者所爭論的問題。①見注[15]P16。”
因此,從吸引外資R&D投入,充分利用外資R&D滲出效應,實現國家目標等方面,需要加強自主創新。即R&D國際化是以自主創新為基礎,它與自主創新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僅僅有市場,而沒有自主創新能力,也難得有外資大量綠色R&D支出;不能吸收外資R&D活動的知識和技術溢出的支持FDI政策是一種失敗的政策。發展民族工業,實現國家目標,獲取重要戰略領域核心競爭力,更需要自主創新。自主創新與引進R&DFDI是不矛盾的,它是會加強 R&DFDI的流入與高端化。
(六)自主創新需要 R&D國際合作,但 R&D國際合作解決不了重大產業自主創新問題②此節主要參考技術社會集團(Technopolis Group)對歐盟成員國的國際R&D雙邊合作政策進行的綜述(2001)。
自主創新不排除研究與開發國際合作,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還依賴于國際合作。一般研究與開發國際合作建立在知識(技術)、人才、設施的互補性上,單純出資金參與某項科技合作,沒有某種知識或產權轉移,在嚴格意義上不叫研究與開發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此處主要指政府間簽有雙邊或多邊研究與開發(R&D)協議為基礎的合作。作為正規合約(條約或理解備忘錄)是由政府有關部門高級官員簽字的書面申明。許多國家間大學和科研機構自行簽訂的雙邊或多邊研究與開發協議不是政府或國家協議,沒有政府預算保證。
技術社會集團(Technopolis Group)對歐盟成員國的國際R&D雙邊合作政策進行的綜述[18],認為政府研究與開發國際合作協議的法律形式是綁定各方的書面法律合同,或是書面理解備忘錄(writte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后者是非強制性的,是闡述各方期待的為什么和怎么合作的宣言。大多數國際科技合作協議的基礎是理解備忘錄,它有彈性空間。但法律條約(合同)能帶來一些利益,如設立法律實體(秘書處、實驗室等)和給與相關研究機構支持,如在國家層面上對有關個人稅收、人員聘用和知識產權做出安排。在實際工作中國家間也有偏愛,如德國偏向于法律合約,而北歐諸國偏向于簽訂諒解備忘錄。當然兩者之間也有關系,一些協議以具有更明確目標的法律合約為基礎。一些國家首先簽訂諒解備忘錄,待進一步發展,再簽法律合約,以制度化。
國際R&D合作協議(雙邊或多邊)的基本目的在大的范疇上分兩類:
意愿性協議(Goodwill Agreements)和戰略性協議(Strategic Agreements)。顧名思義,意愿性協議是表達在廣泛或專門科學技術領域推動合作的意愿。而戰略性協議通過計劃活動,支持較高水平的活動,對伙伴國來說有其科學戰略目的。協議類型與合作類型之間關系不強。所簽的協議內容包括合資研究設施和合資研究中心。
國際科技合作具體方式或模式有多種,從政府間來說有:交換訪問學者和研究人員,為他們支付旅行費用(可能還有生活費);項目合作研究,此類型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研究人員在自己國家完成的;組織科學技術會議或研討會,包括提供培訓;不含人員流動的科學技術信息交換;合作開發和/或分享基礎設施或設備,利用“規模經濟”優勢,避免不必要的重復而浪費。
在實踐中,大多數協議是有關研究人員從學習研究到參加研討會的多種形式的流動。在這些類型中,一般形式的支持是薪金(general stipend),或限制諸如旅行的特殊支出。這些財政支出要求使在協議的支持下開展R&D合作項目(計劃)研究不太可能出現。
政府間多邊和雙邊R&D協議,特別是多邊協議的主要內容主要圍繞著:重大科技挑戰(如粒子物理);對社會具有廣泛重要性的主題(如氣候變化);投資規模要求(如空間)。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就要求發展中國家要參與基礎研究(分攤研究經費)。雙邊R&D協議內容多樣,它與雙邊政治關系和貿易深度有關。
政府間R&D協議一般還附有知識產權內容,以確定合作中涉及到的經濟利益或社會利益的歸屬和控制。在發達國家,如美國,所有實驗室均有知識產權規定,合作中產生的成果事先有約定,特別是研究工具或材料(如生物材料)轉移協議(MTA①MTA:按照可能利用的研究工具,記述約定和條件。),一旦其實驗室材料商業化或申請了專利,對所使用的材料主張權利,保證了其國家基礎研究和實驗室的利益②“研究工具”術語,在廣義上,與“終端產品”相對,它是指在實驗室里科學家所利用的所有資源,按照美NIH的定義,它包括,細胞株、單克隆抗體、試劑、動物模型、生長因子、組合化學文庫、藥物和藥靶、無性系和克隆工具(如PCR)、方法、實驗室設備和機器、數據庫和計算機軟件。研究工具,包括受保護(如專利、植物新品種)的和未受保護的材料,此材料在一機構可能是研究工具,在另一機構可能是終端產品,它常常相對于使用者目的來定義。具體參見田志康《生命形式知識產權及國家政策》第五章,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
不管多邊還是雙邊,政府間R&D合作一般不會牽涉到具有重大商業利益的項目。就是在人類基因組工程上,許多國家雖說參與了,但美國在研究進程中分離了一個私人基因組公司,將大量分離出的基因申請了專利,導致道德爭議,何況現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距離在縮短,一些基礎研究具有直接的商業利益。能源合作亦如此,只要牽涉到重大經濟利益,合作就成為競爭。自主創新需要國際合作,但國際合作解決不了重大產業自主創新問題。
四、堅持自主創新主體性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明確自主創新的主體,厘清自主創新主體的邊界,在一定概念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尺度上,此主體性并不是固定的、明確的,而是動態的;堅持自主創新政策需要原則性和靈活性。
自主創新的主體有時難以明確,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與挑戰:
(1)免費乘車問題。前面說過,外資R&D的重要動力與目標是利用東道國低成本人才、豐富的科技資源,以及科技知識的積累,越是科技發展較快較開放的國家,外資R&D活動越是積極,這就像發展中國家培養的大學生,畢業后為外國服務一樣,東道國培養的科技人員,研究的前期成果可能輕易的轉移或流失至外資公司,被外資公司低成本甚至免費利用,前期外資不投入,后期少量投入就會獲得重大成果,這就是免費乘車問題。換句話,用較苛刻的語言,就是知識、科技“竊取”問題,他會使東道國科技努力白費,科技秘密、知識產權流失。這也是大量外資在東道國高校建立聯合試驗室,進行資助活動的重要原因。
(2)“并購”問題。許多企業并購或兼并活動,目的是目標公司的R&D資源或要獲取目標公司的R&D成果,人力資源,或要抑制目標公司R&D活動,減少并購主導方公司的競爭壓力。并購是R&D活動轉移的重要措施,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跨國公司面前往往成為兼并的對象,一些被兼并企業會有東道國長期科技努力而保存的科技人才、知識積累及知識產權成果。外資在東道國的并購活動威脅到東道國的科技、經濟安全為世界各國所注意,它在政策上對自主創新政策提出了諸多問題。如自主創新需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但政府以何種方式支持企業創新,對企業的支持應該區分國別性嗎?所以也許有必要對并購進行一定的技術安全審核。
(3)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R&D而采取的與國家不一致的競爭政策,可能導致國家知識產權泄露、流失,即稀缺科技資源為他所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特別突出,如我國在前兩年的國家科技計劃中,許多均明確提出國民性問題,即首席科學家或課題牽頭人必須是中國公民,或課題承擔單位必須是中國境內中資R&D機構。但一些地方為吸引外資R&DFDI,在此放寬了尺度,因為國家的許多科研項目是地方在承擔,特別是北京、上海這些地方,地方在政策上放寬,導致外資R&D活動“免費乘車”,國家科技積累、成果或重要資源為外資R&D機構輕易、低成本所掌握。對國家科技、經濟、國防安全造成危害。
(4)科技人員流動中科技成果(包括技術訣竅、技術秘密的知識產權和政府投入而形成的知識積累)流失問題。從理論上此問題不應討論,因流動是雙向的,東道國或中資與外資科技人員進出是動態的,一般在國家創新體系健全,科技投入較大,與政策激勵的情況下,雙方應有一大致均衡,但目前問題是此流向不平衡,從東道國R&D機構流出大于從外資R&D機構流入。這種現象由諸多原因造成,如投入政策不連續,人才激勵政策缺乏、不健全,R&D機構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不合理,薪酬水平懸殊等。對國家關鍵技術或重大科技計劃項目的主要參與人員要建立檔案,對其流動也要有采取某種附加條件和限定措施是必要的。
(5)外籍人員參與問題。外籍人員參與東道國R&D活動是世界普通性的做法,特別在發達國家。他們常采取提供獎學金、綠卡等措施吸引他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參與其R&D活動。這與強調與明確自主創新的主體性不矛盾,也不沖突。當然這種參與有一定前提條件,一是外籍人員受東道國R&D機構聘用,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參與該機構有關R&D活動,其產生的知識產權歸屬該機構。二是作為承擔東道國R&D項目首席科學家的限制。涉及到國家核心行業核心技術研發一般條件下不會讓外籍人員作為首席科學家。不僅如此,許多國家還規定了參與人員的國民條件。這在發達國家的許多國家計劃R&D項目的資格條件中有明確說明,當然不排除例外,即非他莫屬,并簽一定保密和知識產權協定,此例很少見。三是多見于基礎與公益研究,許多聘于東道國高校和一般科研單位的外籍科學家在一定條件下以受聘單位名義承擔東道國國家R&D資助項目。目前的問題是,像中國大量持有發達國家綠卡和國籍的原中國公民研發人員回國,是否能承擔中國政府R&D項目問題,由于他們的流動性和不可控性,常成為爭論的焦點。
目前,國家對此是持支持鼓勵的積極態度,其它發展中國家也類似,而且依靠回國人員,促進了許多研究領域的發展,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發展進程,像原上海交大陳進那樣造假,騙取國家R&D經費畢竟是少數例外(此與我國科技項目的授予評估、監督方式與程序有關)。在假定大多數回國人員對其出生國的忠誠度的條件下,東道國對此應加以鼓勵和支持,并要采取措施予以激勵,加以充分利用,但在關鍵國家項目中,作為首席科學家,要有一定制度和層次。在稅收優惠項目中一視同仁,在國家補貼性項目中和基礎性領域,一般也不加限制,僅在涉及國家重大的資助項目時,要有一定評估和保證制度。總之,充分發揮回國人員在自主創新中的作用是主流。
(6)自主創新產品采購、首購、訂購中的“中國法人”資格問題。“在中國境內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的產品生產單位,均可自愿申請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19],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首購、訂購合同應當授予在中國境內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的企業、事業單位①見財政部有關自主創新產品采購、首購、訂購管理辦法。,那么從中引申的問題是,由于中國法人包括外商在華投資注冊的企業,他們生產的產品也是“自主”創新產品嗎?如是,怎么解釋“自主創新”?如果將中國法人概念應用于政府資助R&D,自主創新的中國國民主體性將不復存在。我們建議將“自主創新產品”改成“中國創新產品”,這樣中國法人均有資格獲得政府采購、首購、訂購合同。
五、結語
討論自主創新的主體性,主張依靠自己的國民進行科技創新,是一個國家科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一些科技強國,如美歐諸國,為保護他們的科技競爭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經濟競爭力,強力主張保護知識產權,并極力維護本國科技創新的控制力,對非國民(法人或個人)承擔政府科技投入項目采取諸多限制,對實施國際有關公約采取許多例外措施。如果不經談判,不實行對等原則,就輕易地將自己的稀缺創新資源拿出共享,這不是叫自主創新,且后患無窮。當一個科技研發力量弱小,一心只想借外力溢出獲取利益的國家,很難重視科技創新的國民主體性。當中國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也會將知識產權的創造和保護優先擺在國家外交關系之中,如美國現今對中國那樣,在歐美諸國強力維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中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那一天一定會到來。因此研究并堅持科技創新的國民主體性有著重要意義。
[1]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EB/OL].[2011-08-10].http://www.gov.cn/zwgk/2010-04/13/content_1579732.htm.2010-04-13.
[2]李若谷.投資環境,自主創新與發展主導權[DB/OL].[2011-08-10].http://www.chinadaily.com.cn/zgrbjx/2011-01/12/content_11830729.htm,2011-01-12.
[3]科技部發展計劃司,財政部教科文司.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及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管理辦法(修訂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EB/OL].[2011-08-10].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107/t20110706_572215.html,2011 -06 -30.
[4]張 煒,楊選良.自主創新概念的討論和界定[J].科學學研究,2006,24(6).
[5]徐冠華.關于自主創新的幾個重大問題[J].中國軟科學,2006(4).
[6]Nelson R R.The Simple Econom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1959,67(3):297–306.
[7]Norgren L;Hauknes J.Economic Rationales of Government Involvemt in Innovation and the Supply of Innovation related services[DB/OL].[2011 -08 -10].STEP Report series 199908,The STEP Group,Studies in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IDEAS,http://www.step.no/reports/Y1999/0899.pdf,1999.
[8]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NCAT).Other Transac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a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NCAT)[DB/OL].[2011 -08-10].DTAFAWA-05-A -00005,Modification 009. http://www.ncat.com/pdf/OTA -Updated.pdf,2005-05.
[9]State of Israel.Encouragement of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w ,5744-1984[DB/OL].[2011-08-10].http://www.tamas.gov.il/NR/exeres/9F263279-B1F7-4E42-828A-4B84160F7684.htm,2005-06.
[10]An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itiative:Policy No.15:Change in Control Policy.http://www.ausindustry.gov.au/INNOVATIONANDRANDD/RANDDSTART/Pages/PolicyNo15ChangeinControlPolicy.aspx,2005-05/2011-08-10.
[11]胡冬云.美國科技政策中“其它交易授權”及其評價研究[J]. 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09,24(4).
[12]Connie K N Chang.ATP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Foreign -Owned,U.S.-Incorporated or U.S.-Organized Companies:Legislation,Implementation,and Results[DB/OA].[2011 -08-10].www.atp.nist.gov/eao/ir-6099/contents.htm,2004-03.
[13]宿希強.不要把品牌并購意識形態化——專訪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J].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2009(8).
[14]科學技術部調研室,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軟科學要報[Z].北京:2008(26).
[15]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DB/OL].[2011 -08-10].www.unctad.org/en/subsites/dite,2005.
[16]肖武嶺.跨國公司對我國科技安全的沖擊及對策[J].理論探索,2007(2):89-91.
[17]Proctor P.Reid and Alan Schriesheim(Editors).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U.S.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sset or Liability?Committee on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U.S.Research and Development[DB/OL].http://www.nap.edu/catalog/4922.html.
[18]Technopolis Group.Bilateral International R&D Cooperation Policies of the EU Member States(Final Report,Volume 1:Overview)(DB/OL).[2011-08 -10].ftp://ftp.cordis.europa.eu/pub/indicators/docs/ind _ report _tp1.pdf,2001 -07 -27.
[19]科技部、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公開征求對《關于開展2010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見稿)》意見 的 公 告[DB/OL].[2011-08-10].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4/t20100409_76710.htm,2010-04-09.
Nationality of Proprietary Innovation
WU Rong - bin1,TIAN Zhi- kang2,WANG Hui3
(1.Management School,Huan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430074,China;2.Hube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430071,China;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e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430074,China)
First of all,an implicit entity for“proprietary innovation”is identified and its definition discussed in the paper.“ Proprietary innovation”is sustainable innovation controlled by a country or national corporations,based on its citizens,main force/body of implementing“proprietary innovation”.And then,main force/body of implementing“proprietary innovation”is expounded from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R&D,national property of foreign R&D institutions,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R & D internationalization,R & 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ird,the mai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insist on the policy of“proprietary innovation”are suggested and briefly discussed.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ain issues for the policy of“proprietary innovation”are R & D property,which is decided by a national and its citizens.Clarifying the main force and body of national and citizen to carry out policy of“proprietary innovation”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a.
Proprietary innovation;Nationality;Main force and body
C01
A
1002-9753(2011)08-0085-18
2010-09-16
2011-07-25
吳榮斌(1964—),男,湖北京山縣人,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企業管理。
(本文責編:海 洋)